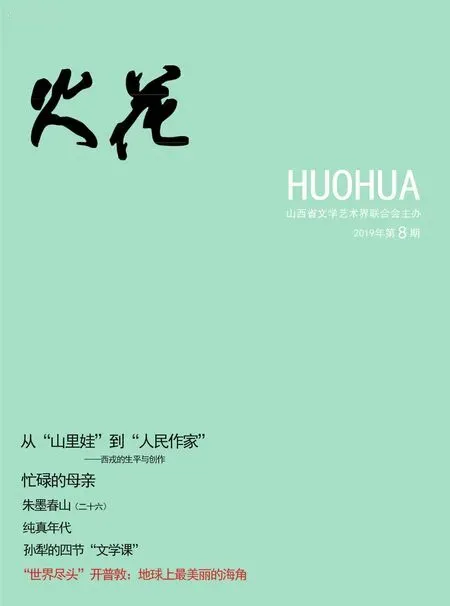忙碌的母亲
介子平
一
我的母亲年轻时曾做过外线电工,之后一直在工厂做事。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终日忙忙碌碌。因不会骑车,所以上班时总比别人早走半个小时,下班则要晚归半小时,星期天、节假日也不歇息。过年时,父亲值班,母亲则加班。母亲生育过五个孩子,活下来三个。我是长子,老三是个女孩。妹妹自小寄养在乡下的庄户人家,后又送回老家由奶奶拉扯,以致至今母女间仍存在着抹不去的隔阂。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母亲总是在我与弟弟还在晨睡的香甜中时便将我们的被子兜去,将窗子推开,逼我们起床。为我们准备好简单的早饭后,母亲便又急着上班去了。
前些年母亲退休了。可刚一歇下来,浑身的毛病便一下子显露了出来,这可能与之年轻时在身体方面的透支有关。她以前所在的工厂目前已处于停产状态,医药费也无从报销。一次,我弟弟请了一位家政服务工来清扫卫生,那人却是旧时厂子里的老姐妹,结果,我妈说什么也不让人家干活,说着说着,相对而泣。自那以后,她说什么也不请人上门服务了。他们那一代人所有的情感几乎全给了厂子,他们曾是工厂的“主人翁”。
母亲将以前对子女的亏欠,现在都补在了孙子辈身上。我的女儿每每外地回来,来时要到车站接,走时也要去送。以前坚毅有加的母亲,每每在火车开动时,禁不住暗抹老泪,这使我及女儿怅然无措。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我的侄儿是母亲一手带大的,去年因与弟媳间出现抵牾,与侄儿多日不见。母亲在侄儿上学路经的道口等了好几天,为的只是与孩子见上一面,递上两袋小食品。由于疾病,母亲上下楼时腿脚极不方便,我无法想象她是如何拖着蹒跚步伐,一次次失望而归的。
如今,最令她高兴的便是我与家人能多回去几趟。也因为忙碌,就连这一点也很难做到。
二
昔时,社会化生产程度不高,凡事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终日不歇。男子下田,手足勤劳,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庄稼收毕,磐石脱壳,臼杵去糠,厨之釜,或为饭,或为粥。女人居内,操持家务,纺纱织布,裁剪缝纫,女红间隙,老小餐食,炊烟三起,饭之桌,闲时稀,忙时干。《木兰辞》开篇即曰:“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孔雀东南飞》也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尺布来之不易,寸衣谈何容易。仅就一双鞋底而言,布屑粘糊,层层叠加,千针万线,密密麻麻。民国课本上的情形,我也遇到过:“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
除夕夜,远处鞭炮依稀响彻,登门的邻里伙伴理了发,洗了脸,穿了新衣,等我出去,母亲手里的线急着收针。街巷里的孩子们穿新衣,戴新帽,陆续聚到了一起,那些没有新衣的孩子,一晚上闷闷不乐,欠了人家东西似的理屈,虽然衣服洗得如此的干净。纵使新衣,纵使出自上海裁缝师傅,也多是大过号的可穿三年可传弟妹的那种。孩子们兴奋地商量着明天如何地不能浪费好时光,串几个门,放几挂鞭,进一趟县城,看一场电影,照一张合影,买一根糖稀。
夜半时玩耍的孩子归来,饺子馅却还未剁就,年夜饭还得等等再等等,姑且塞两个刚炸出的油糕垫垫,丸子也行,花馍也行。拾掇完院落的父亲,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贴对子的糨糊才熬就,上面冒着热气。母亲嘱咐,赶紧把新衣脱下来,刚才赶得着急,扣子还缀得不够牢。
以新衣为礼,以精神饱满为礼。大年初一,匆匆吃过饺子,便紧步出门了。除夕后半夜如约而至的一场雪,早被炮仗炸得碎红一片,一如姑娘们的碎花罩衣。罩衣下依然是平素的棉袄,罩衣被棉袄撅得前仰后翘,罩衣上通常还要覆一块围巾,最是北方冬日里的鲜艳。后生们则要戴顶军帽,用香烟点炮仗的做派,该是格外的潇洒。一天下来,出入硝烟,难免身上不崩出几个口子,的确良的帽子更易燃。新鞋子在雪水里早已浸湿,白鞋边更不知成了什么色。手脚冰冷,脸蛋彤红,却兴奋不觉冻,若在平日,早想贴上炉壁了。
三
晋人在面食上做足了文章,不光下锅煮、上屉蒸、入油炸、贴炉烤者精道,祭供的面塑已然为艺术品,更是精彩。祭天、祭地、祭神、祭祖,满月、开锁、上梁、上坟,皆不离面塑。昔时每近寒食,便会家家捏面“燕燕”。
“燕燕”即“寒燕”,盖寒食前后,燕子归来,家户接应,属肖形塑。经衍演,飞禽之外,添了走兽。蒸熟后晾干,贯穿于麻绳,间隔以干枣,悬于门楣,禁火断炊期间,便可开食,是寒食节的民俗装点,也是平民人家的磨牙点心,上古遗风矣。据说早年间穿拴者非麻绳,为柳枝。柳者,“留”也,寒食悼亡,清明佑生,故“燕燕”也念作“念念”。
我母亲是做“寒燕”的好手。余幼时,每遇她操作,便围于面案,帮衬着递个梳子,传个剪子,充当小工角色,且有一种游戏的享乐。或豚或鼠,似鱼似蛙,剪子绞出脚形,梳子压作鳍状,辅以搓捻成型的须髯,再以花椒籽点睛,传神极了。至于翎毛鳞介,随意几剪子便可概括。塑归塑,待出笼后,另当别论,意想不到如窑变,肿胀而不龟裂,夸张却不出式。而最后一道工序点红痣,则由我等完成,快快送上筷子来,点红用的是筷尖,我的小工是我弟弟。那一酒樽吉祥红,说不上是什么料做的,使用时以水溶解,用后晾干,而盛器竟几十年未变。花糕点,月饼点,过寿的生日桃点,七夕女孩子的巧馍馍点,结婚小登科的乳头馍点,外甥满月的囫囵点,祭神的大供小供点,凡遇点施,定在节庆。小孩串门,邻居大婶于眉宇间点上的那一点,用的也是这点馍的红料。
试碱时,团作小丸,半生不熟揭锅,掰开查看后,便分由孩子们吃下,据说此丸可治小儿胡说。女儿幼时,告状说我用她姥姥的擦脸毛巾擦了脚,我哭笑不得,直怨没有喂食过试碱团丸。
某年探母归来,带了一串“寒燕”分发同事,年轻人皆不知此为何物。我说:若在女红时代,好媳妇的标准之一,便是作花馍捏寒燕的手艺。新媳妇上门,婆婆指着门挂的“寒燕”予客人品赏,客人总不免当面称道几句,背地里则早就撇了嘴。
年根里,八十多岁的老母仍保留着蒸馍习俗。切发面成条状,两头各卷一枣,合拢后便成了元宝状,称“发财馍”。顺便还会蒸几笼肖形鸟兽,出锅后,再也没了孩子们争食场景的出现,老人木木地看着一簸箩的手艺,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