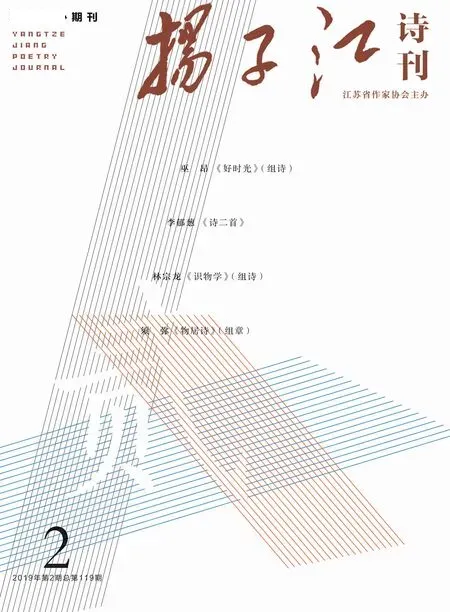有一种渴望(组诗)
谢炯
绝望与深情
没有什么能够安慰我
还没老到
能够告诉自己
已经老了
满地的斑驳落叶
脚步穿针引线
也许能织出一件华丽的秋装
我却只愿见枝头的金黄
没有什么
能够安慰我
除非你就在我身旁
我的要求过分吗?
孤寂中
谁不想遇到怜悯的目光
一只鸟抢在我前面穿过阴雨
那么多树
我从来不知道名字
还没老到
可以忘却这小小的缺憾
银杏与梧桐混为一谈
堆积的诗
无法自己收拾
你的围巾
你可以
送我一条围巾吗?
你可以织进一点荒唐吗?
不需要很多
一点点
荒唐
使巾角微微飘扬
使围着它的人脚步轻盈
使风不用扯帆就能远渡重洋
你可以再绘上几朵堕落的借口吗?
让我坠入绝望
如同跌入来不及关闭的深井
再让我用你织的围巾
一步步爬回自己的阳光
你可以绣上你的名字吗?
你可以使名字失去象征意义吗?
你可以使意义永恒吗?
你可以使永恒无常吗?
你可以在天气
尚未转冷之前送给我吗?
坐在出租车后排去某地
他的眼神如此犀利
他在镜子里看着我
他在后视镜里看着我
他仿佛已经见过我的裸体
他仿佛已经摇过我童年的树
他仿佛已经咬过我少年的果
他仿佛已看破我的前尘
他仿佛已经预料了我的未来
他在我还没把门关紧之前伸进他的腿
他在我还未想好谎言之前编好台词
他准备了浴缸
他拿出致幻剂
他一定要和我一起死去
他一定要和我挤在一块坟地
他的目光如此熟悉
他的眼神如此犀利
我敲敲隔板
停下,快给我停下
不去了,就在这儿下
有一种渴望
有一种渴望
是渴望被你捏住致命的地方
被卡紧,转动不了,如琥珀中的昆虫
是仍然活着,仍有希望
却不再有流逝
是使你无法松手
你一松手
我和时光便溜走了
未必是
未必是一条船
未必是一只船形的蜜橘
未必是一只像蜜橘一样鲜艳的眸子
未必是你眸子中转瞬即逝的火焰
敲响这存在
动摇这存在,奠定这存在
未必是六月的风和日丽
未必是海平面的悠远缥缈
未必是你或我一生的相知相遇
改变这存在,美丽这存在, 点燃这存在
哦,大海
大海的每一朵浪花
每一朵粉身碎骨中莺黄色的浪腹
每一朵玫瑰色的浪尖碧蓝的浪瓣
都在诉说它们的粉身碎骨
痕 迹
有一天,一张
白底暗花的追悼卡到处传送
人们稍稍惊讶地问
噢,昨天死了?
就是左边角落里那间办公室里的
安静的东方女人吗?
叹息后,他们回到自己手边的活计
她是谁?来自何方?
又去了哪里?
只有那些爱过她的人才会不断追问
而她
也只是在他们的问题中
短暂地存在过一回
狮子座
一只乌鸦,一棵侧柏,一只独角兽
全都站在夜晚的高原上
高原很旧了
女娲补天时失手甩下的最后一块泥巴
这么旧的地方已很少存在了
这样的男人也濒于绝迹
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枕着钢板睡觉
半夜站在怒江边撒尿,吹口哨
双手弹奏轰鸣的黄果树瀑布
高声朗读黄色笑话
却不敢掏出口袋里送你的一首小诗
这样的日子远去了,老去了。
星光抵达落日和森林
抵达一头雄狮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