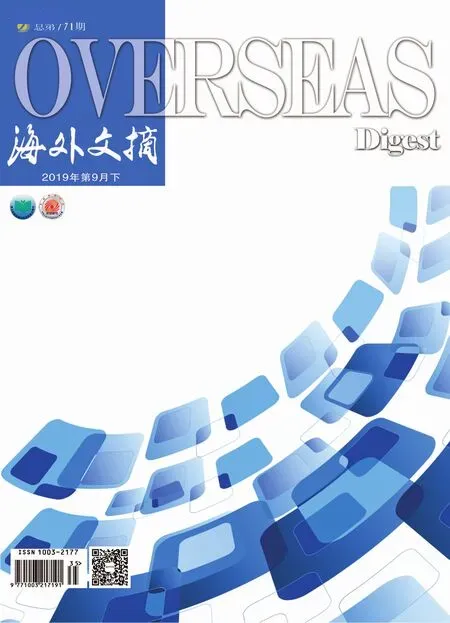简析在社会文化语境下如何转换译者的主体性
梁岩
(上海市应用技术大学,上海 201418)
1 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制约型
任何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任何文化都是以社会为基础是社会的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而形成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换句话说,社会和文化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个语言社团的世界观、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多种方式集合体总和。社会文化的主要承载体就是语言、并以语言沟通交流传播和延续为目的,因此,社会文化是通过语言反映出的核心内容并对它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进而推知,社会文化所形成的环境是任何一种语言根植的母体,而语言的使用是存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并适用于当代沟通的一种表达方式。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文化语境这一概念,他认为,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事情、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参见留润清1999:278-284)。由于民族的不同,所以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文化环境不同,各个民族的人们对外部世界反映产生的印象和概念也有不同并产生出不同的差异性,由此得出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使人们对事物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概念,并产生了包含不同文化意义的语言、语句、语词、包括一些新型的网络用语。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语言也随之发展和增长,社会文化的因素也不断渗透到词语选择性和定型性的各个环节,词语的运用和特定音义是一个民族各文化的折射和呈现,能够细致、全面地体现民族文化的特色和特征。图里指出,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译语文化中的社会规范和文学惯例制约着译者的审美趋向并向影响着译者具体做出的选择(愈佳乐2006:109)。图里所指的社会规范和文学惯例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是语言间的活动并关涉两种社会文化语境,在原始语言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原文本,一旦进入目标语社会文化语境,必定化产生差异。这种差异的体现实质上是译者受不同社会文化制约的结果。社会文化语境包括多种因素,如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宗教信仰、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这些因素都直接地影响着译者对原文意义的把握以及译文形式的表达。
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制约性主要体现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上,它不仅影响社会翻译政策的制定、原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的确定以及理论探讨的重心。在微观上,它直接影响译者翻译思维的切入点和策略并最终影响着译文的最终完成形式。社会文化的发展呈现阶段式,因此,在不同历史阶段,翻译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希腊后,西方掀起了第一次翻译高潮。在与强大的军事机器相比,罗马的文化远远落后与希腊文化,它迫切需要吸收先进的希腊文化。在此背景下,罗马人开始大量翻译希腊的戏剧、哲学、文化和艺术等作品。但是,征服者的自豪和文化的自卑使得罗马人把翻译当作加强文化地位的工具。由此,这个阶段诞生的西方译论(以西赛罗为代表)更趋向于意译,主张译文体超越原文,译者高于原作者。中国的佛经翻译呈现的历史形态也反映了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相比较古罗马,中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盛于隋唐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为佛经翻译提供了滋养生存的土壤。当时西汉末年于东汉初期政治腐败,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长期处于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们渴望有一种精神力量来慰藉、解脱自己,从而为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翻译提供了所需的社会条件。随之到东汉时期,先秦诸学子学说纷纷在兴,中国的思想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多元、理论系统日渐续密的百家争鸣的崭新时代。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既为佛经翻译与佛教的传播留下空间,也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一种适宜的文化氛围。大量佛家经典翻译成汉语通用语言,并在中国广泛流传。支谦的《法句经序》是中国佛经打开翻译史上的开篇之文。佛经翻译的直译和意译之争便是当时社会文化对翻译影响的体现。
2 主体性对文化的映像
社会文化语境在微观上制约着翻译的直接结果便是目标译文中的主体差异,即由于译者采取不同翻译策略而致使译文形式不同。译界曾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译者作为译文的第一读者,其单个体间的差异必定导致译文形式多样性。主体差异源自译者风格,译者风格形成于其所根植的社会文化语境。比较译文的不同,可以看出主体差异的体现以及原因所在。下面我们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所取的句子简单进行对比、考察并分析杨(宪益)译与霍(克斯)译在社会文化语境制约下,对原语文化现象处理方式的不同。
例1: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都未必这样巧啊。” (第7回)
杨译:“Gracious Buddha!”Mrs Zhou Chuckled。“How terribly chancy! You might wait for ten years without such a run of luck”
霍译:“God bless my soul!”Zhou Rui’s wife exclaimed。“You would certainly need some patience!Why,you might wait ten years before getting all those things at the proper times!”
我们清晰的看出,从用语看,杨较为简洁且趋于口语化,简单易懂。从选词用语看,二者的文化背景可谓是一目了然,杨译忠于原文对文化的形式,并将汉语中的感叹词“阿弥陀佛”译“Gracious Buddha!”,而霍译则使用英语文化形式去处理为“God bless my soul!”。佛教文化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阿弥陀佛”是众人口中寻求慰藉心灵放松的一个常用语,常挂嘴边,久而久之,便演变成一种感叹词往往表示惊讶或者惋惜。杨译英文用词忠于原文并直译而且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体现出很强的文化差异,而霍译则彻底融入了基督的色彩,消融了文化差异。
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曾指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愈佳乐2006:11)。这一论断在文化翻译上便演变成为异化与归化之争,异化主张直译原文的语言形式,保留构成原语文化因子,归化则主张以地道的语言表示形式和相应文化因子进行翻译。异化是受原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归化则是受译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主题差异是异化和归化两种相反努力的结果。且看下例中,译者是如何利用归化方法来体现社会文化语境的。
例2: 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a maid,die maiden-widowed。他要借你(软梯)作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 (朱生豪译)
原文:朱丽叶决心去死的前夜,对着软梯感叹,盼望心上人能在流亡前,爬进闺房与她共度一夜。“to my bed”原文中表述意“上我的床”,但朱生豪却刻意将其译“相思”,因为在当时的中文化中,一个尚未出嫁的闺女是不能与心上人“上床”或有任何亲密的接触。
3 结语
翻译绝对不是一种语言形式的转化,它是代表着两种文化的交流、沟通,语言根植于文化并受其支配。因此,译者使用某种语言的同时必定反映出其文化背景,译文的形式差异不同也产生于译者所受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也可以说,社会文化语境制约着译者主体型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