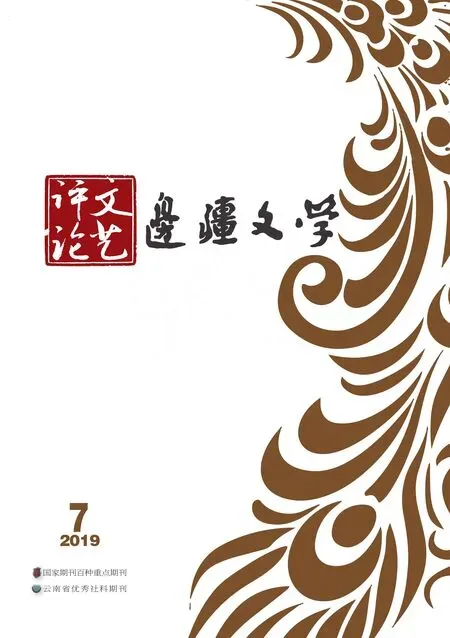略论雷平阳的诗歌精神
……………………………………………·鲁守广
在当代诗坛野怪黑乱的杀伐和战鼓声中,雷平阳的诗歌在三十年中默默前行,以一种个体话语形成了自我的传统。这三十年间,“远在天边”的他甘心处于旷野之上,很少参与诗歌界“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系列意义寥寥的运动、浪潮甚或方向之争,只是热心的冷眼旁观,从一条看起来有些边缘的似路非路中走了出来。在“时间”这个永恒的上帝的裁决之下,大浪淘沙,真正的诗人终于水落石出。与食洋不化的“转基因”诗歌截然不同,雷平阳的诗歌是从中国乡野大地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与传统的古典诗歌精神相接续的现代汉语诗歌,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诗歌受众如此之多的原因。雷平阳以他的创作实绩说明:诗歌不在“庙堂”之上,而在“江湖之远”,不在“运动”之中,而在“山水”之间。尽管雷平阳有诗歌界的“获奖专业户”之称,被广泛认可,但他的诗歌内蕴还是被低估了。他的诗歌绝不只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所谓苦难的叙事,而是与中国传统的古典诗文创作一脉相承,蕴含着关注现实的理性思考,针砭时弊的忧患意识,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以及遗世而独立的出世精神。可以说,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既有儒家的修己安人,也有佛家的自渡渡人,还有道家的道法自然。
一、儒家担当
在今天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动时代,许多所谓的诗人缺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担当情怀,把诗歌娱乐化、粗鄙化和低端化,终至于边缘化。在物欲、权利和市场的多重挤压下,心慌焦虑的诗人们不再“道成肉身”式的为永恒而歌,放弃了良知与担当,从而放弃了对现实的发声即对这个时代所应该有的刻不容缓的命名,而最终他们也会被这个时代所遗弃。雷平阳却一直关注日常生存处境和生活经验,他的诗歌不是观念和概念的写作,不是“语言的空壳”,而是向“担当”走出了一步。伟大的诗人无不是具有担当及救世情怀的,在这一点上,雷平阳与伟大的诗歌传统或者说“正声”是相一致的。如果说于坚的诗歌是“守正出奇”的话,那么雷平阳的诗歌便是“由奇入正”,具有一种普世性和大乘性。
雷平阳在一篇访谈中这样说道:“所谓诗人的担当,一是内省和自我完善;二是在流亡的路上仍然泣血呐喊,为真理而歌;三是悲天悯人,良心沛然。雷平阳是知行合一的人,说出了一个有担当的诗人所应该说出的话。其诗歌不但是“及物”的,而且是有担当的,对现实发声,对时代发声,喊出了这个时代大地之上江河山川和芸芸众生的疼痛。如这首《妄想症》:
……
这座失忆的城市,它理应
充作集中营或牢狱……
一杯苦茶,已经喝淡了
我没有等来一个人,反而
这城市的声浪,一波接一波
不停地送上来,感觉它
就是一口巨大的铁锅,烈火之上
正在熬着疯狂的骨头汤
正在煎着鬼迷心窍的魂魄
天呀,只有天空稍空
闪电与闪电,雷霆与雷霆之间
飘着一片云朵。我灵机一动
突然想在上面建一座庙
让自己有一个下跪的地方
但我又不知道,怎么才能
爬上这一片云朵,怎么才能
在空空如也的云朵上,安放
怒目金刚抑或地藏菩萨的宝座
诗人之所以想在云朵之上建造一座寺庙,“让自己有一个下跪的地方”,自然不是对某种宗教的皈依,而是为了召唤迷失的信仰与走丢的灵魂,为了诗意的安居在大地之上,从而避免精神平面化和生活娱乐化甚至人性的异化。宗教的终极价值是在世界之外,是在来世,或者说“彼岸”。而“诗”是要回到人世间,回到大地上。在这里,“寺庙”意指慈悲、道德之根、文化底线和道德正气。雷平阳在诗文中主张生活在有寺庙的地方,是想“为天地立心”,通过文字使“心”出场,继而在场,从而守护着大地,体现出儒家的担当精神。诗中,人的肉身处在巨大的建筑空间里面,却找不到精神归宿之所。城市已然“失忆”,丧失了传统,没有了历史。诗人对这样一座“失忆的城市”没有归属感,终究是漂泊无依,无处还乡。这一点在《我的家乡已面目全非》中体现的更为明显:
回去的时候,我总是处处碰壁
认识的人已经很少,老的那一辈
身体缩小;同辈的人
仿佛在举行一场寒冷的比赛
看谁更老,看谁比石头
还要苍老。生机勃勃的那些
我一个也不认识,其中几个
发烟给我,让我到他们家里坐坐
他们的神态,让我想到了死去的亲戚
也顺带看见了光阴深处
一根根骨头在逃跑
苹果树已换了品种;稻子
杂交了很多代;一棵桃树
从种下到挂果据说只要三年时间
人们已经用不着怀疑时光的艰韧
我有几个堂姐和堂妹,以前
她们像奶浆花一样开在田野上
纯朴、自然,贴着土地的美
很少有人称赞,但也没人忽略
但现在,她们都死了,喝下的农药
让她们的坟堆上,不长花,只长草
我的兄弟姐妹都离开了村庄
那一片连着天空的屋顶下
只剩下孤独的父母。我希望一家人
能全部回来,但父亲裂着掉了牙齿的嘴巴
笑我幼稚:“怎么可能呢
生活的魅力就在于它总是跑调。”
的确,我看见了一个村庄的变化
说它好,我们可以找出
一千个证据,可要想说它
只是命运在重复,也未尝不可
正如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
站在村边的一个高台上
我想说,我爱这个村庄
可我胀红了双颊,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它已经面目全非了,而且我的父亲
和母亲,也觉得我已是一个外人
像传说中的一种花,长到一尺高
花朵像玫瑰,长到三尺
花朵就成了猪脸,催促它渐变的
绝不是脚下有情有义的泥土
还乡是诗歌的一个基本母体,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程中,古典诗歌对乡愁的表述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并没有多少变化。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以来,随着故乡的“沦陷”,“乡愁”出了问题。雷平阳在《村庄,村庄集》中写道:
我不敢设想,落魄江湖的人
你该从哪一条路上归来
如芒在背啊,躲在底下的田鼠兄弟
如芒在背啊,脑子失灵的小表妹
如芒在背啊,礼崩乐坏的大地
乡愁不再是那种甜蜜的忧伤了,而是让人无望的痛楚。尽管有的人从未离开故乡,但在越来越陌生的故乡却成为“流放者”,乡愁被彻底的解构。由于现实中的故乡已经“面目全非”,诗人只能在诗歌之中一次次的还乡了,诗歌通过语词建构起故乡最后的渐行渐远的背影。雷平阳写乡土的诗差不多都是挽歌,这首诗也是,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毁坏了乡村的伦理,美好的过往烟消云散。
雷平阳的这些诗指向并深入时代,尖锐而有力的直击当代生存题材,是对现实生存和生命的揭示,体现出诗人儒家式的“铁肩担道义”的生命态度。在《雨林叙事·后记》中雷平阳这样谈到:“作为一个诗人,我有失斯文地与生活贴身肉搏,我失魂落魄,现实生活却依然按照它的方式不为所动的前行,这是我为之痛苦却又无能为力的,而且我还会这样做并接受以卵击石的命运。诗歌之血是红的,这个信条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我相信我以诗歌记录下来的人心与世道的场景终会被人们所珍视,因为我作为证人没有选择逃离。”他本人也说过从不反对现代文明,而是反对那种受伤的文明。文明应该是加法而不是减法,应该是累积而不是取代。在《敌意》中雷平阳这样写道:
我对乡政府所在的小镇
顿生敌意:它攒动的人群中
大多数的人头已经被洗劫一空
大多数的人心布满了弹洞
大多数的人影,离开小镇时
醉得踉踉跄跄,却不知道
有人偷换了自己的味觉和视力
还将自己的五官、四肢和灵魂
一一调小了比例
诗人在这里写的就是人们精神上的荒芜和对“布满了弹洞”的人心的失望,以及对人们精神上和肉体上双重萎缩的忧虑。在《大江东去帖》中,雷平阳这样写道:
草丛被铲除了,青蛙找不到地方交配
茅屋被推倒了,又一批老人,没有角落
寿终正寝。我卖掉了马或驴,坐火车,乘飞机
我是儒,我是佛,我是道。铁路的两边
庄稼被软禁于大棚;天空之下
山高人为峰,人工降雨的炮管,笔直地
插进了云朵,抵到了雨神客厅的天花板……
我置身在巨人国,欲望和暴力
果断地将我隔离,关押在荒废的图书馆里
看着一条条高速公路,比江水更孔武百倍
更能迅速掠走仅有的血滴,请允许我战栗
现代化为人们带来庞大的物质财富和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带给人们太多的生态灾难,比如说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和文化生态危机等,使得森林面积萎缩、水土大量流失、河海污染严重、物种或退化或灭绝。更为重要的是颠覆了传统文明,摧毁了生命世界的丰富性和诸多细节,使社会趋向于同质化。敏感的诗人发现这个世界空虚了,人们的精神失落,心态失衡。雷平阳之所以“战栗”与金斯堡之所以“嚎叫”可以说是相通的,都是源于精神上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一种抗拒。还有《渡口》:
单一的橡胶林,取代了雨林的迷局
而且矿洞连通了地狱,山也要死了
流淌的江河已被改造成一个个湖泊
而且波涛里的闪电全部被抽走
水也要死了
“礼失而求诸野”。作为边地的云南自然难免现代工业文明的侵袭,但依然存在着狂欢的诸神和无法言说的东西,有着大地之“魅”和旷野之“惑”。然而这些也开始渐行渐远。雷平阳游走于其间的千山万水,只想将这大地之“魅”和旷野之“惑”复现于书纸之上,形成一片纸上的旷野,聊以无望的反抗暴力般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也正因为无望,才显得更悲壮。雷平阳的这种“无望的反抗”即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精神。雷平阳的担当是存在的担当,也是道义的担当。
二、佛家心肠
雷平阳与历来大多数优秀的诗人一样,出身于乡野。但他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昭通农村,从《背着母亲上高山》《祭父帖》与《我为什么要歌唱故乡和亲人》等诗文中能够看出他的成长过程中不堪回顾的惨怆怛悼,所以“一生下来就是老的”。苦难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在坎坷的半生中,尤其是在云南建工集团的13年中,他较为广泛的接触了现实社会,对底层各式身份的人有深入了解。雷平阳用沉重和压抑的语词,以佛家的悲悯情怀为民工、上访者、乞讨者、偷渡客、毒贩、土匪、逃犯、牧羊人、卖麻雀肉的人和妓女等发声,写出了他们用命、血和骨头扑腾在死亡线上,对抗着无力对抗的命运。
对人世间生命的体察与感悟是雷平阳诗歌写作的根基与核心。“人世间”,在佛家信仰中,是一个特别的场所。只有“人世间”才能容纳万千气象,那种种的苦乐悲喜,也只有在“人世间”才蕴蓄着能够使人觉悟的力量。在“人世间”,存在苦难与罪恶黑洞的同时也有慈悲与向上的乐土,充斥着贪婪和无明的蒙昧之地也有解脱与觉悟的般若,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于坚在《道成肉身》一文中有这样一个论断:“不能总是跳梁之辈在表演。时间到了,文明在呼唤守成,呼唤高僧大德”,雷平阳身上正有一种佛性,一种真正的佛性。真正的佛性并非绝对的虚空,而恰恰要通过对于充满妄念无明和逐求骚动的芸芸众生的生命省察才能得以实现。《离开》一诗中有这样一段自剖:……在昭通市/或昆明近郊,我亦一再地碰上/那个发誓要为天地立心的青年,他有着/冲天而起的豪情,像缪斯的私生子/单薄,易碎,偏执,一直/想把菩提请到作品里来……雷平阳正是以诗歌的方式参悟世间法,以诗歌的方式撕开了他的悲悯心肠。如这首《战栗》:
那个躲在玻璃后面数钱的人
她是我乡下的穷亲戚。她在工地
苦干了一年,月经提前中断
返乡的日子一推再推
为了领取不多的薪水,她哭过多少次
哭着哭着,下垂的乳房
就变成了秋风中的玉米棒子
哭着哭着,就把城市泡在了泪水里
哭着哭着,就想死在包工头的怀中
哭着哭着啊,干起活计来
就更加卖力,忘了自己也有生命
你看,她现在的模样多么幸福
手有些战栗,心有些战栗
还以为这是恩赐,还以为别人
看不见她在数钱,她在战栗
嘘,好心人啊,请别惊动她
让她好好战栗,最好能让
安静的世界,只剩下她,在战栗
诗中这位战栗着数钱的来自乡下的女工,月经提前中断,下垂的乳房变成了“秋风中的玉米棒子”,繁重的活计使她丧失了女人之为女人的女性特征。抛离家园的她有多少泪水才可以“把城市泡在了泪水里”,有多绝望才“想死在包工头的怀中”。她是千千万万底层劳动人民中的一员,用无数汗水堆建起了栋栋高楼,而最终却还要对剥削压榨她的端坐在高楼之上的人的“恩赐”感激涕零。生活的苦难让她经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是谁在为我们的城市坚守?是那些饱受生活苦难,默默奉献青春和生命,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的人。他们拿着最低的工资,干着最脏最累的活,还要被人嘲笑。这首《战栗》写出了雷平阳对现代化的“城市文明病”的恐惧以及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苍凉,进而试图用一颗悲悯之心唤醒人与人之间被忘却的善良。类似的诗还有《贫穷记》:
一位丈夫截掉了妻子的两根手指
因为她遗失了两毛钱。一毛钱一根手指
家庭中的市场价,时间史里的经济观
他让她增长必要的记忆,要像
鹰那样,闪电似的,飞抵生活的彼岸
她没有用沉默抵制暴力,而是用忏悔
用更加辛苦的劳作,弥补自己的过失
人们总是说“金钱是万恶之源”,但实际上真正的万恶之源是“贫穷”。一个丈夫生生地剁掉遗失了两毛钱的妻子的两根手指,一根手指在家庭中的市场价是一毛钱。而妻子对于这样的惩罚竟然也是认同的,根本没有不满,而是用更加辛苦的劳作来忏悔自己的“罪过”。雷平阳在此用他的诗歌去伸张正义,用诗人的良知和底线去谴责伤天害理,用他的菩萨心肠去感化恶念和残暴。正如他的诗歌《疑问》:
在滇东北,在我的故乡昭通
有个疑问我一直无法问:多少柄小刀
才能结束一头羊的性命?多少头羊
才能组合成一个牧羊人?我知道
所有人都会选择终身沉默
因为一个牧羊人和一根草
他们的尺寸相等
雷平阳在诗中发出直指人心的追问:多少柄小刀才能结束一头羊的生命?多少头羊才能组合成一个牧羊人?每一问都那么沉重,作者设想的答案更是使人为之动容。为什么所有的人面对这样的疑问,都会选择终身沉默?因为一个没有“话语权利”的牧羊人和一根草的尺寸相等,和刍狗无异,雷平阳写出了这些人“肉身和精神双重的卑贱”。诗人是想用诗歌为这些人留一点“雪泥鸿爪”,从而使人们意识到对生命的悲悯敬畏。雷平阳以他的诗歌来召唤社会的良善,让人痛心,甚至产生罪恶感,这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为生民立命”。
他的诗歌中所提到的大自然的生物与非生物,如蚂蚁、蜘蛛、蟋蟀、土拔鼠、鲸鱼、鹭鸶、鹦鹉、羊、飞鸟、梨树、草原与河流等都是人格化、有情化的,体现出诗人对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敬畏。如《在会泽迤车看风景》:
在云南省会泽县
一个叫迤车的小地方
我看见大路两旁的大树
一种叫做白杨的树,全都很粗
在冬天,大雪已经落了多次
这成长了多年的树
在这个到处是荒山野岭
缺少更多树木的地方,在一个个
贫穷的村落旁边,在大路旁边
全被齐腰砍伐!
像被大火烧毁的古代建筑群
这些被齐腰砍伐的树
是一根根寂寞的石柱子,横切面
全都敷着高原上最普通的红土
也许来年这些树都会长出新的枝叶
但在今年冬天,我看见它们
就像看见了古代的刑场,看见了
那些被砍掉了头颅依然狂奔几步
才倒下的罪人。它们令我感到恐怖
恐怖之中暗含着一种愤怒,一种真正的愤怒。但这在这种“愤怒”中没有暴力,没有杀气、戾气,相反,有的却是悲悯。雷平阳写了很多残酷的暴力和杀戮,但是在这些单刀直入的暴力和凶残中有一颗滴血的悲悯心肠。正因为诗人的悲悯之心,这些震颤人心的疼痛才被写了下来。如《一棵漆树》中这样写道:还能快乐的生长,这需要/怎样的狠劲,怎样的铁石心肠/割漆人的刀,完全可以不抽掉/年年都从他身体路过,有多薄,有多凉/他比割漆人知道的还多/“来吧,我的肋骨!”他可以/这么对刀讲,像受暴的女子/成了案犯的新娘。如《杀狗的过程》写的是在嗜血看客的围观下,一条狗毙命于它所忠诚的主人的刀下。具体的时间与地点,详细的狗和狗主人的动作与情态,狗中刀的次数和死亡的过程等等都使这首诗极具感染力。再看《卖麻雀肉的人》:
卖菜人的脸色偶尔有明亮的
衰枯的占了绝大多数。有一个人
他来自闷热的红河峡谷
黑色的脸膛,分泌着黑夜的水汁
我一直都想知道,他成堆的麻雀
从何而来,他的背后
站着多少在空中捉鸟的人
但每一次他都丧着脸
并转向黑处。他更愿意与卖瓜人
共享寂静,也更愿意,把分散的
麻雀的小小的尸体,用一根红线串起
或者,出于礼貌,他会递一支
红河牌香烟给我,交谈
始终被他视为多余
把这么多胸膛都剖开了
把这么多的飞行和叫鸣终止了
他的沉默,谁都无力反对
这样的场景真让人万箭穿心般的难受和压抑,使人想起奥斯维辛和柬埔寨的屠杀。人性的残忍,不是非得等到特殊年代才会显露出来。但更痛苦的是我们能说“刽子手”是有罪的吗?对于这位黑色脸膛的人而言,与家中的贫困相比,成堆的麻雀的生命微不足道,把麻雀开膛破肚只是他谋生的方式,“谁都无力反对”。正是因为雷平阳有一种佛家的慈悲心肠,诗歌中对人世的体察和对众生生命的尊重才如此的直抵人心。
三、道家理想
雷平阳在2017年出版《击壤歌》与《送流水》之前,给人的感觉一直是向人世间“挺身而出”的。但是积极入世是有风险的,许多人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斗争中丧失名誉甚至生命,最终满盘皆输。就像雷平阳在《2002年冬天日记》中所描述的:我解说不清生活之痛、文学之苦/尖酸刻薄的不是命中注定/而是人事。一回回站在风口/在刀俎之间,闻着乌云一样的口臭/我真不想玩了,不想玩的理由/别人知道的比我还多。“安宁遥不可及,你抵挡不了来自世界的繁杂恶意”。他心目中最理想的诗歌是《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诗相传是在天下太和,百姓无事的帝尧之世,一位澹然虚静,心无所虑的老人击壤而歌出的。雷平阳认为这首诗是诗中极品,显现出他想要过这样一种庄子式的自在生活。试看他的《寺庙》:
有没有一个寺庙,只住一个人
让我在那儿,心不在焉地度过一生
我会像贴地的青草,不关心枯荣
还会像棵松树
从来都麻木不仁……
我一旦住在那儿,手机就将永恒地
关闭,谁都找不到我了
自由、不安全感、焦虑,文坛上的是非
一律交给朋友。也许,他们会扼腕叹息
一个情绪激越的人、内心矛盾的人
苦大仇深的人,从生活中走开
是多么的吊诡!可我再不关心这些
也绝不会在某个深夜
踏着月光,摸下山来……
这首诗写出了雷平阳想要逃脱尘世而寄身于寺庙之中的梦幻想法。
梁漱溟曾把人生态度分为“逐求、厌离和郑重”。逐求意指人在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颠倒迷离于苦乐之中不可自拔。当人回转头来冷静的反省自己,便感觉到人生太苦。一方面被饮食男女等欲望纠缠,所谓“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另一方面,人世间又充满了偏私、仇怨以及生离死别等种种现象,从而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这种厌离的人生态度即是宗教产生的缘由。郑重是以自觉的力量去生活,自觉地听其生命的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从雷平阳的许多诗歌可以看出,在他写诗的时候是身处厌离之中,但是厌而不能离。在《演员》这首诗中,雷平阳这样写道,“我突然就想去当一个演员/在一部接一部的影视剧里/只演一个重复的角色:走投无路的人/悄悄地在深山里当了和尚/这样,我就可以不断地绝望,不断的出家/戏剧性的一会儿在俗世捶胸顿足/一会儿又在空门里穿着袈裟”。内心焦灼的雷平阳彷徨无定,尘世的纠缠无法斩断。正如《行为艺术》中所写:深陷囹圄,我仍然固执地/向往独立;在亡命徒似的生涯中/我仍然梦想着逃亡……雷平阳入世太深,牵绊太多,精神上难免会产生痛苦感和疲惫感,甚至于灵魂业已极度分裂。他的诗篇中有众多的“我”,多个主体在同一具肉身中徘徊继而冲撞。但多个“我”依然被禁锢在过于沉重的肉身之中,无法挣脱,这样就使得诗人一直在垂死挣扎。如《生活》中所写:
我始终跑不出自己的生活
谁能跑出这落在地上的生活
我就羡慕他;如果谁还能从埋在土里的
生活中,跑出,我就会寂然一笑
满脸成灰。已经39岁了
我还幻想着有一天能登上
一列陌生的火车,到不为人知的地方去
把自己的骨头全拆下来
洗干净了,再蒸一蒸
……已经尽力了,整整39年
我都是一个清洁工
一直都在生活的天空里,打扫灰尘
人是社会性动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谁又能冲撞得出去呢?类似的诗还有《高速公路》:
我想找一个地方,建一座房子
东边最好有山,南边最好有水
北边,应该有可以耕种的几亩地
至于西边,必须有一条高速公路
我哪儿都不想去了
就想住在那儿,读几本书
诗经,论语,聊斋;种几棵菜
南瓜,白菜,豆荚;听几声鸟叫
斑鸠,麻雀,画眉……
如果真的闲下来,无所事事
就让我坐在屋檐下,在寂静的水声中
看路上飞速穿梭的车辆
替我复述我一生高速奔波的苦楚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雷平阳一直想要逃离这世间。但是从这首想要逃离和解脱的诗篇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对这个世界所怀抱的炽热希望以及不甘心,所以才要“在寂静的水声中”,“热”眼旁观。2013年春节,雷平阳一家飞赴泰国清迈。“清迈是寂静的,安详的,体面地,它的神祇在山中也在社区里。更重要的是那儿的每一个人,似乎身体中都带着菩萨的影子。有一天清晨,妻儿还在睡,我到旅馆旁边的社区走了一圈。所有的人家都有小院,老树、藤蔓、果树和鲜花丛里的家,有鸟儿在鸣叫,松鼠在悠闲地蹿动……看着那景象,我忍不住眼眶一热,联想起自己的家,感觉就是集中营或避难所。”我们知道他仍然是热爱人生、酷爱世间的。大半生身处在拆迁和工地中的雷平阳一直有一个梦想:诗意的安居在大地之上。但是这样的念想只能存在于语言中,只能在诗歌中一次次抵达。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说道: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十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承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王国维之意也就是说,有生活自然有欲望,有欲望自然也就有随之而来的痛苦,所以生活、苦痛和欲望三位一体。王国维太过悲观,虽然说人类的总体命运是沉重和残酷的,人生的结局或许“望远皆悲”, 但“人是可以思考的芦苇”,当我们看透生活的真相之后,更应该热爱生活,而不是放弃斗争,束手就擒。对于内心强大的人,焦灼的痛苦只是一个净化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只有经过这一净化过程才会走向澄明,走向郑重。所以说“厌而不能离”这个阶段,是到达“郑重的尽力于生活”这一状态所必须经历的。雷平阳很长一个时期都是处在王国维所叙述的“钟表之摆”中,厌而不能离,而使他挣脱痛苦的是澄怀观道,进而“道法自然”。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多以儒家为指导,以天下为己任。而在遇到困境,无路可走的时候,则多以道家为调适,超然通达,静观待时。道家较为注重人的个体性,倡导“自然”“自在”“自适”“自得”“自乐”“自事其心”。他们善于站在大道的立场上,以超然的态度观察人生于社会,认为人不应被世俗的价值和规则所拘泥,而要保持独立自主的意志和自由思想的能力。道家思想对个性的张扬和对自由精神的推崇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和保留了另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为了不被痛苦所异化,诗人自然要寻求化解,于是向道家倾斜,产生了想要遁入深山与糜鹤为伍的冲动,力图用回归自然的方法来避免、克服和矫正异化,从而净化心灵,返朴归真。像诗集《送流水》中的《怒江上》:
在丙中洛,我想有一座房子
建在飘着经幡的雪山脚下
在丙中洛,我还想有一座
插着十字架的坟墓
怒江的水,从平躺着的墓碑上流过
这首诗体现出明显的道家倾向。道家代表着文学与人生中的田园理想,倡导返归自然,浪漫地逃避尘世,反对儒家文化中的责任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尤其是庄子,主张“齐万物”“齐物我”“人与天一”“以人入天”。雷平阳受其影响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精神复归方式,重回乡土,感受生命大地。如:风在空中凉了,碎了,我来送一送流水/人在世上笑了,哭了,我来送一送流水/爱在雾里生了,灭了,我来送一送流水……雷平阳的诗歌在捕捉人与自然刹那间的交流上体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他的喜怒哀乐与跌宕起伏的山山水水相辅相成,达到一种澄明之境。“天地大美,四时明法”,都在诗人心中。雷平阳超然于利害荣辱,把世俗中的利害荣辱,在“道”的自然境界中,也是在艺术精神的境界中化掉了,诗人的人格与山水精神合为了一体。比如诗集《送流水》中的《伐竹》:
登山及顶,有古松成片
清风吹动单衣
几座古墓的对联也写得贴心,不羡死生
我想坐上半天,看青草凌乱,看白云变形
但电话响个没完,一个声音在咆哮
“快速下山,喝酒、吃肉、畅谈
多年不见的老友已经到齐!”
我斫一根竹子扛在肩头
下山路上,逢人便说:“春酒上桌了,
我伐竹而归;春酒上桌了,我伐竹而归!”
在这首诗中,“看青草凌乱,看白云变形”的雷平阳俨然是一位怡然自得“不羡生死”的高士。所以说,从雷平阳的新诗集《送流水》和《击壤歌》中,可以看到一个刚柔相济,能屈能神,进退自如,心态上和写作上具有了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的诗人。当然,新诗集中依然有许多诗作体现着诗人的良知、担当与慈悲,像《安生》中有这么一段:我绝不僭越本分,我只关心一个诗人/他写下的文字,有多少会为他顽强的活着/有多少可以让读者活的更安生。这是典型的儒家修己安人的思想,“惟其义尽,所以仁至”(文天祥语)。还有《在弘忍真身下》:
“恩典赐降我等有罪之身
不是唯一的。应该多赐降一些给寺庙外
无缘到此的那些热锅上的蚂蚁
那些放生后又被捕获的鱼类……”
我匍匐伏在那儿,没有祈求醍醐灌顶
这位佛的使者,我只是恭请他
把上面几句话,转告给佛
“热锅上的蚂蚁”可以是实指,也可以说是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放生后又被捕获的鱼类”也可以是实指,自然也可以喻指被一个接一个欲望所束缚着的人类本身。这首诗写出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式的悲天悯人。所以笔者认为当下的雷平阳最终走向了儒、佛与道互补互渗之路即梁漱溟所实践的自觉自主的郑重之路。
结语
总体而言,雷平阳以儒家担当、佛家心肠和道家理想树立起一种生命形态和诗学品格的典范。然而,近年来,如上所述,在雷平阳的诗歌中,儒家忧患黎元的入世担当精神渐趋向于道家的旷达超拔和清悠淡远。“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愿诗人不要像白居易那样“穷则兼济,达则独善”,愿诗人不再妄自菲薄为“野狐禅”“地鼠”等等,愿诗人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器宇(已经显现,如主编《诗收获》、编选《东大陆青年诗丛》等)。既然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把一个有担当的诗人做到底。当然,在斗争的间隙远离名利场,喘上一口气,让身心得到一刻休息,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这是必要的。在这期间,可以重整过去的经验以作再出发的准备,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记作为一个“时代的歌者”的担当和使命,要以更旺盛的精力去一次次的“狮子吼”。如果雷平阳可以做到这一点,则必将添列屈原、陈子昂、杜甫、韩愈、苏轼……这些伟大诗人之中,成为这一大变动时代的经典,他有这个潜质。让我们翘首以盼吧!
【注释】
[1]于坚从《尚义街六号》到“拒绝隐喻”,到《零档案》,再到“盘峰论争”,一次次的叛“道”而不离道,可以说是“守正出奇”。雷平阳或许受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古代笔记体小说及地方方志的影响,诗文中有一种奇逸之气。
[2] 杨昭编:《温暖的钟声:雷平阳对话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122页。
[3] 雷平阳:《天上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9页。
[4] 雷平阳:《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94页。
[5] 海德格尔著 郜元宝译:《人,诗意的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86页。
[6] 雷平阳:《悬崖上的沉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165页。
[7] 雷平阳:《雨林叙事》,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246页。
[8] 雷平阳:《天上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44页。
[9] 雷平阳:《天上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40页。
[10] 雷平阳:《雨林叙事》,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242页。
[11] 于坚:还乡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第1版,19页。
[12] 雷平阳:《云南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29页。
[13] 雷平阳:《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7页。
[14] 雷平阳:《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198页。
[15] 雷平阳:《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32页。
[16] 雷平阳:《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30页。
[17] 雷平阳:《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53页。
[18] 雷平阳:《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50页。
[19] 雷平阳:《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187页。
[20] 雷平阳:《击壤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10月北京第1版,123页。
[21] 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6月新1版,1页。
[22] 雷平阳:《悬崖上的沉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49页。
[23] 梁漱溟:《人生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6页。
[24] 雷平阳:《击壤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2页。
[25] 雷平阳:《悬崖上的沉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210页。
[26] 雷平阳:《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44页。
[27] 雷平阳:《天上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56页。
[28] 杨昭编:《温暖的钟声:雷平阳对话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11页。
[29] 雷平阳:《送流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22页。
[30] 雷平阳:《送流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封底。
[31] 雷平阳:《送流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2页。
[32] 雷平阳:《击壤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74页。
[33] 雷平阳:《击壤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3页。
[34] 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9月第1版,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