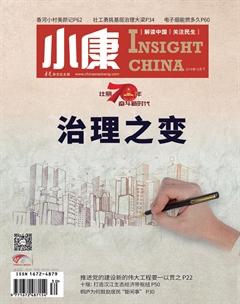基层社会治理大变革
刘建华

延伸 从“最多跑一次”延伸至“最多跑一地”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化解了许多矛盾纠纷。
在浙江省诸暨市的枫桥镇,每天晚上都有一支穿着红色马甲的群众队伍穿梭在枫桥镇的大街小巷,他们是一支代表“枫桥经验”的群众队伍。近半年来,《小康》记者调研所到之处,谈及社会治理,无不提及“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影响深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从管理到治理这一字之差,成为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理念深刻革命的生动写照,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飞跃。
基层社会治理的变革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也是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到城乡社区,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因为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落地,关系到城乡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形象生动地比喻指出,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张网,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实践证明,县域一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央政令的贯彻落实、地方政策的制定执行、社会秩序的管理维护、群众民生福祉的保障等等,都维系于良好的县域治理。
新时代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实践,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的使命要求。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农村,无论是环境还是人口结构都有巨大的改变。
70年来,中国农业人口比重减少五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户籍、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保和住房等一系列改革的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明显加快。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现代化的特征。社会治理从国家一元管理向多元社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转变,这是大势所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这是从传统的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理念和思维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社会治理创新思想的重大飞跃,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念引领。”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但已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居民组织、社会公众等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各级政府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突破城市“单位制”“街居制”的约束,有力推动和引导社会流动,特别是人口在城乡之间、农村之间、城市之间以及企业之间流动。
社会治理变革,是新中国发展历史变革的缩影。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社会稳定功不可没。
“枫桥经验”遍地开花
1963年,枫桥干部群眾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如今,党建引领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灵魂,基层群众、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治理,成为鲜明特征。
近半年来,《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调研采访社会治理所到之处,从浙江、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到广东等十几个省市区,地方执政者一再强调“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56年慷慨激昂,“枫桥经验”从枫桥镇发端,在全国开枝散叶、硕果累累,成为社会治理的典范。
经毛泽东同志批示总结推广,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的“枫桥经验”已经走过了56年的历程。浙江警察学院副院长黄兴瑞教授表示,虽然“枫桥经验”在不同时期发挥作用的对象和方式具有差异,但其对党的执政根基的夯实以及对基层政权的巩固的意义和价值从未改变。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杭州师范大学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余钊飞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具体落实到基层,就必须积极推动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建设,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挥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源头上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送钱、送物,不如送好一个党支部,这是枫桥干部群众几十年来的深刻认识。”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汪世荣说,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打牢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在枫桥镇,一个党员是一片“枫叶”,一个支部是一株“枫树”,一个党委是一片“枫林”。只有坚持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动员一切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才能为干事创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实现平安和谐目标。
现代化治理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在被称为“城市大脑”的衢州“城市联动中心”,《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亲眼目睹一个盗车贼在30分钟内被抓获的过程,不得不感叹,在科技设备的辅助下,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公安人员只需分析内部天眼系统便能发现目标、人像盲比,抓获嫌疑人……
在上海,用“绣花”精神交出一份特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答卷——积极布局城市管理“神经元系统”,升级建设“城市大脑”,已建成1个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16个区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214个街镇网格化管理中心、5902个居村工作站,实现城市管理公共空间全覆盖。
在湖北,“智慧警务”建设,带动形成互联、互通的公安信息网,信息技术手段破案数占比持续达到80%以上。
在贵州,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务服务“一张网”,“一网通办”全省事,政务服务网上可查询和办理事项达58.8万项。
在安徽合肥,企业办事“不求人”“少跑腿”、居民生活“一键通”、堵车与上学等民生痛点逐步解决,人工智能让老百姓享受到越来越多“数字便利”。
高科技助力社会治理,现已是各地政府的标准配置。网络时代,社会治理方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重头戏,我国公共安全、社会治理正加快进入云时代。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对城市监测预警、应急指挥、智能决策、事件管理、协同联动等实现综合服务,让社会治理驶上“高速公路”,正在全国落地见效。
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正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向新境界。纵观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变革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探索、开拓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既有高歌猛进,也有曲折徘徊,更有飞跃变革,中国人正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记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