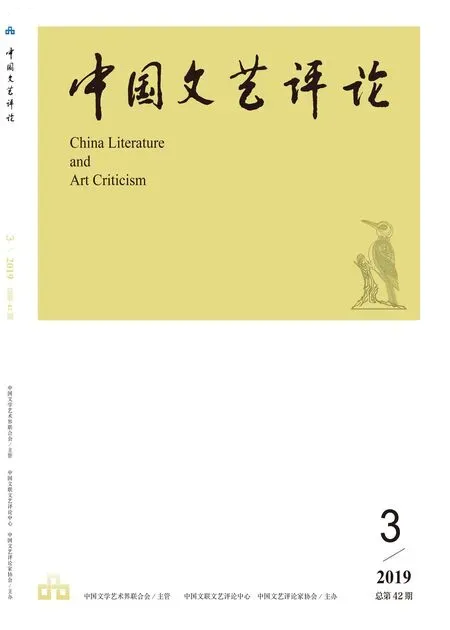感受生命的诗意与吟唱
——评话剧《生命行歌》
吴 戈
话剧《生命行歌》的整台演出营造了一种鲜明生动的生命诗意,氤氲成为整个舞台意象。“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中有诗赞美生命,诗化生死;“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在生离死别中淡然枯荣。论生死,泰戈尔极言其存在形式的美感;看生死,白居易吟唱其更迭交替的自然。两位大诗人,都不约而同地用了自然界节令的夏秋有别或岁月循环的枯荣意象。《生命行歌》采撷这种意象,并置性地组接渗透到了整台演出中,于是舞台传递出来的生命的诗意,是绵延不绝的生机,是生生不息的气象,是生死相依的轮回,是四季交替的自然。于是,这种生命形态的解读,不仅仅属于剧中某一个舒缓医院的特殊人群,其实,生命过程的绚烂精致和生死枯荣的代谢更迭,也是主创人员所理解的人类所共有的、应该从容面对的生命意象。
但是,这种生命意象传递给观众的情感内容,不是当下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对临终关怀问题的淡然、漠然处之,或者人之常情中与至爱亲人作别时弥留终点的凄然、惨然相对,而是具体生命过程中的体察入微,感同身受的生命挣扎、生命意识和生命感悟。话剧《生命行歌》没有给观众讲这种需要切身体会与需要静心参悟的道理,而是通过一群人的变化来感染、感化观众去获得感受。
一、舞台意象:生死枯荣间漾起的生命诗意
话剧《生命行歌》的规定情境设置在一群人于生命挣扎的焦虑困境当中。剧情一开始,就是象征病床,也体现临终关怀医院的入住者的活动方式的六把轮椅一字排开,给观众片刻思考的静场,让人悟出这种“虚席以待”的人生场景,其实是绝大多数人生命阶段中的某个时刻都可能面临的生命处境——等死。生命退守在孱弱的肉身里、昏花的眼神中、游丝般的呼吸上……总之,就是在想要终结自己的生命也已经缺少体力的时候,人,就前所未有地感觉到了对他人的需要——需要帮助。《生命行歌》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群生命困境中的人。
查明哲的导演手段十分老辣,他不露声色地营造了舒缓医院里那种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沉重气氛:角色扮演者从舞台两边走出来,各就各位,坐上轮椅,也像躺上病床,刚刚坐稳,舞台左侧一辆运送逝者的担架车被一位男护士推出来,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穿过舞台,消失在右台侧。无论观者当时有多么烦躁的心情、多么不甘的内心、多么隐秘的希望、多么不舍的牵挂……这一刻,所有心情都停顿、所有大脑都空白、所有眼光都无法挪移、所有注意力都无法分神。大家的眼光追随那辆担架车,大家的耳朵静听几乎悄寂无声走过的那辆车的响动。那是死神的声音、死神的脚步、死神的节奏……大家明白了,住进舒缓医院接受临终关怀,就进入了死亡倒计时的生命处境,这是一种生命困境——他们去到了一个等死的场所。去日苦多,来日苦短,走到了舒缓医院那纯白色的六合世界,走到了那不算长的走廊,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不管进入那个环境之前做过多少猜想,终于身处其中的人仍然觉得突然。其实不是突然,而是觉得难以接受……入院就与死亡迎面相逢,还是让人觉得不好受。所有人在沉默中学会了:必须面对,必须习惯,在将死未死、欲死还生、生死之间的这种挣扎,在死神前来叩门时刻的预判焦灼,不知死神何时降临的忐忑熬煎,和了犹未了的离世纠结中,习惯于身边一个个病友的撒手离去,逐日减员。
导演查明哲一次又一次地在剧情发展的紧要关头让观众喘口气、歇歇脚,一次又一次地调度那个沉默的男医护人员推着担架车缓缓穿过舞台,一次又一次地提示剧中人的生命困境与生命进程,为剧情节奏打点、作情绪起伏调适、给人物处境提醒、渲染环境氛围——死亡的阴影,牢牢地笼罩住了人心。由“死”去强烈地感受“生”,因“枯”而热切地认知“荣”,生命的诗意,就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那样荡漾起来。恐惧消退了,焦虑冷却了,躁动宁静了,负担放下了。生是诗意,死亦诗意,生命行歌中,生死大事,就变成了可以吟唱的诗意组接。
二、演出意义:缺少宗教信仰的我们怎么死
在死亡阴影笼罩当中的人如何诗意?这是一个难题,一个必须参透生死、顿悟枯荣后才能升华起来的生命哲思问题。是的,死亡阴影中寻找诗意芬芳,多么弄险。面对一群被死亡阴影笼罩的人,看他们如何面对死,走出恐惧、负担、纠结,甚至生活的戾气,远离颠倒梦想,走向心无挂碍、无有恐怖的平和宁静,其实蛮困难。
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关怀面对死亡的生者?是《生命行歌》提出的很重要的思考:没有宗教信仰的我们怎么死?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因此有不同的生死观、生死文化。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使我们看到了外国人的死——常常有教堂钟声、牧师的祷告或者追忏、墓地的十字架……善良的人、受苦的人、有罪的人、大英雄、小人物……各种各样的濒死者弥留之际,最重要的是在牧师的陪伴和祷告中安静下来,安详离世。我们中国呢?《生命行歌》中,舒缓医院像是安魂的教堂,而医护人员就像是牧师和天使,她们扮演了生命行程中我们现实生活里最容易忽略的送行人与摆渡者。一定程度上,她们是生死摆渡阶段临终者灵魂的救度者。
剧情中舒缓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提供了有别于西方文化宗教仪式的生命告别,她们不靠应许天国的纯净、伊甸园的美妙、天使的迎候,不靠心理暗示天堂的歌声、天堂之门漏下的光线诸如此类,而是用情真、心善、意美去感化、顺化、融化临终病人心不甘、气不顺、意不平的郁结。为了表现这样的内容,剧情设计了六个受关怀的临终者。其中有因为“反右”运动而在发配地甘肃默默当了一辈子教师,晚年回到上海的孤身老头陈阿公;有当过志愿军但是晚年因自己的没用而表现得脾气极端暴躁的吴老伯;有曾经风靡曲艺界而晚年几乎痴呆的评弹演员黄阿婆;有惦着回家与老妻重操旧业卖粉丝汤的许老伯;有坑过人也被人坑过的恨世者高总;还有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拖着病体、瞒着病情一直到家族遗传的白血病爆发倒下前还总是默默关怀别人的洪护士长。洪护士长从一个守护临终者的白衣天使变为一个被临终者守护和送走的特殊病人,在剧中是人性光辉的一个高点。是她让剧情中孤傲冷酷的高总化解了心中的冰窟死结,让高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看到了人间有真爱,人间有利他,人间有纯善,人间有至美。与高总非亲非故的洪护士长常在他人生狼狈至极、沮丧至极也丑陋至极的时候,给予了超乎常人可能的帮助,让高总改变了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死观,使其重新评估了自己的一生,重新打量他怀有仇恨又怀有太多不舍不甘的世界,然后忏悔了,改过了,放下了。洪护士长是他的天使、引路人、母亲、度母……而其他如美丽的小护士嘟嘟、稳重的苏院长,他们对于被关怀的人群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悉心照顾病人,化解人们的不适与不快,解开他们的心结。嘟嘟联系千里之外的学生群体慰藉陈阿公的孤独愁苦,引导陈阿公宣泄早年爱情被狂热时代和动乱生活埋葬的那种刻骨铭心与愁情万种,甚至通过扮演学生的角色找到与陈阿公的沟通交流方式,也让陈阿公乐于发挥教师角色擅长循循善诱的本领。同时疏导了吴老伯的暴躁情绪,使其珍惜亲人亲情,因为吴老伯的命,是用志愿军战友们的命换来的、留下的,吴老伯认识到,对自己生命一点一滴的不敬重不珍惜,都是对战友的大亏欠、大辜负……就这样,在护士们善心、真情、美意的感化中,一个因各自等死的处境而各有烦恼、散乱难处的群体,变成了一个会关心别人、替别人着想的友爱互助的整体。生命行歌,原来是一曲彼此搀扶、相互支撑、友爱互助、携手远行的长歌!
这世俗的爱,与西方濒死文化中的宗教救度相比,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来得更实在、更有针对性、更能解决问题。在人间烟火里产生的问题,在人间烟火中解决,这是《生命行歌》对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已经全面到来的中国老年社会提供的一份“中国式”临终方案。
三、联欢节目:仪式结构与贯穿动作
《生命行歌》的整个演出,具有精心设计的节奏性发展与套层意义的形式感。节奏性,就是上述提到的死亡阴影的提示:四次担架车的穿场而过,警示剧中人,也提示看戏者,如此剧情节奏“节拍”和氛围营造的作用都十分到位,而且是剧情规定情境中环境处所的常态现象,不是故意创造出来的细节,这是大手笔。至于形式感,就要说到“仪式”了。整个剧情,意义层面上说,就是人生的生离死别的一次特殊仪式,人人皆是看客,人人皆是参与者,人人又都会成为主角,这是剧情有意暗示给观众的。在这种意义层面之下,一开始医护人员就宣布了来年元旦的联欢会需要大家出节目,在整个剧情的推进中,围绕着临终者欢庆新春“出节目”的安排一次又一次推进、强调,终于成为现实。
显然,联欢会是剧情的一个结构框架,是筹划一次远行之前的告别仪式。这种比喻,本身就是诗意的。而联欢会之歌之诗又是自然存在的,与剧情故事的生命“行”与生命“歌”的主题意蕴顺理成章地衔接起来,看似漫不经心的展示,其实有不动声色的设计。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两次齐唱,意义别样。第一次是儿童们唱给老人们听的,像是新生命对长辈们的致敬;第二次是老人们唱给自己的,像是为自己壮行。两次吟唱,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巧妙地完成了枯荣循环、生死交替的感性形象的塑造。这吟唱,是人类生死送别仪式的吟唱。这是《生命行歌》演出形式感的创造。
演出形式除了是一次告别演出的形式框架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为这次告别演出艰难推进的一次次努力”,这是形式感最终形成过程中的“戏剧贯穿动作”。联欢会的主题是“迎新春,长一岁”,在常人那里,准备一次联欢或者庆典活动稀松平常,但对于临终等死、医疗判断下生存时间可能只有28天的人来说就不容易了。“长一岁”是何等奢侈的愿景,“迎新春”是多么珍稀的可能!于是,医护人员为这次活动做出的努力就格外艰难,看似漫不经心,其实煞费苦心,而且贯穿了演出始终。最值得击节欣赏的是,临终作别的老人们齐唱了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那是剧情发展到中段的时候,到舒缓医院慰问老人们的孩子们齐唱过的歌,老人们这个时候来唱,在经历了生死纠结、枯荣思量之后唱出来,就把人生的通达、生死的彻悟、生命的轮回,接力往复,表达为歌声,挥洒成诗意。不多不少,不早不晚,恰到好处。于是,歌声中,他们从容地上路了,走向生命的隧道,走向远方,在绚烂的秋叶簇拥下,渐行渐远,融入地边天际。
四、技术含量:“人表演”与“物传递”的舞台
这台演出由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构成的五代演员阵容出演创作。若25年算一代的话,这个剧目的创演,可谓承载了百年沧桑,呈现了代代薪火相传。最年长的演员刘子枫81岁高龄,还有78岁、73岁的,最小的26岁。这本身就是一个话题,因为五代演员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话题。强大的演员阵容塑造了个性鲜明、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充分诠释了普通人都会面对、但是未必通达透彻的生命哲学问题。无论从演职员的阵容来说,还是从剧目的整体呈现水准去讲,这真是体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学研究创作展演的成果,是一次检阅。演出中演员们出色的表演作为核心,牵引着整个演出形象,传递艺术信息,出色地完成了演出的最高任务。
此外,配合着这台演出的精彩表演,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伊天夫率领的团队所创造的演出“物造型”也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因为演出“物造型”的信息传递便捷精彩,使其成为一台技术含量很高的话剧演出。这次演出中至少用了六块LED屏幕,除延续戏剧演出中“物造型”的物质环节框定规定情境中的环境、提示时间的功能之外,LED屏幕作为“物”的环节,已经不仅仅是“造型”功能,不仅仅是“物造型”给定时间、地点之类的剧情环境特征,而是参与了剧情的表达表现。参与了人物心境与天光外景应和式的“表演、表现”,LED不但从屏幕上拉近了舞台后部表演区的表演场景,更重要的是,放大了剧场观众不可能看清的场面细节、演员表演,甚至面部表情,一如电影的近景和特写镜头。这样一来,原来框定规定情境中剧情时间空间的“物造型”,参与了、改变了、放大了“人表演”的视觉效果、表达强度和情感浓度。而且,当LED的影像与场面中的人物的心境、情绪应和的时候,影像获得了表现性。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演出“物造型”具有了表现“物传递”的功能,在戏剧演出的整体效果的创造中,具有了更为积极的姿态,更为丰富的意义。
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物传递”元素,就是六把轮椅的运用。这是“人表演”与“物造型”的紧密结合,实际上,“物造型”在满足实用功能、特点强调之外,还参与了“表演”。一群病入膏肓、生命垂危的临终者,在舞台上如何行动?以常人健康人的方式移动,显然有违规定情境;以病者弱者垂死者的方式移动,舞台行动节奏就会慢得让观众无法忍受。在这里,导演查明哲想到了“轮椅”。静,是病床;动,是轮椅;如此,临终者的生活状态和行动特点,就很直观地展现在舞台上、剧情中了,且十分自然。重要的是,这里的临终者坐上轮椅之后,产生了“人”与“物”的高度结合,发生了“人表演”与“物传递”的奇妙效果。在《生命行歌》的演出中,演出舞台具有了垂直层级的两级平台——一级是规定情境中的舒缓医院的平台,人来人往,上场下场都在这个平台上;第二级是这个平台上的轮椅,舞台平台是不动的,轮椅却是游动的。轮椅是临终病人的病床,是他们的私人空间,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一句话,是临终者的生存领域和生命阵地。在临终者充满焦虑、表现烦躁、出现郁闷、表达关切,显现出超越病体的自由自在的渴望时,变化的表情与前进、倒退、直行、拐弯、快起、急停的轮椅功能融成了一体,“人表演”的情感内涵与心理节奏,也通过“物传递”获得了别样的实现。
五、艺术创造:典型宣传与艺术典型
当下的剧本创作中有一种顽症,就是把好人好事、新事新风的典型材料的搜集整理当创作采风,编成个故事就作为艺术作品上演,然后调动舆论手段去宣传推广剧目。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剧目在观众心中留不住,热闹一段,也就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关键在于,我们常常把新闻价值当作文艺价值,把宣传典型当作艺术典型,这就有点误会了,结果是,艺术生产的努力最终事与愿违。文化育人,艺术养心,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对人的影响远远不止宣传材料中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传播的那点内容,即使要传播那点内容,经过文艺创作的点化、深化、人化,会产生奇妙变化,形象大于思想,包含的思想含量、社会内容就会被感人的形象、丰富的情感所“涵化”,让人获得比新闻材料新闻典型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也动情得多的思想情感内容。这方面,此次的《生命行歌》是一个可以分析的例子。
作品剧情表现的内容本来是上海市金山区希望宣传的一个社会文明建设的典型材料,结果变成了一次艺术创造,也许这是一次意外的惊喜,也是一次刻意的创造。为了增加分量、提升意义,让《生命行歌》成为艺术品,编剧陆军、顾云月动了不少心思,想要在其中关涉一些社会问题,走出“宣传好人好事”的“报道剧”的局限。首先,“临终关怀”是中国老年社会到来的一个大问题;其次,每个人身后都有故事,可以牵引出与人物经历有关的社会问题来。这就有两个选择:是写社会问题剧,让临终的人们悲怆吐槽,带着各种社会戾气离去?还是找出生活经历的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诗意,让人怀着美好和慰藉,心平气和地往生?归根到底,是宣传演出,还是艺术创造?是社会戾气,还是生命诗意?这是问题。主创人员从编剧到导演、到演员,同心协力,从提升“好人好事宣传材料”的社会意义的高度上再前进、再提升,于是找到了生命价值与生命诗意的更大主题:每个人体面地离开人世,走向未知的可能与途径。这个问题,大可讲生命哲学,小能说我们的现实问题,可大可小,可中可外的普遍生命处境和生命难题,一下子就把剧目要讲述传递的“最高任务”所触及的“问题”放得更大了。于是,观众看到整个剧目演出的状况是:叙述体框架存、日记内容有、评判立场在。但是,特别“说出来”的奉献精神与感人事迹,更多地被剧情的行动、场面、细节、形象所替代,被更博大的情怀、更广泛的关联、更深刻的思考、更丰富的内涵所替代。“说”的宣传少了,“做”的感人多了,而且剧中人物避免了我们通常所见的那种宣传戏剧的“道德符号”“楷模符号”的弊病,都是一些有血有肉的有个性的“这一个”。苏院长、洪护士长、护士嘟嘟,都有自己在舒缓医院坚守和奉献的个人原因和选择理由。人生际遇与人生选择连在一起,有血有肉。在她们的陪护、照顾和引导下,孤老头陈阿公、倔老头吴老伯、拗老头许老伯、傲老头吴总、痴老太黄阿婆,最后都在舒缓医院真的舒缓了,放下了,安详了,在爱的簇拥下,情的感化下,细心的呵护下,暖心的融化下,孤独的有爱有陪伴了,倔强的平和平易了,执拗的获得满足了,冷傲的谦卑忏悔了,痴呆的霎时聪慧了……在生死交会之时,枯荣更替之际,一群临终者被照顾的是身体,被修复的是灵魂。
对于临终者,除了病理缓解外,要他们体面宁静有尊严地离去,恐怕还是灵魂疗救、情感复位和爱心温暖起了作用。临终关怀是人类主题,但是《生命行歌》表现的是“中国式关怀”,把大爱体现在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温暖当中。红尘的事,用红尘的办法解决。中国人的生死,有中国人的方式。这是剧组为一个广泛的人类主题贡献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查明哲给演出总体形象提炼出来的形象种子:一首穿越生命隧道的啸吟行歌。有声、有色、有动感、有豪情,而且,有过程。
六、意象/形象:《生命行歌》的结尾处理及其他
戏剧演出的结尾,在LED屏变化的画面簇拥中,终于度过艰难时刻的临终者举行了热烈的告别仪式。一群“老小孩”在舒缓医院的医护人员的陪护过程中,各吹各打,个性互异的生命个体终于融成了一个生命群体,一个坦然走向死亡,走向那个未知世界的整体。唱完《赋得古原草送别》,他们完成了生命接力的交接棒,姿态各异,脚步蹒跚,但是毫无畏缩感地迈向医院那个长长的内走廊——走廊被处理成无限延伸的视觉形象,与地平线相接,与蓝天白云相连,那是往生之路。
本来,举行完告别仪式,唱着歌满身轻松地走向走廊深处,走向远方,走向天边,应该是一个意象悠远的画面。但这个时候舞台呈现的“形象表达”出现了泰戈尔诗句形象与白居易诗句意境的冲撞。泰戈尔诗句对生命不同季节的形象比喻遮蔽或者干扰了白居易诗句对生命更迭交替意象的渲染。LED屏幕上浓重瑰丽的色彩,让老人们手上举着的可爱的彩色气球显得暗淡,老人们的身影,也被LED屏幕的色彩“吃”掉了。如果,此时的舞台形象素净一些,淡雅一些,宁静一些,可能更能彰显老人们渐行渐远的背影,更能突出老人们手上的彩色气球。演出者应该想清楚,是需要突出彩色瑰丽的舞台,还是需要衬托有彩色的人和写意他们富于故事的一生形成的彩色的灵魂。可以说,结尾处的形象追求遮蔽了意象创造。
演出结尾令人遗憾的是,缺少余音袅袅的延续,没有了应该有的令人回味无穷的隽永。在老人们齐唱结束转身走向无限延伸的长廊时,观众还在泪眼迷离中目送老人们的背影,尤其是老演员刘子枫还在以他惯常的角色姿态走向长廊深处的时候,谢幕就开始了。一方面干扰了刘子枫善始善终的最后表演,一方面把营造起来的“萋萋满别情”的诗意给破坏了,再一方面是使得刚刚出现的悠远静美的意境戛然而止,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诚挚谢幕、鞠躬再三的套路。此外,演出中角色嘟嘟经常抱着一把吉他,不时拨弄一下,伴奏一下。但大部分时间这把吉他没有太大用场,尤其是在“行歌”的音乐形象中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还常常觉得碍手碍脚。道具的存在应该像挂在墙上就必然出鞘的那把剑一样重要,成为剧情与人物特别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否则显得多余,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