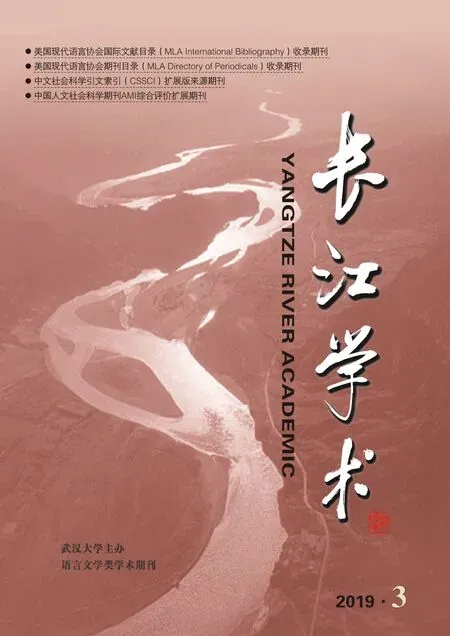“失事求似”:历史的症候与伦理
——重评郭沫若抗战史剧
陈若谷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沫若自日返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从此展开各种复杂的战时文化工作。肩负重任的郭沫若不仅要操持国民党政府的各类官方活动,主办《抗战日报》,还于1941至1943年之间,创作了六部历史话剧。在“皖南事变”的背景下,国统区内掀起坚持统一抗战的浪潮,要求坚决清除抗战中的不利因素,而郭沫若的史剧更是对此一民族情绪有推波助澜之功。
20世纪20年代中期,郭沫若写作完成《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三部历史剧。当时,剧作家顾仲彝、作家向培良等人就对郭沫若的历史剪裁方法提出过批评,认为他的剧作是话剧而非史剧。20年后,郭沫若作于抗战时期的几部历史剧依然面对着相似的质疑声音。
历史真实、艺术倾向和时代诉求等多种因素必然会共同参与到文学创作中,并制约其对历史认识的表意。更关键的是,用不同的伦理观念去捏合历史,以艺术的方式呈现现实诉求,其中必然包含时代对于个体情感的召唤以及个体意识参与历史的渴望。开放性的战争状态为知识分子社会参与和历史想象提供了条件,也推动着抒情个体向大历史敞开胸襟,与时代携手并进。
一、时代的症候
《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选取战国题材,《孔雀胆》《南冠草》本事则来自元和明的亡朝之际。这几个历史时期,同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一样,政治局势不稳、民族矛盾尖锐。二者的相似性有利于引发历史殷鉴,比如,屈原借信陵君之口说“你把我当成人,我把你当成人,相互的把人当成人,这就是克服秦兵的秘诀,也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秘诀”;夏完淳杀身成仁,寄望于“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的胜利前景;聂政短暂辉煌的人生说明了舍生取义比苟且偷安更能彰显人的价值;屈原虽忠而被谤,但大夫士子必须以一己承担来唤醒民众内心对气节的向往——这些历史形象在郭沫若的阐释中都彰显出了人的生存价值和精神力量,也是他在对群众进行情感教育和政治动员方面有意而为的文化努力。
肯定和赞扬郭沫若历史话剧的声音皆出自同一立场,而且与政党政治紧密关联。孙伏园就撰文为其“定调”,称话剧《屈原》为一篇“新正气歌”。各大报纸也竞相报道公演盛况,意在促进凝聚民心团结抗战之作用。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有不少批评的声音,比如不尊重戏剧艺术规律、剧作描写不符合史实等。在这几部话剧中,郭沫若创造了许多无法印证于史料的人物,有些情节甚至与史实相悖。比如魏太妃、婵娟的形象,如姬对信陵君的复杂感情,《招魂》的归属……对于这些艺术虚构乃至刻意的“张冠李戴”,郭沫若极为坦然直率。“失事求似”是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创作原则,也是他对历史刻意偏离的自我辩护。几乎在每一部史剧创作的前后,他都要撰写相关的“史实”介绍甚至是考证性文章,这是在展示诗情融合的努力。我们暂且可将这一原则视为,郭沫若的历史观和文学观,二者井水不犯河水的孤立联系。阐释起来,也即历史不能够限制史剧创作,因为这本质上是科学和艺术的区别、是实事求是和“失事求似”的区别。但这句话,“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却不期然地展示了历史和(一种更复杂的文化政治所主导的)艺术之间的高下之别。在这里,现实并非二者的分野,而是一个发展的环节。史剧创作并非对现实的逃避,而是描述一种更美好的品格和可期许的未来。
也就是说,“失事求似”内部可能暗含着一个时间箭头。郭沫若并不是希望观众/读者在“(严谨的)科学—史实—真的”与“(洒脱的)艺术—戏剧—美的”,这二者中做一个选择。因为真的和假的、实然和应然之间也许没有明确的边界。他不相信有绝对的“历史语言”,因为这个“现在”无法定位,“刚动一念,刚写一字,已经成了过去。”“认真说凡是世间上的事无一非史,因而所有的戏剧也无一非史剧。”这一番妙论剖白,自然可以其上天入地的浪漫气质来加以解释,但更合理的维度,也许应以他的历史伦理观作为理解的抓手。
坦白说来,郭沫若的史剧具有一些现在看来愈发明显的症候,不仅仅在于挪用史实、创造史实这么简单。在《屈原》里,渔父、仆夫等民众的觉悟产生于屈原之诚与忠的感召,最终落脚于爱国之情,这是一个陡峭的转化。从“楚国的老百姓”到“中国的老百姓”可见其超前性。这个突然的置换,使得郭沫若把秦楚之争与现代民族国家沟通起来,建立了互通互喻的对应关系,开启了以旧有的文化去探讨新的时代的可能,但不能回避的是,一些形象和概念仍旧没有实现“现代”价值转化。
比如对“国”的理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郭沫若描写的道德只能接纳屈原的文人士大夫忠君报国的传统,却遮蔽了张仪这种国界开拓者对“大一统”的探路先锋之功。这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历史语境中自有其道理。其次,发展形成中的小知识分子,此前仅仅是进退失据手足无措,那么他们终于在这里兑换了一副可鄙的面孔——剧作轻易地放弃了宋玉,且将其置于价值洼地,以至于地位低微的婵娟都有资格唾弃他。再者,古代的荆轲、豫让是以“士为知己者死”的义气流传于“江湖”上千年,而聂政之死则是献身于昌盛国家和太平黎民,这就取消了“侠义”的草莽英雄气。与此类似的,是国难当头之际伟大母亲的叙事符号,《棠棣之花》里酒家母愿让女儿赴死是因为希望女儿“成为有名的烈女”。其他女性形象的粗糙更可堪回味,比如南后只手遮天的能量,竟仅仅来源于其女性魅惑……在这里,女性被拉来成为古老“文化”的点缀甚至祭奠。
另一方面,历史剧中更多地是在强调精英和贵族的责任,而普遍心灵觉醒的过程被简化甚至忽视了。在《棠棣之花》第五幕中,众人合唱:“中华需要兄弟,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把主人翁们唤起。快快团结一致,高举起解放的大旗!”这里的民众,更像是为了圣人的召唤,就可以为正义而战、为国族而死的客体对象。让人不禁产生怀疑,对政治涡旋懵懵懂懂的贩夫走卒,他们投入战争是清醒的吗?拯救民族的力量,究竟是来自破家亡国时刻本能的反击,还是自上而下的精神感化?在这个轻易被理性接纳的秩序里,民间世界的诸多杂质被过滤掉了,流向了精英分子所雕凿的路向,上下一起,振动着节奏一致的精神脉搏,郭沫若毫不犹豫地弥合了精英分子与民间世界之间的精神裂痕。唯一不同的是,英雄与圣人为一个整体的大众和模糊的国家牺牲,但是平民,作为圣人贤者的奴仆,可以为英雄个体牺牲,比如婵娟、盲叟父女等人。郭沫若对民间世界的理解路向体现在他一系列有关民间大众的表述中,呈现出立场分明的阶级意识。比如,群众、如姬、信陵君,这个等级几乎分别对应着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暗暗通向了20世纪60年代文学生态限定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只不过,这时候历史还在虚位以待,等待那个真正的无产阶级英雄。
在当时抗战总动员的背景下,郭沫若所选取的任何材料都不应与爱国团结的主题相疏离,然而艺术的价值判断标准是顽固的。项羽乌江自刎的故事之所以具有雄壮的悲剧美感,是因为曾经铁塔一般的英雄也有末路穷途的时刻,而不仅是大业未成,又陷美人,更加不是一切厄运始自谗佞陷害。同样的,将盲目地不惜以己之命换取忠诚永生的群众推到历史前台,都是在放大时代(所需)主潮的同时,对于复杂斑驳的历史意蕴的遮蔽。精英个人的清醒意识和孤独精神与粗粝马虎的历史之间必然龃龉的深沉悲剧,也就无法获得历久弥新的思想力量。这是始终绕不开的缺陷。
史剧的体裁决定了浪漫激情必须与历史视阈平行发射,“以古鉴今”的前提是传统与历史之间有相通的确然价值,过去要作为一种可供追慕或者抵制的参照物,因此必然要对古老精神做一番辩驳或者回护。借用传统的文化因素或者符号,在国难之际,以历史剧承载民族自我保存的诉求,目的都在于创造新的人性骄傲和文化辉煌。然而,这几部剧作再次证明了一种不加甄别的历史惯性,而搁置了创造新世界的初衷,好似在不知向何处去的历史裂缝里,画下了一个问号。郭沫若的历史所展示的是一种潜藏的宏大时代危机——面对历史经验,在一个战乱时代,郭沫若虽然想象出来一个人民的天下,可是却不得不借用旧的伦理。
因此,这造成了我们当下的认识和当时具体历史情境之间的鸿沟。对于历史和传统的借用呈现,若一旦遭遇语境的转换,其时代内涵就会捉襟见肘。这可能更加证明了,离开具体的理解和史家笔法的描述,历史的面孔不会绝对中立,而是更加模糊和无用。我们仍旧需要以“历史化”的态度去正视人对历史的涂抹和征用。
二、抒情对冲历史
在1926年与1927年左右,眼见得大革命颓势不可挽回,郭沫若此前作品里狂飙突进的纯粹“自我”,逐渐成为具体环境里具有现实精神的“我”。他鼓吹“文学=F(时代精神)”,“文学=F(革命)”,“文学是革命的函数”。在等号一边,时代精神变了,那么文学的意义便随之变化。也许,郭沫若自我人格的设计早在时代潜流暗涌之时就已发生了。因此,考察这几部写于战时的历史剧,最重要的目的不在于看时代的潮汐把什么抛到了岸上,又带走了什么,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寻根和先后排序。关键要看到,历史剧对历史事件的价值表述起步于哪里,在哪里汇入了创造者本身的个性诉求。艺术在此刻成为充满张力和弹性的移动边界,是一种携带着容纳、反应、想象和塑造等各种基因和功能的形式。
战乱时代里最棘手的问题是要促进民族凝聚力与团结御侮精神的生成,借用可利用和阐释的时代精神。郭沫若深入历史后,找到的是仁义思想:“战国时代是以仁义的思想来打破旧束缚的时代,仁义是当时的新思想,也是当时的新名词。”他的《十批判书》最鲜明的特色就是现实针对性,为了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未来的政治文化思想建设,坚持“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是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他的历史剧创作和扬儒非墨的主张一样,是为了呼吁把人这个自然的权利体张扬起来,“人”字大旗将会成为未来政治的文化基础,而不能仅仅重复“新文化运动”时强调个体解放的路径。因为有“我”的精神介入,文学与历史的界限也就根本不能构成作者情绪抒发行为的焦虑。对郭沫若而言,历史和现实,都是他表达自我感受的材料。飞扬的人格意识使郭沫若的史剧呈现出跨文体、跨时代的强大缝合力,古与今更是可以处在同一时空平面,相互借用认识。他不仅借用了历史,还以自我的强烈情感,为其赋予废墟的面目,使早已完结的过去变成可供主体介入的未完结状态。
郭沫若的文学气质波流涌动,性情强烈,最开始的创作缘于,“于听取客观的声音不大方便”,“爱驰骋空想而局限在自己的生活里”,因此“爱写历史的东西和爱写自己”。而这必定让其在考虑历史和自我之间的价值关联时进行倾向性选择。早期的《天狗》《女神》,都是这种个性在时代搅拌下混合而生的产物。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并不强调能指之实,而强调所指之虚,“‘奥德赛’这个名字是否有一个意谓,对我们来说就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奥德赛”所唤起的感动。因此,抒情一直是郭沫若创作的关键词,文学的感染力是他真正的着力点。即便是要讲述历史故事和注重舞台表现的历史话剧,其创作也没有抛下自身的“抒情传统”。
“抒情传统”论述由汉学家陈世骧首倡,再通过王德威与陈国球等学者推动,逐渐形成了一套“抒情现代性”理论。大陆学者研究的成果是抒情同样可以对接政治的情感结构。尤其战争时期,存放新青年式抒情的政治空间被撑开得更广阔,“这不仅意味着政治和社会动员利用了文学的情感调节机制,或者说,浪漫主义的情感机制本身就具有社会动员的潜在力量,还在于,政治从本体上就具有诗性的情感维度”。
以此视角观郭沫若,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充满了“我”的文学起步,郭沫若一直都在自己的文化园地里播种。不同于周作人埋头沉浸于“苦雨斋”,郭要收集他人的目光,汇入时代的合唱。他这样嘱咐青年:“我希望你们成革命的文学家,不希望你们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这也并不是在替你们打算,这是在替我们全体的民众打算。”这种要求进步的思想主张与自我抒情并不犄角相抵。关键是对“情”的理解必须突破现代视阈里个人主义的内面自我之发觉,也不是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潮流孕育的针对自然的局限。抒情与历史的对冲、诗骚和史传的对话,绝不仅仅塑造了一些长于自我抒发的主人公,比如屈原的大段独白,也不在于在气氛的设置上增加了浪漫奇诡的色彩,而是敞开了个人的精神视阈,并且激情地投入时代,和时代互相探察,一同成长。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郭沫若,不断有精神调整,不断在其文学里裂变出新的自我。而这个自我,每每都呈现主动与他人发生关联之势。郭沫若在当代的写作和政治表现,与其本人的爱国主义、个性解放和英雄情结并不矛盾。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但是它与现实接壤处潜藏着多种可能性,而“此刻”情感的参与常常能改变重大的走向,甚至直接产生改变史实、构造历史的作用。
屈原的形象、聂嫈的形象,他们的独特自白和抒情,都是“史实”和诗情的双向建构。戏剧是利用情感来阐释理想之人。这和贬斥奸佞、团结抗战的时代功利性是相互兼容的。无论是创办《救亡日报》,还是开展第三厅的工作,都是在此紧张战时凝聚力量,摒弃松散和无聊的自由主张,快速地实现一种“共同生活的愿望”,每一个微小细节都与人息息相关,“冷漠的超脱可能掩藏着道德情感的缺乏”,历史需要利用这个能量发动第一次引擎。李健吾也承认:“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要容易。”
历史的进步有赖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无论是在历史研究中还是史剧中,郭沫若都不断在强调:“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故尔有这仁和义的新思想出现。”抒情主体要携带着普遍的人性基因,穿越历史的隧道,与现实的人们形成情感的共鸣。朴素的做人准则、重新发现的民族感情和激荡的爱国精神,扭结在特殊的时代氛围里,合奏成了抒情的咏叹。艺术和政治的结合转化、个人抒情和历史价值的相互扭结、诚挚的诗心和个人的理想转换成动员民众的口号,这是他自我革命主体再生产的条件,也是融合了抒情的史诗在短期内所迸发的能量。
郭沫若深受尼采思想影响。他的“创造”是在尼采的“超人意识”里产生的个体意志。在现实的情感教育考量之外,郭沫若的抒情方式也表达了他对于“人”的信心。人是君临一切的主宰,就像尼采强调,“他知道,完全是他自己赋予事物荣誉;他是价值的创造者。”郭沫若同样应如是。他并不是一个历史的迟到者,请看《屈原》里屈原的愤怒——“但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呵!”这种将自我放大到群体的逻辑其实是,认定每个人都既是自己的时代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搅动它的力量,无论是诗作还是神话剧、历史剧,郭沫若的文本一直都有一番与滚滚向前的时代相互对质的信心。
“一个可以许诺的人,他有一种骄傲的、在每一条肌肉中震颤着的意识,他终于赢得了这意识、这生动活泼的意识,这关于力量和自由的真实意识,总之,这是一种人的成就感。”郭沫若自身肯定没有实现完美的道德理想,但他相信有一个必然性的存在,让人可以借此估测未来,掌握现在。虽然写的是过去,但是因为“现实”的“现在”根本不可信,因此屈原、信陵君、夏完淳等形象的双脚,都立在一个可被期许的未来。
三、面向未来的历史伦理
亚里士多德“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的观点,直接奠定了诗比历史更真的认识,因此文学被赋予了整理和描绘历史的重大责任。立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发出疑问,如果历史脱离了严密的考古记录和精致的文学描述,它是否依旧存在?而人的认识又真的能与“真实”完全契合吗?答案是模糊的。那么暂时可以说,作为延伸的文本,历史被人们从中摘取出自己认同的阐释方法,并且经由加工,衍生成了一个审美与道德的全新产物。对于这个全新的产物,不能再用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来臧否,而需要用当下的经验和道德加以利用。
历史不仅仅作为一个可以被借用的对象,还是一个可以释放反作用力的实在物质。“历史通过一种对抗的意志和一种解释的意志获得生命力。”反过来说,人也是通过历史的存在来使自己与他者和时间产生关联。借历史抒情、任意裁剪历史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我们理解郭沫若史剧的终点,而仅仅是一个出发点。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如果无可避免要粉饰、颠倒历史,那么怎样的标准是适当的?在文学功能层面,我们已经可以得知,郭沫若的戏剧实践是极为成功的。不过,在功能、历史真实和作者人品之外,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伦理来裁定文学艺术活动的自由限度?
中国人心目中的历史,永远在未来凝视着此刻的高尚与卑微,这种静默的“不胜而胜”蕴含在历史颠覆现实的潜能中。之所以对历史怀抱这种期待,主要源于对伟大心灵和高尚人格的期许。在潜意识中,过去永远作为庄严的“此刻”存在着,鞭笞卑下的现实,庇护受刑的理想。因此,如果要求历史完全保持着知识化的纯净,就是对其最大的蔑视。
一个被归纳成一种知识的历史现象是死的。司马迁的《史记》真的是在历史意义的层面被接纳和流传的吗?未必。这里面首先有司马迁本人对历史的认识,且在后人看来,这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同时也在阅读中将司马迁的史官之笔历史化了。在承受宫刑后仍旧拿起笔的那一刻,司马迁就打败了为胜利者服务的历史。虽然承受着现实的失败,却最终主客颠倒,高高地矗立在历史之上。“你只能用现在最强有力的东西来解释过去,只有通过用尽你所拥有的最高贵的品质,你才会发现过去之中什么是最伟大的,是最值得了解和保存的。”人类在历史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人们理解到的伟大让他们知道,历史永生的奥秘在哪里。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其实不必去批评“忘记”,却需要质疑“背叛”。背叛的对象是谁,以及为什么要背叛?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来解答:“过去一切并没有在过去中消失,因为‘观念’永远是现在的;……既然只有现在,故‘精神’的现在形态必然是把先前的一切阶段都包括在内。这些阶段自然是独立地、接二连三地展开它们自己。”那么,遗忘本身并不会斩断历史各阶段的内部本质。因此,人所“背叛”的对象恐怕是现在。更进一步说,有时候是对未来的期待统治了对过去的描述。这就直接将“过去”进一步架空,而凸显了历史的伦理在于理想和现实的衔接。过去并不比现在拥有更多珍贵的美德和公正,人为了自己的现世生存,有权力为过去盖棺定论,更有权力创造另一个过去。“为了生活,人们必须要有力量去打破过去,同时运用过去。”实际上,不论是历史的早生代还是晚生代,统揽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才有资格谈论“历史的进程”,才能进行新一轮的创造。
真的存在“女神”这个神祇吗?“女神”是潜藏在诗人胸膛里的诗心,仅仅是等待一个秘密信号,当那一瞬间降临,她就会雄壮地喷发。1921年,郭沫若写下《女神之再生》,这是一部从散文改写成的诗剧。石像女神们高高在上,眼见得共工和颛顼“争为帝”而不为所动,却各自思索着自己的意义:重造光明和温热。最有意思的是,最后舞台监督上台来,对观众说:“作这幕诗剧的诗人做到这儿便停了笔,他真正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诸君,你们要望新生的太阳出现吗?还是请去自行创造来!”
历史并不是被封存打包好的毫无关系的数据资料和神奇图景,为了走向历史,文学表达携带着未完成的承诺。有意思的是,用文学艺术来做战时动员,不是因为文学艺术有着摧枯拉朽的强大势能,而是它太脆弱,它可能遭到各种误解,但也可能被敏锐的耳朵细致甄别出其中百转千回的惆怅和余音绕梁的抒情。之所以说“叙述”和“表演”更具有蛊惑性,是因为其虚构和意识层面的恍惚与不可确信,文学因此成为一种我们以想象和象征方式改变日常现实的形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可以重塑艺术化的历史,在文学创造中,而不是历史研究中,塑造历史的伦理。
《棠棣之花》《屈原》之类剧作的上演,“它是民众蓄势已久的政治欲望的集体上演,是被压抑者曲折表达政治情感的一种政治行为艺术,当然也成为党派力量所倚重的一篇特殊的政治檄文”,是主观和客观共生、抒情和史诗相互缠绕所形成的作品。艺术本来就拥有这份自由,去摆脱过量的历史知识和层峦叠嶂的政治姿态,所以会刻意选择忽略、遗忘、隐藏。在完成了艺术的这重塑造、再生、治愈功能之后,人才能成为“超历史的人”。也就是说,他把刻画自己,以及刻画自己同时代人的重任,扛在了肩上。郭沫若显然将自己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两个身份既结合又区分,拿来相互利用,完全不遮掩自己的造物者雄心。
不过,历史的邪魅又一次降临了。郭沫若将历史的重要任务塑造成了创造历史的人。但是创造历史的人如何可信?如何才能证明他们确实有能力创造历史?于是,非常吊诡的,他们紧接着创造了历史的迟到者和追随者——群众,谁都愿意为伟大的灵魂而献出自己单薄的生命。这是无法回避的伦理问题。是重复了很多遍的现代伦理困境的难题——历史只属于“超人”吗?人会因为情感的倾诉冲动而向历史敞开,最终获取一个有情感又有行动能量的主体,但是有没有可能在他敞开的同时,也被另一种力量排斥了呢?郭沫若强调个人人格的重要性,其实也就是在强调秩序。人所能够彰显的历史的价值,本质上是把自己也编织到历史里去。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郭沫若的评价可极为简单也可极为复杂。因为历史本身是在变化的。而他是一个无法得知“现在”的人,意欲创造历史的人。一味回护历史真实的价值是无“我”的。大胆采用历史,以古鉴今,展示了剧作家郭沫若的历史观:历史是属人的,而不是人所敬畏的神的世界。
结 语
郭沫若从事抗战事业,政治方面自然以驱逐侵略为旨归,文化方面则重在重建人性,民族救亡与精神重塑始终立在这一时代趋向的潮头。如火如荼的时代总是呼唤“超人”心灵的自我建构,气势磅礴的历史剧正好是一种个人向时代主动契合的产物。戏剧这一极具轰动效应的艺术形式最受瞩目,它承担了显在的振奋士气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宣传功能。新闻媒体的报道定性和民心向背的对立局面,也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在意义的生成、阐释和传播方面提供了长期有效的政治性方向。
郭沫若史剧的主观色彩与浪漫气息有着浓厚的个人印记,比如屈原被看作郭沫若在写自己,他也亲口承认1949年后塑造的蔡文姬投射了相当多的个人精神。这种透明姿态,让主体自我与历史两者获得了暂时的统一和融合。郭沫若热情地驱逐了可能存在于民族和启蒙精神、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混沌迷思。但在新的时代价值面前,郭沫若和他的作品被一道压抑在了道德评判和对于中国历史道路评价的低气压下,“新时期以来,对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知识界的认识跟50—70年代有了断裂,产生了全新的认识装置。”
一个新的世界破壳于灵感。改造历史的第一步是释放激情与莽撞,但它最终会回到严格的历史框架里。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塑造,其实就是在塑造自身的历史观念和主体位置。有论者认为,“郭沫若本人便是中国现代变革中的内在参与者,他的很多观点不能当作历史常态中的普通见解,而是基于他的社会位置对时代问题做出的即时思考和回应,蕴含着他对历史走向的判断。”应时而变的自我身份、随势而转的历史书写,郭沫若自认为:“它们事实上是一个有机体的各种官能。”这是一种很乐观的想象。因为实际上,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同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一样,只是历史的过渡,他们所吁求的幸福被一再推迟。这是所有具有宏大主题的戏剧的共同病症:在开启未来的同时,也会造成一个融合了记忆、承诺、责任和希望的无底深渊——又一次“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每一个绚烂的瞬间都会轻易被简化,在时间序列中凝固成一个平淡无奇的过往,每一份喧哗最后都融入了庞杂的背景噪音。
但仍然需要肯定的是,“失事求似”确实是郭沫若创造史剧时的艺术观念,但也是历史和政治的修辞术,这出自他对自我的流动性塑造——这就是他所说的“发展历史精神”。对于郭沫若来说,艺术和历史之间的转换,带来的并不是身份认同的危机,而是自我的完成。虽然被形势裹挟,他却更多的是一个试图主动创造历史,为成千上万的人勾勒新的图景的人。历史剧作,其实就是他的个人抒情和历史史论之间的联结。他那些曾经引起狂热追捧的历史剧,以戏剧化的表现将其人文理想和政治想象发扬到了极致。也是那种极致,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只是过于顺畅的进程流动,让它不够完备、细腻、熨帖。然而,作为一种借用过去的历史观、一份昂扬的精神想象,它已经许诺了未来,成全了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