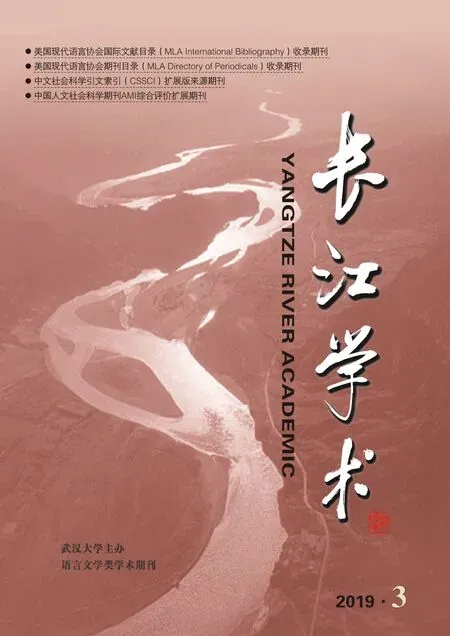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重奏
——陈毅达小说《海边春秋》的政治话语分析
吴子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作为人类确认自身和表现自身的基本方式,叙事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詹姆逊将叙事定义为“社会的象征性行为”,把叙事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射或想象性解决,认为所有叙事都含有政治无意识,即隐含着社会集团或阶级的意识形态愿望或政治幻想。
我国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士大夫包括文人都有经世报国的情怀,这是文学与政治建立关系的文化基础。理想的政治应蕴含对真理的追求和创造性变革社会的奋斗,其最终指向应是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解放。近年来,理论界、创作界一再重申文学的政治维度,彰显的是一种现实关怀,一种对社会、对人民和民族的责任。这是对沉溺于“灯红酒绿的文化放纵”的抵制,对一味追求语言迷宫和感觉狂欢之审美感性的纠偏和补充,表明了人们对于现实社会政治热情的提升。
陈毅达的新作《海边春秋》(百花文艺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2月版)选取了一个比较敏感的现实生活题材——村落的“搬迁”,以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岚岛综合试验区建设开发为背景,讲述了走出书斋到岚岛挂职的文学博士刘书雷,在兰波国际项目与蓝港村整体搬迁工作之间来回穿梭,最终破解困局的故事,生动展示了我党领导下新时代创业的艰辛,同时也预示了新时代创业的远大前程。这是一部政治色彩较为浓厚的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的编者威廉·范·俄康纳在该书序言里说,一个小说家“能帮助我们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或者不是这样知道的;使我们发现一些我们相信是真实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与我们的行为和态度有密切关联”;一个小说家应当找到隐藏在动作里的主题,使这些主题成为活的东西,像一股强烈的电流,“他不应当预先知道他的题材的意义。他必须等待故事开展,逐渐发现他的主题。如果这本书写完以后,主题极清晰地出现,那么作者大概是隐匿了一些证据,写出来的是一套教训或是宣传品”。
陈毅达是精通小说这门手艺的,其《海边春秋》不是以往那种简单图解方针政策的作品,因为小说的政治化不是以一种外部的力量来干预文学,不是以一种明确的目的理性来代替真正的生活,而是通过重新塑造人的感觉和精神世界的方式,通过审美与政治的融合来实现的。因此,《海边春秋》成功跳出了以往小说叙事与历史理性的权力结构同构、沦为权力意志之载体的窠臼。
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说得好,“一本书中的人物是由一连串言辞构成的。”我注意到,《海边春秋》在以报告文学式的手法写作,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时,特意省略了人物对话时常用的引号,使小说叙述的语言与人物的话语重合为一,视角随叙述方便,在叙述者和各个人物之间自由切换。这样,人物的话语便不是在“转译”一种已然形成的思想,而是在言说中探索性地思想,并在行动中实现这种思想。思想在语言行动中诞生,而不是思想决定了将要说出和写下的话语。我们在倾听人物话语的时候知道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从人物话语中获取的东西比放入其中的还要多。通过展示人物之间事件的发生、人物的抉择,小说带引我们去经历,去体验,去思考,深切感知问题的核心所在。由此,小说的写作超越了报告文学式的指意活动,成为一种对于现状甚至未来的勘察与图绘;其间的政治因素寄寓在作品的理想人物(如援岚干部刘书雷、村支书张正海等)身上,也隐藏于曲折的故事情节乃至小说结尾之中,传达出了政治的意味。
陈毅达的《海边春秋》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为政治服务的作品,还因为其中“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小说里的“政治”已然由阶级政治延伸到人民政治,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
首先,小说里的政治已不限于阶级斗争或党派政治,而是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人民政治。
岚岛是闽省第一大岛,邻近台湾,是两岸融亲的摇篮;邻近港澳,是中国大陆面向亚太地区的重要窗口之一。从任榕城市委书记起,习近平总书记先后21次登岛访贫问苦,始终把岚岛的建设发展和岛上群众的生活疾苦放在心上。2009年岚岛被中央确定为闽台合作和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2011年又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区,2014年习总书记专门到岚岛深入考察,提出“一岛两窗三区”的发展战略,做了关于岚岛建设国际自由贸易港口和国际旅游岛的重要指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岚岛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此出台了很多具体举措,还分批次抽调不少年富力强的业务干部入岛援建。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刘书雷是闽省引进的人才,在省文联工作不到一年被派往援岚,在援岚办工作两个多月,又被派往进驻蓝港村,协助解决整体搬迁的难题。蓝港村在岚岛属于发展滞后的村子,由于缺乏竞争力,这个渔村的大部分劳动力从远洋航运、对台贸易转向到岛外各地做生意或务工,留下的基本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跨国机构兰波国际原来与岚岛签订了深度合作协议,计划将蓝港村整体搬迁、清空重建,村民则由兰波国际负责统一安置,没想到全体村民强烈抵触反对,还差点酿成群体性事件。问题如果不解决,兰波国际可能撤出项目,有损岚岛的建设形象。此前,李副省长就此讲了三点处理意见:一要摸清民情,正确对待村民诉求;二要务实唯实,找到具体解决办法;三要力求双赢,注重大局和民心影响。刘书雷的主要任务就是再做最后一次调研,就整体搬迁一事认真听民声、察民意,并提出最终解决的对策和建议。刘书雷到了蓝港村后,通过各种工作渠道和走访交往,深切领会了中央一再强调的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底线的精神;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的最佳境界是各方全赢,一个都不能少,决不能让民利、民意、民心做牺牲。关键时刻,岚岛综合实验区党工委金子铭书记和管委会赵子才主任批示了重要工作意见。赵主任的批示写道:“……为什么我们认为是办好事、实事的一个项目,却引起了蓝港村村民不约而同地反对?是好事没办好,还是实事没做实?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前期的工作有没有真正往实处做?在大处有没有真正为村民着想?在小处有没有真正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金书记的批示同样强调必须有真正求实求真的态度和精神,必须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作,有效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真正落实中央一切为了人民的工作宗旨,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头,让岚岛人民群众能够实实在在地共享改革红利和分享开放成果。刘书雷和张正海瞬间意识到,这两个重要批示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重大转机。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赢得村民的大力支持,最后建议实验区党工委和管委会成功地调整规划,将蓝港村由整体搬迁、清空重建改为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利用、发掘海洋旅游中更为重要的人文底蕴,走上一条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兰波国际公司最终也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不再坚持原来的协议,同意重新商谈旅游开发协议,因为正如其董事长所言:每一个正规的公司,不能不对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政府表示崇高的敬意……
《海边春秋》生动反映的“人民政治”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导、主流话语,它所追求的是代表全体人民的真实利益,是绝大多数人的公平正义;它既强调对群体乃至民族的认同,又极其重视个体的具体性和差异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在小说《海边春秋》里,抽象的群体意识转化为对具体多样的个人生存(如虾米、曾小海、蔡橹子、元海依公、海妹、林晓阳、大依公、陈海明、林定海、蔡思蓝、台商胡老板、台湾艺人余望雨、兰波国际首席温淼淼……)的关切,写得贴心贴肺。
其次,由国家体制、国际交往和社会变革等层面的宏观政治到日常现实生活与个体生命层面的微观政治。
在小说里,一方面,宏观政治影响、制约着微观政治,另一方面,微观政治的作用又不可小觑,对微观政治的关注又有助于对宏观政治的推进。
刘书雷从张正海那里得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岚岛渔村里出现了老人会,村子里很多重大的事都要经过他们的认可;家里族里有什么纷争,都要找老人会来仲裁,裁定的结果比法院判的还管用。老人会在村子里有着极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近些年,村两委力量得到加强,村民法治意识明显增强,老人会人数越来越少,影响力大不如从前,有的就是作为风俗留存,变成一种敬老的象征。大依公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讨海能手,当过乡里的民兵营长,也当过蓝港村的村支书,后来是村里老人会的会长,原先在村里一言九鼎,现在虽在年轻人面前远不如过去,威信仍然很高。搬迁工作组两次进村,村里唯一没有正式表明态度的就是大依公。第一任工作组组长几次去拜访大依公都吃了闭门羹,第二任工作组组长带了镇里、村里的干部一同去,见了面老人一言不发,如同老僧入定一般。刘书雷灵机一动,以到大依公家吃饭为由专程拜访老人:根据村里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去谁家吃饭,他家都不能拒绝。刘书雷带上自己家乡产的四瓶“福茅”,买了些五香花生米、牛肉干、鱼松和肉松,跟张正海一起登门拜访,终于见到了大依公和他的孙女海妹。交谈中,大依公希望刘书雷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想法子解决村子目前的困境,就像明朝这里的书生林杨给朝廷上《奏蠲虚税疏》一样。刘书雷立马答应并把自己喝醉了。第二天,大依公邀请刘书雷、张正海一起到家里吃午饭。大依公敞开心扉,让刘书雷真正明白了蓝港村村民的心愿:“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又不是不能住了,活不下去了,一定非搬不可。要建设得更好,我们真感激不尽呢。干吗不让村里人继续住下去?”大依公的一席话更是让刘书雷心里震动不已:“我只想告诉你们,这地上是有魂的,我们的人最后都要离开,但魂会丢在这里,你说搬走了我们怎么会过得自在,过得好!”
可以说,正是从大依公这里,刘书雷才真正打开了工作局面,开始意识到问题症结所在:岚岛建设的出发点、目标与蓝港村村民的愿望、目标是一致的,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对立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其实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或完全背离了最初愿望和目的的现状来呢?如果不是村民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这边的问题了!可以说,大依公及其老人会对于村子搬迁的看法,构成了蓝港村不容忽视的“微观政治”。后来的事实表明,刘书雷得到了大依公及其老人会的认可与支持,也就得到了广大村民的认可与支持,很多棘手的工作难题都一一化解了。
在“全媒体”时代,人们还常常利用自媒体表达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事件的关注与评论。某些细微的事件,就像巴西那轻拍翅膀的蝴蝶一样,假以时日,也会掀起大的风暴。刘书雷进驻蓝港村前,援岚工作组带队的省政府吴副秘书长特意叮嘱他要留意一个网名叫“海上蓝影”的人,舆情报告显示这个“海上蓝影”通过微博等渠道多次发帖,广邀在外务工、创业、就学的蓝港村人回村共商大计。吴副秘书长要求刘书雷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要密切关注,随时掌握情况,认真对待,把相关工作做到前、做到早、做到实,确保不让他们利用网络扩大事端、扩大影响,让蓝港村搬迁的事情成为网络热点,给岚岛大建设带来负面效应。从村支书张正海那里,刘书雷了解到“海上蓝影”是工作队进村做整体搬迁工作后出现的,他了解蓝港村所有的事情,发了不少议论帖子,在网上带头反对整体搬迁,吁请当地政府能保留村子;“海上蓝影”很懂政策、法律和道理,不支持村民们闹事等不理智的行为,劝说村民通过正常通道、渠道让上面听到下面的声音,相信政府能够认真对待下面的反映。“海上蓝影”出现以后,很快就成了网信部门关注的对象,但一直不知道他是谁。随着调研工作的逐层深入,刘书雷终于知道了“海上蓝影”的庐山真面目:“海上蓝影”不是一个人,而是由林晓阳、海妹、依芳、依华、依秀五个人建立的核心微信群,他们的父亲都是定海依公当年货轮出事的罹难者,那艘大货轮就叫“蓝影号”,所以把微信群取名“海上蓝影”;他们认为,蓝港村是有魂的,这块土地是有魂的,应该为村子担起些事来,借助网络发声,抵制搬迁。到了蓝港村可能出现转机的关键时刻,在深圳创业的群主林晓阳回来跟刘书雷、张正海交流沟通一些想法。“海上蓝影”发出“蓝港之约”,设想建议在外蓝港村人签名请愿,甚至联名向法院告政府。刘书雷、张正海与林晓阳等人推心置腹,分析利弊,让他们认识到问题的核心其实不在于蓝港村是否“搬迁”,而在于其自身应该“怎么发展”,即把对于蓝港村的“思路”引导到“出路”,也就是如何克服后发劣势问题的探讨。林晓阳等人接受了刘书雷的建设性意见,把“蓝港之约”的内容改为“效力故土”,发动大家研究蓝港村持续发展、生态发展可能面对的具体困难,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在充分商议后,林晓阳等人决定回村创业,并到全国各地观摩学习成功的建设、发展经验。顺民心,符民意,上下同心,困难、问题便逐一解决了。
正是刘书雷、张正海等人充分认识到大依公的老人会、“海上蓝影”等微观政治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意义,而在微观政治对日常工作、生活的发声中主动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收拢了近乎散乱的人心,并把所有能量累积起来形成合力,最终克服了微观政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成功化解一次民情危机的同时,把正确的理想和信念贯穿于日常工作、生活之中。
最后,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
小说固然不是安邦定国的奏议或策论,但它要表现人的命运,揭示社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记录时代的诸多波澜和皱褶,必然要直面、洞察、干预现实乃至引领生活。在《海边春秋》里,我们深切感知到了隐身在小说故事、人物及其话语之中的“隐形政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得好,“人是政治的动物。”在这里,“政治”(politics)与“城邦”(polis)是同源的,意谓“每个人都是城邦的产物,势必关心并参与城邦的事务”。脱离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不对社会发言,不引导人们思考,小说的存在就成了问题。著名的英国作家奥威尔被誉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他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里坦言:“回头去看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所写的东西,无一例外地都毫无生气,都成了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矫揉造作的形容词,总之,都是废话。”作为实现人类理想的载体,小说应与符合人民利益的理想政治一道,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的精神的自由发展,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是作家的使命和担当。在我看来,《海边春秋》里的“政治”是一种“隐形政治”,是小说家陈毅达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深入思索,而不是抽象凿空的孱弱清谈。
佛家有一个词,叫“初心”;写作者拥有了“初心”,便能像一个新生儿面对这个世界一样,永远充满好奇、求知欲、赞叹,展示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海边春秋》里写到一个并不让人喜欢的角色——镇上的董书记,此人善于揣摩、逢迎领导心思,不仅不作为,而且还有强烈的权力控制欲。在他的眼里,只有项目、规划、蓝图、大局,唯独没有人。刘书雷问他蓝港村全体村民反对搬迁,镇里考虑怎么解决呢?他只会埋怨村民的觉悟很低,没有一点牺牲精神:“从全镇的发展来说,蓝港村只是个局部,从整个岛来说,这里的村民只是少数中的少数,镇里认为,这村里的村民没有看到长远,认识有问题,觉悟更有问题!我这镇里有几万人口,不能因为这几百人反对,我们就让几万人陪着等。”刘书雷提醒董书记:“你不是当地村民,所以你可能也不理解村民,他们需要对他们选择权的尊重,他们认为他们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董书记回应说:“刘副秘书长,听说你是文人,可以理解。有些东西,我们做基层工作的,跟你们文人看问题、想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没办法有那么多理想的色彩。”刘书雷强压怒火,说:“董书记,如果从内心怀有美好感情和浪漫理想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好干部、好官员,他们一定是比文人还文人。我还觉得,共产党人的初心,里面所装有的信念,是最浪漫的伟大和最理想的崇高!”董书记满面通红,悻悻离去。董书记正是由于失去了共产党员的初心,而被卡在了固有的思维模式之中,永远无法摆脱出来。
《海边春秋》对小说主要人物的设置也是颇具深意的。
在第四批援岚人员中,名校毕业的博士有20人,副高以上职称的有100多人,大都是自贸试验、社会管理、金融投资、文化旅游、科技生态、法治党建等重要领域的业务干部。刘书雷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原为闽省作协副秘书长,在岚岛没有直接对应的单位和工作,只能留在岚岛的援岚办,临时负责办公室的文秘事务。就是这样的“文人”,“临危受命”,进驻蓝港村,竟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工作。
刘书雷的“成功”离不开搭档张正海。作为下派村支书,张正海在桂省大学读的是旅游文化专业,又在浙省一所大学读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硕士。回到闽省在文化旅游委工作,起初在业务科室,几年后调整到综合科。后来蓝港村因为整体搬迁遇到困难,一年前被派往蓝港村任第一村支书,主要任务就是彻底解决搬迁问题。刘书雷下派调研工作的深入,让张正海茅塞顿开,转变了工作思路。在具体事务和运作方面,张正海有着比刘书雷强的优势。围绕蓝港村未来整体的发展规划,张正海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提出了系统的、操作性强的《关于蓝港村振兴计划》《蓝港村移风易俗村规民约》《蓝港村村民美化绿化责任制》《蓝港村党员责任清单》等报告。
蓝港村搬迁问题的大逆转,为什么是由刘书雷和张正海共同完成的呢?这离不开大机缘,即在新时代蓝港村遇上了大机遇——除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屋建瓴关于岚岛建设国际自由贸易港口和国际旅游岛的规划蓝图,还有便是“文化创意创业时代”的降临。
早在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便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指出“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构成了人类生活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我们现在已然进入了“文化创意的时代”,即“文化经济时代”,或称“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审美成为社会的一种结构方式,其中的很多原则直接成了社会改革和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操作的原则。在这文化创意产业勃兴的时代,情感再塑、文化记忆、传统文化等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潜能;人们通过拓展多元化终端,发挥从业人员的创意能力,形成了集群化的各种文化创意产业实体。莱特在《进步简史》一开篇就提醒我们:“文明若要存续,必须依赖自然资本产生的利息,如果无节制地糟蹋本金,必将遭受文明的反噬。”现如今,生态文明已被提升到与政治文明并列的高度予以重视。与之相应,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地区乃至村庄,产业结构的转型迅疾被提升上了议程,刻不容缓。
作为青年文学评论家,刘书雷有优异的审美眼光和审美判断。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的独特性,独特性才是它们存在的理由。”他一方面通过“了解之同情”的培根铸魂的调研工作,把握了蓝港人的情感形式,形成了情感共同体,实现了真正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则敏锐捕捉到了“文创时代”给蓝港村提供的重大发展机遇,而与张正海一道竭力打造蓝港村谋求新发展的广阔空间,使蓝港村免遭整体搬迁的命运并获得新生——还有谁敢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
张正海提交的“振兴计划”里,存在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即投入问题。刘书雷的大胆设想是,建议实验区将蓝港村改为蓝港国际旅游开发区,由村改区,直属实验区管委会领导,进行城镇化尝试。但是问题还是很尖锐,怎么解决资金的来源呢?
在全球化过程中,货币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西美尔(1858—1918)曾援引德国作家汉斯·萨克斯的话说:“金钱是这个世界的世俗之神。”西美尔对货币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发现了货币之于距离的重大影响:首先,货币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发挥着使单个个体原子式裂化的作用,出借给个体一种脱离集体利益的全新的独立性”,人与人交往、联合只是为了“共享一种金钱利益”。其次,货币还扩大了人与世界的距离,一切事物、一切价值都臣服、匍匐于货币的麾下,“事物质的意义上的本质在我们的视阈之外,我们和事物完整的、与众不同的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被瓦解分裂了”。再次,货币扩大了人与自我之间的距离,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客观文化压倒了主观文化,“利益的客体位于其中的外围越来越远离自我这个中心”,“生活的核心与意义从我们的手指间一次次溜走,确定无疑的满足感越来越罕见,所有的努力与活动实际上都没有价值”。斯宾格勒说:“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人只能以金钱的方式来思考。”以货币的方式来思考,空前地压缩了人的丰富可能性,将人的情感的价值扫荡殆尽;以货币的逻辑与性格所型塑的现代人,精于算计,冷漠无情,刻板乏味,不过是马尔库塞所预言的“单面人”。因此,西美尔警告说:“它(金钱)只是通往无穷价值的桥梁,而人不可能在桥上生活。”
在《海边春秋》里,我们也看到了货币在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之间制造的距离或裂痕,但我们也看到了货币还有一种将“世界”联结起来,将一切人、一切事卷入“世界”之进程的弥合作用。在小说的结尾,关系蓝港村命运的投入即资金的来源迎刃而解:当年与大依公一起冒死救过一艘台轮的大副胡先生的“小海鱼”——蔡思蓝,收下胡先生3万元答谢金后,离乡出走创业,几十年后创建了自己的集团公司。有着恋土恋乡情结的蔡思蓝,为了回报蓝港村,认捐3000万元作为蓝港村青年返乡创业的扶助资金,另支持蓝港村3000万元,用于重新规划建设经费。蔡思蓝还请刘书雷转告张正海,如还需用钱,几家银行给自己的思蓝集团还有授信10亿元,集团可以为村里担保向银行借贷。蔡思蓝还跟刘书雷打赌,当年的台轮大副现在的台商胡先生得知消息,一定会来认捐,估计至少会捐1000万元;如果胡老板捐了1000万元,他就再追捐1000万元!果不其然,年迈的胡老板来到蓝港村,见了刘书雷立马认捐1000万元,听说了蔡思蓝设的“赌局”后又加了300万元!
在这个充满碎片、满目断裂的世界,货币之所以还能将“世界”联结起来,使一切人一切事都卷入“世界”之进程,弥合货币所制造的距离以化解现代文化危机,其中关键在于“爱”。凝望生命的苦辛与无常,体味历史的丰饶与短暂,刘书雷理解了人性的参差不齐,懂得理解、同情蓝港村人的处境。如何才能拽住那牵动心灵的细线,洞察生活最为隐秘的肌理,安顿那些卑微、挣扎的灵魂,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欲求,让罹患的肉身不再啜泣或委顿呢?只有爱,故土之爱,家国之爱,民胞物与之爱!爱,使一个历尽沧桑的人变成了赤子,回到赤子之心,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生命的起点,这也许是唯一的出路。爱,是一切伟大事业和真正奇迹的缘由。爱,弥合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之间的裂缝,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
正如小说里林晓阳烂熟于心、刘书雷自己著作中所写下的:“责任感就是时代感,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永远都不知道他处在什么时代,所以,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更不用说他会有与时代相匹配的人文情怀、伟大精神、崇高境界,而这恰恰是我们改变现实、改变生活、追求理想所需要的。”“人文情怀其实是体现在对社会、对时代、对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态度和行动上。……在我们这个紧密型构造的社会里和高度关联性的生活中,个体既渺小又伟大,我们都有可能与所有的个体构建一个推动历史向前的基因组合。”在某种意义上,小说《海边春秋》给各级领导者提出了战略管理的问题:优秀的领导者,必须是人本主义价值理念驱动的追随者;管理是一种智慧,必须从人出发,否则就会失去主体性;文学是人的学问,文学研究人的情感、思维与行为,揭示人性的奥秘,可以提升领导者的格局、勇气、洞察力和反省力;以生态意识尊重管理对象,以美丽人生导引健康生活,最终才能达到一种和谐共享的美好状态。
可以说,《海边春秋》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重奏。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的真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面对一个选项过多的时代,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通过颂扬、描述美好,而不是一味通过批判丑恶,可能更有利于使社会不断地走向完善。那些古典作家深知这一切,陈毅达也深知这一切。他在生活世界高悬的画布上描绘世界的本来面目,描述人的善良、德行和智慧,并让我们从中得到了“美学乐趣”和“精神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