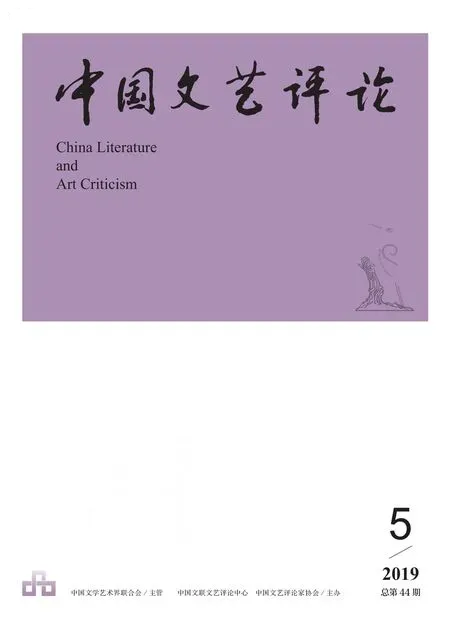互联网视阈下中国原创音乐的审美构建
李长鸿
互联网技术所催生的新媒体、全媒体文化语境对各个艺术门类带来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艺术行业在互联网浪潮的裹挟下,从技术、创意到商业、产业乃至审美特征及社会价值等各层面,都被解构并重构着新的模式,任何形态,概莫能外。这似乎已是被笃定认知的结论。而互联网文化随着自身的逐渐强大,从开始的“非主流文化”“亚文化”的标签中逐渐承担起更加普惠性甚至主流性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思考原创音乐——这个与大众文化结合最紧密的艺术形式之一,至少可立足在一个前提下,即我们需承认基于互联网视域下的音乐本身已成为在当今全媒体时代诠释社会文化语境的一种新方法。相较于传统的音乐生态而言,无论是外延层面的生产、传播、消费,还是内在层次中的语言、形象、意蕴,甚至创作与用户人群等都在呈现一种整体的改观,新的生态模式也是基于此而建立的。
一、关于互联网音乐或新媒体音乐界定的分析
在业界常有互联网音乐与新媒体音乐两种概念,本文从文化属性的角度出发将其等同视之,基于所有新媒体都是通过互联网技术或互联网思维而呈现的。互联网音乐和新媒体音乐都是相较于传统音乐而言,前者包含更广义的概念,后者则更聚焦于技术或传播手段。我们鉴别一首音乐的属性,通常从三个角度出发:内容题材与审美形态层面,创作者与受众人群层面,创作手段与传播及营销模式层面。而这些角度是否也能成为界定互联网音乐、新媒体音乐的标准?
很难最准确地说第一首互联网歌曲是什么,但通常把20世纪以来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视作网络歌曲风潮的肇始,随后2002年的《丁香花》、2004年的《老鼠爱大米》再到后来的《两只蝴蝶》等,似乎互联网音乐从内容层面大体呈现出通俗与浅薄化风格并多以爱情题材为靶向,一些负能量的歌曲也由此流传。然而当2005年《隐形的翅膀》、2009年《最炫民族风》,以及2011年筷子兄弟推出的同名微电影主题曲《老男孩》等作品的出现,让我们发现这类励志歌曲依然能借助互联网平台深入人心,单纯的内容题材与审美特征显然不能作为区分互联网音乐与传统音乐的标准。并且,无论是“新古典主义”流行风的代表《青花瓷》,还是“神曲”的代表作《小苹果》,内容的雅与俗、品位的高与低都可被不同审美品好的人群接纳,评判标准的不一而足,也是互联网文化的一种显著表征。
互联网时代的受众是“分众化”的,传播平台是“去中心化”的,体现着自由意识和权威消解;对于音乐创作者而言,也必然针对受众与平台的不同而实现内容的差异。一段音乐在电视、舞台上表演,抑或是在微信或抖音上播放,针对着不同的群体、体现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与发展路向,但其中也存在着共融性或转化性。比如一首《情歌赛过春江水》最早诞生于网络并被年轻受众广泛熟知,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大地飞歌•2017”晚会上亮相后,又被更多专业人士以及电视观众接受,随后在网络上出现许多广场舞音乐短视频,在一些直播平台上又出现诸多改编化版本。一个作品雅与俗之间的鸿沟逐渐被互联网所建构的多维度平台打破,在全媒体覆盖的传播体系中,音乐创作者与受众人群、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别很难从价值程度上对音乐属性进行区分判定。
同样,以“技术论”划分互联网音乐与传统音乐依然有失偏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背景下,传统技术手段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推广层面也往往是融媒体“整合传播”的结果。2014年8月,汪峰鸟巢演唱会与乐视音乐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播出,六万观众到场观看,而通过乐视TV、移动端及PC端等乐视网平台欣赏的人数则超过了10万人,音乐现场的线上付费模式也由此开启。同样,一些高雅音乐甚至某些“殿堂级”音乐也依然在通过互联网技术或互联网思维进行升级。2014年10月,《木兰诗篇》大型情景交响音乐会在全国巡演,国家交响乐团和爱奇艺视频联手同步播出,互联网和音乐行业的结合正逐步打破音乐类型的藩篱而走向纵深。
由此可见,互联网音乐、新媒体音乐与传统音乐的区别似乎并不存在单一性标准。面对在互联网视阈下原创音乐纷繁杂糅的现状,我们很难归类哪些是互联网音乐、哪些不是,但我们可发现哪些音乐从内容创作与渠道传播层面具有互联网基因或运用了互联网思维。笔者认为界定互联网音乐、新媒体音乐至少需满足两种条件:一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包含创作技术、传播平台与营销方式实现艺术传达;二是满足互联网思维的相关内涵,包含“去中心化”“交互性”“潮流性”等特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是全部具备这种特征的音乐作品。
二、互联网音乐领域的定制化服务与部落集群
互联网时代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分析能通过“用户画像”实现精准推送,当前许多互联网音乐平台都能实现这个功能。从媒介传播角度看,艺术品的传播正逐渐从“点对面的线性传播方式转换为点对点的网状传播方式”从单向性到交互式的改变,深刻地放大了个性化的审美差异,划归了每个人所属的文化圈层。也基于此,许多互联网音乐平台便可通过大数据功能实现作品的精准投放,这也为原创音乐的定制化服务创造了土壤。
定制化传播对应的上游是定制化创作,这种创作方式我们可大致分为:首先,为个人艺术追求的私有定制化,我们或可称其为“作者艺术”,即便在充满“开放、共享”精神的互联网时代,也不可否认少量自我音乐的存在;其二是为艺术表演者定制,大多数较有影响力的歌手或乐手都有较固定的音乐风格和听众人群,通过个人或经纪公司邀约创作者为其量身定制作品,也是行业中的常态式做法;最重要的定制化创作还是体现在针对听众的消费服务层面,将互联网“用户思维”导入创作观念并进行信息互动,能更便捷、有效地完成音乐在产业层面的价值创造。在互联网环境中,无论哪一种定制化服务,都在使音乐创作者、表演者与欣赏者的符号化标签愈发凸显,像近年来火热的“中国有嘻哈”“TFBOYS”“网络春晚”“中国三大男高音演唱会”“国外经典音乐剧改编”“原创民族歌剧展演”等,定制化服务也使不同品类的音乐人群集群效应更加明显。
互联网的定制化特征,导致在原创音乐领域产生了诸多包含创作、表演、传播、欣赏、消费等环节的小部落集群,每个集群类似一个完整的小生态圈,且能自给自足、繁衍生长。麦克卢汉曾在他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观点,并认为“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在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这句发表于五十多年前的“预言”,鲜活地描绘了当今互联网时代的艺术生态图景。在原创音乐领域,我们随处可见由于互联网技术革新带来的智能化创作、碎片化欣赏与场景化消费,这是一个不同于传统音乐生态的全新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原创音乐的生存需要面对非原创音乐甚至人工智能音乐的双重挑战,同时面临差异化竞争、跨界整合和即时性消费转化等一系列问题。而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突围”,必须正视的是,用一首(部)成功的音乐作品满足绝大多数听众的时代已然过去,互联网时代的原创音乐需找准自身所存在的“部落集群”,实现准确定位并施以针对性策略,才是其生存和制胜之道。
三、互联网音乐所处场域中的两个重要变量
艺术的发展都有其“合目的性”原则,小至个人情绪的抒发,大至艺术追求、商业目的、社会效应等等。我们思考互联网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原创音乐的生态模式,需将其放置于一个宏观的背景中进行考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场域”的概念,并对艺术体制所包括的要素功能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概括:“作品不应仅考虑作品在物质方面的直接生产者,还要考虑一整套因素和制度,后者通过生产对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价值和艺术品之间差别价值……参加艺术品的生产……还要考虑所有主管艺术的政治和行政机构,他们能对艺术市场发生影响”。依此理论,我们或可将原创音乐所处的场域空间以内部的“艺术模式”和外部的“产业模式”进行划分。处于内部的艺术模式,主要完成音乐的创作、欣赏及价值评介功能,包含参与者、作词、作曲、编曲、录音师、歌手、听众、专家等;而处于外部的产业模式,主要通过政策、商业、文化、舆论等机制来间接影响原创音乐的发展走向,其中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及相关社会组织等。由此我们探究互联网改变原创音乐生态模式的重要变量。
从艺术模式角度,互联网技术直接影响了音乐的创作与欣赏方式。互联网的资源共享特征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对于音乐创作的素材积累,更多创作者通过简易地网络检索替代了传统的亲身体验或文献资料参照;对于音乐制作技术而言,数字媒体技术在不断迭代升级中收获更优质的声响效果,相较于传统真乐器的使用则展现出更高的性价比;在听众欣赏层面,曾经的磁带、唱片也早已被各种互联网平台的“免费资源”带入了历史。然而,互联网给原创音乐带来最大影响的,是在互联网潮流中音乐作品价值的评价机制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艺术把关人”发生了变化,这是互联网改变原创音乐生态模式的重要变量。在传统的艺术传播过程中,艺术家、评论家是最主要的艺术把关人,而在互联网技术引领的新媒体时代,又增加了新的“把关人”——艺术接受者,或者说艺术消费者。当前,一个原创音乐作品的影响力、社会关注度甚至是商业回报率,除了专业评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点击率、粉丝数、浏览量等数据。作品的成功与否,受众的认可度开始更直接地发挥作用,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受众可以直接地参与其创作与呈现。比如李宇春粉丝群创作的歌曲《我和你一样》,初衷是作为礼物送予偶像,后经李宇春的成功演绎并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认可,成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公益宣传歌曲,在央视“抗洪赈灾义演”演出后得以广泛流传。这是一个积极的案例,但同时“把关人”的改变也必然导致对音乐“专业品质”的权威消解,“商业与艺术品消费者成为强势的把关人后,艺术品的甄别和评价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当音乐创作不再有门槛和标准,一些泛娱乐化、商业化、低俗化作品也将由此而滋生,这也是整个原创音乐行业正在直面并需解决的难题。
从产业模式角度,政策与市场都对原创音乐的发展起着关键的导向作用,各种相关协会组织为此保驾护航。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开放的环境能使多元化的审美需要得以满足。由此我们可见当前原创音乐的差异化方向更加明显:为政策而创作、为市场而创作、为某固定群体而创作以及个性化创作等,均能找到自身的生存空间,并且每一种生存空间都可以形成自身合理性的产业化体系,各体系之间可相互交叉融合,也可互不干涉,这是互联网开放性特征给音乐产业带来的新面貌。然而,正是这种开放性以及各种开放式平台的建立,也使得音乐的产业经济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在中国,互联网改变原创音乐产业模式的重要变量是音乐产业收益从“版权经济”逐渐向“粉丝经济”的转变。在音乐尚在“物质载体”的时代,受众所购买的磁带、CD,实际上是在为版权付费;而到了互联网时代,在著作权、版权法尚未完备的环境下,免费收听、下载等模式让原创音乐的版权价值被无限弱化,盗版侵权屡见不鲜。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产业经济模式悄然成型,由受众或用户们带来的“粉丝经济”。互联网通过“免费”策略汇聚了大量听众,并通过把握他们的心理进行音乐产业消费模式的重构,如付费会员、流量经济、网络直播、线上打榜、线下见面会。与“版权经济”不同的是“粉丝经济”,需要经历一种从“免费培养”到“消费转化”的过程,其后,是互联网音乐市场针对原创音乐或明星音乐人的包装打造,并逐渐通过受众的情感溢价获得收益。“粉丝经济”无疑代表着互联网时代原创音乐产业的新方向,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呼吁并正在努力实现“版权经济”的回归,这是原创音乐得以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全新生态模式中的原创音乐内容与审美建构
无论是新的“艺术把关人”影响下的音乐创作模式,还是“粉丝经济”重构下的音乐产业模式,最终都将影响原创音乐作为艺术本身的内容和审美建构。对于艺术自律性与艺术商品化这一现代美学的悖论,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曾表示:“它是‘独立的’,因为它已经被商品生产所淹没。因此,艺术本身成为一种不断边缘化的探索,但美学不是。”虽然,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固然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和环境下所形成的风格气质会有所不同,但人类社会对于“美”与“爱”的共同认知恒久未变。无论是东方、西方,高雅还是大众,互联网所影响的生态模式变化是颠覆性的,但它并未改变音乐艺术本身所蕴含的人类情感表达的原初意图。因此,我们思考在全新生态模式中原创音乐的正确发展路向,更多是基于对当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适用性和功能性而言。
首先,当今音乐的创作在个性化的创作中应寻求更多的公共审美意识。在互联网时代,创作者个性化的内容风格与受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相匹配,互联网在为不同类型的音乐创作与欣赏者提供互动条件的同时,其实也营造了公共性的音乐文化语境,即“在纯审美与泛审美的互渗中呈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公共性”。真正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在满足“艺术分赏”的前提下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公赏”价值,如一度成为国内“神曲”的《最炫民族风》,以及在世界杯期间风靡全球的《克罗地亚狂想曲》等作品,能在一定条件下从小众影响蔓延至大众,且传递积极的意义,实现作品更高维度的价值彰显。
其次,各种形式的原创音乐应在创意阶段建立“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受众“即时性”“碎片化”及“互动性”的欣赏方式相结合。互联网改变着艺术接受者的欣赏习惯,因此在音乐的内容创作环节应融入对不同听众心理的把握,营造最匹配适宜的审美体验,并借助互联网的翅膀实现更好的艺术传达,如新世纪音乐风格乐队“神秘园”创作于2001年的《you rise me up》,本是一首经典的音乐会作品,十余年后被拍摄成“街头MV”,以及各种“快闪短视频”等流传于互联网,让这首优秀的励志歌曲以全新的形式感染着更多的人。
互联网对于原创音乐的影响从技术平台、产业形态拓展至内容及审美等更深层次的领域。虽然,互联网自带的一系列技术和文化特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打破音乐艺术的传统生态格局。但同时,全新的模式与体系也在日臻成熟,它会不断在改进中构建属于互联网音乐的新生态景观,我们有理由报以更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