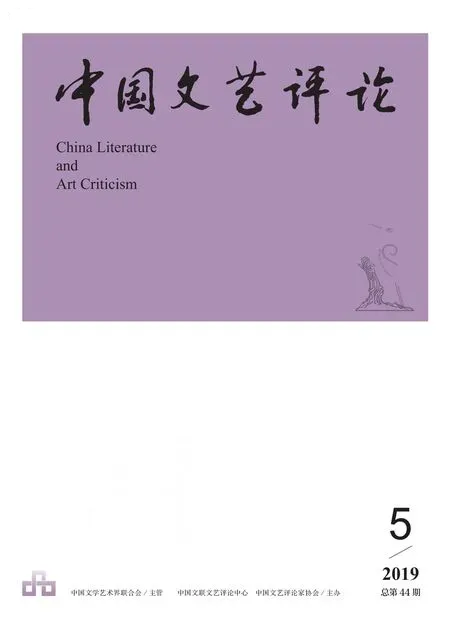当代新诗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以四川新诗群体为例
何光顺
目前学界对四川从“第三代诗歌”到“存在”诗群的演进轨迹,及其背后所折射的地域文化精神还缺少充分关注。从地域诗歌的研究视角出发,将有助于发现四川新诗在中国诗歌版图与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当代四川新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20世纪80年代从四川兴起的“第三代诗歌”席卷全国,更重要的是从“第三代诗歌”到“存在”诗群的演进所折射的“陆地气质”。这种“陆地气质”既是四川文化作为我国大陆文化典型代表的内在品格的体现,同时也是华夏民族作为东亚唯一本原民族的历史精神的结晶,而且最终在与西方文明“海洋精神”的现代遭遇中形成其成熟形态。当代四川新诗群体正是在这种中西方本质精神的遭遇中展开其写作实践,是重造传统又借鉴西方并植根于本土性经验中生成其先锋性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追求。可以说,以四川新诗群体为例来阐释中华民族诗学精神的某种内在本质维度,也有利于在经历中西方文明碰撞的“差异性”体验中为当代中国新诗找到回归华夏文明“同一性”故乡的印度文化为世界四大本原文化,而本原文化论为承接雅斯贝尔斯“轴心文明说”而来,其比“四大文明古国说”更能真实、深刻地揭示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地位。参见黄裕生:《论华夏文化的本原性及其普遍主义精神》,《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道路。本文以四川新诗群体为例来探讨新诗的发展历程、美学品格、艺术追求及其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弘扬,以期有助于探讨新诗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一、从“第三代诗歌”到“存在”诗群:四川新诗群的发展历程
当下,中国新诗的发展已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进。以公刘、白桦等为第一代诗人代表,在四川则主要有孙静轩、傅仇、高缨、梁上泉、白航、流沙河等。以北岛、顾城、舒婷为第二代(朦胧诗人)代表,在四川则有江河、欧阳江河、骆耕野等。“第三代诗人”的概念在1982年底提出,1983年《第三代人》诗集发行,标志着“第三代诗歌”群的正式出现。整个80年代,中国诗歌活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四川成都。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一代、第二代,都主要是基于1982年以后“第三代”概念的提出而做的事后确认。四川“第三代诗歌”又包括了莽汉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净地诗群、巴蜀五君、大学生诗群等许多诗群。
从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代诗歌”所带来的四川新诗为中国新诗打开了更加自由和独立的发展空间,它更注重在现代汉诗的地域性、民族性的肉身中生长出其世界性的品格,重塑一种我们开篇所提出的以“陆地气质”为其内蕴的独特美学品格。这样,以四川“第三代诗歌”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新诗就真正确立了华夏文化作为本原性文化的独特使命担当,而“第三代诗歌”概念的提出,也就是当时一批四川大学生诗人在骤然间遭遇西方文化异质性精神的震惊中对于民族化诗歌道路的自觉。于是,1983年,北望(何继明)、邓翔、牛荒、赵野、唐亚平、胡晓波等人成立“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编辑发行《第三代人》诗集,标志着第三代诗人正式登上中国诗坛。可以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既是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又是四川新诗在全国独领风骚的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四川本土诗歌也在发生着嬗变,而且这种嬗变因为直接从“第三代诗歌”继承而来,就具有了更好地观察当代中国新诗演变的延续性和某些规律性。四川新诗的重要变化,主要以1994年《存在》诗刊的创立为标志,四川“存在”诗群的主要成员包括陶春、刘泽球、谢银恩、索瓦、陈建、胡马、李龙炳等。在“存在”诗群成立后,四川第三代诗人的相关主要代表大多参与了与“存在”诗群的对话和交锋,并形成了四川诗歌的内在承续和相互影响关系。越来越多的诗人也开始集结在“存在”先锋诗群旗帜下,继续拓展着四川本土写作的疆域。目前“存在”诗群已几乎聚集了四川1970年代出生的一批最优秀的诗人,他们与第三代重要诗群的频繁互动,既汲取民间写作的个人立场和日常生活化等优点,又注重知识分子写作向西方诗歌经验学习,既批判趋时媚俗的“下半身”写作、“唯口语”写作风尚,又提倡诗歌写作的本土意识、神性关切,强调在生命与文化、现实与历史、传统与先锋、人性与神性的两端寻找平衡。
二、“陆地气质”:四川新诗的内在美学品格
在从四川“第三代诗人”到“存在”诗群的发展中,有一种独特的美学品格值得关注,那就是四川新诗所代表的“陆地气质”。以“陆地气质”作为四川诗人的精神符码是与我将广东诗人的“南方精神”作为精神符码进行比较后提出的。“南方精神”实际是中国陆地文化与欧美海洋文化在碰撞激荡中形成的广东诗歌的重要品格,它更偏向于一种海洋性精神。“陆地气质”却是以四川诗歌为代表的陆地文化经受欧美海洋文化激烈冲击中所形成的,它既是四川诗歌的地域性品格,也内在地承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它更偏向于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厚重底蕴的陆地气质,它刚建而笃实,宽广而沉稳。这种“陆地气质”可以看作是从《周易》的乾卦和坤卦共同开启的天地境界所昭示的,其渊源还可追溯到商易《归藏》和夏易《连山》,甚至中华古神话和古人文共相交织叠合的三皇、五帝时代,那里有华夏先民与山川河流、鸟兽虫鱼的休戚与共、利害相关。这种肇自远古上古的乾行坤载的大德,此后又在《山海经》的神异博物,《诗经》《尚书》《周礼》《春秋》的礼乐经典,《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的诸子争鸣中发酵和推扬。中华民族诗学中的这种“陆地气质”,此后虽因为各种不利因素而时时被扭曲,但却终究历数千年而不绝,厚植深根,它既锻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锤炼了诗歌的“陆地气质”。
然而,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性的“陆地气质”或内陆品格逐渐被遗忘、被敌视、被否定、被抛弃。太多的人恨不得能够抛弃这片大地与大地上的河流,而奔向蓝色的海洋。然而,一种深刻的艺术精神就在于,它不会停留于初期的否定和挑战,而是会进行新的培育和建构。我们必须理解,大陆并非是海洋的对立之物。海洋是辽阔的,大陆同样是宽广的。如在19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中,“莽汉主义”强调为打铁匠和大脚农妇演奏打击乐式的诗写,“整体主义”强调中国文化的整体生命表达。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存在”诗群强调天人合一精神的回归。这些主张都是对中国诗歌所具有的陆地气质化的民族美学品格的重新肯定。1976年,当整个中国从“文革”的浩劫中苏醒过来以后,先是伤痕派文学、朦胧诗派借着北京的文化优势成为中国文学的引领者,而四川诗人如周伦佑、李亚伟、尚仲敏等却凭借着四川的历史文化传统,酝酿着另一种民间写作姿态。
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特别是中期以后,四川诗歌借助民族和民间传统而来的写作条件就已成熟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四川诗人恰逢其时地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中民族精神的坚守者。万夏的《莽汉》带着狂啸的力量开启莽汉派的时代,周伦佑的《绝对之诗》以奔马向天空自我飞跃的意象来展现一种雄浑的力量,翟永明的《女人》以其独特诡异的语言与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惊文坛,蓝马的《世的界》对复杂文字技巧的探索虽不一定是成功的却是具有艺术先锋的冒险气质。尚仲敏的《黄土地》、李亚伟的《河西走廊》则以其粗犷之笔重构着中国西部的历史或现实的生存处境,柏桦的《望气的人》、石光华的《炼气士》则在风云变幻或山海渺茫中参赞造化的神奇……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维度折射着第三代诗歌的地域性气质和民族性品格,并在诗艺上和现代或后现代艺术的精神相契合和呼应。
四川诗人对于华夏民族“陆地气质”的象征书写,既体现在尚仲敏的《黄土地》,李亚伟的《河西走廊》等关于土地或大地的写作中,也体现在雨田的《麦地》中所叙写的“麦地”的象征寓意中。而雨田的《麦地》组诗尤其可以作为典型,全诗在具有低暗厚实的色调、沉稳密集的叙述、锋利尖锐的思想中直面生活与现实本身,写出一种独属于那个年代诗人经历过苦难和伤痛岁月的沉重和悲凉。在我看来,这种沉重、厚度、密度、广度就很可能源于四川诗人整体上所承受的中华文明的重量,从而让其作品更显露出一种雄浑和粗犷。诗歌中所涉及的对人之生存的处所和自身的不确定存在的发问,始终渗透着一种确定的“哀伤”基调,整组诗从不同角度来展开对于麦地的书写,实际就是将人生置于浩瀚的土地和广阔的时空来述说一种命运。这种写作构思既有诗人对于农业和庄稼的深沉的爱,又同时展现出一个民族数千年来蜇伏于大地的命运轮回的沉思。
四川诗人所展现的“陆地气质”或陆地诗风,具有着与其所承载的悠久历史和所居住的富饶土地相应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们所居住的天府之国是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天眷顾和恩许之地,纯粹、厚重、博大、深广,都可以用来形容四川诗人的“陆地气质”或品格。这种四川诗人所折射的“陆地气质”,不仅仅是四川地域文化特征的体现,同时也是华夏民族美学精神的集萃,它还展现出贯通内外古今的世界性胸襟。这种地域性、民族性、世界性就构成了四川诗人的三重品格,并同时体现在从司马相如、李白、苏轼以来的那种大气豪雄的诗酒文化中,这种与诗酒精神相关的四川诗人的大气豪雄不同于古希腊在酒神节受酒神精神支配的狂野、放纵和毫无忌惮,它有恢弘、雄阔和赤诚,但并不完全毁弃规矩和破坏节度,它有伤痛,有解放的欲求,有自由的向往,有回归自然的渴望,但它却终究关怀着人间,要用诗歌和艺术来柔化痛苦,陶育性灵。四川诗人爱酒,在酒意中挥洒就不仅仅是性情,而是同时默化或行吟出一种艺术的人生,它让美的和爱的精神成为一个民族的信仰。
从诗酒精神陶铸艺术人生的角度来看,在“第三代诗人”那里,酒是一种触发诗歌激情和实现艺术创造的媒介,如万夏和胡冬就是在喝酒中开创第三代莽汉主义诗歌写作的。在1984年春节,无聊、万夏和胡冬在一次喝酒中拍案而起:“居然有人骂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干脆我们就弄他几首‘他妈的诗’给世界看看。”几天之内, 两人就写出近十首“不合时宜 ”的诗,并随便命名为 “莽汉诗”。如在作为莽汉主义最重要代表的李亚伟的《酒中的窗户》一诗中,酒就成为诗歌的内在精神元素,也成为生命的元素,酒带诗人入睡,进入自然的风雨,也进入历史的风雨,人生有酒友,踏雪而来,四季也美,年岁也美,世界在酒中变小,结尾呼应开篇的“酒杯”与“瞌睡”的一体关系,而结句以“白帆”的意象收尾,这白帆与这节前面的大雁裁剪的天空交织,形成一种空茫和虚幻的意境,就进入了庄周梦蝶和禅宗妙悟的空境,这是一个摒弃现代世界的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而回到古典精神的返回式写作,体现了从朦胧诗的反抗体制写作向第三代诗人自我内在化写作的转变。第三代中的大学生诗派代表尚仲敏把酒与讽刺时事人生融为一炉,可谓颇得古风。而作为巴蜀五君之一的柏桦不但写酒,而且喜欢对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进行大量渲染。酒的精神就是一种感性生命的勃发。柏桦的诗纵情于食物与美酒,写出生活的恶俗与丑的东西,不走青春化贵族化的唯美主义路线,注重唤醒身体和生命的全方位的感知觉能力,让人成为真实的人,逃避或抵抗一种技术主义或商业主义对于人的异化和抹平。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存在”诗群的写作,同样继承着中国古老的诗酒精神,而其更独特处,则在于其对酒意和酒性的多维度展现,或浑成,或强劲,或空茫,或辽阔,他们喝出了酒之道,如刘泽球的《赌局》:“依靠酒精加速兴奋的手指/伸出吊绳、滑轮和传输带/熟练地把赌局变成一座井然有序的工地”,在这里,一种酒徒的深沉豪放性格,在刘泽球笔下就得到极好的展现,酒徒饮酒,像赌徒玩牌,也像工人施工,醉在其中,秩序也在其中,他们没有那么多彬彬有礼的讲究,却自然地保持着礼义之邦的最高的诗性精神和乐感节奏,在酒意渐浓中,他们能让扑克、麻将和诗歌那么和谐地相处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已不难看到,四川诗人就体现着一种融大雅入大俗的鲜明地域文化特征。四川是酒楼、茶馆和麻将盛行的市井生活之地,酒让诗人们既保持着激情的理想,又让他们能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刘泽球就以他的诗将历史的宏大叙事(理想)与市井的休闲生活(麻将)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四列牌 也许曾经是四支军队/四座城堡 四个帝国/对垒的虚拟”,在四川诗人的笔下,酒徒并不只是爱着当下的赌博,在他们“兴奋的手指”中有着历史沧桑,有着家国兴亡,那里隐藏着“血和铁的沙盘”,那是狼烟四起中烧尽荣华后只剩断垣残壁的悲伤。这种看似走向更为市井化的酒徒精神,却仍旧内在地承续着莽汉主义诗人李亚伟杯酒中的历史沧桑。
然而,因为“酒徒”又最能洞彻历史和世情,在西方文化中他们向上一步就会成为圣徒,在中国文化中他们向上一步,也即所谓“浪子回头”,就会成为“君子”,就会有华夏民族所重视的“君子”的饮酒之礼,这“礼”如此神秘,又如酒一样被渴求,召唤诗人围拢在一只酒碗的四周翩翩起舞,如陶春的《八月十五》:“蟋蟀摩翅,灿鸣于野——击土鼓/龡《豳诗》/露从今夜白,夜始今夜寒/归来呼酒饮达旦/把酒对青天/此夕羁人独向隅”,这里所展现的中华民族的诗酒精神就并不是古希腊酒神节的完全放纵,而是伴随着礼乐文化的节律起舞的,酒以成礼,中国人的饮酒既有朝着社会群体交往所需要的伦理规范的礼义之邦的精神,又有将人带向神灵、自然和生命的适情快意。四川诗人的“诗酒”颂歌式的写作,注重的是“嘉会以成礼”,这也是中国诗人的最典范写作方式,而这就使其区别于古希腊受海洋商业文化影响的纵欲主义,区别于欧洲中世纪受到基督教神圣文化影响的禁欲主义,而形成其受陆地农耕文明影响的感性与理性平衡的忧乐圆融精神。
三、先锋性:四川新诗的艺术追求
四川从“第三代诗人”到“存在”诗群的发展,始终具有一种先锋性的艺术追求,他们注重引入西方后现代主义等现代诗歌流派的创作方法,但这种艺术追求并非是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生吞活剥。相较于早前的朦胧诗派,从四川19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到90年代的“存在”诗群,都始终强调自己的文化根基,始终在面向自己的民族语言、历史和先知的写作中,来向世界文学展现出当代中国诗歌的独特精神与艺术维度。
首先,是以第三代“莽汉主义”诗人李亚伟为代表的一种具有狂野性的民间姿态的确立,以及在其中呈现出某种“里”和“外”的精神结构的失衡与平衡。李亚伟的诗是大气磅礴的,如其《抒情诗》组诗第一首《河西走廊》,就抒写出了在广袤的乡土大地上劳作和抗争的硬汉形象,而诗歌的语言也极有力度,特别是“长工”和“贵族们”的强烈对比,“命里”和“命的外面”的精神结构的失衡与平衡,借助“河西走廊”这样一条历史的丝路编织出了民族命运的里与外,借助“王家三兄弟”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来诉说个体命运和国家命运的里与外。正是这种“里—外”的结构性布置,让四川诗人的艺术不至于总是局限于内,而是能够充分地学习外,而这也是其诗歌艺术具有先锋性的根源。
其次,是以“第三代诗人”向以鲜《我的孔子》为代表的汉语诗学中的圣人形象的重塑,在这一组诗中,诗人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圣人之像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如开篇的《我的孔子•头上峰壑》就借司马迁《史记》和司马贞索引所述圣人之像却化而创之:“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父亲的脸/还没有来得及/为生民哭泣//就把绝妙的峰壑/造化出来/命名在/苍穹的头颅上//子若不登泰山/泰山必来眼底”,这就将《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和司马贞《索引》所述“圩顶言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完全转化成了新颖的诗歌意象,这可以说开启了现代汉语新诗艺术的新境界,圣人头上有峰壑,胸中有宇宙,诗人头上有穹苍,胸中有造化,这也是诗人精神的道通古今,“闭上明察秋毫的双眼/在音乐的黑夜里/在旷古的神交里/与先人同裳”,正是在古人与今人的对话中,诗人寻得了艺术先锋性的源泉,即一切先锋性的艺术都必须表达最本根性的民族精神。
在90年代以后的诗人笔下,诗歌具有了多重复杂的意蕴,如刘泽球的《春夜,那场骤来的雨》写到的身体、春雨、镜子、灵魂都是不断重复和繁殖的意象,并因着“我固执的咒语”展开着对于“时辰”与“梦境”的复制。陶春的《自然的奇迹》所写的“镜子”与魔法相关,是变幻的、不稳定的,它可以看作是当代网络新媒体时代变化多端的生活写照。谢银恩的《黑夜诞生的文字》同样写到镜子的透明消失,成为遮蔽的镜像。应当说,四川90年代以后“存在”诗群所写的“镜子”意象表现着一种复杂性、瞬间性和荒诞化的体验,其关于“镜子”意象的艺术创造,也形成了对于“第三代诗人”的某个维度的超越。
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三代诗人”尚仲敏的先锋语言实验、李亚伟的历史写作、向以鲜的先知写作,就体现出四川诗歌艺术的先锋性在多维度的拓进,它有着“反文化”和“逃避自我”的表象,却又找到了文化和自我的另一种形象,那就是李亚伟等人确立的民间立场以及他们在诗歌中避免直接言说自我的写作姿态。虽然,“第三代诗歌”有强调对于“规范化诗歌语言的背叛”,有“反意象与超意象”的特点,但总体看来,在四川新诗从20世纪80年代承接“第三代诗歌”到今天的发展中,它并没有完全抛弃或超越意象,比如向以鲜所塑造的圣人意象,“存在”诗群所构建的“镜子”意象,都表现了意象写作从“第三代诗歌”以后的延续,只不过在融入厚重的文化传统与表达破碎的现代性体验方面实现了更好的结合。在这些探讨之外,我们特别应当重视的是,从“第三代诗歌”到“存在”诗群的先锋艺术实践,就不仅仅是艺术技巧的,而且也是艺术精神的。
四、以四川新诗为例看本土美学精神的弘扬
在对本土美学精神的领悟中,当代四川诗人并不固化地看待诗歌中的“陆地气质”或品格,而是能在注重时变中领悟西方的“海洋精神”。胡马的诗将西方宗教文化的神、末日、伊卡洛斯等与中国文化中的禅坐、圣水寺、佛法等关联起来,展现中西方的本原文化精神融汇的可能,表现一种源于更高法则的“分割”和“筛选”,“指认”和“领受”,从而渴望人类“点亮星空”,其实也是表明华夏文明向着世界开放的新生。正是在精神的自由交接中,古老的灵魂得以醒来,他在《“末日”后在圣水寺迎接新年》中写道“拒绝麻醉、伪装和与世沉浮”“将灵魂的芳香一缕缕释放”,诗人渴望着朝向异域的远行中“进入另一片更广阔寂静的旷野”,这也是四川诗人所承载的作为东方陆地本原性文化的历史性精神的自觉和主体性的确立。张卫东的诗则写到博尔赫斯从美洲到欧洲的远游,这既是体验“异”,却又是“同”的回归,是精神故乡的再次发现,当一个文明播撒太远,它的苗裔必得返回其文明的故乡。诗人所写到的博尔赫斯,实际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诗人的一个象征,我们操着西方的思维和语言,遗忘了古老的传统,我们必须在阳光初生的早晨,重新回到华夏文明的发源之地,去练习我们的母语,去练习纯粹的汉语写作。诗人在《博尔赫斯》中所叙述的那位美洲少年,“游遍了人类文明的每个角落”,最后,他终将获得圣灵的启迪,“让整个世界都惊异于一道灵魂的光束”。当代中国诗人,也必将与圣哲邂逅,而后在普遍性的超越中获知文明的真谛。
在跨越古典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精神游历中,四川新诗开始创造具有现代性的“海洋”意象。如四川诗人陈建的《海》(组诗)包括了《海上海》《海上月》《海下夜》《海边晨》等18首,就是一组气势磅礴之诗,从不同视角切入,诗人似乎想穷尽一切关于海的奥秘,时间、空间、颜色、声音、物事、精神……这是一位四川大陆诗人对于海的遥远想象和意义赋予。四川诗人就不曾苟安于乡土的安逸与静谧,他们必须从初见那来自异域的海洋怪兽的惊骇中深入异域之地,他们对于海洋的写作,就可以看作是一种传统诗歌在其“陆地气质”的形成中又遭遇西方海洋文化后的精神再造,这样,他们笔下的海洋就不再仅仅是西方式的掠夺和征服,不是对象化的主宰自然和万物,而只是以君子之德和诗人之情去感受大海所承载和赋予人类的某种精神象征,这也就是从大陆向海洋的精神旅行,是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汇,就如《周易》太极阴阳鱼图形的跨越临界线。
从李亚伟、向以鲜、陶春所倾听的老子、孔子等东方圣哲的声音,到胡马、陈建、梁珩所看到的西方的神圣和大海的气象,四川诗人在不断地实现着自己的突破,他们所运用的诗歌意象、语言、结构、修辞等,既有着中国古典抒情诗学的悠久承传,却同时紧密跟踪从古希腊到基督教中世纪再到现代的西方诗学的历史进路,特别是他们对于现象学、存在主义诗学、解释学的深度领悟,让他们的作品能够把握复杂变幻中的当代世界本身,不作本质主义的先验预设和浪漫主义的虚夸式怀想,而是在具体感受民族精神和异域精神相遇中达乎天命之道说,并从而为中国诗歌引入了神性的元素,让中国精神运行到群星璀璨的高处。
因此,我理解了曾令勇的诗《假象》所展示的有关“同”和“异”的深刻哲思,诗人领悟了自然的神奇,自然善于隐藏自己,而只在诗人的道说中涌现和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世界有时显现给我们以差异,而隐蔽其相通,有时显现给我们以相通,却隐藏其差异,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国古老易学的阴阳对反又互化的太极思想,我们就知道这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我们也就不会陷入一神论宗教的绝对主义和近代启蒙主义盲目自信的主体论,我们需要“听万物寂寞的自语/听花开花落,看自然的深处”,而后进入东方思想的无言之境,“哎!人的境况如何?/我明白/但无言”。四川诗人对于技术文明侵蚀中所造成的人的晦暗图景的深度忧伤,让我们在文明的一往无前中保持一种反向性的维度,让我们时刻回望家园。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每一位四川诗人从华夏文明根柢处而来的现代性忧思,比如索瓦的《中断》所引出的古老的哲学之问或诗人之问。当古老的经典赋予人们一个神圣起源以解决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时,当代诗人却在物质驱赶灵魂的时代坚守着人的本身。诗人所写的“穿着你的躯壳的脸”中的“你”既是一个旁观者,也是“我”的幻影,“你”既是我试图僭越的“隐藏者”,却又是“我”所无法走近的“神圣者”,“我”只有你所赋予的形式和躯壳,却最终失去了灵魂,甚至也失去了躯壳,我成了变幻不定的网络符号,一切皆在虚拟中幻影式的存在,“我”又能走向何方?
现代人要回到神圣,就必须要有所选择和决断,如吴新川的《自由》就将每一个现代人比喻为沉睡在路上的石子,诗人的使命就是“把他带上”,要将其“还给召唤”,让人回到圣哲和神灵的召唤中。这也就是吴新川在《中断》中所写的:“一代人在命运波涛中坚韧前进/一代人在癌变的河岸上流脓狂吠”,这里有两个“一代人”,但指向却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句的“一代人”是诗人“还给召唤”的觉醒者,第二句的“一代人”是那些仍旧沉睡者,他们拒绝被唤醒。四川诗人们开启了象征着中华民族诗学精神向着苍天聚集的超越之门,这也就是谢银恩的诗篇《天》对于“天”的象征性书写,诗人感觉到了神秘力量的指引,“天”是孕育苍生者,汉语的神圣道说就构成世界历史的神圣起源与归宿,汉语是最切近自然和神圣的语言,仅仅一个汉字“天”和它衍生的语词“天空”“天堂”“天命”“天气”“天运”“天道”“天平”……就像诗人所写的,“魔咒般的跳舞汉字”“纠结成沉默的钥匙”“试图打开死亡的大门”,就在为世人开启着神圣,指引着方向。诗人的诗作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得救必得从自己的语言之中去寻绎生死之门,这就是在忧患和危机中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