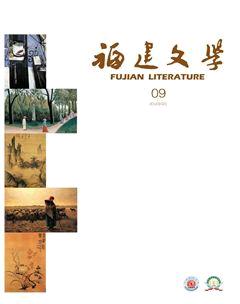对“闽东诗群”的几点思考
“闽东诗群”从形成到发展,走过了三十多年的道路,已成为福建诗歌的重镇,并在全国诗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那么,“闽东诗群”有什么成功经验和不足?有什么值得其他诗群借鉴的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闽东诗群”并进行思考,今天略作一下梳理。
曾记得20世纪80年代最流行的做法是,几个诗友一商量,就打出一个旗号,发布流派宣言,宣告一个流派的诞生,然后大家按照流派宣言进行创作。一时间,诗派林立,“诗歌运动”轰轰烈烈。这种以“求同”为目的的所谓诗派,短时间内有其成功之处,但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诗派同仁们的艺术追求过于相似或相近;二是诗派中创作和批评“抱成一团”,成为对外打笔战的“圈子批评”。这样的诗派,热闹了几年就过去了,并没有留下什么诗派的代表作。创作说到底,还是诗人的个人行为。群体的聚集,有利有弊。不是加入某个诗派,个体诗人的艺术就能得到提升——你还是你。
20世纪80 年代的诗评界,也开始兴起诗歌流派研究,后来逐渐成为显学。比如对于新诗现代主义思潮中诸诗派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九叶”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这种以“求同”为方法,以概括群体特征的诗派研究,也因淡化诗派中个体诗人的独特性,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开始对“闽东诗群”进行跟踪研究:从个体的评论,到整体的扫描。
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诗群与诗派的区别。诗派强调群体的共同点,而诗群则是推崇个体的独特性。所以,我明确提出“闽东诗群”是诗群而不是诗派,“闽东诗群”的发展要保持诗群的特征,不要走向诗派。
“闽东诗群”是以闽东籍诗人和诗评家为主,加上外地在闽东的诗人,所形成的一个松散的诗歌群落。平时大家散居各地,有诗歌活动才聚集在一起。没有旗号,也没有流派宣言。在创作和评论中,“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锣”。
我觉得,在诗群活动中,“团结才有力量”,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时代,诗人们更需要“抱团取暖”,在精神上相互鼓励、相互支持。这就是“求同”。但在创作中,“不团结才有力量”,“不团结”才能发挥个体的独创性,这就是“求异”。 所以,在2004年“闽东诗群”的研讨会上,我提出“闽东诗群”的发展,应该是“求同”和“求异”的互补。
在“闽东诗群”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报刊:早年有汤养宗主编的《麦笛》,哈雷和宋瑜主编的《三角帆》,谢宜兴和刘伟雄主编的《福建丑石诗报》和丑石诗歌网,还有游刃担任斑主的网易现代诗歌网,近年来有迪夫主持的福鼎一片瓦诗社。聚集在这些诗报刊和网站的周围,诗友们自由地发表作品,并参加相关的各种诗歌活动。在相互吸引、相互交流、相互激励中,慢慢形成一个诗歌“场”,显示出群体的力量。
“求同”,主要表现在诗歌活动的组织层面,诗友们自觉地聚集为一个群体。但“求同”的目的,不是组成一个有共同美学理想的诗派。恰恰相反,“求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求异”:探索和发展各自不同的诗艺。或者说,“求同”是手段,“求异”是目的。借诗群的合力,促个性的发展。诗歌史上一再证明:那些成熟的诗人,总是像回避瘟疫一样,回避雷同。置身于诗群中的诗人,也理应如此。
我明确提出,“闽东诗群”要在“求异”中发展,“求异”是“闽东诗群”发展的内在动力。
当时我就意识到,群体特征的概括,是以牺牲个体的特征为代价。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的个体诗人批评,不是寻找诗群的共同点,而是尽可能地挖掘个体诗人在艺术上的特异性。换言之,“求异”成了我对“闽东诗群”个体诗人评论的出发点。
当汤养宗的海洋诗在当年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诗群中的一些青年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并出现了模仿现象。于是,我在“闽东诗群”的活动中,一再提出不要盲目追随汤养宗写海洋诗,除非你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发现,最重要的是去寻找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
20世纪80年代,谢宜兴和刘伟雄声名鹊起,人称“诗歌兄弟”。我写了一篇诗评,题目是《双峰并连,两水分流》。“双峰并连”是称赞他们创办《丑石》的团结合作精神;“两水分流”,是强调两个人在诗艺上要“各奔东西”,不要搞成诗歌的“双胞胎”。
我对于诗人在艺术上的独特性,有着特殊的兴趣。比如,对汤养宗、谢宜兴、刘伟雄、伊路、叶玉琳、宋瑜、游刃、王祥康、庄文等,都做了长期跟踪研究,写了四十多篇诗评。“闽东诗群”群体的更新和发展,正是依赖诗群中的个体在“求异”中的不断自我超越和更新。没有个体的艺术蜕变,就不可能有群体的艺术更新。
21世纪以来,随着后现代理论影响的深入,以概括为手段,总结群体特征的本质主义方法,遭到了严肃的质疑。受此影响,我更明确了“闽东诗群”的研究,其实就是寻找不同点。于是在2013年的“闽东诗群”研讨会上,我提出“闽东诗群差异性”的命题。诗群的发展,在艺术上不但不是“求同”,恰恰相反是“求异”。由众多诗人在“求异”中,而构成群体的“差异性”,才是诗群成熟和繁荣的标志。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流派和群体中,获得某种启示。“文革”前的“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这两个流派的共同点,都是“宗师与弟子”的组合。“荷花淀派”是孙犁与他青年弟子们的聚集,“山药蛋派”是赵树理与他追随者的组合。所以,最近有人提出“荷花淀派”是孙犁“一个人的流派”;同理,“山药蛋派”也是赵树理“一个人的流派”。“一个人的流派”,虽然其宗师孙犁和赵树理,都是大作家,但作为流派、作为群体,在艺术上,弟子多追随宗师,所以其风格是“大同小异”,缺少丰富和多样的“差异性”。
“九叶诗派”和“七月诗派”,就不是这种宗师与弟子组合的诗派,而是诗歌同仁的自然聚集。他们各有各的写法,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每个人都自成一家。特别是“九叶”。比如,穆旦与杜运燮,郑敏与陈敬容,唐祈与唐湜,都各不相同。还有“九叶”的老大哥辛笛,他的主要成就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与其他诗友40年代的成就,更是差异极大。所以,“九叶诗派”具有艺术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其实,诗派和诗群,都是评论家们的理论概括。“九叶”是不是诗派,在当下已成为一个问题:从最初似乎是定论的诗派,到现在却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我个人是把“九叶”,看成是“九叶诗群”,因为很难概括出“九叶”的群体特征,即使花大力气概括了,也多流于空泛。
我觉得,诗群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形成艺术上多中心的格局,避免宗师与弟子的“近亲繁殖”,避免成为“一个人的流派”,或“一个人的诗群”。我理想中的诗群是“六神无主”。所谓“无主”,就是没有君临一切的宗师;所谓“六神”,就是要有好多个在艺术上各自成家的著名诗人。比如,“九叶”可以看作是“九神无主”。这样才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形成艺术多中心的诗群格局。
就今天而言,“闽东诗群”这种“六神无主”的艺术多中心的格局,已具雏形。因为它有一个由四代人(创作和评论)组成的梯队,显示了“闽东诗群”发展的连续性和丰富性:
20世纪40年代有诗评家游有基和诗人薛宗碧。
20世纪50年代有汤养宗、伊路、余禺、哈雷、闻小泾、还非、伊漪、杜星等,还有写诗评的余峥、邱景华。
20世纪60年代有谢宜兴、刘伟雄、叶玉琳、游刃、王祥康、空林子、郭友钊、迪夫、庄文、石城、阿角、周宗飞、白鹭、林著等,还有写诗评的陈建、潘有强、王宇、郜积意。
20世纪70年代有俞昌雄、友来、林典铇、张幸福、李师江、王丽枫、何钊、李晓健等,还有写评论的许陈颖、林翠萍。
衡量一个诗群是否成熟,主要看是否形成“六神无主”的艺术多中心的局面,是否已经出现6个以上在全国有影响、在艺术上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人和诗评家。从以上这份不完整的名单中,我们看到“闽东诗群”确实有近十个已经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和诗评家。
概言之,二十多年来,从诗群的“求异”开始,到强调“双峰并连,两水分流”,再到提出“闽东诗群”的“差异性”,最后落实到诗群要形成“六神无主”的艺术多元格局,这就是我对“闽东诗群”理论思考的轨迹。
责任编辑 刘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