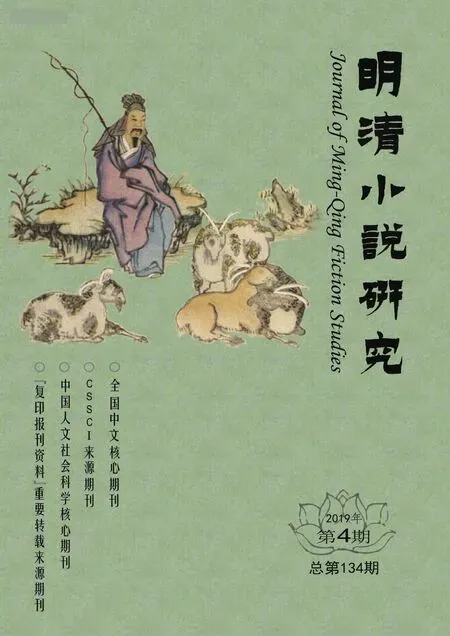论晚明女性总集中的小说人物与诗词著录∗
·吴 琳·
内容提要 自嘉靖至明出现的众多女性总集中,皆收录了大量源自小说、传奇、话本的女性诗词与相关故事。这一现象,既反映出晚明女性总集编者的商业嗅觉和编辑策略,也可从中观察到古代女性诗词与小说故事共生混杂的流传途径与编纂环境。晚明编者对这类小说文本的裁剪增饰与自我辩护,体现了迥异于传统总集的选录标准与文学观念,在此观念下构建的古代女性“贞淫互记”、“良贱并存”的文学图景,对后世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女性文学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晚明是当之无愧的“女性文学的突破的时代”。才女群体的崛起、女性诗词的流播及新型女性观念的涌现等种种现象,都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其中《彤管新编》《名媛诗归》等三十多种女性总集的陆续问世,尤其引人瞩目。关于这部分的晚明女性总集研究,学界已有若干成果问世,多从文献叙录与女性创作的角度阐述其意义。虽间有注意到这些总集收录小说的情况,但还未有专门的探讨。就笔者所阅晚明女性总集收录的数十篇源自小说传奇的诗词及故事来看,这些总集不仅首次在历史上构建了古代女性文学的作品序列,也汇集了古代小说中的各类假托女性创作的诗词以及相关的故事脉络。倘若摆脱文献辨伪的研究范式,小说文本在晚明女性总集中的集中植入与传播,实为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要从文献入手,对女性总集所涉小说篇目进行全面的梳理。
一、晚明女性总集所录小说篇目及来源
明代嘉靖以后,受到“后七子”复古运动影响,又因印刷出版业的繁荣,各类文学总集编纂刊刻逐渐兴盛,蔚为大观。选家贪多务博,上下收罗,推出了众多以“历代”、“古今”命名的通代诗文总集或选本,其中就有多种专门收录女性诗文的总集。目前所知较早的女性总集,是嘉靖年间先后刊行的张之象《彤管新编》八卷与田艺衡《诗女史》十四卷。隆庆元年丁卯(1567)会稽郦琥纂《姑苏新刻彤管遗编》二十卷,这部总集影响颇大,时见后世选家称引,万历时期胡文焕《新刻彤管摘奇》二卷,编次体例就与之一模一样。万历而下,女性总集编纂进入了兴盛时期,并呈现出细化和专门化的趋势,出现了专门汇辑女性文章的总集如新安蘧觉生《夜珠轩纂刻历代女骚》九卷、竹溪主人《丰韵情书》六卷、江元禧《玉台文苑》八卷、江元祚《续玉台文苑》四卷;专门辑录青楼女性诗词佚事的总集如周公辅《古今青楼集》四卷、冒愈昌的《秦淮四美人诗》一卷、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十三卷、张梦徵《青楼韵语》四卷与《闲情女肆》四卷。此外,还有侧重评诗的郭炜《古今女诗选》二卷,整理了十几页“璇玑图读法”的池上客《名媛玑囊》二卷,以及晚明公安派作家江盈科的《闺秀诗评》一卷等。到了天启、崇祯时期,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二十卷、托名钟惺的《名媛诗归》三十六卷、赵世杰《古今女史》十二卷相继问世,选录规模大大超过以往,尤以《名媛诗归》规模最大、影响深远,不仅囊括了前出总集的大部分篇目,还新增大量明代中后期的作品。这些总集的流传,塑造了世人对古代女性创作的总体印象。
由于时间跨度大、女性地位低下、各种附会伪托等因素,使得历代女性创作的甄选十分烦难。从现存的女性通代总集看,编选者为求广博,对于作品几乎是有闻必录、不加考辩的,或陈陈相因,或妄下断语。大量野史、杂传甚至仙怪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创作的诗文与故事,被编者不加注明地收录,则是一个较为普遍而有趣的现象。
所录诗词涉及小说,第一类是神话传说、志怪杂俎。如皇娥嫘祖《清歌》出自东晋王嘉《拾遗记》。西王母《天子谣》《西王母吟》出自旧题郭璞撰《穆天子传》,《问上元夫人书》出自佚名《汉武帝内传》。杜兰香《赠张硕诗》《八月复来又赠》(一作《复赠张硕》),紫玉《紫玉歌》,韩凭妻何氏《乌鹊歌》《答夫歌》,崔氏女《赠卢充》,皆出自东晋干宝《搜神记》。刘妙容《宛转歌》出自梁代吴均《续齐谐记》。樊夫人《答裴航》出自唐代裴铏《传奇》。鲍四弦《劝韦酒歌》《歌送酒》出自宋人李昉等编《太平广记》所引唐代李枚《纂异记》。葛氏女《和潘雍》出自宋代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所引唐代何光远《宾仙传》。红绡《坐吟》(一作《忆崔生》),本事出自唐代裴铏《传奇·昆仑奴》,但并无此诗,或为后人所拟。张立本女《失题》,出自《太平广记》所引唐代佚名所作《会昌解颐录》。
第二类是野史杂传与传奇、话本。赵合德《遗飞燕书》出自汉代小说集《西京杂记》。梅妃《谢赐珍珠》《楼东赋》出自宋代佚名《梅妃传》。杨贵妃《赠张云容舞》出自唐代裴鉶《传奇》。崔莺莺《明月三五夜》《别张生》《赠张生》《答张生书》出自唐代元稹《莺莺传》。侯夫人《自伤》《妆成》《自遣》《自感三首》《看梅二首》出自宋代佚名《迷楼记》。步非烟《酬赵生》《寄赵生蝉锦香囊并诗一首》《寄赵生书并诗一首》《赠赵生》出自唐代皇甫枚《非烟传》。史凤《迷香洞》《神鸡枕》《锁莲灯》《交红被》《传香枕》《八分羊》《闭门羹》,出自题名唐代冯贽《云仙杂记》所引《常新录》。梁意娘《述怀》《忆秦娥》,出自宋代罗烨《醉翁谈录》已集卷一《梁意娘与李生诗曲引》。楚娘《遊春》《桂花》《生查子》,出自《醉翁谈录》乙集卷一《林叔茂私挈楚娘》。
在以《名媛诗归》为代表的天启、崇祯年间女性总集中,还新增了元明以来小说戏曲中的诗词。如玉箫《别诗》,谢金莲《答赵生红梨花诗》《理发》,分别取自元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谢金莲诗酒红梨花》与传奇《梨花记》。吴氏《酬郑生诗》《病中答郑生》,出自元郑僖《春梦录》。贾云华《题魏生卧屏》《七夕(二首)》《永别诗(十首)》《生员期醉卧戏题练裙》出自魏鹏《贾云华还魂记》。娇红《记怀(五首)》《题西窗》《寄申生》《留别》《送别》《寄别申生》《永别》《感怀》《一剪梅·赠别》出自元代宋梅洞《娇红记》。吴氏《木兰花·寄和》,出自元末陶宗仪《说郛》,明代梅鼎祚曾据此敷衍为《才鬼记》。谢希孟《题芍药》出自明代瞿佑《香台集·陆姬楼记》,冯梦龙《古今谭概·鸳鸯楼》亦见收录。赵鸾鸾《檀口》《柳眉》《云鬟》《纤指》《酥乳》,出自明代李昌祺《剪灯馀话》卷二《鸾鸾传》。吴氏女《酬江情》,见于明代吴大震《广艳异编》卷八,《续艳异编》卷四题作《彩舟记》,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八《吴衙内邻舟赴约》即敷衍此事。王娇鸾《长恨歌》《闺怨》,见于冯梦龙《情史》卷十六《周廷章》和《警世通言》卷三十四《王娇鸾百年长恨》。娟娟《寄木元经》《寄别》,见于冯梦龙《情史》卷九《娟娟》。闽女《答太曼生》,见于冯梦龙《情史》卷十三《太曼生》。翠翘《寄左公诗》,见于万历《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等类书中。莲华女《呈陈处士》,见于《丽情集》。
上述虚构伪托的女性作品,在数十部晚明女性总集中反复出现,而相关的小说戏曲故事片段,也时常以序文的形式夹带于诗词首尾。对此现象,前人通常将原因归结为坊刻书籍的编校工作不够严谨。为了降低成本、缩短周期,书商常将已经出版的著作抄袭搬用一番后重新付梓,新增的内容极少,更谈不上对所抄资料的甄辨。小说诗词的著录,尤其凸显了沿袭的痕迹。关于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赵世杰《古今女史》与《名媛诗归》之间递相祖述的痕迹,前人早有发覆。赵世杰《古今女史》十二卷“文集则袭自《玉台文苑》,诗集乃采自《名媛诗归》,是必坊贾合并二书,刊为合集”。四库提要评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曾云:“此书较《名媛诗归》等书,不过增入杂文,其余皆互相出入,伪谬亦复相沿。”由于《名媛诗归》较他书后出,孰为底本尚未可知,但内容重复则是显见的事实。不少作者入选作品的数量一模一样。更为明显的证据,是那些采自小说、诗话、杂俎的篇目,比如崔莺莺《明月三五夜》《初绝微之》,贾云华《题魏生卧屏》《永别诗》之类,作者姓名与诗歌题目,常常是总集编者在采录过程中随意拟造的。而三部总集中,除了将诗篇顺序稍作调换外,作者姓名、作品题目和诗文内容几乎分毫无差。
因此,女性总集同小说一样出于坊间,确信无疑。质量粗糙,是坊刻本的一大特征。现存可知编者身份的案例,也证实了这一点。胡文焕为杭州地区有名的书坊主,出版过《格致丛书》等多种大型丛书和日用类书。《诗女史》署名田艺衡编,《名媛诗归》署名钟惺编。而这两部总集迥异于精英著述的面貌,使编者身份不断遭到后人的质疑。清初王士禄论及《名媛诗归》,称其“虽略备古今,似出坊贾射利所为,收采猥杂,舛伪不可悉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诗女史》云:“采庶颇富,而考证太疏。……艺衡未必至此。毋乃书肆所托名耶?”托名现象,在书坊中颇为常见。《古今名媛汇诗》卷首列出“同校姓氏”十四人,就网罗了林古度、茅元仪、张正岳这些知名文人。借用名人效应,可以扩大影响力、增加销量,在丰富多变、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中获得可观利润。既属托名,编者便不必承担责任,有意的作伪可以免除追究,无心的疏漏也有人来背黑锅。这样更加重了刊校粗疏、错讹频出的现象。不过,晚明女性总集与小说的文本混杂,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出版者的粗制滥造,还与出版市场的现实制约因素有关,也包含了一些编者的主观意图。其间的内在联系,值得进一步的追究。
二、女性诗词与小说文本的混融及成因
女性作品总集兴起于书坊的历史根源,与小说传奇文本颇为相似。小说传奇之流,一直为以史学为尊的文献传统所排斥。而女性作者在明代以前的各类总集中,也大都和“释道”类目一起附于卷末,选录数量也寥寥无几。历代女性作品多叙写闺情,不受文人士大夫的重视,但在通俗市场中却颇受欢迎。刻书既以盈利为目的,书坊刊行的书籍自然以读者的好尚为转移。明代中后期社会各阶层娱乐消遣的需求,推动了商业化出版市场的兴盛。小说文本的通俗性和娱乐性,使其拥有广阔的受众面,“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这样庞大的读者群体,便造成了“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的现象。一些女性诗词便依赖野史杂传、小说传奇文本而流传下来。晚明时期出版的一些小说合集、通俗类书如《绣谷春容》《万锦情林》《国色天香》《花阵绮言》《燕居笔记》等,校印精良,包含的女性诗词也是真伪并存,已经颇为近似文学总集,在当时就引起了较大反响,“施之于初学弄笔咬文嚼字之人,最为相宜;即士夫儒流,亦粗可攀附。”这些汇辑女性题材的类书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也进一步推动了女性总集编纂的兴盛。



编者一面对小说素材进行处理,以适应总集的编纂需要;一方面也在总集的体例编排之中,更多地迁就小说的叙事性。一般来说,诗文总集当以作品为核心,人物小传则以简明扼要为本。比如《乐府诗集》收录《紫玉歌》,只是简单介绍作者姓名籍贯。而在晚明总集中,却直接引用了《搜神记》中紫玉故事的完整细节。为了迎合市场,追求雅俗共赏,晚明女性总集常常表现出强烈的“叙事”的爱好,不仅收录诗词,还保留了大量仙鬼故事、世俗传奇的文本。像《名媛诗归》卷二十八所载吴氏女《酬江情》七绝及小传,述吴姓太守之女与一位名叫江情的少年在船中密约偷期的故事。诗作不过短短二十八字,但收入总集中的叙事部分几达近千字,不免本末倒置。不过,从小说研究的角度来看,由于编者在采录小说文本的过程中时常对情节文字进行修改,客观上却为类似《酬江情》这样的小说故事保存了一个重要的版本。
《非烟传》故事在不同总集中的编排模式,为探究小说文本与总集体例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比如《名媛诗归》卷十五,收入步非烟与赵生几次会面的酬答之作。编者为了符合总集条目中人物、小序、诗文依次编排的惯例,遂将有关赵生的故事情节和诗文置于小序中,每次到非烟酬答的部分,只交代“答诗曰”,将答诗的具体内容暂时略过。最后统一集中到序文之后作品部分一一列出。然而这一做法牺牲了小序的完整性,对不熟悉本事的读者而言,难免不知所云。《古今名媛汇诗》则采用了另一种方案,编者将赵生酬答的故事情节分散在每一首作品前面,以诗题下小序的形式出现,这样做似乎解决了诗文与故事割裂的问题,全篇头绪分明不影响阅读,但却影响了总集体例的一致性,已经跟直接收录小说没什么区别。
相似的编纂环境、编者群体与读者受众,造成了女性诗词与小说文本交织混融的格局,使晚明女性总集呈现出迥异于正统总集的特殊面貌。小说中的诗词,绝大部分是特定情节中人物的自题自吟或赠答酬对,不仅在小说中承担着推进情节、刻画人物的任务,也充当了男女主人公对话的媒介,自有其不可分割性。但从诗文总集的角度来说,作品本身才是独立自足的审美对象,过多的叙事并不会使其诗歌增色,反而会喧宾夺主,削弱了诗境的想象空间。编者热衷于为作品补充前因后果、建立联系,其用意显然已经超越了诗歌本身。除了保留小说的完整脉络、增加传奇性与故事性的努力,我们还可以从编者的自我声明,观察到通俗文学观念在女性总集中的深层渗透。
三、小说文本著录与晚明女性总集的选录观念
在正统总集的常见编排模式中,以身份区隔不同的文学群体,是揭示主流与边缘、高雅与粗俗的含蓄方式。长期以来,编者按照既定的惯例为各类身份群体排座次,无人置疑这套规则所代表的等级秩序的合理性。然而,晚明编者并没有对小说诗词作出专门区分,而将这类出自青楼婢妾、失行妇人“鄙秽”之辞,与后妃、闺秀的作品混杂在一起。从他们的解释来看,是为了彰显各阶层的“平等”,可以视为一种对抗等级秩序的努力。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与蘧觉生《夜珠轩篆刻历代女骚》,在凡例中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这一点:








注释:
① 陈广宏《中晚明女性诗歌总集编刊宗旨及选录标准的文化解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
② 研究成果除上引陈广宏论文外,还有陈正宏、朱邦薇《明诗总集编刊史略——明代篇(下)》第五部分“晚明时期女子、僧侣诗的流行”,载《中西学术》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39页;王艳《明代女性作品总集研究》第一章“明代女性作品总集叙录”(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
③ [明]池上客《名媛玑囊》,万历刻本,第28b-38a页。
④ 参见陈尚君《何光远的生平和著作——〈宾仙传〉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⑤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总集类·通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53页。
⑥⑧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766、1759页。

⑨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⑩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