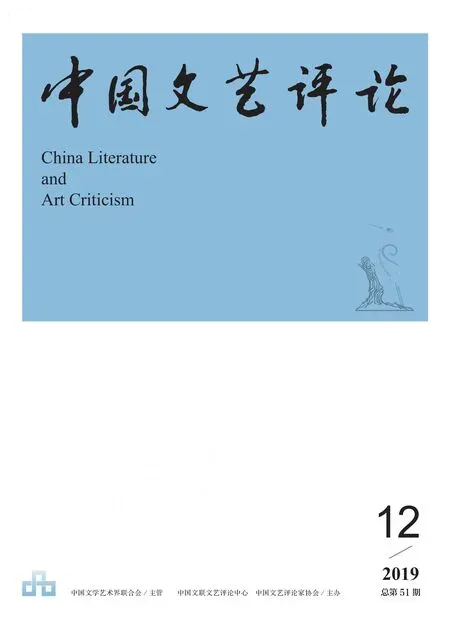艺术的成本
——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为例
韩子勇
凡事皆有成本。
战争成本最高,和平最为珍贵。战争是以命相抵。随着武器进步,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死亡和破坏越来越大。现在到了可以摧毁地球、同归于尽的地步。也因此,和平居然是最大的“红利”。
自由价值最高,生命的自由是本质。裴多菲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与爱情》)不自由,毋宁死。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与自由,比和平、比生命还要贵重,它们处在价值链顶端,值得勒石、立碑、铸鼎、镌刻于青铜板上。读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吧,那是近代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由与幸福之誓铭。
劳动创造人。劳动是价值之源,劳动者最光荣。猿和人,中间隔着的,是劳动、是动物本能和人类实践的鸿沟。劳动的进步产生分工,生产出现剩余,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成为可能,人类开始复杂化,出现阶级、利益斗争和国家机器。人类的理想,是消灭剥削压迫,实现财富极大丰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美是自由的象征,美是生命的自由状态。到那时,劳动不再是生存之需,到处都是自由的创造,社会洋溢着人类本质的光辉。
清风明月不花一文钱,好像没有成本。吊诡的是:人是自然之子,以石为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匍匐于自然之下,无暇欣赏自然之美。人是社会之子,一刻不停地进化、发展与生产。一万年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两百多年以来,人类大规模干预自然,改变地球面貌,已经成为自然的主宰。但终于有臭氧层空洞,气候变暖,物种消失,水体、空气、土壤的污染……清风明月真的不用花一文钱?越是看起来没有成本、似乎无限供给的资源,其实有更大、更隐蔽的成本。
是的,凡事皆有成本。能量只能守恒和转化,“永动机”的美事不存在。物质的生产是这样,精神、文化、艺术的生产也是这样。人们只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清洁生产、减少污染,一点点进步,但不能无成本生产。经济领域的成本分析与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对象。艺术创作与生产的成本,除了与一般经济规律相关联,还有更为复杂的因素。
2013年7月,我奉命筹备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同年12月30日,国家艺术基金正式成立。国家艺术基金是一项新生事物。英美等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采用基金制的方法,资助和推动艺术发展。在我国,伴随改革开放,先后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基金。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下,作为艺术领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尝试,国家艺术基金应运而生。作为国家对艺术投入方式的创新,由直接投入变为间接投入;由行政审批变为面向社会发布资助指南、机构和个人自由申报、同行专家进行评审、竞争择优进行资助。因此,艺术创作与生产中的成本及结构问题,就成为艺术基金资助管理工作中无法回避的课题。
国家艺术基金作为资助艺术发展的公益性基金,原则上所资助的是那些无法通过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艺术门类,这些艺术门类的成本情况更具有行业和机构的内部性,社会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因而也更难看清楚、更容易被忽视。
艺术项目成本的影响因子有哪些呢?
一是体制机制。一方面,传统上,我们有“君子远庖厨”的观念,文化人对自身的工作往往缺乏经济成本的筹算。历史地看,我们没有“文化工业”的经验,直接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形态,进入到近代的混乱状态。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战争时期的文艺体制、机制和传统,顺理成章延伸到新社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环境里,文艺的创作生产方式和传播消费曾长期地带有强烈的计划特点。国有文艺机构一花独放,文化艺术人才和文化艺术活动几乎都发生在体制内部,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封闭的单位形式嵌套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开放、变革、流动和市场因素日渐增加的环境下,社会力量办文化开始兴起,出现民办文化艺术机构和自由职业者。但直到今天,总体上,在那些很难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获取利润的艺术领域,国有文化机构仍占有质和量的绝对优势,文艺创作生产的投入形式主要是财政拨款,文艺机构的管理者和主创人员面向社会筹集经费的能力虽有提高,但成本意识、成本计算能力仍然偏弱,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主要在艺术方面,对内容考虑多,对成本和回报考虑少。因此产生一些“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大制作”“豪华包装”的流弊。因为经费投入主要来自财政,成本压力不足,市场营销乏力,缺乏竞争活力和倒逼机制,从而导致疏于成本的核算和控制。管理者、创作者、生产者较少考虑艺术的经济成本合理性的情况普遍存在。
二是客观上,对于需要保护传承的传统艺术和曲高和寡的艺术门类,东西方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就是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而要更多地体现为公益性,由政府、非盈利基金机构和社会来支持赞助。但即使这样,并不意味可以放松成本控制、不考虑经济的合理性,仍应该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争取最大可能的经济回报。
三是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共时地看,中国不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和文化多样,而且历史悠久,特别是发展的不平衡和环境的千差万别。艺术门类之间、各地之间、不同所有制艺术机构之间,艺术项目的创作生产成本差别很大。即使同一艺术门类、同一地方、同一所有制艺术机构之间,也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别,主要是由生产条件、人才队伍能力、机构管理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方面的巨大差异形成的。历时地看,社会变迁、审美和文化的变迁,以及科技介入带来的工具和表现手段的变化,使艺术的创作生产条件也发生改变,艺术成本也随之发生变化。
四是现代、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艺术创作生产要素市场不健全。成本价格是在频繁的交易交换中形成的。交易交换不充分,成本价格就不透明。总体上,目前我国艺术机构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生产要素等的区域性、内部性、随意性比较强,社会性、市场性、流动性、竞争性比较弱,且外部的交易交换不充分,难以形成现代、开放、统一、流动、竞争、有序的价格体系和外部约束。
五是艺术创作生产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艺术创作不同于物质生产。物质生产的市场程度高,物质生产是通用技术,追求规模化、标准化、批量复制,同批量产品的差异越小越好,差异大、脱离标准的产品是残次品,因而成本趋于平均。艺术创作和生产是单个创作和生产,没有通用技术,更不能批量生产。即使同一主题、同一题材、同一组创作生产力量,可选择的路径和最后的作品也可以千变万化,由此造成成本的不尽相同。艺术创作与生产,讲究个性化、独创性、唯一性、不可复制性,最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识别度低,过于雷同的作品反而是残次品,甚至可能涉嫌抄袭,因而其成本千差万别。艺术创作是失败率、淘汰率很高的领域。文化艺术如同农业,“艺”字的象形繁体,意指种植。艺术的生长,有一个缓慢的、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生长周期,人努力还得天帮忙,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谁也不能保证每颗种子最后都硕果累累。而失败的艺术,也不同于残次的物质产品,有质量问题的物质产品并不会使价值归零,失败的艺术不仅使价值归零,甚至可能是负数。
六是艺术作品的质量和投入有关,但不是正相关。没有投入不行,特别是多人合作才能完成的、由机构推动的综合艺术,要有一定的投入。但不是投入越多质量越好,有时过于宽松的经费条件,可能使创作人员变得懒惰,脱离艺术本体,忙于猎奇和感官冲击、堆砌场景场面。特别是,杰出的灵感和天才的创作,总是会节省大量成本,真正的奇思妙想决不拖泥带水,总是拨开云雾见青天,是减法,是以少胜多、简洁凝练,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使不可能成为可能。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是艺术领域成本与质量关系的另一种规律。肉身太沉重,灵魂难飞升。比如,根植于市井阡陌、勾栏瓦舍的中国传统戏曲,以写意取胜,出将入相,一桌二椅,以戏为生,随走随演,戏班子人都很少,关键是有角儿,主要靠角儿出彩出新。而现在的大剧场、导演制、声光电和各种舞台美术手段,使戏曲越来越复杂,人物越来越多,写意性减弱,越来越脱离戏曲本体,创作生产的成本也急剧上升。
总之,艺术成本与结构的影响因子是如此复杂、晦暗不明,它们在综合地起作用,叠加折冲,笼统的分析和判断是失效的,亟待深入到细部的实证研究。
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范围,涉及影视和文学之外的所有艺术门类,有十几个大类,近百个小类。每个门类的成本情况十分复杂,加上上述影响成本的因子,更是千变万化。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是艺术活动,除了对艺术各门类的创作生产进行资助,还资助优秀艺术作品的传播交流与推广、艺术人才培养和青年艺术创作。从资助对象看,是面向社会进行资助,突破了地域限制、行业限制、身份限制,有机构申报,也有个人申报。这些情况,都增添了成本和结构的分析、权衡和取舍的难度。
所谓管理,首先要有标准。即使弹性管理、多目标管理、动态管理,也要有标准、标准体系。但最完善的管理,也不足以应对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在这时,就要注意给具体的实践预留空间。国家艺术基金正式运行前,曾起草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准备以财政部名义发布。但大家在共同讨论和修改这个办法时,普遍感到用项目制的方法推动艺术活动在我国还不普遍、是新生事物,特别是艺术活动的成本和开支比较复杂,不宜一开始就预定一个统一的、刚性的、包罗万象的,但可能有很多缺陷的制度,从而被一下子框死。于是,我们退回一步,从“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申报指南”和“项目申报表”入手,资助指南和与之配套的申报表有五个,我们在申报指南和申报表中把资助额度、结构和相关的经费开支规定分门别类地写清楚,远比一开始就搞一个统一的、刚性的、包罗万象的,但可能是很不成熟的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更科学、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制度具有稳定性,不可能一年一改,但申报指南和申报表是按年度每年重新修订发布的,这也便于针对运行中反馈的普遍问题及时进行微调。同时,申报者的行为逻辑是对号入座、各取所需,更多地关注与己有关的申报指南和申报表,因此我们在申报指南和申报表中列明资助额度、结构和经费开支规定,更具有实际意义。
艺术项目的资助额度和结构,对应的是艺术活动的成本和结构,这个成本和结构从管理操作上,只能是求得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国家艺术基金初始运行的五年,艺术项目成本与结构对应的资助额度和资助结构,是通过广泛调研后分门别类地写进每个申报指南和项目申报表中,在全国征求意见,经艺术基金理事会审议通过并报送原文化部、财政部审定同意后发布的。相关内容每年还会根据运行中反馈的普遍问题进行微调,再经理事会和原文化部、财政部审定同意后发布。这样,申报指南、申报表就经历了五年五版的升级改造。五年的实践表明,这个思路和方法是可行的,没有出现大的偏差,没有出现颠覆性改动。
在国家艺术基金运行五周年之际,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从总结经验、深化管理的角度,感到制定一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使这个办法的出台有扎实的科学基础,首先要进一步总结五年实践的经验得失,集中力量,深化艺术项目成本、结构与标准的研究。
艺术的创作,不是完全依靠缪斯女神的灵光一闪。马克思揭示了这一点。他将艺术视作一种审美的劳动,第一次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待艺术创作。从他的劳动二重性和劳动产品双因素理论出发,艺术这一主要是审美内容、创造精神愉悦的特殊劳动,生产和消费也是一体的,“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所以,从艺术的生产过程来看,她依靠美的规律来行事。同时,她的生产又是一种特殊商品生产,消费中兼具两种价值、两种效益。因而,我们的艺术创作生产,其思想内容本身应当坚持艺术思维,但在其“物化”为具体形态的产品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物质消耗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则应适当引入一种经济的思维。
西方学术界已就此发出先声,并催生出一门独立的学科——艺术经济学。艺术经济学是艺术与社会经济研究的新兴交叉领域,它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而兴起。鲍莫尔和鲍温(Baumol&Bowen)合著的《表演艺术:经济困境》是该学科的开山之作。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表演艺术“成本病”理论,指的是日益增长的表演艺术生产成本与滞后的生产率、生产效益之间的矛盾。
国内也不乏将艺术经济学引入实践的学术成果,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进行研究,但较多的还是运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艺术行业、艺术政策的发展状况。这其中,对多门类的、纯粹的艺术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成本问题的关注较少,特别在实证研究方面,缺乏广泛而翔实的大数据统计分析。2017年年底至2018年,在上级部门和艺术基金理事会的支持下,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用一年的时间,集中力量开展资助项目成本结构的大规模调研活动。首先是问题导向,梳理五年来的难点、疑点及相持不下的争议点,确立调研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其次,确立实证分析和大数据统计的方法,利用了国家艺术基金申报、评审、管理的综合信息平台抓取和积累大数据的能力优势,同时请中国文联的相关文艺家协会分门别类进行大数据收集。这期间,管理中心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全国分大区、面对面,和各式各样获得过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单位和个人进行密集的座谈讨论和数据收集,获得第一手经验和感受;最后,对海量意见、建议和数据进行梳理、分类、甄别、分析,为当下中国艺术创作生产的成本和结构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个切片式的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作为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2018年度核心调研课题,历时长、范围广、样本足、代表性强,既是着眼于完善优化资助项目经费管理工作的政策型调研报告,为出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不乏学术探索的勇气,从成本经济角度掀开艺术生产的面纱,填补了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实证研究的“空白”,对建立立足本土的中国特色艺术经济学科体系也会有所裨益,相信也会对艺术创作生产领域的相关机构和个人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