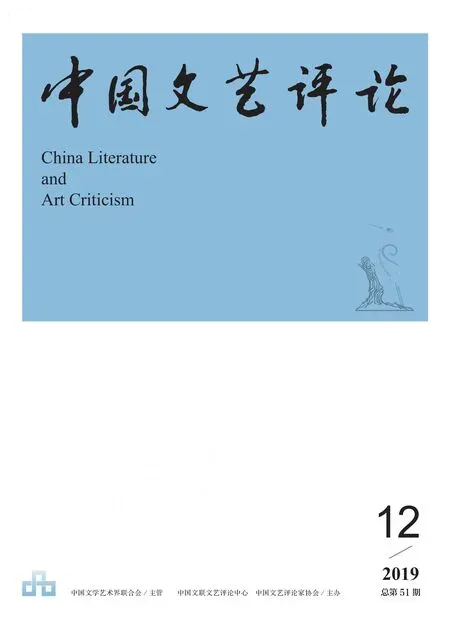主题电影类型化新趋势与电影高峰之路
王一川
随着2019年度国庆档国产电影观影潮的高涨,有关主题电影创作或“主旋律电影”的话题被再度激发起来。当观众如潮水般涌向影院争相观看《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影片时,人们有理由惊喜于如下事实:主题电影创作也能有高票房?!也因此而有理由进一步思考:这些主题电影创作是靠什么样的艺术表达来吸引巨量观众的?而回望中国主题电影创作的来路,其间又可以抽绎出哪些有益于未来主题电影创作的得与失?
一、主题电影创作及其美学特性
这里探讨的主题电影创作,其实是通常的“主旋律电影”的另一种称谓。在我看来,“主旋律电影”只是一种过于宽泛的比喻性称谓,而非正式的或标准的称谓。从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对电影艺术的资助政策惯例看,不如改称“主题电影创作”更恰当。这是因为,这种主题电影创作往往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核立项并委托特定艺术产业制作的、旨在实现特定年份国家重点或重大选题目标的影片。例如,2018年和2019年,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政府主管部门就先后审核立项了一批重点或重大主题艺术创作,涉及各种艺术门类,其中就包括一批主题电影创作。这样的主题电影创作,其核心的美学特性及社会使命就是运用富有审美魅力的影像形式系统去实现国家的重要年度选题目标,其中的基本主题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艺术表达。按照国家电影创作资助政策惯例回看,1987年3月以来的“主旋律电影”,实际上也具有大体相同的性质:都是指那些由政府立项资助的重点主题电影创作项目,其目标在于实现特定年份重要主题的电影表达。由此,本文一律以“主题电影创作”这一有政府政策根据的概念,取代通常的“主旋律电影”这个比喻性称谓(当然也不影响人们继续使用)。
实施主题电影创作计划,必然涉及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的美学要素或环节:一是主题委托,也就是政府拟定特定年份重点创作选题立项,委托特定的电影产业予以实施;二是主题落实,即特定电影产业为上述选题表达而制作相应的影像形式系统。这意味着,主题电影创作的必然程序往往是先有政府主题委托,然后才有电影产业的主题落实即影像制作。问题在于,主题委托的创作能够产生艺术精品或佳作吗?其实,这样的主题委托式艺术创作,在中外艺术史上不仅早就有先例可寻,而且更有艺术高峰可予追慕。名震中外的敦煌石窟艺术群,都是特定的订户委托无名艺术家们精心创作的。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哀悼基督》、壁画《创世纪》《最后的审判》等也是接受委托而创作的。说近点,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精品之一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上海音乐学院师生集体创作而成,也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主题音乐创作立项(尽管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健全的主题艺术创作资助政策)。显然,主题委托不仅可以产生艺术精品,而且可以创造出传世的或不朽的艺术高峰。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妥善协调处理主题定向委托与艺术创作自主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恰恰直接关系到主题艺术创作的成败。
因此,主题电影创作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如何使政府委托的主题思想或观念,能够在具体的影像形式系统中获得完满的艺术表达。简要地讲,这就需要妥善处理先有的观念与随后创作的影像之间的关系。
二、回望主题电影创作历程
任何一部电影主题创作,都必然是以一个完整的影像形式系统去实现特定观念的艺术表达。回看1987年以来的既往主题电影创作历程,粗略分析,就观念与影像的关系状况而言,可以见出如下大约三个时段的演进:观念高于影像时段、观念入于影像时段、观念化于影像时段。
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大致属于观念高于影像时段。从《开国大典》(1989)、《大决战》(含《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 役 》三 部,1990、1991、1992)、《蒋 筑 英 》(1992)等影片可见,那时的主题电影创作不仅其影像内容本身属于重大主题,而且其表达方式也必须确保重大主题处于优先或优越地位,对观众实施“寓教于乐”式的教化作用。而观众方面,进影院观看这些影片,本身也就相当于参加一次主导思想的宣传教育课。当然,在此前提下,那时的这类影片也尽力在局部环节中有限地借鉴外国类型片的惊险、悬念等手法。例如,《蒋筑英》在叙述蒋筑英的妻子去太平间探望的过程中,就吸收了惊险片特有的悬念设计及音响伴奏等手法,以期渲染气氛,激发观众的共鸣情怀,从而达到强化主题电影创作的社会效益的目的。
2003年至2012年的十年间,为观念入于影像时段。这时段的主题电影创作更加注重让主导观念降低自身的身段而平行于影像形式系统中,便于观众在娱乐之余获得思想领悟。此时段的一个新变化在于,随着基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或文化经济的日益拓展和普及,电影越来越经常地成为国家重要节庆时刻的节庆消费或节庆经济方式之一,例如贺岁档、春节档、暑期档、国庆档、双十一档等,主题电影创作同时承担起既满足观众的审美需要,又拉动国家消费经济,以及对观众实施主导思想宣传等三重使命。如此一来,主题电影创作势必会走到比照节庆经济需要而委托定做的路径上去,其结果就是主题电影创作的类型化势在必行。因为,当今世界电影的类型片或类型电影模式,例如动画片、幻想电影、科幻片、西部片、体育电影、悬念片、浪漫喜剧、法庭电影、史诗片等,似乎正是让特定的观念融化于既有的影像形式系统的常规范式。类型片范式的一个简明扼要的美学功能在于,便于让特定的主导观念找到娴熟地表达自身的对应的影像范式。《建国大业》(2009)和《建党伟业》(2011)的突破在于,先后为了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创造出以大批明星或“爱豆”饰演历史名人,以便拉近观念与影像、影片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的新范式。这种群星贺节片新范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观念与影像、影片与观众的距离,曾经创造出巨量观众争相进影院“数星星”的奇观,标明主题电影创作不仅在贴近观众方面、而且也在拉动消费方面都同时取得新进展。但是,其美学代价也不容小视:观众在“数星星”的同时,是否确已深入于影像故事的领悟和品味之中?人们对此影像奇观持有一种审慎的保留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013年至今则出现了观念化于影像的作品。进入新时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主题电影创作的影像表达问题,特别重视的是观念是否能够成功地融化于富有感染力的影像形式系统中,以及这样的影片是否能够真正创造高票房、从而成为消费文化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2019年国庆档的三部热门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虽然它们之间各有其美学得失)共同提供了观念化于影像、并以此创造高票房奇观的成功范例。不过,同时也需要看到,这个时段的主题电影创作状况,其实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着多样性面貌:另几部主题电影创作如《古田军号》《决胜时刻》《红星照耀中国》等的票房低迷状况,则提供了有所不同的另外的情形。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恰是这里需要加以探讨的。
三、2019年度主题电影创作的多样化景观
考察新时代以来主题电影创作的状况,需要看到一个虽然是逐渐发生但确实越来越明显的新变化:观念化于影像。
这种状况的出现,来自于两方面的动力或压力:一方面,国家锐意高扬重要主题宣传的社会效果,要求电影产业承担起以影像形式系统去宣传重要主题的严肃使命;另一方面,观众、特别是其中的网民观众,则产生越来越高的艺术审美需要,要求电影产业让任何主题宣传都自觉融化于感人的影像形式系统中,以便不是在强制压抑下被动接受、而是在休闲或娱乐的轻松中领略重要主题宣传的教益作用。于是,新时代主题电影创作面临的新任务在于,让社会主导作用越来越强盛的重要主题电影宣传,如何对普通网民观众来说变得和蔼可亲。当上一时段主题电影创作已然树立观念入于影像的成功经验后,留给新时代电影产业的主题创作的经验在于:你必须懂得,不是将主题观念高高溢出于影像形式系统之上而成为高不可攀或望而生畏的外在强制,而是要让它们融化于审美魅力充足的感人肺腑的影像形式系统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让国家所孜孜以求的重要主题观念真正深入普通观众心灵这一特定意图。
应当看到,进入新时代的头几年,主题电影创作仍然一度延续上一时段的状况而变化不明朗。2013年的《国徽》《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雷锋在1959》《雷锋的微笑》《青春雷锋》《南泥湾》等,2014年的《黄克功案件》《兰辉》《毛泽东在上海1924》等,2015年的《红军乡》《百团大战》《邓小平登黄山》等,2016年的《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大会师》《知心法官》等,2017年的《建军大业》《十八洞村》等,2018年的《浴血广昌》《最后一公里》《古城片警》《信仰者》等,大多尽力继续沿着观念入于影像的路径走,有的甚至返回到观念高于影像的老路径上。不过,变化毕竟出现了:一方面,主题电影创作政策大力度要求电影产业提升观念的影像化水平,实现主导观念的大众化,也就是探索观念化于影像的新境界;另一方面,来自于香港电影类型化传统的经验,也在积极寻求加入到主导观念的影像表达行列,加速主题电影创作的类型化进程。于是,一种合力出现了:主题电影创作不仅实施了明显的类型化转向,而且还取得了系列标志性进展。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徐克执导),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林超贤执导),以及2018年的《红海行动》(林超贤执导),都是出自香港导演与内地电影人的合作,共同走出了主题电影创作的类型化路径。
在这样的论述基础上,回头来看2019年度主题电影创作状况及其新突破,就可以发现,这一年度的主题电影创作不仅出现了观念化于影像的盛况,而且也同时呈现出其他面貌,例如观念高于影像和观念入于影像等,从而形成了一种多样化景观,恰似呈现出过去两个时段与当前时段之间的三径并行状况。三径并行,是指观念高于影像、观念入于影像和观念化于影像这三条路径都同时并存于当前主题电影创作中的情形。简要地看,2019年的主题电影创作的三径并行状况由下列三条路径构成:第一条是观念高于影像路径,如《红星照耀中国》等;第二条是观念入于影像路径,如《古田军号》《决胜时刻》《歌声的翅膀》等;第三条是观念化于影像路径,如《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
不过,我在这里倒宁愿舍弃三径并行之类论述,转而看到这些主题电影创作呈现出来的一种不约而同的共同选择:主题电影创作的类型化。这就是尽力探索沿着不同类型片的成熟套路去分别实施主题电影创作的美学策略。如此,为特定的主导观念寻求对应的类型片范式,就成为当前主题电影创作的必由之路。由此可以看出2019年度中国主题电影创作的多样化类型片路径。
最受瞩目的一种类型片,自然是国庆档中的群星贺节片《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任总导演,管虎、张一白、徐峥、薛晓路、宁浩、陈凯歌、文牧野分任单元导演)。这种群星贺节片是以2009年为建国60周年节庆而委托定制的《建国大业》为开端和典范范本的,属于中国原创或中国特色的主题电影创作类型片。只是这一次不再沿用一部完整剧情片的路数,而是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历史,精选七个里程碑式时间节点,透过普通小人物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七个小故事的集束,即《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小中见大地依次回顾共和国70年风雨历程,让观众与影片一道重温共和国沧桑巨变印迹,激发起情感、理智、幻想、理想、期待等多重群体共鸣,从而达到宣传主导思想的目的。这里面既有共和国70年重要时刻的历史重现,又有普通人被激发起来的对自身亲身经历的再度体验,还有众多知名电影明星合力亮相、共同组合成2019年国庆长假期间节庆消费热点,使得影院及其周边餐饮业都成为国庆长假期间众多观众争相前往的消费目的地。既有高票房,又实现国庆长假期间家庭及亲友大联欢,主题电影创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一道终于达成双赢局面。
其次就是票房与之几乎并驾齐驱的以灾难片范式亮相的《中国机长》(刘伟强执导)。这部影片本来应该是一部英模人物剧情片,取材于发生在2018年5月14日的川航3U8633航班机长刘传健这一真实事件原型,该机组和刘传健分别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的“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及“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称号,副驾驶、第二机长等也获得表彰。但该片没有按照一般英模人物剧情片的套路走,而是完全借鉴了灾难片的类型片范式,尽力渲染空中灾难时刻的夺命惊魂效应,满足观众观看灾难奇观的愿望。不过,这部中国特色灾难片毕竟突破了国外灾难片通常的个人英雄主义套路,注入了强烈的中国特色:突出了以机长为核心的全体驾驶员、乘务员、乘客、乘务员家属、地勤人员、军用机场指挥员、民航管理机构等各方面的相互配合和倾力支援,凸显出重大灾难时刻举国一盘棋的主导观念。这就使得观众既可以宛若身临其境般亲历重大灾难奇观,又能深切地感受到国家主导下集体主义精神力挽狂澜、转危为安的强劲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任何个人英雄主义都无法替代的、也无法达成的。
再有就是按照冒险片范式摄制的《攀登者》(李仁港执导)。该片的主导观念自然是通过中国登山英雄两次登顶珠峰的壮举,展现中国式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的力量,但也是按照冒险片特有的类型片范式去精心摄制的。其具体表现在动用一切影像手段,重点刻画登山英雄们经历的一次次冒险场景,并将这种冒险场景渲染到极致,由此让集体英雄主义显示出感染力。应当说,单从这点看,本来是可以成功取得预期效果的。可惜的是,影片设计的第一男主人公方五洲与其恋人徐缨的恋爱情节不适当地过于繁多和抢戏,直到生出喧宾夺主的负面效果。这是主题电影创作需要认真吸取的一次教训。
假如说,上述三种主题类型片的票房成功,称得上是有些异乎寻常的主题电影创作的高票房奇迹的话,那么,一批主题传记历史片的低票房境遇却是原本就可以预期的,属于主题电影创作的常态情形。《古田军号》(陈力执导)走出了通常直接叙述古田会议过程的旧套路,转而十分努力地将主要镜头对准古田会议举行之前的一系列前事,刻画出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动人形象。《决胜时刻》(黄建新、宁海强执导)首度叙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香山领导夺取全国胜利的故事,同样展现出人民领袖的平常而又崇高的群像。《红星照耀中国》(王冀邢执导)则是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奔赴延安采访的过程记录下来,透过这名美国记者的旁观者视角,刻画出毛泽东和他领导的红军的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形象。
还应当提及的是音乐歌舞片《歌声的翅膀》(高黄刚任总导演)。该片意在借助三名新疆青年歌手返回家乡采风的故事,挖掘新疆特有的音乐与舞蹈艺术的雄厚资源,展现全疆多形态地域美景的迷人魅力。同时,它还把公路片、风光片、爱情片、教育片等多重类型片元素都尽情融入其中。这样的集中呈现,可以向国内外观众呈现一种预期中的主题电影创作效果:今日的新疆依旧是人们热爱和向往的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好地方”。
从上面的远不完备的列举中可以见出,2019年主题电影创作的新趋势可以简要概括为类型化,具体说是多类型并举,也就是让主题电影创作沿着多种中国式类型片的范式走,各归其类,各循其矩,分头发展。越是重要的主题电影创作,越需要遵循特定的类型片的范式去摄制。《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分别在群星贺节片、灾难片、冒险片上取得了远超于其他主题电影创作的惊人业绩,表明中国式类型片路径是可以通向成功的。
四、从主题电影创作类型化之得失看电影高峰之路
总结2019年度主题电影创作,需要一种相比于简单地评功摆好或全然否定来说更加全面而理智的得失并论的辩证眼光:既应看到突出的高票房业绩,也应认真对待明显的低票房情形。可以简要地说,一方面,这次主题电影创作之得,集中在国庆档三部高票房影片所呈现的类型化范例上:分别以群星贺节片、冒险片和灾难片的类型片范式,成功地吸引巨量观众在国庆长假期间涌向影院,从而实现了主导观念的大众传播效应。另一方面,这次主题电影创作之失,集中在其他几种类型片的类型化路径及其效益还存在颇为宽阔的拓展空间,从而出现了看似难以理解的不平衡状况。
其实,对主题电影创作的这种得与失的情形,需要予以冷静看待。主题电影创作的类型化路径,绝非一剂可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为不是任何一种类型片都必须按照票房去衡量其水平的,需要具体分析。当主题电影创作的类型化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时,更需要做的是全面地分析和衡量主题电影创作的多类型格局及其前景。不同类型的主题电影类型片,应当各有不同的预期观众以及票房指标,而不能指望所有的主题电影类型片都能像《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那样一举获取高票房业绩。这是由于,主题电影创作的素材原型及故事各有不同的特点,并非每一种素材原型及故事都适合于拍摄故事长片。例如,有的英模事迹可能更适合于新闻报道、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而未必适合于摄制故事片;即便适合于摄制故事片,也可能只是适合拍成微电影故事片而非故事长片。像《中国机长》这样罕见的素材原型,天然地适合于灾难片。但相比而言,《古田军号》创作所依据的重大历史性事件素材原型本身,就难以像《中国机长》那样具备强烈吸引观众的超级惊险及超强刺激元素了。
同时,更应看到,当前中国主题电影创作面临的一项新使命在于,如何汇入“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这一时代巨流之中,推动属于这个时代文艺高峰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电影高峰的生成。这样的电影高峰,当然不是如古代文人士大夫后花园那种可以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的假山,而应是当今世界公认和敬仰的世界性电影高峰。由此高峰尺度回看,目前中国主题电影创作可以提升水平的空间颇大,或者说,通向世界性电影高峰的路程依旧崎岖而漫长。不过,空间颇大,有利于腾挪跌宕;崎岖而漫长,有助于涵养勇气与毅力。基于此,中国主题电影创作有理由果敢跨越2019年度的高度,向着更高的险峰攀登。
这样,通向未来电影高峰的中国主题电影创作,应当综合考虑如下问题并制订相应的政府艺术管理及电影产业对策。
首先,主题电影创作应继续类型化路径并实施多类型并举策略。这意味着,主题电影创作不可能全部都走《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由政府主管部门直接委托定制的路径,而需要兼顾多方面因素,进一步调动民营电影产业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共同投入和支持。这就是说,需要根据众多主题电影创作素材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类型片路径,包括让参与的电影产业自主选择适合于特定素材的类型片范式。《古田军号》《决胜时刻》的经验表明,传记历史片应当是主题电影创作的常规的类型片种选择之一。
其次,一部主题电影类型片虽然可以渗透其他类型片元素,但不宜过多或过杂,以免产生喧宾夺主的后果。《攀登者》在其冒险片主导元素中融入了过量的爱情片元素后,导致关键时刻历险剧情被生生隔断,阻碍了叙事的流畅性,削弱了应有的节奏感。《歌声的翅膀》让一部电影同时承载音乐歌舞片、公路片、风光片、爱情片、教育片等多重类型片元素,虽然看点颇多,但也容易流于题旨过杂而不便集中和深化。当前主题电影类型片创作迫切需要减去不必要的类型片枝蔓,大力强化主导性类型片元素的主导地位。
再次,主题电影创作的效益,不宜完全由票房去衡量。如前所述,主题电影创作的素材各不相同,有的未必就能获取高票房。这时,应当冷静地分析素材蕴藏的可能的类型片特点,做合理的选择。《古田军号》这类素材就不必去强行考虑票房问题,而是集中考虑如何以高质量的美学水平去获取应有的社会效益。
最后,未来主题电影创作应着眼于长远效益而非短时效应,故把好质量关是关键。在其最初的主题素材选择环节,就应实行更加严格的筛选及准入制度。有的素材如果只具有短期宣传效应而缺乏长远传播效益,难以生成为电影高峰,就应当果断舍弃。假如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师生选择的不是“梁祝”素材,而是本来分列第一、二位的“大炼钢铁”“全民皆兵”,那世上就不会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一当代音乐高峰之作了。有的不适宜拍成电影的主题艺术创作素材,完全可以果断地转化成文学(纪实小说、报告文学等)、美术、戏剧或微电影等艺术门类、样式或方式去表达,千万不要硬性拍摄成故事长片,因为那时浪费的就远不只是国库经费了,更有普通观众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2019年国庆档期那样旺盛的观影热情,以及他们对中国式主题电影创作的尊重和更高期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