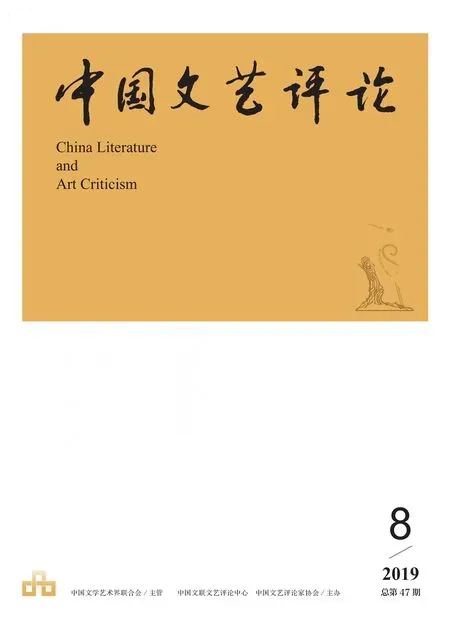“城市诗”美学散论
徐 芳
城市诗该有什么样的美学轮廓,一千个城市诗人可能有一千种不同的回答。我当然也有着我的答案。要回答我心目中的城市诗是什么样子,可以从我十分喜爱的日本当代诗人谷川俊太郎谈起。他是个十分奇怪的混合体,在社会生活中,像个街垒斗士,但在诗歌实践中又绝然排斥生活中的热词、酷词。他觉得诗存在两种本体:社会本体与宇宙本体。我十分赞赏他的说法,只是想把他的宇宙本体,改为“生命”。持社会本体论的有惠特曼、勃洛克,持生命本体论的有狄金森、普拉斯,而有些诗人的创作可能复杂些,比如聂鲁达,他的《伐木者,醒来吧》是典型的社会本体论,而《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又是典型的生命本体论。所以,我觉得好的城市诗,应该从生命本体出发,有一种生命向度的存在,这种存在的状态无论是呐喊或喟叹,爆发或深匿,都和生命的本源与衍化形态相关。同时,它必须是城市的,而且是当下的城市的,必须具有当下的城市的形态、城市生活的形态。
一、城市诗的“他者”及其美学结构
对于城市诗,每一个诗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艺术探索,而我的探索是围绕如何处理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展开的。
一般而言,我们将那些未经人工改造过的自然,称之为第一自然,而将那些沾染人工痕迹的自然称之为第二自然。城市是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混合体。在法语中,有一个饶有理趣的语词现象,即“自然”一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当它以小写的字母开头时,它指的是大自然的存在;当它以大写字母开头时,它指向的是人的生命的自然存在,并包含人自身的所有存在物之总和。法语的“自然”的释义也可视作我们对历史中的人的自然进行观察的逻辑起点。在我们这片母土上,对第一自然把玩咂摸的诗篇不胜枚举。这也许和道家的影响有关:“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而所谓“恍惚”“窈冥”,无形之义也。所谓“物”,物质也。所谓“象”,亦物也。所谓“精”,种子也,物生之原也,即所谓“物”也。言道体无形,而其中有万物之所以生之种子也。亦与道生万物,万物取法自然,因而万物皆自然之说,不谋而合。
或许,在风格上,“城市诗”也有“大江东去”与“小桥流水”之分,骨子里却可能都潜行于、匍匐于第一自然的笼罩之下。那么,“城市诗”的“他者”,是否就一定是那些以第一自然作为表现对象的诗歌作品呢?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是否就一定是一种相互排斥和否定的关系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回到生命本体论上,让我看到了生命本源中的自然崇拜。对自然的亲近、敬畏乃至崇拜,这种情感、这种愿望也许从来没有远离过人类。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对此予以了详尽的论述。对人类来说,与自然和谐相处,远比征服、掠夺、占有自然更为重要。在终极的意义上,自然是无法征服也无法超越的。认清了这一点,也就认清了第二自然的价值所在。它仅仅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不同驿站的风貌而已。
在我的创作实践中,会有意识地、自觉地引进第一自然的存在物。河流、阳光、花、茶叶、金鱼、雪、天空……它们与晕眩、无奈、离散、无中心感、匿名、无方位感,那些城市症候,水乳交融般在同一个纸上空间展现。
请看这首只有三段的《星期日:茶杯》:
一只瓷杯里泡着
整个上午的天光
洗衣的……
做饭的……
走来走去的廊间
消失了
风的呼啸
从沉寂的杯底
窜起一些灰黄的叶片
那是茶——
从春天的树间摘下的
生命……
娇嫩的爱……
一片嘴唇无意中沾上
这销蚀的灵魂
它大声地噗噗吐出……
——整个下午便只有一种沉降的运动
第一自然仍然强悍地存在,那句“从春天的树间摘下的/生命…… /娇嫩的爱……”力图在水泥砌就的四壁里,打开一扇远眺“牧野”的窗,那里有最原始最庞大的第一自然。但最终我们还得回到这个“星期日”,这个“茶杯”,这种特定的城市生活状态之中。意义或许存在,或许并不存在,但整首诗充满了对特定的城市生活的自嘲:有时(当然不是所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下午,就只剩下“一种沉降的运动”。
那些灰色的词语,比如“泡着”“迷失”“窜起”“噗噗吐出”,既勾勒出一种困惑的生存状态,同时又与充满生命质感的“春天”和“树间”构成了一种反讽,一种如同梵高笔下抽搐的、反抗的蓝色的反讽色调。全诗也许因此而隐隐传递出现代城市生活对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异化,一声浅浅的对于回归自然本真状态的喟叹。
我的这种艺术尝试,与“现代城市诗”的鼻祖波特莱尔的美学趣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波特莱尔触摸着、梳理着巴黎的肌理,但总有一种比忧郁更忧郁的绝望弥漫于街衢之间、砖石之上。在巴黎,他看到的自然存在物都是丑的、恶的。天空像裹尸布,千万条线的雨水,变成了像监狱的栅栏的无数铁条,晚祷或晨祷像可怕的幽灵的长啸,而整个世界索性变成了潮湿的囚牢……
现在或可以说出,决定城市诗里所谓情绪或美学模式的,就是以上几种极端的看法之间的对立,但我以为这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对立——应该仅仅是城市诗写者在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之间的分别与歧见。换了角度和阶段,可能许多看法也会随之改变,甚至对立双方的立场,会互相颠倒过来……但是长久以来,我的阅读影响了我的写作——也许在阅读的有限选择中,本身就提供了我自己对城市的感情与态度的线索,似乎我更倾向于欣赏博尔赫斯在城市诗方面做出的艺术努力。他笔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既有着现代城市所带给人的那种迷乱、晕眩、无奈,又让人趋之若鹜、无法避舍。他在《城市》一诗中写道:
就像一块燃烧的煤
我永远都不会丢弃
尽管烧到了我的手……
他还对城市的形态既做了物理性的描摹,又进行了精神性的嘲讽和鞭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横向的轴线优于纵向的轴线”;这个城市的房屋建筑都是清一色地蹲伏在那里,很胆小又很骄傲,其住户的“宿命论”思想,也在砖瓦和泥灰上表现出来。而博尔赫斯的城市诗,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在他的关于城市诗寓言式的或左拉式的描摹中,总离不开一个第一自然的意象:日落景象。它是一个中心、一个主要的意象。也就是说,正是通过“日落景象”,博尔赫斯的许多城市诗,将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熔铸成一个崭新的富有参差变化的艺术整体。
而在诗歌的语言实践上,我也有意识地尝试着将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杂糅整合在一起。评论家方克强在我的诗歌作品研讨会上,曾经这样说过:徐芳的语言自然流畅,但是又有一种动感,又有一种节奏。她的自然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一自然是天然自然,第二自然是人工自然。我们城市水泥、马路、高楼也是构成城市的自然,但是人工的自然。我觉得她写第二自然,用的语言就是第一自然的语言,用的语言就是贴近第一自然的语言,表现第一自然的语言。所以她的文字不反复,不复杂,不搞太多词句上的技巧。她每一句都很明白,但是你连在一起看,一个词语和另一个词语之间没有空档——给人感觉明白而没有空档。而她的句子没有反复,这种纯净语句的状态就像第一自然的状态。你看每一句都不会产生一种复杂感,但是在句与句之间却留下了空白。你全部看下来以后觉得这些空白就触发了你的再思考。这种自然、朴素、清新的句子,还有一种自然人性的状态。
“城市诗”既可能是一个或多个流派、思潮、风格、地方性,还可能是,也应该是一种审美机制——与城市诗一起来到我们中间的,除了要表达城市生活的新内容,还一定有着表达的新角度、新感受,还可能同时携带来新的技法、新的表现方式等。如何在城市生活形态中,建立城市诗的美学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形态已经先验地规定了城市生活的形态。那么,在这种城市生活的形态之中,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法国学者潘什梅尔曾如是说:城市既是一种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地说,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一种灵魂。在潘什梅尔这段话里,中心词语是:气氛、特征、灵魂。我深以为然。
认识城市、把握城市,其实是可以从“他者”开始的。如果说“城市诗”的“他者”,未见得一定是那些咏唱第一自然的诗歌。那么,城市生活形态的“他者”,无疑是乡村生活形态。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如果没有“他者”,人类是不可能认识到自身的。没有“他者”的存在,主体对自身的认识就不可能清晰。乡村生活形态,正是我们认识城市生活形态的“他者”。
可以从最细微处去发现这种乡村礼俗社会、宗亲社会与城市生活的法理社会、陌生社会的差异性。比如,陌生感是我们在城市社会中最易体会的人际感受。桂冠诗人杰夫•戴尔曾写过一篇以巴黎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臭麻》,《臭麻》的旨趣就是:巴黎在麻辣的舌尖上,既清逸又浪漫,既让你如坠深渊,又欲罢不能,既让你陌生——你不认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你叫得出名字的,但又让你熟悉,那熟悉的街头拐角,那行色匆匆的步履,那紧闭的每一扇窗户,你都依稀在哪儿见过。在这时,你触摸到的是庞大的城市所建立的美学结构:在陌生中被放逐,在陌生中追求无奈,在陌生中与陌生互相取暖,在陌生中践踏陌生但又被陌生所驾驭。城市最强悍的逻辑就是:几千万人在一起,而与你发生勾连的也就是那么几个、几十个。
在我的诗集《日历诗》中,有一首《四月十七日,地址不详》,我努力捕捉的,也是类似于杰夫•戴尔在巴黎所遭遇的那种陌生感:车,是陌生的,因为坐错了;你,是陌生的,却用很大的动静,去打开一扇门,却不是进门,而是后退;归来,那路的前方,但不知有多长多短;自然景观是陌生的,微风会变成黄土,一种流动会变成凝固;而最重要的陌生还是“你”,熟悉的“你”,却依然“地址不详”。
再比如,碎片化。在城市生活的形态中,登峰造极的碎片化可能就是时间,时间被切割成无数碎片。按照博尔赫斯的说法:生命只是一个各种不完整时刻的混合体。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我;或者,极言之:我并不存在。我非一个能用现实去把握、去衡量的我。在《八月二十七日 夜色》中,我表达了这层意思:
我的眼睛
一如这个人
一起停放在门边
还把手臂
借给了门框
当它们
也一起
颤抖着说出了:
走吧……
此一刻恍如来世
江中满月
长天独眼
如是,形神乃离
对我来说,城市因我而存在,或者说,我存在着看到了这个城市,但这个“我”,偏偏又是“手臂借给了门框”,变化之中的“我”。时间在此刻,又如玻璃碎片那样具有着恍惚和不确定性:此一刻恍如来世。“江中满月长天独眼如是,形神乃离”。因而与博尔赫斯在《剑桥》中所悟,也许就有了几分相似性:“我们是我们的记忆我们是不连贯的空想博物馆一大堆打碎的镜子”。我认为其中一个关键词是分离,另一个关键词是破碎,它们统合在一起,体现的正是:“生命只是一个各种不完整时刻的混合体。”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的整个《日历诗》诗集,就是企图整合这种断片化的时间——这每一个日子的不同时刻、不完整的时刻。抒情主人公的身份、角色,都在断片化的时间里不停地变化着、变幻着。城市,为这种断片美学提供了新的审美机制。
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文章中,曾提出过“断片美学”的概念,即他认为中国古代诗人对往事的再现,总体上是不完整的、残缺的。斯蒂芬•欧文把它归结为“记忆本身就是来自过去的断裂与碎片”。但现在,如同爱情为罗兰•巴特的《恋爱絮语》提供了断片的审美机制一样,本雅明所阐述的城市生活形态,也具备了一种离散化的表征;而博尔赫斯所阐述的:“生命只是一个各种不完整时刻的混合体”。也就在断片美学的机制之上凸显了时间这一维度。以上种种,皆为“断片美学”注入了或者说打开了另一扇门,另一种审美机制。《日历诗》或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对“断片美学”的新的艺术注解。
二、城市诗的内涵和源头
广义上说,以城市作为表现对象的诗,皆可以称之为城市诗。如果说汉朝时期的长安、洛阳,能称之为城市,那么《两京赋》(它与《上林赋》还是有着差异的)也可以称之为古典城市诗的源头之一,而古典城市诗(词)在柳永的《望海潮》中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古典城市诗中,是有着对城市风貌及风情的某些展示的,如《西京赋》中,张衡对巍峨的城市建筑的抒怀:长廊广庑,途阁云蔓。闬庭诡异,门千户万。而《东京赋》中,他还生动地展现了杂技艺术风靡城市的场景: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谲诡,灿烂炳焕。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及至柳永的《望海潮》,更是以一种凝练、简约的笔触,将城市风貌予以了展现: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然而,如同斯时斯刻,城市被淹没在无边无际的牧野之中一样,无论是《两京赋》,还是《望海潮》,对城市风貌的描写,被更多篇幅的对于第一自然的抒写所包围,所裹挟,被“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类的表达所消解、所统摄,毕竟,究其宏阔的社会背景而言,那还是一个农耕社会所主导的历史时期。
世界范围里的现代的城市诗,应该没有疑义地肇始于波特莱尔。福柯曾有言:诗人波特莱尔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散文《现代生活的画家》,在打破旧的美学观念、欢呼现代世界的到来上,是标志性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波德莱尔对现代世界的美学想象,是围绕着漫游者这一活跃的角色构建的,他观察着巴黎街头和拱廊街内的生活,并对其作出评价,其作用被认为契合于现代人的特性。
存在着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城市诗吗?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设问,存在着一种本体意义上的诗,但作为诗的一个分支,一个诗系统下的子系统的城市诗,它的本体意义何在?在逻辑上,城市诗的异质性是它存在的理由。那么问题紧接着变成:何为诗的异质性?任何风格、流派的好诗,都有诗歌意义上的同质性,都有某种共同的规定、标准恒定在那儿。一首“纯正的”城市诗,必须接触、梳理现代城市的肌理。对现代城市,完全可以持矛又持盾,秉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如德国社会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那样做一个虔诚的城市主义者,如同一个啤酒主义者热爱泡沫那样,热爱城市的奢靡繁华、喧嚣嘈杂;也可以像本雅明那样,对现代城市所有症候进行问诊切脉,用一种艺术语言去考察它对人性、生命所导致的扭曲,所施予的伤害。在这其中,肯定有许多值得诗人用诗去诠释、去观照的母题,比如说,孤独。 现代城市最大的伦理问题之一:是它制造了人际交往的壁垒,阻滞着人们的沟通和了解。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它制造了城市人半封闭的生存状态,从而制造了无处不在的孤独。
但“孤独”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正是诗人们要努力捍卫的吗?聂鲁达为了捍卫他的孤独,不惜远离母土,到大西洋的一座孤岛上去寻找孤独,拥抱孤独——谁在他需要孤独的时候破坏他的孤独,谁就是他的敌人。但孤独的悖论就是人还是群居动物,人与生俱来就具有群体性特征。按照拉康的“他者”哲学,人进入 “镜像时期”之后,他不是通过自我而发现自我,恰恰是通过“他者”来发现自我,通过群体来发现自我。
如果能把城市病症候中的“孤独”母题,加以举一反三、层层剥笋式的辩证思考,那不就是一首纯正的“城市诗”吗?
在英国玄学派诗歌时代里,多恩就写过一首《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对“孤独”进行既“形而下”又“形而上”的辩证思考。只不过可惜的是,从城市的角度而言,它不够纯正,是因为没有飘迹在城市的或灿烂或鬼魅的影子。
而所谓诗的纯正性——所谓纯诗,即追求诗歌艺术纯粹美学上的价值。不难发现,追求 “诗的纯正性”乃源于我国古代的诗歌传统。对此中国台湾现代派诗人洛夫说过:“现代诗人所追求的是那种真能影响深远。升华人生,‘不涉理路, 不落言诠’,为盛唐北宋所宗的那种纯粹诗。”在理论上,显然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美国诗人爱伦坡,法国诗人波特莱尔、马拉美等, 都认为诗只有一种纯粹美学上的价值。如爱伦坡认为诗的本质是一种由张力所形成的抒情状态,其效果与音乐相似。
城市诗对诗人身份肯定有特定要求,山顶洞人、半坡人肯定写不出“一日看尽长安花”,而古代的长安人、临安人,一定也写不出现代上海霓虹灯彩的怪眼、哥特式建筑的迷离剪影。但所有这些问题,身份也好,居住者、闯入者也好,都离不开一个关键的节点:城市意识。
何谓城市意识?或者进而言之,何谓现代的城市意识?
波特莱尔在解释现代城市的现代性时,无意中触摸到的也是城市意识的核心: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齐奥尔格•西美尔则用更明确的语言,分解了波特莱尔的意思,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书中,他写道: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
我们可以从一个文学的经典母题“在路上”切入,看看在城市意识观照下的“在路上”,与在乡村意识观照下的“在路上”的差异性。
在梭罗《冬日漫步》中,路,像文中标点符号一样,随处可见。捡拾一段:现在,我们转身折回,向山下林地湖泊的边缘地带走去。这湖泊坐落在一个幽静的小山谷中,仿佛是周围山丘把大量的落叶当香料,经过历年浸泡过后榨出的果汁。湖水从哪里来,要流向何方,我们难以看出,不过,它自有它的历史,那湖中流逝的水波,岸边浑圆的鹅卵石以及沿岸生长着的连绵松树就是最好的记载者。梭罗的“在路上”,是狄金森看着鸟飞向天尽头的小路,是王维见清泉石上流的小路,是叶芝在茵纳斯弗利岛上徜徉的小路,是让爱情长成星辰再回首铺满叹息的小路,是从前的日子都慢,是乡村的缓慢、宁静、重复、单调的小路,像一首悠久的俄罗斯歌曲《小路》所歌咏的那样:曲曲折折,横在原野深处,不见人迹,少见人迹,却要固化,仿佛要完成千年的愿望。人的心理机制,在这样的小路上,也该会有一种平稳,一种类似的执念吧?会常有“停车坐爱枫林晚”之慨叹吧?
但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他一语双关:“在路上,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可这《在路上》,后来也风景突变:全国最蓬头垢面的人都拥挤在人行道上——空气中飘荡着茶、大麻、辣椒煮豆子和啤酒的气味。在美国的夜晚,啤酒屋里传来震耳欲聋的、狂野的爵士音乐,牛仔音乐和各种流行音乐混合在一起;就像所有的人都在说话,哪里分得清这一个和那一个。而在泪眼模糊中,一切都似乎消失得太快:也许,凯鲁亚克看到的“在路上”,既是普拉斯(美国自白派诗人)吞服了半瓶安眠药醒来时看到的“在路上”,又是当年波特莱尔在巴黎看到的“在路上”:闲逛者的视觉之路、收藏家的触觉之路、歌女舞女的飘忽之路、捡垃圾人的无奈之路,是有着拱门、街、桥、新式材料、工厂、烟囱、橱窗以及霓虹之路。人的心理机制,在这样的路上,或许会有那种怎样的躁动、紧张以及焦虑不安吧?还是同一个波特莱尔,他发现了“在路上”,在巴黎的“路上”的“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所带来的那种紧张:在这种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入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
如果说,乡村的“在路上”它对应的是坚定而缓慢、宁静的心理节奏,那么,都市的“在路上”它必然会培育出一种心理机制,使得自己免于这种瞬时之变、速度之变,或者可能的偶然之变给自己带来的意外打击。久而久之,都市人的心理会形成一种只关心外部的变化,或者只关心外部与自身的那段所谓的距离。这就是乡村意识与都市意识(或称城市意识)区别性的原点。
从文艺母题、生存状态而言,我们永远都在路上,这也是波特莱尔所言的“永恒的另一半”。而我们观照的都市的“在路上”,它不仅仅有物理学方面的意义,城市地理学方面的意义,它还浓缩了或者说象征了城市意识的建立和觉醒。它是生存状态,也触及到都市生存的本质;它是生活中的某种过程,是生活被城市节奏殖民化的具体例证(哈贝马斯之意),但那也是生活本身,是城市意识得以建立的土壤。
三、城市诗的“海派”特色
已经呈现的上海城市诗是否有着饱满的海派特色,尚待研究者的考察。但上海城市诗应该具有上海的况味,或者换一种说法,叫上海的城市精神——无疑是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毫无疑问的一种方向性的选择。
那么,何为海派特色?何为上海的城市精神呢?这一问题还真不好回答。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上海人,眼里就有一千个不同的上海——上海也实在是太大了,也太复杂了。
在太平洋的弓形海岸的中轴与长江之矢的终极地,汇聚了这一片息壤。从它的开埠之日起,它就“撰写”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寓言与现代神话。德国有一句古谚语说:城市,使得空气自由。这句谚语或许也可以解释海派精神的真髓;当然也可以说创新是上海这座城市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懈追求的精神皇冠。
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有一批得风气之先的文人,写出了一时“网红”的“城市诗”——而所谓新感觉派的“新感觉”,既是那时候刚刚萌发并且开花结果的“都市意识”,以致一时“洛阳纸贵”。
但上海委实太大了,一种抽象的概括,总面临着顾此失彼的风险。而所谓上海的现代性,也许本来也是一个寓意繁复、歧义更繁复的话题。面对这样的上海,我们或必须常易常新自己的眼耳鼻喉,或者也就是坚守、坚守再坚守。换句话说,所谓的海派特色,它飘在空中,但也就在脚下。所谓的上海精神,也就是你我他……
我写了四十多年了,要是从不成诗的阶段开始,可能近50年了。我也是受惠于上海作协,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相当于当年的“80后”,读书时就加入作协,那时候作品并不多,只有三十多首诗。而现在标准要高得多,这么多年诗歌的整个历程,我可以作为一个在场者或者是经历者,所经历的很多诗歌的运动、诗歌的争论、讨论都看在眼里。我自己写诗出于初心,就是热爱。四十多年过去了,也是经历过高潮期和低潮期,换句话说,因为我写诗时间太长了,所以蜜月期相对就较短,现在写诗,常常就像夫妻吵架,互相在压力很大的时候蹦词,词语呈弹跳状——对我个人来说甚至跟诗歌有一种内在的吵闹,很多争论,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样那样的争论,实际上有些也载入史册了,也可能有些只是对个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对于诗歌创作来说,这个环境空间、历史,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从自己的诗歌发展来说,或许是很重要的。
目前我出版了四本诗集,占我已出版的11本个人集中的一半不到,但我还是自认身份为诗人,因为——我不说理由了,理由已说了无数次,在心里,自己对自己——在自己不确认自己,自己也怀疑自己的时候,我就说自己真是个诗人。眼下我还在按照诗歌美学高大上的规则写诗,但我担心这样的作品,是否有人愿意用十目一行的慢速来读。在这么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这么做,是否有些逆潮流而动?是否有悖于努力奋斗的新世纪?此种阅读的要求,可能——非但不能表现出优雅人士的雍容闲适,反倒显出的是一种接近于嫉妒速度的疯狂——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象密度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心理机制的问题;所以,我总在夜深人静时,开始酝酿,就像我的微信名,只叫个:唯有夜晚可以读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