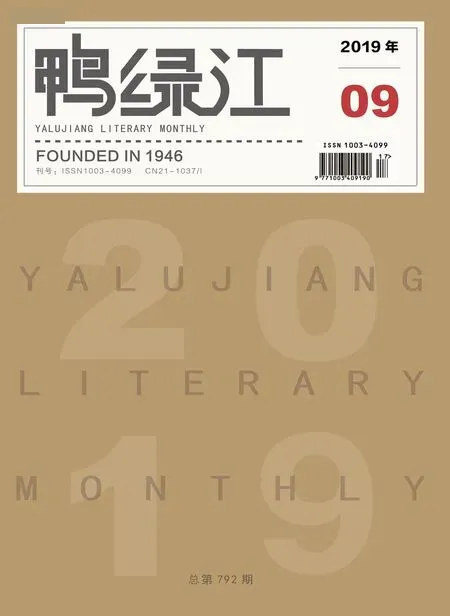“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谈李伶伶的小说创作
张立军
李伶伶用独特的坚毅诠释了其创作的短篇小说及微小说所具有的特殊的美学风格。她于2019年5月16日荣获了“全国自强模范荣誉称号”,靠着自己的毅力完成了二百多篇微型小说,出版了两部小说集。她凭借勤奋昭示了生命的光彩。她因病高度残疾,却用两根手指支撑起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她娇小柔弱,可她病弱的身躯下却掩藏着大千世界生存者们的百般图景。
庄子在《天道》篇中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庄子看来,淳朴素质、无为虚静才是万物的根本,是令人崇尚和尊重的,它的美无人与之相争。李伶伶的小说便隐含着这种具有本源性的“朴素”特质,她用质朴的言说来关照世界,介入生活,她运用那最为淳朴的笔触奠定了小说的基调,她小说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构成了中国乡村众生的日常生活。透过李伶伶拙质的叙述,中国东北质朴劳动人民的人生百味竟一览无余。
一
李伶伶善写爱情,特别是那种具有乡村况味的爱情,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对爱的执着与坚贞为爱情增添了锋芒和骨感。她的成名作《翠兰的爱情》便是最好一例,李伶伶只用一句单刀直入的“翠兰看上了村里的单身汉马成”,便将主动权和整个行为的主视角交给了一个叫翠兰的农村妇女。翠兰机敏、果敢,不被固有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她能够为了自己的幸福和爱情主动出击,甚至不惜以一种机巧疏离马成和桂芳之间的关系。尽管动用心机,但翠兰显得无比坦诚,“没过多久,翠兰听说桂芳和马成闹僵了,桂芳说马成心不诚,和别的女人不清不白。翠兰心里喜,可表面上却显得很焦急,她去找马成,问他传言是不是真的,桂芳是不是在说她,她可以跟桂芳解释清楚。马成说,不用解释,越解释越不清。”(《翠兰的爱情》)翠兰的爱情,缠绕了些许的理智和世俗逻辑,然而她的爱情观念又是那样简单纯朴,在她那里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和卿卿我我,她心里驻藏的只是纠缠了柴米油盐的自己“看上了”的人,为了这样一个人她可以委屈自己,也可以不顾代价去争夺,更可以无私地付出。
李伶伶在《素枝的春节》中也同样描写了这样一位追求爱情的素枝形象。不同之处在于素枝更加温婉含蓄。相比之下素枝所承担的责任要比翠兰多了很多,素枝扮演着乡村中妇女的多重面向,她既是要为小儿子操办婚事的母亲,也是进城打工的家庭保姆;她是无法照顾心爱孙子的奶奶,又是被孙子姥姥挤对的亲家;她更是自己故去丈夫家里的长媳。素枝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她要挣钱迎娶儿媳,要组织完成年夜的祭祖仪式。责备和误解从前夫家庭结构的根底里蔓延并常常伴随在素枝左右,素枝被重重的责任所裹挟,为此,她生活得并不轻松。然而,爱情,对素枝来说无疑是窒息水底时出现的一股清新空气,是寒风中萌长的一株新绿。它让素枝在外界的压抑环境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自我的存在。但事实上,她的爱情却在众多的社会责任夹缝中生长,仿佛其他的一切都重于素枝的爱情,为此,素枝之于长有之间的爱情是躲闪的、收敛的、压抑的。素枝只能把翠兰般的耿直掩藏起来,她对爱情的追求更多的是隐忍和避让,在她看来只有安顿好家里的一切才有自己爱情的空间,这种意识是一种愚忠,也是素枝性格中的一种执拗。
翠兰把自己的爱情与生活纠合在一起,把爱情变成了生活,在翠兰那里爱情与生活两者之间有了对等的关系,怎么也掰不开、辨不明。因而,素枝的生活永远压抑着自己的爱情,爱情只是她生活序列的一个小分子。然而,素枝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渴求与翠兰却是共通的,她们都有着乡村女性对爱情的最为质朴的殷切期盼。她们会因爱生妒,翠兰之于桂芳和素枝对夏莲的嫉妒是她们对自己假想敌的惩戒,不论是以实际行动设局破坏马成和桂芳的关系,还是以凭空的想象误解长有与夏莲,两人都是对自己爱情的追求和捍卫。她们的爱情并不是单纯的,它总是或多或少与生活纠缠在一起,爱情是素枝们生活的希望和动力,但却被生活牢牢地攥在手里,像掉进佛祖的手心,难以逃脱。这种爱情实际上是中国广大农村爱情关系的原生态,特别是在承载了太多的外在附加的观念、价值、责任的农村妇女身上,这种被捆绑的爱情才是最为真实和质朴的。李伶伶的小说,将中国乡村妇女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这种真实的爱情现状描绘得生动淋漓,在其间李伶伶向读者展现出了她们爱情观中的蒙昧与觉醒、主动与压抑、纯净与混沌等复杂的心理关系纠葛,爱情在桂芳们那里既是生活也是生存,更是她们解困压抑和疗救创伤的汤剂。她们的爱情离不开生活,结结实实地扎根于日常的各种琐碎之中,然而也正是这种并不单纯、并不理想化的爱情的存在,让桂芳们成了勇于言说、敢于成为自己的幸运儿,是爱情,让她们变得坚韧而倔强。
二
李伶伶小说的基调、结构都是以一种最为单纯的叙事方式展开的,她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认知置于其中,让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在平淡的叙述语言中自然地流淌。她的小说特别是微小说故事性强,冲突感鲜明,承接了最本真的中国式故事叙事模式。因果昭彰是中国故事叙事中的基本模式,它与中国佛经故事的善恶循环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就形式而言它结构单纯、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然而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容小觑,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这种因果故事一度承担着知识普及、价值观建构甚至民间信仰维系的重任,它是中国接受度最广、认可度最高的叙事模式。
李伶伶的微小说可以说正秉承了这种模式,因果循环式的故事表述方式被李伶伶运用得精当而纯熟,在《烟事》《一袋香水梨》中表现得极为鲜明。《一袋香水梨》仿佛借助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叙事逻辑,把人心的怨念演绎到了极致。赵先生因丢了一袋香水梨而怀疑自己的邻居,于是“剐破了对门的车”,而钱先生、孙女士又把这种找不到源头的怨愤发泄在了整个小区和其他住户的身上,邻里之间的争斗、动手、谩骂、互相毁坏财物被不断放大,而最终的恶果还是回落到了顺手牵走那袋“香水梨”的吴先生身上,结果吴先生的车被砸,于是他搬离了是非频仍的小区。她的《烟事》把因果关系定格于“陈平戒烟”,陈平合法伐木兼盗伐行为以及后来的没买到修缮牛棚的砖,均源自于伐木间隙没给羊倌递一支烟,这样一种看似巧合却又隐含着因果必然性的故事逻辑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而《一场车祸所改变的》因一场意外的车祸直接改变了四个人的命运,其中有生命的消亡、仕途的转轨、人生路径的改变,还有驱之不散的氤氲。
在这类因果关系维系下的故事中,李伶伶用巧合的方式组构了因果延展的必然性,如《一袋香水梨》般,故事发展看似以各种巧合事件连接,实际上却是被一种必然性逻辑所驱动。揭开巧合的面纱我们便不难发现,李伶伶通过一个个短小故事的表述为读者织就了一张张互相连接的因果关系网。故事冲突在连锁反应下表征出了哲理的意味,因此,李伶伶的微小说又像极了中国传统寓言故事。中国思想史上,素有老子庄子以小寓言写大哲理,《庄子》中曾记载了一则“相忘于江湖”的寓言故事,这是“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时,老子在反驳孔子“仁义”主张时所讲述的。面对孔子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极致的“仁义”关怀,老子给孔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内篇·大宗师》)这是两种境界截然不同的生存理念,生命个体之间“相忘于江湖”般自然的、适宜的生存状态显然要远远超过“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般的个体生命关怀。然而在真实的现实世界里,尤其是在春秋战争频繁的时代里,“相忘于江湖”成为被尘封的理想。李伶伶的《哲学家》就某种程度而言继承了这种具有中国传统况味的哲理寓言的神韵。哲学家以理服人拯救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并因此而平息雪城和雨城之间的战争,却又因自身声名大振而引发了新的战争和惨剧,这其中深深地隐含了“为”与“不为”之间的悖论。这与“相忘于江湖”还是“相濡以沫”竟有几分神似。
也正是由此,李伶伶小说的结尾总是那么耐人寻味,其中总有一种对世道人心、天理昭彰的启示。《云空和尚》的结尾既荒诞又具有宿命性,老马为了家庭、为了儿子上学,把自己一步步推向了与家庭分裂的地步,究竟是家庭推开了老马,还是老马远离了自己的家庭,唯有云空和尚的不断摇头和老马如梦如幻的偈语才能深晓其中的深意。而《火山即将喷发》中陈博士和助理为了避免火山爆发的严重后果,采取了各种极端方式引走村民。他们冒充绑匪绑架镇长的孩子,却发现镇长的功绩和村民的爱戴都是报纸上伪造出来的,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于是胁迫不成索性利诱,然而利诱也并不能满足大部分人的欲望,“可是第二天,陈博士得到的消息跟他想的完全相反,几乎整个平镇的人都被埋在了火山的熔岩里。陈博士万分惊讶,说,不是都出来了吗,怎么被埋的?方镇人说,平镇人不遵守协议,他们买完金子后,趁天黑,又悄悄溜回了平镇。”(《火山即将喷发》)而活下来的只有睡着的老人和不忍叫醒他的儿子。结尾处,人的利益之心、父贤子孝等与生命的关系被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一场车祸所改变的》更从结尾处,把车祸所改变的关涉人的命运指向了一连串的悲剧,这便昭示了在不仁之行下没有赢家,经营好自己的良心才是人的生存之道。
三
李伶伶小说具有极强的社会参与度和干预性,可以说小说是李伶伶关照世界,介入生活的重要方式和媒介。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强调“文以载道”,特别是注重文艺对于社会和世道人心的教化功能,在李伶伶的微小说和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这种匡正扭曲价值观念、承载社会道德良知的责任感的存在。在《羊事》中,谷雨以他近乎执着的忠厚憨实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为了让第三只小羊羔活下来,谷雨把它送给了邻居冬至,而冬至却因为父亲生病,从第二天开始就把小羊羔寄养在谷雨的家里,谷雨精心为朋友照看小羊羔,不计成本,一直把它喂大。于是,羊的归属权成了一个困扰所有人的问题:在谷雨的心里,它可是冬至的羊,一切由冬至处置;而在冬至看来,自己没有尽到一天饲养的义务,羊理应归冬至所有。故事虽然在“羊事”间游走,却一直在呈现人事,兄弟情义、邻里关系、为人诚信等在此间竟一一得到展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兔事》中清明相对自私的为人处世方式。他喜欢撵野兔,也是撵兔子的好手,可是有几次“清明把野兔从山上撵到了村里,跑到别人家院子里,清明都是拿上兔子就走,没有邀请他们一起吃兔肉。清明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是村里人都觉得清明这人有点问题。”(《乡村兔事》)显然,清明在邻里关系上显得漠然,他的身上全无那种互助互惠的处世之道,于是,在庄稼干旱的时节里家家户户都忙着浇地,可偏偏没有人愿意把自家的井借给清明使用。后来,清明吃一堑长一智,而读者也同样从中受到了教益。
在世俗变迁的境况下,各种诱惑因素腐蚀并且变异了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对利益的追逐,对现状的不满,致使人们失掉了本应负载的家庭责任以及对爱情的坚贞,追求更具表象性的快适,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解脱自我,释放焦虑的一种途径。然而,李伶伶小说中的爱情观却显得传统而保守,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对变异的爱情观的抵御和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守持。《我们都是陈世美》以一种无厘头的方式描述了一个陈世美的角色成为男人外遇的谶语,看似偶然但却又充满了命定,男人周围的朋友们和外在环境成为松动男人家庭观念的重要因素,而禁果尝遍后,留给男人的只有懊悔和遗憾。如果说“陈世美”是一种背叛的无可挽回,那么《马哈的恋爱史》中的马哈则可以被称为“浪子回头”,他对柳梅的同情转变成一种异样的恋情,而生活中菊英的硬朗和柳梅的温婉让马哈心生畏惧,于是马哈和柳梅生出了私奔的举动。柳梅儿子的出现是对马哈的“当头棒喝”,一时间,家庭、责任、生活五味杂陈,它们召唤回了马哈远走高飞的心。于是,“马哈后来没再跟菊英吵过架,也不轻易跟别人发生争执。人们都觉得马哈像换了个人,说他是浪子回头,是幡然悔悟,是知错就改。马哈知道这些都不是,是因为他心里有了爱。”(《马哈的恋爱史》)《将离婚进行到底》中张平受不了腊月的脾气而在很久之前就萌生了离婚的念头,腊月对他帮助雪梅的误解更加剧了张平的家庭矛盾,然而雪梅的世俗却令张平失望不堪,于是回归家庭成了张平最好的结局。
李伶伶的爱情观或是家庭观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承袭,它所负载的家庭责任和奉献精神要多于家庭成员中各自对彼此的索取,这是千百年来维系中国式家庭的重要纽带和力量。然而,李伶伶的小说对传统的尊崇却并非顽固和陈腐,她有着求变的一面,也有着应对时局变迁时自我的叩问和思考。在她的近作《不肯妥协》中,她把家庭矛盾与社会责任和心理问题勾连在了一起,通过短篇小说的篇幅扩展了她以往所创作的微小说的容量和涵纳度,这无疑是她自身创作道路的新拓展,也是她对自身不断追问的社会问题、家庭关系问题等的新思考的具体呈现。梨花与徐文之间的“冷战”因梨花坚持把五妹的孩子“小埋汰鬼”朱云飞接到家里住而引发了徐文的不适,梨花想让妹妹的孩子能得到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以此来弥补自己心里对五妹的亏欠,而徐文不喜欢一个不讲卫生的孩子,他也无法理解梨花。于是夫妻之间的“冷战”在徐文的父母之间,在梨花和徐文的心理以及各自的原生家庭间辗转腾挪,而徐文和梨花在冲突中又相互克制,希望把对彼此的伤害和对家庭的消极影响压缩到最小。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无论从叙述方式还是问题关注的视角看,都是李伶伶新的拓展和自我的突破。她的《素枝的春节》对农村新女性的塑造更是这种求变思想的一种侧影。
总体而言,李伶伶关注乡村,关注女性,关注家庭伦理,她的小说承袭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她采用最为质朴的方式展开言说,将自己对生存与死亡、行善与为恶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融入其中。她的叙述模式平实,却并不妨害丰富性在小说中的滋长。她通过艺术真实来描摹乡村图景,人生百况在她的小说中具有了隐喻性的彰显。她的小说有时候更像寓言,赋予小说一种人伦价值观念的指向,于是她的小说看似体量不大却具有了追问人生、直通灵魂的效果。所以,李伶伶的文字是生命的律动,字里行间充满了力量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