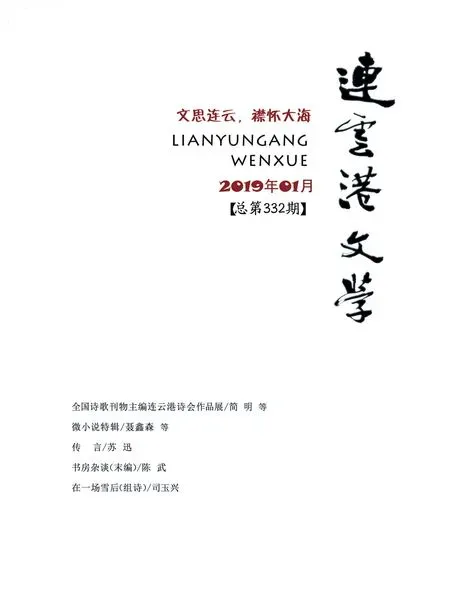清贫的味道
佳虹
今天是母亲九十岁寿辰,除了生病的大姐,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又聚齐在老妈妈的身边,两个姐姐准备了一大桌好吃的。但是,老年痴呆症让老妈妈已经辨不清鸡鱼肉蛋。
三年前,母亲思维尚好,常对我们讲起大饥荒那年头,她和父亲带着我年幼的哥哥和两个刚会走路的姐姐以及尚未出嫁的三姑和四姑,与饥饿抗争的往事。母亲说春荒是最残忍的,家里经常没有米下锅,一家人连那照人影子的稀饭也上顿不接下顿,疲惫的母亲拿起镰刀到门前大水塘边把那棵老榆树皮一点点刮下来,捣碎了放进石磨里磨成“面粉”做成稀饭让家人糊口。熬到野菜返青燕子呢喃的日子,母亲又用清水煮榆树叶和野菜让家人充饥。老父亲晚年时常对我们讲母亲年轻时,无论是刮榆树皮还是挖野菜都眼尖手快,让家人少受了不少饥饿之苦。我记事起印象中老家庄子上的老老少少经常吃不饱肚子,母亲多数时间都在为全家人的吃穿犯愁。记得那难以下咽的酸浆稀饭总让我望而生畏,母亲却变戏法似的偶尔在那讨厌的稀饭里放上少许的米粒,有时还丢进一小把黄豆,我们几个孩子为了那几粒米或一两颗黄豆,便一口气喝下两三碗酸浆稀饭,肚子被撑得像个皮球,嚼着难得的几粒米或一两颗豆,那份幸福和满足一直持续好多天。
山芋是我儿时记忆中的主粮,母亲每天都在酸浆稀饭里下半篮子山芋让人与猪同吃,我和弟弟面对那大锅煮山芋经常“绝食”,母亲便特意在灶膛的火灰中埋三四个山芋,这灶膛烧山芋是母亲专为我和弟弟开的小灶,记得母亲在大锅饭熟了之后,用那根细长的烧火棍,从灶膛的热灰里扒出焦黑的山芋,麻利地将其拨弄到灶膛口等它们的温度退去一点,急急地用指尖捏起热乎乎山芋两手反复拍打几下,对着那烫手的山芋不停地吹气,让它尽快散热,直到温度适宜时,才递到我俩手里,叮嘱我和弟弟:“小口咬,别烫着……”当年,我虽然揣测不清母亲心底被清贫覆盖着的怜子之情有多深厚,但是那烧烤的山芋的香味至今仍在我的血脉里温暖着我的人生。
轮椅上的老母亲,满头白发不知哪天稀疏得让儿女们看了就生出心疼的感觉,三姐姐为老妈妈穿上新买的紫红的夹袄,母亲平静的脸上映着浅浅的红色的光晕,那份安详与静好,让我无法联想到她年轻时竟吃过那么多辛苦,受过那么多磨难。
我贴近母亲耳边,逗她:“妈妈,灶膛里的山芋烧熟了吗?”她竟笑着应答:“烧熟了,快吃吧,小口咬,别烫着!”这清晰的话语里,满满的都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疼与爱!老妈妈这一辈子历经风雨,想一想平日里我对她的照顾和侍奉的时间太少,心里一酸,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姐姐问我是否记得小时候,老妈妈把大山芋切成玉米粒一样大的山芋丁,再拌上同样大小的萝卜丁和南瓜丁,然后象征性地加一小碗米,做一大锅“杂花粥”,我们几个孩子围着那黑乎乎的土灶台又蹦又跳地等着母亲揭开锅盖,而母亲总是等我们都吃饱了才拿起碗去盛饭……我说,一辈子也不会忘的。
这顿围着母亲而团聚的中饭,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都顺着母亲的思路和她说过去的那些往事,这才是母亲最开心的话题。三姐帮轮椅上的老妈妈梳理着头发,我看一眼她那塌陷的眼窝,下垂的眼睑,满是老年斑的清瘦而平静的神情,我一面感慨九十年风雨岁月的沧桑与无情,一面感动那些清贫的岁月打磨出母亲骨子里的坚强与不屈。
母亲虽已进入鲐背之年,可她仍然不会忘记清贫岁月里养儿育女的苦与乐,一个中午她总是反复自言自语地说:“过去太穷了,没法子让你们几个吃饱呀!”不知是感动还是担心母亲的健康,六十七岁的老大哥抚着母亲的双手,眼眶潮湿了好几次。
两个姐姐心疼地说,老妈妈的勤劳和手巧是我们的幸福之源。是的,清贫的岁月里母亲能把不起眼的山芋做出好多样让我们喜欢吃的饭食,尤其是那山芋干面水饼沾猪油渗到骨子里的那份香,萝卜烩粉条做汤底贴山芋干面锅饼咸中带甜的滋味,葱姜炒山芋干面饼诱人的口感……为了节省粮食母亲把黑乎乎的山芋干面粉用热水搅拌均匀加些葱油和盐,做成美味的黑“馅子”包进小麦面饼中间,母亲的聪明在于这让孩子们既有饼吃又省下主粮来细水长流。
五十出头的弟弟靠近老母亲的轮椅,笑着说,老妈妈做的“炒老粉”,我想起来就流口水呀。我接着弟弟的话茬说,那“炒老粉”有两种口味,一种甜的,是把凉透的老粉切成片加上盐猪油红糖炒得热乎乎油晃晃的,入口甜又爽滑,那咸的就是把老粉切成片加上盐和猪油、葱姜、香菜等炒到外表焦黄,吃起来油而不腻,淡淡的香辣中有令人兴奋的肉的味道。母亲半闭着眼在认真地听,脸上挂满了微笑。
三姐姐拍拍老母亲的肩膀说:“老妈妈你当年做的那些过冬的小菜,才是我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呢!”母亲依旧微微闭着眼,问三姐说的是腌腊菜、腌茶豆丝,还是梅干菜、萝卜干呢?我说肯定是您做的冬瓜酱豆呀!老妈妈努力睁开眼,不停地微笑,浑浊的目光缓缓扫过儿女们的脸,似乎沉浸在当年的情景中:秋末冬初,苦霜把娇嫩的绿叶和茂盛的藤蔓抹上橘黄的颜色,母亲在父亲的协助下把沟边上几十斤重的大冬瓜抬进院子里,洗净削皮后切成长方形的条块状,每片长大约六七厘米,宽三四厘米左右,厚度五毫米上下,分层撒上些盐放在大木桶里。之前,母亲把七千克黄豆洗净煮熟,用外祖父手编的蒲包装好封上口放在灶膛里焐着,等黄豆发酵到最佳状态时,从灶膛取出来倒进大坛子里,用凉开水加盐和酱油以及姜葱之类的农家调料混合在一起,把木桶里的冬瓜片倒进来搅拌均匀,拿一只盘子或大黑碗盖住坛口,抓几把黄泥封上坛口,大约过上两三个星期,扒开坛口上的黄泥,香喷喷的冬瓜酱豆就可以吃了。那冬瓜片呈透明的鹅黄色,夹一片咬上一点儿再喝一口玉米稀饭或山芋之类的农家饭,真是一种美味!那酱过的黄豆,饱满圆润光亮亮的像秋天里熟透的柿子一样黄里带点儿红色,丢一颗在嘴里,清香微辣中透着淡淡的甜味,清晰的酱香中带着甘醇的味道,从舌尖延伸到心底,化作脸庞上漾起的幸福的涟漪。
从母亲的笑容里,我可以断定那些随时光远去的千事万物里,唯有这清贫的味道正逆向归来,让母亲的晚年快乐而幸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