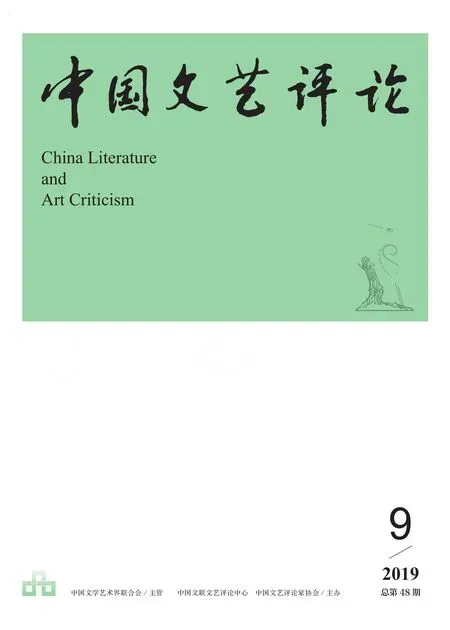中日当代文艺对城市化进程的书写探析
——以城乡冲突为中心
张文颖
引言
“城市化”一词是典型的工业文明词汇,但“城市”一词在汉语中很早就已经出现。过去的“城市”具有行政和商业两重含义,“城”最初指城墙,而“市”指集市。虽然古代就有了城市,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近代的一个概念,人的物化与商品符号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表征。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城市化进程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社会变迁十分敏感的文学艺术家们,率先通过他们的笔创作描绘了以城市化进程为主题的作品。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单一化趋势下,反而可能诞生更多充满矛盾性的、暧昧的,以及更有启发性的东西。对于文艺作品而言,城市化指代一个大背景,但这一背景在文艺作品中并不会一直维持尖锐对立的冲突。2000年左右的中国,现代化与乡土味之间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势态,并构成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基本行为依据,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巧珍让我们意识到了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差别之大。但随着城市化的加深,这种差别可能会越来越小;这种矛盾冲突可能会深藏于人物的心灵内部,变得更日常化,同时,也慢慢沉淀为人的基本特性,而不是突发的某些品质。
日本的城市化步伐比中国要早一些,二战后随着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推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再到后来田中角荣的列岛改造计划,日本的城市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逐步达到了一个顶峰。京滨工业地带、阪神工业地带、中京工业地带等工业带的形成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到城市就业。20世纪70年代,随着服务业就职比例的增加,所谓的工薪阶层日渐增多,到2010年日本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都集中在城市。在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生活也是伴随着矛盾、冲突和阵痛的,乡下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对土地的眷恋以及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绝望构成了诸多无奈的人生图景。日本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刻画和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各色人物以及他们的多彩人生,并呈现出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世间百态。
关于城市化袭来的“温柔”书写
随着城市化浪潮趋于柔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阵痛也早已被许多人忘记。但铁凝塑造的“香雪”这个人物形象将永远被铭记。
《哦,香雪》(1982年)是一篇抒情意味浓厚的短篇小说,也是铁凝的成名作。小说以北方小山村台儿沟为背景,叙写了每天只停留一分钟的火车给一向宁静的山村生活带来的波澜。作者通过纯真美丽的香雪们对这种实则猛烈的波澜进行了“温柔”的描述。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的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然而,两根纤细、闪亮地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的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粱,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这部作品一般被当作抒情作品来读,但如果细细品味的话会发现,它其实是为即将被城市化侵袭的乡村唱起的一曲哀婉动听的挽歌。道路是迈向城市化的第一步,也是最坚实的一步,通过铁路人们可以接触到外面的大千世界。
火车原本是不在台儿沟村停留的,因为这里太贫瘠了,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但不知什么原因列车破例在这里停留一分钟。就是这宝贵的一分钟,让小村庄有了和外部接触的机会,给这个小村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好奇心让村子里的女孩子们率先捕捉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她们开始向外部展示自我,她们人生中第一次有了成为主角的机会。
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从前,台儿沟人历来都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于是,台儿沟那一小片石头房子在同一时刻忽然完全静止了,静的那样深沉、真切,好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自己的虔诚。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的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
时间和空间比以前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过去一天天在单调中被打发,现在一天中短暂的一分钟都好像有着难以估量的沉甸甸的分量。火车旁这个狭小空间在这短暂的一分钟里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
姑娘们对火车的恐惧感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开始观察和接近这个陌生而又新鲜的东西了。她们观察到坐在火车里面的乘客穿着打扮比她们时髦得多,他们使用的东西,手表、水果刀、发卡等,都是村里没见过的。香雪最关心的是皮书包、文具盒等文具类用品。火车带来了物质文明与商机,闭塞的空间被打破,渐渐地姑娘们有了淳朴的商业意识:
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她们踮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香皂。有时,有人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
商业理念开始形成了,讨价还价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香雪们对物质的价值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香雪是村里唯一一名中学生。因台儿沟没有学校,香雪每天上学要到15里以外的公社去上学。在公社学校里,香雪体会到了强烈的地域差别,尽管这里并不是城市,但对乡下人的歧视已经很明显了。在学校里她处处能感受到其他同学的傲慢和无礼。她也想拥有和她同桌一样的可以自动合上的文具盒。她开始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明白了贫穷是件丢人的事情。摆脱贫困在潜意识中成了她未来奋斗的目标。
天渐渐冷了,火车仿佛开始冷落香雪们了,车窗紧闭,香雪们变得可有可无了。一年四季,火车给香雪们展示的是不同的面孔,让香雪们品尝到了人世间的冷暖。就在这时,香雪透过车窗发现了她梦寐以求的文具盒,被文具盒吸引着,她平生第一次踏上了火车这个庞然大物,和它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在她讨价还价时,由于太过于投入,以至于忘记下火车了,火车载着这个陌生却又熟悉的乘客开动了。
在这里香雪经历了空间的变幻,她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空间,在这里她用40个鸡蛋跟城里大学生换回来了宝贝文具盒。文具盒代表着乡下人对城里生活的向往,火车就是缩短城乡差距的快捷工具,香雪与火车的亲密接触圆满成功了。在下一站下车后,她开始害怕了。由一个陌生空间来到了另一个陌生空间,30里的回家路让她感觉是那么的遥远,但因为有了这个文具盒她忽然什么都不怕了,她又有了无穷的力量,这是物质文明带来的力量,仿佛占有物质就等于占有了一切。
故事的结尾,村里的其他姑娘们沿着铁轨来迎接她的归来,“她忽然觉得心头一紧,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起来,那是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她用手背抹净眼泪,拿下插在辫子里的那根草棍儿,然后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从故事结尾我们可以看到,物质的力量并不是无限大的。香雪沿着铁轨孤独地朝着村庄的方向走着,她的心里装满了不安和恐惧。但当她看到了其他姑娘们来接她,顿时又兴奋无比。善良淳朴的美好心灵打动了香雪,也打动了我们。然而这种美好和纯真还能维持多久?我们不得而知。经历了城市化洗礼的香雪,很大的可能性会认同和臣服于城市规则,并积极成为一个城里人,这是许多乡下人的必经之路。香雪应该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依然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她不被物质所腐蚀,依然保持纯真和美好。
哦,香雪!你现在还好吗?
这是对于城市化浪潮入侵最为经典且柔美的描述。中国当代文学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书写中经常会出现纯真美丽贤淑的农村女性形象。纯洁、贤淑和包容代表了乡土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日本近现代文学对于城市化的描写也有其温柔的一面,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可以看作是城里人去乡下寻求重生的故事。乡村人的淳朴善良打动了来自城里的主人公。乡下俨然成了城里人的再生之处。而《雪国》描述的是经历了城市化洗礼后的乡村女孩对于城市的向往、困惑和无奈。
中国当代文学对待城市化浪潮一开始并没有充满极高的警惕性,相反是主动迎合的。因为人们贫穷和落后的时间太久了,普通民众对于富裕的向往超乎想象。因此这部作品明显对于城市化的威力和负面效应估计不足。
城市化进程中的伤痛书写
如果说铁凝的《哦,香雪》描写的是城市文明刚刚闯进乡村时产生的相对柔和的震荡的话,日本当代作家立松和平的作品《远雷》(1980年)描写的则是城市文明彻底侵占乡村后给乡村带来的巨变。原本靠土地生活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突然间被剥夺了,在原来的土地上拔地而起的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住宅楼;在原来的田埂上突然冒出来的是一座座工厂和酒吧。没了土地的人们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土地可以生金子,人却因金子而乱了性,家庭因为金子而散了架。没了土地心里就没了着落的人们陷入到极大的迷茫中。
主人公满夫就是这样一个因失去土地而陷入困惑和迷茫的郊区年轻人,他憎恨家附近那些高楼和居住在高楼里的人们,憎恨带有城市味道的一切东西。该作品以郊外为舞台上演了一场终极土地保卫战。
从塑料大棚的缝隙挤进来几张脸。她们好像没有注意到躲在阴凉处的满夫。透过塑料布看到三个女人在翘脚往里看。
干啥呢,有事吗?
因为充满怒气的声音从意想不到的地方传过来,女人们吓了一大跳。满夫慢慢地从阴凉处走过来。加上他上身赤裸,让三个城市女人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下。满夫每走一步从他的沾满泥土的皮靴里传出扑哧扑哧的漏气声。
满夫对这些小区里来的人们充满了敌意,因为正是以她们为代表的城里人搅乱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的家庭稳定,让他的父亲带着出卖土地得到的300万日元离开了家,跟一个酒吧女郎混在了一起。他在仅剩下来的一块土地上盖了一个塑料大棚,种起了西红柿。只有在这块土地上他才能和土地连接在一起,就像鱼儿又回到了水里,充满了活力。虽然这个塑料大棚不过是乡村土地的替代品而已。
从塑料大棚的缝隙能够看到小区楼群,由钢筋混凝土建成的新的建筑物足有30栋,整齐地排列着。不知里面住着多少人,小区楼群的噪音顺着风吵吵嚷嚷地飘了过来。
城市空间在这里逐渐形成,楼区、小超市、酒吧、饭店,这些城市元素彻底改变了过去以土地为核心的空间结构。而与城市空间格格不入的塑料大棚预示着这场土地保卫战注定将惨烈而悲壮。
这个西红柿塑料大棚建在满夫家靠卖地得来的钱新盖好的大房子旁边,他家和周围邻居们都靠卖地成了暴发户,有了钱,许多人开始走向堕落。
满夫的好友广次跟满夫一样,从小和土地在一起,可以说两人之前的人生轨迹是一样的,卖了土地之后,广次和满夫的母亲一样在工地上干活。但广次却鬼使神差地和一个有夫之妇酒吧女郎好上了,后来竟然拿着家里卖地的钱和那个女人私奔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从家里拿走的钱花光后,两个人开始互相埋怨,最终发生了血案,广次成了杀人犯。
没有这个可恶的小区就好了!都怪他们,他们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满夫)
也许是吧,可你卖了地,拿了人家的钱了啊。(广次)
满夫因为有人介绍对象恰巧遇到了他喜欢的姑娘绫子,假如身边没有绫子,没有拴住他心里的那块土地他不知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也许他会和广次一样成为杀人犯。满夫的祖母在这部作品中以一个有些老年痴呆症状的老太婆形象出现,嘴里说出的话却非常有深意,她看不惯眼前的一切,她嘴里讲的都是过去农村发生的事情,或农村人认的理儿。
我刚嫁过来那会儿,田地被水淹,变成了白花花的沙石地,你知道怎么一点点回复土色的吗?当时田里根本没有杂草,我和你爷爷到深山里砍柴拾叶子,背着满满一箩筐,压得我蜷缩着,这样坚持好多天,后来又把沙石地里的石子拣出来扔掉。这样才长出了杂草,有了杂草才能种水稻。那是我们俩一点点让沙石地变成绿洲的!
可以说祖母就是乡土的象征。但她确实老了,老得大家都无视她的存在,每当有节庆活动时都会把她关到仓库里,免得碍事。这也预示着乡土的没落。
在小说的结尾,满夫迎来了他自己大喜的日子,但他实在高兴不起来,好友入狱、父亲再次离家不归、祖母衰老、塑料大棚还能不能维持下去、西红柿销售情况将来会怎样,这一切都是未知数。都市化的雷声由远及近、步步紧逼,他该何去何从?
这部作品以立松和平的故乡栃木县宇都宫市的郊外为背景,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城市化的到来给普通家庭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从而也引发了人性的变化。
郊区比邻城市,是城市化进程中受到冲击最大最惨烈的地区。该作品直观深入地描写了城市化的狂暴,在它面前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那么渺小和不堪一击。主人公的反抗给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滑稽感,但正因如此才使得他的抵抗弥足珍贵。
关于城市化进程的伤痛书写,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路遥的《人生》。路遥写出了中国的那个时代城乡巨变带来的震动。《哦,香雪!》中的香雪对城市充满憧憬,但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进入到城市,并接受城市的洗礼。而《人生》中的高加林则不同,他积极尝试着进入城市,但最终却惨败而归。
作为一个陕北农民作家,路遥和立松和平一样十分关注城乡交叉地带人们的生活,特别是重点关注了生活在那里的农村青年。不同的是,路遥作品中的农村青年对于城市充满了憧憬与期待,并积极采取行动奔向城市的怀抱。在路遥的 “城乡交叉地带”文学叙事中,往往有一个城乡临界点。在他的小说《人生》中,多次出现 “大马河桥”,而 “大马河桥”正处于这个临界点上,桥的两端分别连接着主人公高加林活动过程的城市和乡村。
“大马河桥”处于城乡结合部,一头连接着城市现代文明,另一头连接着农村传统文明。尽管从高家村到县城只有十来里路,但是巨大的城乡差别显露无遗。高家村和县城分别代表了 “城乡交叉地带”的两个面,农村与城市的两个文明空间。在这里资本还未涌入,农村空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不堪一击,而是顽强地与城市空间对抗着。
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的改变直接导致了人们心理的改变。资本的涌入让《远雷》中乡村最主要的土地空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耸林立的住宅楼;田间小径摇身一变成为灯红酒绿的酒吧。这些诱人的夜灯让原本安分守己的乡下人不安分了。
中国的都市化也催生了许多暴发户,他们在享受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富庶的同时,也会因巨额财富来得太容易、太突然而不知所措。一夜暴富使得他们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模式出现了失衡,面对巨额财富的诱惑和冲击,其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容易走向极端,直接导致的社会问题和《远雷》中类似,具体表现在家庭矛盾和个人的扭曲生活。例如,争财产、赌博、斗奢、吸毒、玩刺激、兄弟反目成仇等。令人好奇的是不知这些暴发户们是否会像满夫一样因失去土地而伤痛不已,怀念过去的土地,或是已经被改造成了彻头彻尾的都市人?
香雪们是否也经历了失去土地的痛苦,我们不得而知。但城市化浪潮席卷过程中一定夹杂着困惑、迷茫、痛苦和抗争。
逆向城市化进程书写
《哦,香雪》描述了城市文明的闯入以及乡土文明对城市文明的膜拜与反思;《远雷》描述了土地丧失者对城市文明的憎恶和无奈。还有些作品描写了在城市里无法找到自我而毅然决然逃离城市的故事。
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书写一般经常出现在小说或诗歌世界里。但日本动漫作品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触及了这个主题。其中有一位动漫大师不应被忘记,他就是高畑勋。
高畑勋的《岁月的童话》于1991年公开上映,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东京,27岁的公司职员妙子过着忙忙碌碌、普普通通的都市生活,但她从小一直抱有体验乡村生活的梦想。幸而姐夫的老家在乡下,她终于圆了体验乡下生活的梦想。她从公司请了10天假,前往姐夫家所在的山形县乡村度假。一路上她回忆起了自己小学五年级时的种种往事。
故事就是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展开的。火车成为了承载她记忆和现实的重要载体。在这里火车不是《哦,香雪!》中突然闯入乡村的象征城市化进程的庞然大物,而是承载着记忆,带着主人公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的象征。主人公妙子坐在开往乡村的火车上,时不时被过去的记忆打扰着,而这些记忆主要集中在小学五年级。
小学五年级正是一个人记忆十分活跃的年龄段,同时也是女孩子成长过程中由儿童向成人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间段留给孩子们的大多都是美好的记忆。那是个可以自由做梦的年龄段,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人世界的烦恼就会越来越多,工作压力、婚姻压力等就会一股脑地袭来。因此,妙子不时地回忆起小学五年级那段美好时光。
细细品味一下作品中关于妙子小学五年级的记忆会发现,这些记忆本身并不美好,反而是充满压抑感和苦涩的。数学成绩差会被周围人嘲笑;男孩的主动示爱要被集体围观;永远只能穿姐姐们剩下的衣服;难得的爱好被家长无情扼杀;发个小脾气还会挨打等。这些关于童年的记忆正如主人公第一次吃到味道平淡且有些苦涩的菠萝一样,外表和气味都很美好,而真正品尝到的满是苦涩。成长总是伴随着苦涩的,而回味永远是甘甜的,这个道理只有当一个人长大了才会明白。
妙子小学五年级时,正值日本经济刚刚步入高速增长期,日本现代化浪潮不断高涨,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物质开始极大地丰富起来。而那时的人们尽情享受着物质带来的幸福感。
那时周围有乡下亲戚的同学在假期都纷纷去乡下过假期,而妙子却只能去都市热海的温泉旅馆泡泡温泉。这让她对乡下的憧憬和向往与日俱增。物质的极大丰富并没有带来心灵的充盈,长大后,都市里有形无形的各种压力压得她有些透不过气来。所以她自从有了姐夫老家这个乡下度假地后,如获至宝,每年都要去住上几天。这次是第二次体验乡村生活了,可这次度假不同以往,她需要真正做出改变。因为28岁,她已经不再年轻了。
这次回乡下前来迎接她的是一名农村青年敏雄。敏雄虽然比妙子小两岁,但显得老成稳重,两人也很能聊得来。和往年一样,妙子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临时过客,享受着短暂且惬意的乡下生活。在田间尽情挥洒汗水、在乡间欣赏城里见不到的纯天然美景,在这里不需要小心翼翼地看别人脸色,也没有令人窒息的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一切都让妙子感觉十分美好。此时,在妙子大脑里逃离城市的想法还没有形成,她依然把自己看成个局外人,但10岁时的记忆不停地闯入,让妙子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记忆成了催促她做出改变的催化剂。
成长充满了尴尬和不堪回首,女孩子来月经成为了那个时候十分尴尬的事情,同时也成为了童年记忆中苦涩部分的象征。踏入社会后的妙子表面上整天没心没肺、快快乐乐,其实她只是想尽情地舞动自己那双翅膀而已,至于这些舞动具体有何意义,她从未去思考过。28岁单身未婚成了成年后的她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尴尬。
与稳重老成的青年敏雄的相遇成了这次旅行中的最大收获。妙子这次度假最主要的目的是来采摘红花,而敏雄说红花对于当地人来讲只不过是农作物的一种,并没有什么稀奇的,而且快绝种了。过去从事摘花作业的女人们一辈子也没有机会涂一涂红花,言外之意只有外人才会关注这个东西,他把妙子自然而然地看成了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
在两人聊天过程中妙子说现在把工作当做生存价值的人越来越少了,敏雄马上问道:妙子小姐您呢?妙子说我也这样认为,但同时强调她并不讨厌自己的工作。对于妙子的回答,敏雄谈起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他喜欢从事农业这个工作,因为可以培育生命。其实他不久以前也是个公司职员,在一个朋友的劝说下放弃了原来城里不错的工作,开始进入到有机农业这个行业。所以可以说敏雄是日本战后第一代重回乡土的青年农民。其实敏雄小的时候曾十分向往去东京,但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这和妙子儿时对于乡村的向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进城市,造成农村人员大量减少、乡村凋敝。农业的衰微引起了有识人士的警醒,这才有了后来的热血青年回乡发展有机农业的契机。高畑勋正是关注了返乡这一主题,通过这部作品引发人们对于生存价值、都市和农村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这部动漫作品中虽然也描写了都市和乡村的对立,但与《远雷》相比十分含蓄,而且乡村人也没有了对城里人的排斥与羡慕。他们自给自足、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足。相反城里人却越发变得空虚和不自信,他们失去了自我认同的根基。
敏雄虽然年龄比妙子小两岁,但他的成熟、乐观让妙子十分羡慕,转眼妙子的度假就要结束了,作品的高潮部分出现了。乡下的奶奶不舍得妙子离开,说出了一个让妙子为难的提议——嫁给敏雄,做个乡下媳妇。这个看似唐突的提议实际暗示了奶奶已经没把她看成局外人,她开始被乡下人认可了。妙子一下子心绪烦乱,逃了出来。她开始反省自己对于乡村生活的轻率的态度,觉得对不住乡下人对自己的信任。这时儿时的记忆又不约而至。
那时她的同桌是个新转来的脏兮兮的小男孩。因家里穷,加上行为举止粗俗不堪,而被大家歧视。在班里他没有一个朋友,大家都同情妙子跟他同桌。可妙子却装作高尚,违心地说她不在乎。直到有一天这个同桌要转学了,临走时和同学们一一握手,唯独没有跟妙子握手,而且还对妙子说,我才不会跟你握手呢。这让妙子很意外和受伤。她内心最嫌同桌手脏,表面却装作自己最善良,实际上最虚伪。妙子心里明白她的虚伪同桌很清楚,所以坚决不跟她握手。这次的乡下之旅本身也是一个不敢面对现实的虚伪的作秀之旅、自私的表演之旅。她对自己的虚伪痛恨不已。这时再次与敏雄相遇,他帮助妙子解开了这个心结。敏雄告诉她正因为同桌喜欢你,不想分开,才不和你握手的。一个小男孩越是喜欢一个女生就越会在她面前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随着这个心结的打开她终于可以开始真实面对自己内心,而不用逃避了。影片的最后,她坐上了开往都市的火车,但很快在下一站的时候,她下车了,重新返回到了那个小村庄。
日本当代文学中的返乡主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城市化进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以外,与2011年发生的311东日本大地震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日本大地震中核电站事故让灾区重建困难重重,同时更加激发了灾区人民的凝聚力,尽管有许多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但依然有人重返故乡,想要通过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311后日本文坛以及影视界创作出了许多与311相关的作品,后福岛时代的日本文学(日本电影)这一课题也备受关注。
电影《家路》(2014)就是其中的精品。311和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之后,千百万人的生活被彻底改变。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人被迫搬离,他们远离了熟悉的土地,心中惶恐不安。回家对于一个有家的人来说是一件十分普通平常的事,而对于影片中的家庭来说确是无比艰难。311前一直在家务农的大儿子总一丢掉了从祖先手中继承来的土地,只会干农活的他手足无措,在陌生的环境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妻子美佐暂时找了一份短期兼职,勉强维持生活,夫妻俩的心渐行渐远。总一终日闷闷不乐,慨叹上苍的不公。
不久,总一得知在外飘荡多年的弟弟次郎突然返乡的消息。次郎无所顾忌闯入隔离区,在原本自家的土地上耕作。总一对此心中有着复杂的情感,而次郎则向哥哥宣布了“想要重新再来一次”的决定。在此之后,次郎来到临时住所见到母亲登美子,一家人总算团聚,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第二天,次郎背着母亲踏上了从前回家时的必经之路。
城市化进程中记忆成了人们重新认识自我、改变自我的催化剂。《岁月的童话》中小学五年级的记忆不断暗示着主人公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要做出改变。《家路》中故乡的记忆深深印刻在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的心底,不断地呼唤他们重返故乡、重建家园。
结语
城市化像一列疾驰的火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所到之处弄了个天翻地覆。被破坏后的乡土转瞬间变成了花花绿绿的城市,刚刚失去了土地的人们被这花花世界搞得晕头转向。有的成为了欲望的奴隶,有的变成了夜猫子,夜里开着车在城市里游荡,有的怀念土地,在自己搭建的塑料大棚里像个大烟鬼一样疯狂吸食着泥土的芳香。彻底被改造成城里人的灵魂深处依然有着对土地的记忆,这个记忆时不时地跳出来诱惑着人们远离城市,回归乡土。
中国当代文学对城市化进程的书写还在路上,还有许多领域值得去挖掘。例如,通过空间变化来捕捉人物心理变化的作品以及研究还不多,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探究。香雪与火车的邂逅其实是与新的空间布局的邂逅,香雪踏上火车意味着她开始融入新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到底蕴藏着什么,她不得而知。《远雷》主人公满夫驾车夜间穿梭于城里也意味着他对新空间的臣服,虽然车像一把利刃可以戳穿城市这个怪物,但满夫并没有这样做,只是茫然地飘荡在城里,变成一个野鬼游魂。《岁月的童话》主人公妙子从一个过客变成一个永住者,也可理解为对乡村空间的认可,而记忆成为了她做出决断的诱因。
当下城市化进程依然在不断被推进,城乡间的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个体化的人对于城市或乡土的情感依然浓厚且复杂。未来城市化的发展存在着极大的变数和不可知性。以AI技术和大数据为依托的智能城市将成为主流,都市对于人的异化依然十分猛烈,而乡土的存在意义可能被更加放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家和研究者文学对于城市化进程的多维度探究将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