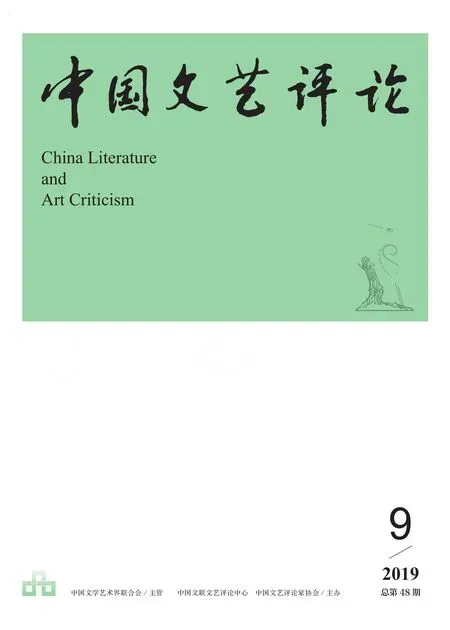音乐学家冯文慈的批评实践
陈荃有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历程中的一位音乐学者,冯文慈(1926—2015)在中国音乐史学的乐律学、中外音乐交流史等领域卓有贡献。但完整梳理并总结冯文慈的学术历程后,发现他在音乐批评领域的成就同样显著,其社会影响度也更为广大致远。
冯文慈自195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留校任教,起初从事过和声、钢琴伴奏等科目的教学,之后不断聆听并参与音乐史学领域(含中国音乐史、欧洲音乐史)的活动,于1959年在当时中国音乐研究所参与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结束这项工作的同期,他即在自己任教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编写、刻印了《中国近代音乐史》讲义并授课,自此开始比较专门化地步入中国音乐史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1973年9月,他再度进入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参与《中国音乐简史》编写组的工作,开始将较多的精力投身中国古代音乐文明的研究之中。因此,冯文慈的自我评价就是:我于1973年方真正步入学术领域,1978年发表的成果“是我学术生命的开始”。那么,他所自认的“学术生命开始”的文章是怎样的一篇学术成果呢?
对于冯文慈批评实践成就的梳理,就可以从此篇他自认的学术成果的源头开启。
批评实践的历史脉络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中的“儒法斗争”成为当时政治、文化领域路线斗争与文化观察的一支主要脉络。反映在音乐领域,由此而起的理论认识及其“成果”辐射面亦蔚为可观。至1977年,虽然“文革”作为政治运动已经宣告结束,但中国社会的意识领域仍处于极左思想的笼罩之下。此时,冯文慈就音乐领域存在的对于古代传统器乐作品无端上纲上线的歪曲深有感触,在工作之余便撰写了自己的见解——以对琵琶曲《十面埋伏》及相关联的《霸王卸甲》作为观照对象,通过搜集史料、分析作品音调及曲体结构,对两部作品形成的源流史事、人文寓含乃至涉及的研究主体的学风问题等,以万言长文逐一书写,既对“四人帮”集团借用古代音乐文明成果作为篡党夺权工具的意图开展批判,也对当时的唯心主义治学遗风进行抨击。假如关注此文发表的时间节点,我们会发现,冯文得以正式刊发的时间是1978年5月份,与当时掀起中国社会思想大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推出时间正相吻合。也就是说,冯文慈以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作为切入话题的音乐批评实践,并非对于社会政治主流意识所推动“大讨论”之后的学习“心得”,而是个人主动地、自觉地给予音乐文化解读方式审视的批评行为,可谓具有勇立时代潮头的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客观体现。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音乐艺术与学术的各个方面都进入快速恢复、发展阶段,被学界称之为“跳跃式发展”甚或“学术大跃进”的历史时期,部分学术成果缺乏扎实而系统的史料分析与严密的论证,或者囿于研究者自身学术素养的局限、或者被某种局部利益所左右,在匆忙之下仓促推出。对这一时期学术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共性化的问题,当时留学海外的青年音乐学者杨沐(1947— )曾于1988年撰写长文,以“格式问题——以注释为例”“引文问题”“实证问题”三个方面对于这种艺术科研方面暴露的问题给予批评,而对于相对具体而深入的学术个案中显露的种种问题,只能由学术共同体内的同行以学术的自觉展开“自评”了。
在这一历史时期,冯文慈正接受中国音协的委托,带领几位青年学者展开对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律学成果的点注工作,对于古代音乐文献的校点、释读,以及乐律问题、朱载堉生平等,可谓格外留意并了然于胸。基于这种学术前提与背景,他对于这一领域新的学术成果尤为关注。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冯文慈在努力做好自己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尚对音乐学术界在此领域的成果给予认真审视,以学者的学术自觉和社会责任感,就音乐学家黄翔鹏(1927—1997)在探讨中国音阶起源时对《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276—324)注所引文献的解读提出批评,撰写了《释伶州鸠答“七律者何”——附论对古代文献的解释》;之后,随着1986年9月于河南郑州、沁阳举办“纪念伟大的律学家朱载堉诞辰450周年”活动而发生的对于朱载堉研究、历史评价方面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先后撰写了《关于朱载堉年谱的补充说明——兼答吉联抗先生》(《人民音乐》1987年第3期)、《简评“朱载堉纪念大会”中的〈函告〉》(为1986年9月“纪念大会”而写,载《音乐研究》1994年第3期)等。这些文论,对于今人在评价和认识古人、读解古文献过程中存在的过誉、偏颇、臆测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些学术批评文章的相继发表,使得学界对相关的问题增进了了解,也提高了辨识的能力。
历史进入20世纪末期,冯文慈的批评实践无论从成果数量还是社会影响力均达到一个“高峰值”。按照这些成果发表的时间排序,冯文慈在这几年中的批评活动大体围绕着三个方面开展:
1. 1997年春季,发表了他本人的代表性成果《近代中外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音乐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这篇近三万言的长大学术评价式文章,原是为他个人专著《中外音乐交流史》的收尾而撰写,因涉及的诸多问题均是20世纪末叶带有普遍性的音乐学术争议乃至社会文化思潮,因此他在书稿“结语”杀青后就先期投稿给国内重要的学术期刊,以期盼早日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听取大家的意见。文章在系统阐述中国古代音乐交流史之后,自然地转入到近代及现代社会与“音乐交流”相关联的诸般方面: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引入学堂乐歌历史功过的评价、对近代“国民乐派”的阐释与评价、对贺绿汀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作品属性的认识等,尤其是通过对于“欧洲音乐中心论”学术影响的估计与批判,辩证地认识“文化价值相对论”的积极作用及其理论弱点——冯文的这些评说,对于当时社会音乐思潮的分宗辨流、泾渭之别的认知极为有益。
2. 对老一代音乐学家杨荫浏(1899—1984)代表性著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做连续性的评价。1998年岁尾,《音乐研究》杂志办刊人相约冯文慈,希望他撰写一些能够活跃学术氛围的文章,冯文慈便以每文数千字篇幅的小型评论文章开启了连续四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择评”,即《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雅乐新论:转向唯物史观路途中的迷失——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之二》《防范心态与理性思考——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之三》(相继发表于《音乐研究》1999年第1—3期)、《转向唯物史观的起步——略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历史地位》(《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之后,还将1999年底参加纪念杨荫浏百年诞辰活动时的发言要点汇纳成《〈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历史性成就及其局限——在纪念杨荫浏诞辰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刊发于《人民音乐》2000年第1期。由此,推起了一轮延续数年的批评、反批评乃至泛批评的影响深远的音乐史学批评事件。
3. 《评黄翔鹏“‘九歌’是九声音列”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针对黄翔鹏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唯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乐问——中国传统音乐百题〉之八》演讲整理文字中的观点,冯文慈围绕此文作者依据自身对于清代文人王引之《经义述闻》文献的诠释,由而推导并提出夏代音乐文化已达到相当水平、夏启从天帝处获得的“九歌”是一种复杂的音乐、“‘九歌’是九声音列”之说等进行批评。进而冯文慈认为,黄翔鹏之说属于“浮游无根的玄谈”,他通过对黄翔鹏多年来一而再地发生的对古代文献的主观化解读,认为黄已经“陷入浪漫主义之泥沼”。由此案例入手,冯文慈延及阐述了音乐学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解读问题,并提出了更多具有现实主义治学态度的期待。
新旧世纪交接之际,学术界同仁在普遍开展各学科领域的回顾与展望并重的“温故知新”,冯文慈于五年间(1997—2001)连续在国内重要的专业期刊(《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等)发表近十篇批评、回应批评的文论,所面向的对象均为名人、名著、名说,由此这些文章所产生的学术能量与社会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推动其批评实践的缘由
对于冯文慈将大量时间、精力分配于批评领域,特别是在新旧世纪交接之际连续的批评行为,其针对的对象要么是当时学界已笃信不移的理论体系、要么是在音乐领域被视为学术“高峰”的里程碑式著述、要么是已被推上神坛的知名学者。他的这种批评实践,自然引起部分音乐人士的好奇乃至情绪反弹:冯文慈怎么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探求学界人士的这种作为,立足其从事的学术以寻找答案是最为可靠的方法。分析冯文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的音乐史学,发现他始终在追求两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及应用能力的提升:
第一,唯物史观的统领与实事求是原则给予学术的指引。我国现代史学建设异于传统史学的关键,就在于史学观念的更新——传统史学多以唯心史观统领,讲求为政者“知古鉴今”的“资治”之需;现代史学则以唯物史观统领,追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的一般性规律——这也是现代史学家孜孜追求的学术境界。对此,冯文慈曾经提出:
不管流派如何分野,三家五家、九家十家,或者以超然派别之上自居,所谓以“实事求是”精神选择史料、描述史事,心田之中不可能不存在着思想支柱。……但是无论如何,说到底,如果从宏观上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奥秘,解释重大历史事件,褒贬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即或时而需要相关学科的支持与协助,然而最基本的靠山还是要仰仗唯物史观。
由此可知,冯文慈治学中追寻的理念是唯物史观统领下的实事求是原则,他将之视为现代学者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去推动学术发展的一种基础力量。
第二,微观史料与宏阔视野相互作用的学术支撑能力。史料之于历史学的基础性作用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以至于近代史家傅斯年提出了著名的“史学只是史料学”之说。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音乐史学究竟为怎样的学问?又需要怎样的方式得以获取呢?结合冯文慈对于学术、学问的期冀以及他对于人才培养问题的阐发,可以概括为“抓住两头”——冯氏高足刘勇教授简练地总结为“两对关系”:一是“史料与前沿”,即一方面要追踪学术前沿成果,另一方面要熟悉原始史料,这样才能贯通源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以获得对新的学术观点的判断力。二是“微观与宏观”,即具备微观分析的能力和宏观研究的能力。冯文慈倡导并践行的音乐史学,即是具备了既“熟悉原始史料”且“能贯通源流”的“微观”之术,又能够掌握正确的史学观、方法论来“追踪学术前沿”的能力。
基于他在学术领域如上两方面的一贯诉求,我们再结合其他多方面的资料,认为冯文慈钟情于批评实践的缘由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
第一,人生态度的自觉显露。冯文慈为人处世的态度,异于多数音乐理论学术领域的同仁。记得在1998年获赠他刚出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一书,随书附赠的一页打印再复制的纸片使笔者甚感诧异,上面列述了多条该书因编校而致错讹的“勘误表”——对于已经出版了的长达近400页的著作,作者竟然如此敝帚千金,以尽力保证更多读者能够看到更显完美的内容呈现。2005年笔者再度获赠冯文慈个人文集诗,随书(贴于扉页)仍然附赠了自纠式的“勘误表”,看来此种做法并非一时之举。2015年笔者在对冯文慈一些未刊著述进行整理时,发现由他编写、北京艺术师范学院(1956—1960年办学)刻印于1959年9月份的《中国近代音乐史》讲义,即已在文本最后装订了四页“勘误表”,内以“页数”“行数”“误”“正”四列设置,对于已经刻印即将装订的教学讲义中发现的疏误逐一罗列,详书其正误,其字斟句酌的“较真儿”劲头跃然纸端。
第二,寻求事物之真的治学追求。冯文慈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习,比较推崇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治学精神。他曾在自己治学的“心态自述”中写道:
我之所以破除杂念,评论大师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确并非事出偶然。自1986年以后我就开始批评中国音乐史学界的知名方家,除了在《中外音乐交流史》中针对早年故世的音乐学家王光祈之外,以批评挚友黄翔鹏着力最多。而且对方家都是指名道姓,此外指事不指人或针对音乐学界以外知名方家的也还有。对这些方家,我心中是尊崇敬爱并存,同时我又愿意学习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的“直书”原则,借鉴所谓“爱而知其丑”的批评精神。当然我所批评的所谓“丑”,不过是我判断的缺点和失误,与刘知几所直书的过去史家的肮脏“秽迹”有原则区别。
以追寻学术中更爱之“真理”为己任,更因心中的挚爱而自愿勘查其“丑”并予“直书”,这种为寻求事物之真而非申述个人学术观点而起的批评行为,体现了他更加高远的批评情怀。当然,冯文慈也明确指出,他所批评的音乐界各色的所谓“丑”迹,与刘知几《史通•直书》(710)中所述说的史家隐匿骄主贼臣“秽迹”的情况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冯式批评”的特征与要旨
对于冯文慈的学术遗产,包括他长期从事的高等音乐教育、践行的音乐批评领域等所作出的贡献,均值得引起音乐界人士做进一步研究。
就音乐批评领域来讲,冯文慈多年以来以大量的批评实践而树立起的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批评成就与其社会影响,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术、音乐艺术健康前行的一季清风。梳理冯文慈二十多年的批评实践,发现其已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批评范式,笔者将此范式简括地命名为“冯式批评”。根据上文的简要分析与概括,依据批评活动的构成要件,“冯式批评”的特征与操作要旨主要表现为如下四点:
第一,就开展批评活动的动机与意图来讲,“冯式批评”不唯上、不唯师、不唯友、不唯己,但求学术公理于堂堂正正之间。冯文慈从事音乐批评的目的,并无追求哪位个体可作为受益方或者明确的个体利益倾向,实乃为追求学术与艺术的本真存在或发扬光大而为之。正因为这样一种批评动机的设定,在他长期的批评实践历程中,除了针对社会思潮、公共艺术现象等具有全局性音乐事象展开的批评之外,其他所面对的主要批评对象多涉及到他本人敬重的师长、挚友,因着需要借此匡正对古代文献的读解问题、需要树立正确的史学观和方法论、需要去除人们心头先在构建的无谓“神坛”,而必须通过批评活动以使相关问题很好地得到揭示甚至遏制。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于音乐学家黄翔鹏的数度批评,而他与黄翔鹏乃是有着数十年交情的好友甚或学术知己,黄翔鹏更是奉冯文慈为可以“无碍的、交换心里话的同志”,由而称之为“畏友”;1999年对于杨荫浏代表性著述的择评,而被评者乃是冯文慈自20世纪50年代就听课、受业的老一代学者,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音乐界更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凡此批评对象及其形成的批评文本,他都以刊发媒体、研讨会发言等方式公开地予以探讨。
第二,就批评活动的论域与观照视野而言,“冯式批评”显现了批评者的胸中既有“小我”之田园,更怀“大我”之天地的广阔胸怀。当代的艺术与学术活动中,时而也能见闻因批评而泛起的涟漪甚或朵朵浪花,但参与批评的当事各方多就某部作品、某项成果而发生彼此之间相互关连的观点之争、方法之议,甚或一些批评活动只是为当事者“荣誉”、面子而掀起的些许波澜。冯文慈的批评实践,自1978年5月对于《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的论说开始,直至对于“文化价值相对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乃至于对黄翔鹏治学态度的批评,均起于个人专业识见之上的事关时代艺术思想、学术理念的“大我”的思考,是起于“小我”但早已抛开了“小我”情怀的更为广袤的“大我”天地。这是“冯式批评”异于众多批评行为的尤其值得赞誉的重要一面。
第三,批评过程呈现的胸襟与气度,乃开展批评活动或者相互争鸣时的保障,是决定批评动机与情怀能否得以良好体现的关键。在批评实践的初期,多数批评活动的参与者尚能够操控有度,按照既定的批评设想开展相应的实践,但随着被批评者或被批评观点拥趸者的介入,往往使得批评实践的行为走向发生偏转,此时也最能窥察批评者的艺术修养、人文情怀。冯文慈的批评活动是以直接、公开、坦率的态度和方式而展开的,相左的认识与朋友般的建言均呈现于媒体,以坦荡的方式公之于众。在1999—2002年围绕《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而展开的多方论辩中,他身处有形、无形的反批评群体的对立面,似几分“舌战群儒”的状态,从批评杨著所激起的社会浪花而言,参与论战的各方实已处于情绪的对垒状态,但从反映在冯文之中的叙说方式来说,仍然不失谦谦儒者的君子风范。以他所正面应对的唯一一篇具反批评色彩的文章来说,约一万字的篇幅量,呈以10个小标题的内容设定(第11个标题为“尾语”),围绕五个方面展开答辩式“反批评”。全文可谓论说大度、申之有矩,表达逻辑严谨而语言运用简练。从开篇首句至结尾的收束,无一句论题之外的冗语,更无激辩文章常见的情绪化表达或过激的言辞。
第四,就开展批评实践的具体策略而言,冯文慈主张“擒贼先擒王”的操作法则,力求抓住批评实践意欲达到的实质性问题的源头,以达到最佳的批评效果。当然,此处欲擒之“贼”与“王”并非指向具体人物,而只是批评事项的关键问题与其对象的源头。冯文慈在阐述自己的批评实践时曾经提及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批评原则(即“爱而知其丑”),在他的批评行为中比较讲求“擒王”式的对象设置,为达到求实目的而对孔子所编订《尚书》《春秋》亦做“仗气直书,不避长御”(《史通•直书》)的客观批评,从而直达史学著述的起点。冯文慈多年来所选择的批评对象,即比较关注其处于核心问题的相应地位及其学术影响,以追求批评实践能够直达主要矛盾的焦点。这在他1978年发表的对于琵琶曲《十面埋伏》的论述、对黄翔鹏解读古代文献的“浪漫主义”方法,以及20世纪末对于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择评”,都坦露无余地得以体现——不以解析某首作品、文论或者评价某部著述为批评行为的最终追求,而是由典型作品(含文论著述)的分析、评价为切入,直指引起一时文化思想、社会认知、学术现象的关键问题或事发源头——诸如治学心态与方法的浮躁、简单,或摒除盲目崇拜心态给予历史著述以客观辩证的认识。
结语
由对冯文慈音乐批评实践历程的梳理、推动缘由的分析,而至对其批评实践的动机、批评活动涉及的论域,再到批评过程体现的胸襟、气度及批评行为采取的方法、策略,可以发现“冯式批评”的特点、风貌若放在整个中国文艺批评的大背景下,或许难言壮阔,但在中国现代音乐学术领域则可谓贡献卓著,堪称时代学术发展之楷模。
如今,斯人已逝,但批评公器应该为后来学者所汲取。笔者曾读到当代史学理论家瞿林东教授阐述史学批评之时的精彩见解: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史学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由于史学批评的逐渐展开,还不断滋生出一些新的史学概念,而这些概念的提出和运用,久之乃成为史学范畴,进而促进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批评的展开,不仅有益于当世和后世史学发展,同时对以往的史学也有拾遗补阙、阐发新意之功。史学批评还在推动史学成果走向社会、扩大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凡此,都显示出了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发展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历史学科如此,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学、音乐艺术乃至其他的艺术领域的批评问题,何不如此呢?
21世纪的中国艺术与学术领域,仍急迫地呼唤并期待光大“冯式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