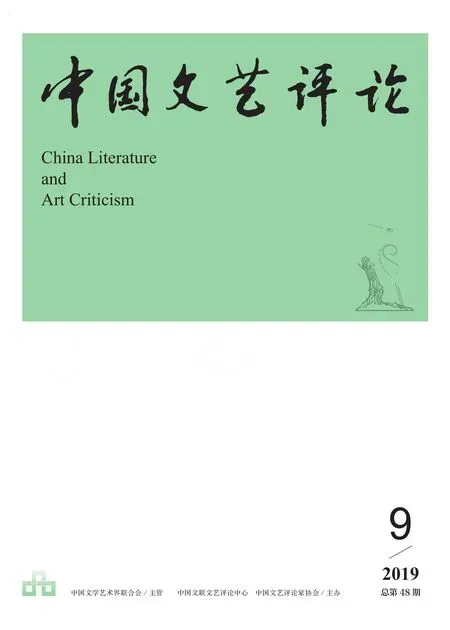在艺术与文化的有机整合中推动中国音乐史学转型
项 阳
如果以1922年叶伯和著《中国音乐史》为始,中国音乐史学尚不足百年,真是年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30年间,是中国音乐史学奠定百年基石的重要阶段。先后有郑觐文、萧友梅、许之衡、孔德、王光祈、杨荫浏等多位学者的著作且各具特色,夯实中国音乐史学“地基”,并使之成型。学者们不懈努力,学科发展与学术进步同行。我们应向学科先驱致敬,因他们的存在而成学。这些著作以通史为主,其共同特征是治史理念受西方或称欧洲专业影响,重文献梳理,其中王光祈所著以比较音乐学方法论反观,形成特色。
音乐是以音声为主导的技艺形态,具有稍纵即逝的时空特性,现代人不可能听到古人的唱奏,所以研究音乐史学是困难的事情。既然是音乐,首先应对音乐本体进行辨析。音乐本体为律调谱器,是音乐的基础构成。律调应用需借助相关载体,或为人声,或由人创制的乐器。在留声机发明之前古代人声无可觅,在文字尚未成熟的情状下,若对音乐进行辨析,须借助考古出土与音乐相关的文物以及文献资料去把握音乐的存在。
70年两阶段:以改革开放为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占据了中国音乐史学立学后三分之二强的时空。以改革开放为标志,我们可将中国音乐史学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阶段。就古代音乐史学来讲,前30年是对民国时期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理念的夯实与发展。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为民国时期中国音乐史学的典型代表,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起由文化部牵头,将全国致力于音乐史学的相关学者和高校教师多次集于音乐研究所,定位研究理念和方法,提升学术认知,建立理论框架,深入研讨相关文献,注重考古资料和相关文献中与音乐相关事项的把握,亦从传统音乐活态中追寻回溯,依朝代将不同阶段的音乐机构和承载的音乐形态系统化梳理,侧重音乐本体深入探究,形成治史理念以为导引,不懈努力,终将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脉络相对清晰地展现于学界,功绩卓著。
通史是最为主要的撰述方式,显现对中国传统社会音乐发展的整体把握;专题史在民国时期即有涉猎,但较少进入史家视野;至于断代史,李纯一依通史方式撰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第一分册),亦可以断代史认知,其后先生由治中国古代音乐史而侧重音乐考古,聚焦先秦,使之逐渐系统化,挖掘新材料对音乐史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音乐史学界在文献梳理基础上倚重考古材料,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阶段的40年以世纪之交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主要特征有二,由于高校教学全面恢复,出于教学需要,多种音乐史著作得以出版,且在通史为主导前提下有多种专题史和断代史;因改革开放,多种外来学术理念和方法论被引入,致使新学科建立,诸如音乐地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民族学、音乐民俗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图像学、音乐形态学、音乐语言学、音乐传播学、音乐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经济学、戏曲音乐学等,加之业已成学的音乐美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学科建立显现多视角,观察音乐的存在,音乐学研究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在对音乐本体形态体系化认知基础上,以这些学科视角探讨中国先民何以如此创造,成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在国家意义上,一些重学科建设、系统化研究课题得以确立,诸如《琴曲集成》,全国十大集成志书中的《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舞蹈音乐集成》等浩大工程举全国力量在这一时期立项并完成。作为传统的活态存在,定与历史音乐文化千丝万缕,特别为研究音声为主导的技艺形态提供了可靠依凭;随着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对音乐史学界带来的冲击与震撼,由音乐研究所提出动议,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启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工程,将与音乐相关的文物系统收集,迄今已经出版近20个省、市、自治区卷本,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黄翔鹏领军,从全国多院校和科研机构聚合学术研究团队,成立《中国乐律学史》课题组,既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又结合音乐考古提供的一手实物辨析,并以传统音乐活态相印证,一系列前沿性学术成果丰富、甚至改变和深化了人们既有认知,有力推动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进步。至于本世纪以来国家所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与传统音乐相关的门类众多,四级代表作项目更是不可胜计,成为我们认知传统音乐活态存在的有力保障。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成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60年的里程碑,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从学术理念、方法到学术材料不断丰富,致使学界产生新思考。20世纪90年代初,某出版社有意出版多卷本《中国音乐通史》,黄翔鹏认为,如若再出版通史著作,难以突破杨荫浏既有的框架结构和内容,他建议在较长时间段内不再写通史,大家都来研究问题,探寻新学术理念,以新视角、新材料把握学术点深研,待有更多学术积淀之后再重新架构,会展现音乐史的新面貌。爱因斯坦的名言:理念决定你所能够看到的东西。学术理念和方法可从中外学界引入,但面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定然要明了自身意义,换言之,引入理念重在适合、有用,应在回归传统前提下、把握学术前辈开拓的道路上发展前行。
学术理念拓展对音乐史学研究之影响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多种外来学术理念或称学术方法论被引入,中国音乐学界也重新审视既有治史理念。《欧洲音乐史》是以音乐舞台为中心、强调艺术与审美的撰史模式,同样在西方,却有《Why Soya Song
》以及仪式音声的探寻,这显然不是仅将音乐作为艺术的考量。何以西方有音乐文化人类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地理学等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是仅关注音乐本体形态,还是将音乐置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化创造中整体观照?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生活中重要的精神现象而存在,作为音乐构成要素的音声技艺,在社会生活中究竟有怎样的功用,是否仅以审美欣赏认知?何以在欧洲专业音乐治史模式对这些基本忽略?反观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何以在“二十四史”中对音乐如此重视,特别以“礼乐志”设目为论?既然在传统社会国家制度下这礼乐分出类型和等级一以贯之地存在,何以我们对这种连续性视而不见?文史学界对中国文化有礼乐文化、礼乐文明的认知,这礼乐如何定位、音乐史如何显现值得辨析。中国文化有儒释道三足鼎立之说,其用乐有怎样的特征,是否仅是审美欣赏意义?既然礼乐的基本特征是乐与人类情感的仪式性诉求相须为用,那么,人们对于乐显然不会仅限于仪式性诉求为用,这非仪式性诉求中的用乐该如何把握?这些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如何记述,我们此前音乐史著作是否能够接近历史文献记载的真实样貌?何以在为用意义上历史文献记述会被治史者有意无意地“忽略”?有必要将学界逐渐形成多视角整体认知的相关探讨予以整合,回归历史语境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色内涵。音乐是艺术,更是文化有机构成,既从艺术本体又从文化整体进行多视角考量。特别是把握住功能视角,明确作为音声技艺主导形态的乐所具有的时空特性,考量先哲为何以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应建立在诸多具有独立性分支学科研究的基础之上。每一分支学科为视角和切入点,从不同层面研究深入,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开拓与发展架构有极大助益。应明确,分支学科是以中国音乐史学为主轴的存在,须有整体史学观念、或称整体观照的前提下从事分支研究,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分支学科的重要性就在于共同架构史学研究的大厦。这些分支学科的迅猛发展与研究深度,决定了中国音乐史学的深层内涵,由此重新架构与确立发展方向,这恰恰是黄翔鹏期望先研究问题、多年后重写音乐史的意义所在,音乐史学界研究的确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视角多元必然导致理念更新。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音乐史学在研究走向深入、新理念逐渐成熟的情状下发展前行,学界有重写音乐史的呼声,重写需薪传代继,在充分汲取前辈学者学术成果以及当下学界新研究前提下进行有效整合,形成坐标系整体架构。将应考量的论域厘清,将基本概念定位,或称把握内涵与边界,当下应该是到了这个重要的阶段。治史理念的丰富,多学科的发展,成为架构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基本保障。拓展论域和研究理念,在辨析和界定中逐步取得学术认同后“群起而攻之”,撰写出新的音乐史著作,以回应大学术界。
以音声技艺为主导的技艺形态,与它种形态的治史有着“先天”缺憾,我们难以听到先民唱奏的实际音响,若不能够寻求有效地解决办法接近历史样貌,不能够回归历史语境、仅以当下科技发展以及城市中乐的存在方式去理解,很难相对准确地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乐的存在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研究不能够只重纵向而忽略横向和当下,应将历史上的相关文献、器物、图像资料所展现的音乐文化现象与积淀在当下的音乐形态及其存在方式整合认知,实现“九个接通”的理念,即:当下与历史接通;传统与现代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宫廷与地方接通;官方与民间接通;中原与边地接通;中国与周边接通;宗教与世俗接通;个案与整体接通。如此可贴近历史的真实。
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将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和精神成果以文化认知,而不仅局限于具体形态自身。先民们认定乐为“六艺”中音声为主导的技艺,而技艺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存在。艺术应是技艺之术,应置于人类创造大背景中整体认知。既把握艺术本体,又考量艺术创造的主体和整体。
功能者,为功用意义。音声为人类表意抒情的载体与工具,社会中人将音乐作为艺术呈精细化创制,重鉴赏和抒发,往往忽略其多种功能性。实际上,先民对音声与乐进入国家为用有定位。《周礼•春官》多以乐论,而“地官”则以音声定位。这音声具独立性亦可转化为乐。作为欣赏与审美意义的乐更多反映人们以世俗性、个体为主导的情感方式,而乐群体性、仪式性存在不仅仅为欣赏与审美,这是先民的理念。当社会具组织态,这乐类分明确,涵盖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以乐作为工具的教化功能凸显。
音乐文化史中的礼、俗两脉
礼乐和俗乐分野的标志在于仪式性,先民认知明确,乐与仪式相须固化为用,即为礼乐意义。“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礼有多种仪式类型,在不同类下又有不同层级,彰显礼的体系化;凡用乐的礼必定有仪式化存在,乐在仪式之不同仪程中相须为用呈固化存在,仪式类下又可分出层级。
遗憾的是,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之指代,音乐史著作却没有将其置于应有地位。我们可从9000年的舞阳贾湖、7000年的余姚河姆渡,四千余载的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等遗址中把握礼乐文明早期存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高礼制仪式是祭祀,在多个具有国家性质的遗址中都有大型祭祀场所存在,其中石峁遗址出土乐器口弦、骨笛、陶响器、石哨等数十件;陶寺遗址中出土特磬、陶铃、铜铃、土鼓、鼍鼓、埙等乐器26件,这些都在国家祭祀中具组合意义,应与仪式相须为用,是礼乐制度的滥觞阶段。祭祀场合用乐,彰显时人对天地之敬畏,对自然之尊崇,对祖先之缅怀,形成用乐的国家意义。我们很难想象庄严的仪式场合会悄无声息。乐是以音声技艺为主导,歌舞乐三位一体形态的存在。数种、几十件“乐器”、应有“干戚羽旄”等舞器,加之语义明确的颂词——乐语/乐言融为一体,造成强烈的音声仪式氛围,参与祭祀的群体均具虔敬心态,由于祭祀对象各不相同,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和特定仪式场合固化为用,会逐渐形成专任职业群体,否则无论歌、舞乃至乐器都不可能术业专攻,国家最高礼制仪式用乐应有整体意义。历经夏商时代的涵化,终在周代逐渐形成吉嘉军宾凶多种类分,多种层级为用(涵盖王室和诸侯国)、以国家制度规范、且有国家用乐机构统一创制、管理、训练、实施的样态,为后世国家礼乐文明开先河。
国家礼乐文明必有制度保障,制度非松散无序。国家用乐显现引领意义,必须整合国家制度对历史上不同时期与音乐文化相关的现象和事件,找出内在逻辑关系。在史前文明阶段,我们需通过考古等手段对其考辨,进入文明阶段,文字系统相对成熟,虽然依旧不能听到古人的演奏和演唱,却能够借助考古、图像学以及多种文献资料,相对清晰地把握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音乐本体的中心特征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音乐形态及其为用。
当下成熟的信史文献从周代始,此前阶段仍在探索,反映出经历长时间孕育、夯实、积淀,到这一时期先民的整体认知。如果说,此前人们对音声与乐的把握尚属朦胧,周代在国家用乐之礼乐文化层面则属有意识地提升和强化。从制度上引礼入乐,导致中国礼乐制度彰显,这是拜周公制礼作乐所成。周公首先定位国之大事用乐,并设置专门机构掌管训练、教育与实施。标竿以立,大祭祀用乐定位,这是“六乐”意义。由此定“国之小事”用乐以为区隔,再有它种礼制仪式用乐类型,后世定位为五礼加卤簿仪式用乐类型和层级,反映人们情感仪式用乐诉求的丰富性内涵。这是以国家制度规范的礼乐形态,仪式为用,依制王室、诸侯、卿大夫、士四级拥有。宗周国家疆域广阔,加之非宗周国家效法,使得国家礼乐制度遍布华夏。虽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礼乐形态在不同朝代显现新变化,但其用乐理念依循周制,三千载一以贯之,成为国家用乐的一条主脉。汉魏以降,周边国度多种音乐部伎进入中土,导致音乐形态不断丰富,生发出多种乐制类型,使得国家用乐机构在吸纳外来的同时更加注重本土音乐文化深层内涵。在礼乐文化的主导层面、从乐制上作出类分,将以金石乐悬领衔的乐制类型定位为“华夏正声”,所用律调谱器等为中原自产,以“雅乐”(涵盖佾舞)定名保证其“正统”。汉魏至唐,雅乐类型只在宫廷,其后随科举制度建立,在全国县治以上普设文庙,《文庙祭礼乐》由国家太常创制颁行,由此雅乐一支来到县治以上官府,呈全国为用样态。除此之外这礼乐有“胡汉杂陈”的鼓吹乐类型。这种类型汉代成型后在不同历史阶段其领衔乐器有所变化,早期有笳(觱篥)、角、鼓等,其后有唢呐进入,比雅乐类型用途更为广泛,从宫廷到军旅、各级官府依制存在,且五礼加卤簿均用之(等级差异显现),形成硕大用乐网络。唐代将西域等多部伎宫廷嘉礼为用,礼乐一脉内涵十分丰富,官书正史对其记述详备。
礼乐是群体性、多类型仪式性固化为用,反映国家与社会群体丰富性的情感仪式性诉求,但国家用乐非仅仪式性,如此非仪式性用乐与礼乐对应,所谓俗乐意义。总体讲来,仪式为用——礼乐,非仪式为用——俗乐。周公定位仪式用乐,则将非仪式用乐与之对应,形成中国用乐传统两分样态。俗乐亦有群体性诉求,但重个体性。国家礼乐强势,与仪式对应的俗乐认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趋于明朗。我们看到,最初对俗乐认知出于与祭祀之神圣性对应考量,《仪礼》用乐有四种,这就是“乡饮酒”“乡射礼”“大射仪”“燕礼”,为人际交往礼仪用乐,其时并未明确属性。隋文帝将太常承载国家用乐分为“雅部乐”和“俗部乐”,学界对俗部乐辨析追溯到《仪礼》用乐,将非祭祀仪式用乐定位为俗乐。唐代开元间玄宗皇帝认为太常乃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另置教坊归之,由此开倡优杂伎非仪式为用独立机构之先河。问题在于,唐开元之前俗乐归谁管理和实施?是否此前非雅乐类型都认定为俗乐?开元前这俗乐应是涵盖了仪式和非仪式两种样态,而仪式为用明为礼乐,对应为神奏乐的神圣性意义属交往之礼仪,有世俗性,这是学界将其以俗乐论的道理。然而,当国家用乐机构明确教坊承载倡优杂伎之乐,却在其后发展中既实施非仪式用乐(当然有专门的群体与团队),也承载除雅乐之外的礼乐,实际上是回到隋代之太常俗部乐样态,以礼俗兼用为主要特征。
社会明确教坊乐为非仪式类型,全国各高级别官府有专事这种用乐群体的存在,这是乐营机构的意义,为宫廷、军镇、高级别地方官府的体系化存在,“岂唯夸耀军功,实乃宴饮宾客”,催生多种俗乐体裁,诸如说唱、戏曲等形式。宋代教坊“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惟以杂剧为正色”(《都城纪胜》)。在国家用乐体制下,仪式和非仪式用乐均由国家管理,只不过仪式用乐由太常统一创制并依制在规定范围实施,非仪式用乐既有专业机构创制,亦有遍布全国承载俗乐的专业乐人在与社会人士互动中创制,通过国家体制自下而上规范后反播,成为各地官属乐人的范本、甚至教科书般为用。这当然是不断创造、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以满足社会多层次人士的精神诉求。宫廷和各级地方官府之官属乐人,承载国家用乐有着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所谓“男记四十大曲,女记小令三千”。这是大致类分,非严格意义,诸如戏曲等形态需按性别分配角色,显然分工不会如此明确。
需考量社会提倡礼乐文化,即便俗乐亦要“合礼乐”,在国家用乐层面若有过于“出格”之举,必受社会舆论指斥,诸如“郑卫之音”“靡靡之音”“桑间濮上之乐”,说唱与戏曲等后生的艺术形态,在供世人审美欣赏的同时,更是将国家与社会倡导的道德规范以宣教,具有“合礼乐”意义。
把握历史节点,探寻演化关系
研究中国音乐文化史,要把握许多节点,所谓节点,即是因社会变革、与研究对象相关、事件发生的重要时间点。应以学术敏感认知真正的节点,然后将节点前样态与节点后的发展状况产生对比。明确因循、变异与消解,以及新元素的融入。整体意义上讲节点众多,但应首先把握国家形成之前诸种与音乐相关现象或事件的存在,看其被国家整合之后制度化发展的演化脉络,此前之存在有哪些延续,新元素对既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
鉴于乐的时空特性,国家用乐以制度为保障,必有专业乐人群体的存在,但缺失早期专业乐人全国性体系化存在的文献记载,直到北朝乐籍制度的建立,方使国家专业乐人群体明晰。当下学界已有多个社科基金项目对这种制度进行研讨,相关文论上百篇,基本厘清这个群体自宫廷、京师、军镇和各级官府中的存在,及其对礼乐和俗乐的承载,这是重要研究成果。学界循此上溯,对涵盖“六乐”和《诗经》在内的音乐形态进行辨析,既然这些能够在宗周国家存在,定然不会仅仅是名称意义。况且这《诗经》所谓“弦诗三百,舞诗三百,诵诗三百”,应是歌舞乐三位一体;《韶》《濩》《武》的记录在齐鲁,远离王庭,则应把握最高礼制仪式用乐诸侯国群体性固化且一致性的意义。再有,姚小鸥教授和王克家教授对秦时专业乐人“践更”制度的解析,说明其时有国家专业乐人制度的存在。所有这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既有的认知理念。
周代基本以中原为中心,汉代凿空西域,周边诸国音乐形态逐渐进入,对中土音乐文化造成实质性影响。这些外来音乐形态以部伎存在,最高形态为大曲,亦有次曲和小曲,经历两晋南北朝的浸润,隋将部伎中的佼佼者收入太常,唐代拓展,在太常中将大曲、次曲、小曲一并教习,其中的大曲被用于国家礼制仪式之嘉礼,次曲和小曲除了宫廷娱乐为用,通过入宫接受轮值轮训的官属乐人带至全国各地高级别官府,由于特色独具,引发官员和社会人士的追捧,所谓“洛阳家家学胡乐”正是这种盛况之写照。需要思考的是,中原音乐原本多以齐言为主导,但隋唐以降重心转向杂言,五代以曲子词定位。宋代王灼敏锐地注意到这种现象,所谓“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曲子的基本特征为长短,无论曲体结构还是词格均如此。应探究中国用乐传统从齐言向长短过渡的动因。曲子确立,由曲子成曲牌,既独立存在,亦归入不同宫调,诸宫调形式成为宋代说唱的主导。因角色意义生发出多种行当以成戏曲,戏曲成熟后相当长时段以曲牌体为重,延续后世千余载;曲牌体与板腔体互动影响了多种器乐形态。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一直在动态中发展,抓主导脉络和节点对认知演化过程至关重要,特别对于俗乐文化更是如此。
国家用乐向民间礼俗用乐的转化,应把握雍正禁除乐籍的意义。原本国家用乐重在官属乐人群体的体系化存在,雍正将承载国家用乐的群体放归民籍,导致从宫廷、军镇到各级官府国家用乐群体下移到“民间”,国家用乐地方官府中为用的部分转为民间礼俗为用(地方官府为用改为雇佣),经数百年涵化,这是民间积淀国家礼乐和俗乐的道理。由于乾隆禁女伶,则见既往所有专业体裁形式(涵盖说唱、戏曲等)直至20世纪之前均由男性承担,戏曲中“男唱女声”的存在恰由于此。
回归历史语境与整体把握
对于乐这种形态,特别需要考虑如何回归历史语境,通过所能把握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去“感知”先民的所思所想。认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不是将其作为无生命存在的解剖对象,而是要“回归历史现场”,努力营造“活态”环境,把握不同时段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并揣度先民们在怎样的理念下创造这些音乐形态。不回归历史语境,则很可能对古人的创造产生“误读”,或断章取义,或由于种种因素对某些存在回避和扭曲。只要是历史上的现实存在,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应辨析其合理性,这是著史依循的原则,否则难以把握“历史的真实”。回归历史语境的研究理念应是音乐学界必有的认知。在认知之后再“跳出”历史语境,方能真正把握其与当下的相通与差异。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定有其规律性与合理性,我们不应割裂式地关注其某些层面而忽略整体意义。将目光盯在形态本体,可以专题论,却不是整体。回归历史语境,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书写中国特色,应是建构中国音乐文化史的意义所在。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面对的是数千年文明传统。
乐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创造,艺术是文化的有机构成。文化具有整体意义,所以应有整体视角,应把握艺术本体和文化整体的关系。仅从本体论有些现象很难解释,从整体视角会有相对合理的解释。文化不是贴在艺术本体上的膏药,我们应考量技艺与文化之关系,以及中国音乐艺术史与中国音乐文化史之关系,何以产生如此艺术形态。并非礼乐不可以艺术论,而是当下学界仅仅将乐作为欣赏、审美意义,而忽略了它种功能意义的存在,将两条主导脉络之一整体“忽略”。学界承认两周礼乐的存在,却对后世2000年礼乐文化认知不足,这是问题的关键:对礼乐只从形而上探讨,却忽略礼乐的基本特征,以及礼乐基本功用,如此方有两周是全民礼乐,后世则礼乐文明消解,人们越来越重俗乐意义或称无所谓礼与俗的认知,这就将“二十四史”中的乐志、礼乐志所反映的理念和形态置于不顾。真应辨析汉魏以降礼乐文明是否消解,礼乐一脉是否不再,国人对于乐是否仅仅在欣赏审美层面等诸多问题。
明确从国家乃至民间虽然情感的仪式诉求不会时时为用,却不可或阙;情感仪式诉求不仅祭祀为用,更是涉及多种仪式类型,且显现层级,应该能够把握礼乐体系化存在及一以贯之。从整体意义上把握乐的功能性,会看到礼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未缺席。既然乐作为周之六艺之一种,是立学之存在,音乐学界应有自己的视角并与大学术界相接,将成果与学界共享,而非亦步亦趋,缺失独立性。明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特色鲜明的两条主导脉络,何以学界只是认同娱乐、审美、欣赏为用的一脉,值得反思。
在认知音乐本体中心特征和技术理论的前提下,把握不同历史时期音乐体裁、形式之存在,看其演化关系,以及社会在创造和使用这些形态的认同,侧重审美、娱乐、欣赏,这种无所谓礼俗的认知会忽略乐在传统文化中的多种功能性存在。音乐文化史研究实际上是对音乐艺术史思维和理念的拓展,回归历史语境在把握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去关注中国音乐文化两条主脉的存在与发展延续,两脉互为张力之存在方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整体意义。礼乐一脉其音乐本体中心特征与俗乐一脉相辅相成且具一致性。传统国家用乐重礼乐一脉(从理念上如此),国家用乐机构音乐创制首先围绕其展开,如此与俗乐一脉相通,音乐文化须整体把握,不如此则从学理和方法上存在局限。俗乐一脉更加贴近社会世俗生活,其发展定然比礼乐一脉迅猛,在技术理论乃至体裁、题材等多方面会不断创新,也会反作用于礼乐,诸如在乐调乃至旋宫等多方面的运用。先哲们这样认知和创造音乐文化,何以我们会如此局限的把握呢?原本整体认知,何以当下学界从单一视角考量?是什么导致我们与先哲的思维方式差距这么大!撰史应尽可能贴近,而非选择性把握。
中国音乐史学是年轻的学科,初创时期学者们从音乐艺术视角切入,以此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虽有涉及礼乐,却未贯穿。作为阶段性把握,这样撰史确有其合理性,只不过缺失了一条主脉,难以形成中国音乐文化史的整体认知。我们回归历史语境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色构成,形成新的学术理念和视角,非另起炉灶,而是在充分把握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行。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必须挖掘其深层内涵,梳理先民们数千年创造与发展传承的体系化意义。
中国音乐学界围绕史学和传统音乐所成的众多学科已经积累的丰硕成果,只有从不同视角“群起而攻之”,方使得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基石稳固。《乐记》有云:“累累乎端如贯珠”,大家都是打造珠子和串珠之人,从不同视角研究和解决相关学术问题,就好比在打磨一颗颗高质量的珠子,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依黄翔鹏等前辈学者指引的路径将中国音乐文化史展现于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