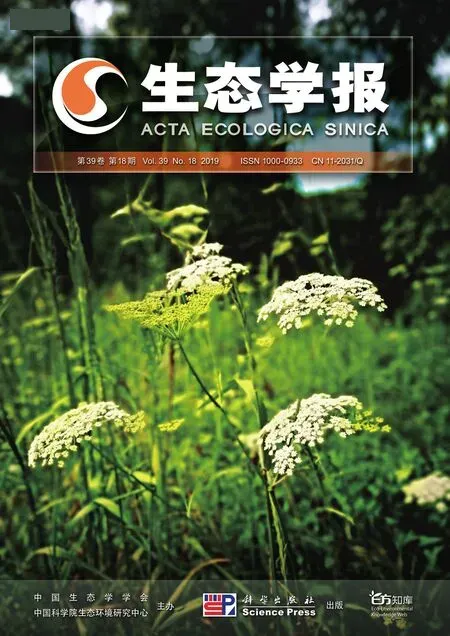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地区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
陆文聪,谢昌财
1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杭州 310058 2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 3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阳 550025
当前全球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由单纯科学技术转变成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人们逐步意识到碳排放交易对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低碳发展的重要意义[1]。碳排放交易是用经济手段推动环保的国际通行办法,其核心内容是清洁生产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该机制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确立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是现存唯一可以得到国际公认的碳交易机制[2]。CDM项目有利于优化能源利用结构,进而改善地区生态环境[3]。因此,通过CDM项目来开发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成为实施CDM项目的目的之一[4]。据美国能源情报署预测,到2020年,中国由于消费煤炭而排放的CO2将超过发达国家之和,占世界的40.3%[5]。在国际减排承诺和国内资源环境双重压力之下,中国政府于2012年启动了“两省五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分别为:湖北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天津市和重庆市,七个试点横跨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异较大,制度设计体现出一定的区域特征。中国碳排放的空间分布格局差异明显,地区碳排放强度呈现自东向西递减分布[6],且碳交易市场发展具有分阶段、市场规模大、发展不平衡等特征[7]。政府在排污权一级市场上,采取招标、拍卖等方式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排污者购买到排污权后,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权买入或卖出,使温室气体排放企业负担的环保义务转化为融资或交易产品[8],这对于政府寻找适当的碳减排空间,提升地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具有重要的意义[9]。
理论上,政策试点有助于地区内企业经营者对从使用清洁能源、清洁原料到清洁生产过程,再到最后的清洁产品在思想观念和生产行为上发生根本性转变,从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的传统生产模式中转换升级,实现节能降耗和减污减排,从源头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总结已有文献,国内外现有关于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估算方法、影响因素和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在估算方法上,姚亮等[10]采用结构分解法(SDA)分析了碳排放效率、经济结构、消费结构、人均消费水平、城市化和人口总量等六项因素对碳排放总量变化的驱动作用;Jones等[11]运用碳足迹从交通、居住、食品、商品和服务五个类别对美国居民生活进行评估;崔琦等[12]采用碳排放系数法估计了中国地区碳排放量;曾静静等[13]则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居民生活碳排放评价指标体系。在因素分析上,邓吉祥等[14]采用Divisia、突变级数、STIRPAT 分解等方法研究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胡初枝等[15]、陈彦玲等[16]采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模型,指出我国CO2排放的EKC曲线呈倒U型。在政策建议上,谭显春等[17]基于经济、人口、省级能耗量等数据构建了适用于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碳排放核算方案;刘晓等[18]研究了区域碳排放配额目标给定下的最优碳排放控制率和适合中国推进的碳减排配额方案。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对国际公认的清洁生产机制是否存在影响的文献研究尚处空白。本文以此为背景,基于我国2012年启动的“两省五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该试点政策对我国各地区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验证该政策对地区空气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并为国家制定科学的、针对性的、差别化的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图1 CDM批准项目2016年按减排类型分布Fig.1 Type of emission reduction distribution for CDM in 2016
清洁生产机制的实施与完善不仅有助于改善气候环境,它还为我国吸引外商投资以及加速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作为主要参与方,我国的清洁生产机制项目也正在跟随国际形势。根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CDM项目数据库系统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CDM项目共计5 074个,其中四川、云南、内蒙古、甘肃和河北的CDM项目数量位居前五位,分别为565、483、381、269和258个。从减排量看,四川、山西、内蒙古、云南和江苏2016年减排量居于前五,分别为8884.71、5582.24、5517.72、4964.51和4449.20万t。从减排类型分布上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减排是当前我国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实现减排目标的主力军。如图1所示,2016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减排占比为73.59%,节能和提高能效以及甲烷回收利用也是减排的重要形式,占比分别为12.46%和9.38%,三种形式占比达到近95%。
2 方法、模型与数据
2.1 方法
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政策效果评估方法,其核心是构造双重差分估计量,将政策干预对实验个体的纵向差异(干预前和干预后)和横向差异(实验组与对照组)有效结合,同时在模型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存在的干扰因素,进而弥补自然实验在样本分配上不能完全随机这一缺陷。双重差分法既能控制样本之间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又能控制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总体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到对政策干预效果的无偏估计。如果样本是面板数据,那么双重差分模型不仅可以利用解释变量的外生性,而且可以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19]。西方经济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从自然科学界引入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法,得到社会学者的普遍重视[20- 21]。在国内文献中,此方法近年来也被广泛运用于政策效果评价[22-24]。
本文关注的是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各地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如果简单观察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各地区开展清洁生产的企业比重情况,并不能说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提升了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以及改善了空气环境,因为这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难以衡量政策的真实效果。影响各地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因素不仅仅有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各地区的工业化率、能源消费水平、环境治理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等。某地区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比重较高,并不一定是由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导致的;某地区大气环境改善效果明显,也可能是环境治理投资的作用。因此,要研究这一科学命题,需要比较各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的清洁生产行为,可以引入上文介绍的双重差分法来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中国各地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效果。


上式右边的第一项称为“特征差异”,表示由于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因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不同所引起的分布差异部分;第二项称为“系数差异”,表示由于回归系数不同所引起分布的差异部分,这部分差异主要是由于试点政策引起的,也可称为“政策歧视”。
2.2 模型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来评估国家发改委2012年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各地区企业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PCDMit=β0+β1Groupit+β2Eventit+γ(Groupit×Eventit)+ηZit+μi+εit
上式中,PCDMit为地区i在时期t的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比例;Groupit为地区虚拟变量,如果个体i属于实验组则Groupit=1,属于非实验组则Groupit=0;Eventit为时间虚拟变量,Eventit=1表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开展后(实验期),Eventit=0表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开展前(非实验期);Groupit×Eventit表示时间与地区的交互作用,其中β1控制实验组与非实验组的差异(地区效应),β2则控制时间对实验组与非实验组的影响(时间效应);μi表示各地区的固定效应,是各地区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差异,考虑到各地区之间本身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引入μi是合理的;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γ是我们真正关心的系数,反映政策的综合效果,具体解释如下:
对于非实验组,即Groupit=0,各地区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比例为:
因此,非实验组在试点政策前后企业清洁生产比例变动为(β0+β2)-β0=β2。
对于实验组,即Groupit=1,各地区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比例为:
因此,实验组在试点政策前后地区清洁生产比例变动为(β0+β1+β2+γ)-(β0+β1)=β2+γ。所以,碳排放权交易对各地区开展清洁生产的净效应为(β2+γ)-β2=γ,即交互项Groupit×Eventit的回归系数。Z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工业化率、能源消费总量、环境治理投资额和人均GDP。选择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特征的宏观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的理由在于:第一,本文研究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以区域为单元研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机制和排放权分配机制,旨在推动地区清洁生产机制的构建[26];第二,由于暂时无法获取各地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微观数据,本文以全国30个地区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各样本区域内企业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可以反映出试点政策开展前后地区内企业对清洁生产总体意愿的变化。
(1)工业化率(Industrialization Rate,IR)。环境污染是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杜雯翠等[27]指出,现阶段以工业化发展为主的地区,其环境问题主要是大气污染;张亚斌等[28]研究发现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该阶段会产生较多的工业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弱化环境治理的效果。根据胡佛与费希尔1949年在《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中提出的城市经济增长“标准阶段次序”:自给自足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业生产结构转换阶段、工业化阶段和服务业输出阶段,与北、上、广、深等以服务业为主的一线城市相比,我国大部分城市还处于工业化阶段。
(2)能源消费总量(Total Energy Consumption,TEC)。能源的消耗伴随着二氧化碳的产生,消费者对能源密集型产品需求的上升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直接驱动力[29]。徐国泉等[30]采用Kaya恒等式对CO2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指出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增长等因素对CO2排放量有正向影响;刘志雄[31]利用我国1991—2011年数据的发现能源消费对环境污染产生正效应,即能源消费越多,环境污染越严重。Apergis等[32]利用美国1971—2004年的数据检验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3)环境治理投资额(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vestment,EGI)。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作为污染防治的末端治理与前端预防,对于遏制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作用。王鹏等[33]以我国30个省市相关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要素投入产出的视角构建包含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指标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污染治理投资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金投入上。石龙宇等[34]指出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应增加城市环境污染处理的投入,并改进城市环境污染处理技术。
(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PGDP)。能源技术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需的增长动力,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可以提高能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进而优化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经济发达地区为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会更加依赖外部先进的技术水平来优化资源配置[35]。Zhang等[36]对中国1991—2006年的与能源消费有关的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并利用 Kaya方程进行因子分解,得出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增长仍然是驱动中国碳排放量增加的最重要的因素。
2.3 数据
变量数据来源于多个数据库,其中“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比例”、“能源消耗总量”、“环境治理投资额”数据源于2011—2017年各年度《中国环境年鉴》;“工业化率”和“人均GDP”数据根据2011—2017年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数据时间跨度为2011—2017年,涉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共计210个样本。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PCDM为各地区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企业比例;IR为各地区工业化率;TEC为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EGI为各地区环境治理投资额;PGDP为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其中PCDM的计算方式是:先从《中国环境年鉴》获取“清洁生产当年审核企业数”和“当年强制性审核完成数”,两者之差记为“当年自愿开展清洁生产企业数”,这一指标与“清洁生产当年审核企业数”比值即为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比例
记2011—2012年为非实验期,2013—2017年为实验期;“两省五市”为实验组,其他地区为对照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两省五市”中涉及广东省与深圳市,为避免重复计量,下文分析中取广东省样本,即实验组分别为:湖北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庆市。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3.1 双重差分参数估计
在综合考虑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后,采用WHITE稳健性估计,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模型拟合系数逐渐增大,其中模型5的R2为0.2623;Group×Event系数值较为稳定,且显著,t值为2.70,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碳交易权试点地区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比其他地区平均高出22.03%。观察模型5控制变量系数:一是工业化率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工业化率越高的地区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不强,这与目前全球发达城市普遍认同的“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二是人均GDP的对数系数显著为正,即越富裕的地区越有利于清洁生产机制构建。其他控制变量系数不显著。

表2 双重差分参数估计
(1)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2)*、**、***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为进一步分析碳交易权试点对地区环境的影响效应,分别将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和二氧化氮(NO2)年平均浓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DID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碳交易权试点地区PM10、SO2和NO2的年平均浓度平均比其他地区要低0.0288、0.0170和0.0105 mg/m3,且在统计意义上均显著。这说明,碳交易权试点政策对地区环境改善起到明显效果,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表2实证分析的稳健性。

表3 环境效应的参数估计
3.2 分位数回归参数估计
由于均值回归的参数是自变量对因变量条件期望的边际效果,如果能够估计出若干重要条件分位数的分布,则能对整体分布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借助Koenker等[37]提出的分位数回归(Regression Quantiles)对模型1进行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随分位数增加,Groupit×Eventit系数呈现先降后升趋势,但高分位系数不显著。这说明,碳交易权试点对于当前清洁生产水平较低的地区,提升企业清洁生产意愿效果更为明显。这一趋势也可以从图2交互项分位数回归系数变化中进一步得到验证。

表4 清洁生产意愿的分位数回归

图2 交互项系数随分位数变化图 Fig.2 Trend of interaction term coefficient with the different of quantiles
3.3 清洁生产意愿地区差异分解
根据2.1节所介绍的不同分位数下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均值差异的计算方法,可分别计算由于经济发展特征不同所引起的“特征差异”和由于回归系数不同所引起“政策歧视”,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取λ=13)。结果表明:第一,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企业自愿开展CDM的比例差异受系数差异和特征差异的共同影响;第二,碳排放交易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企业自愿开展CDM的比例差异在低分位、中分位和高分位呈现倒U型,即在低分位和高分位地区差异较小,而中分位差异较大;第三,企业自愿开展CDM的比例差异在低分位时主要受试点政策影响(即系数差异),在高分位时主要受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影响(即特征差异),而在中分位时两种影响力量较为均衡。以上结论可通过取λ=99计算出所有分位数上的差异值作进一步验证。如图2所示,在分位数1%—99%上采用自助法(本文取reps=100)做分位数回归,得到τ个分位数下的相应回归参数估计,受篇幅所限,不同分位数下的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以及方差值不在文中列出。由图3可知,总差异在低、中、高分位呈现倒U型结构,且在低分位时总差异主要受系数差异影响,在高分位时主要受特征差异影响。

表5 不同分位数上试点与非试点地区CDM差异分解
总差异(Total differential, TD); 特征差异(Characteristic differential, CHD); 系数差异(Coefficient differential, COD); 影响程度(Influence level, IL)

图3 CDM地区差异随分位数变化图 Fig.3 Trend of pilot and non-pilot areas CDM′ differential on all of the quantiles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2012年国家发改委提出的“两省五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中国各地区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影响,并通过分位数分解方法分析了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特征差异与系数差异,以期为我国科学推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供参考。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试点地区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比例比非试点地区平均要高出22个百分点;(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当前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比例较低的地区影响程度更为显著;(3)试点地区环境改善效果明显,PM10、SO2和NO2的年平均浓度显著下降了0.0288、0.0170和0.0105 mg/m3。
综合上述结论,本文建议:(1)鉴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区域内生产单位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为了科学有序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除“两省五市”试点地区外,下一步应优先推广CDM项目较为聚集的地区(如四川、云南、内蒙古、甘肃和河北),这些地区开展清洁生产的外部环境优势明显,边际成本较低,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2)在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比例较低的地区(如海南、新疆、青海、贵州和陕西)政府要加大CDM项目的宣传工作,强化企业的节能意识、环保意识以及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合作意识,这些地区在清洁发展机制的构建上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各地政府可结合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优势,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与CDM相关的招商引资项目。(3)各地区应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加快自身产业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助力企业开展并提升清洁生产技术,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耗,同时加大环境治理投资额,引导企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促进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38]。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国内CDM项目数据库系统暂未公布各地企业具体的清洁生产数据,因此本文还无法研究企业层面的生产行为,取而代之的是运用基于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研究地区层面企业的清洁生产意愿以及对地区环境改善的效果。随着政府对清洁生产机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将在收集企业层面的样本数据后做更为深入细致地微观研究进而弥补以上不足。
致谢: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CDM项目数据库的给予支持;Godwin Seyram Agbemavor Horlu帮助写作,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