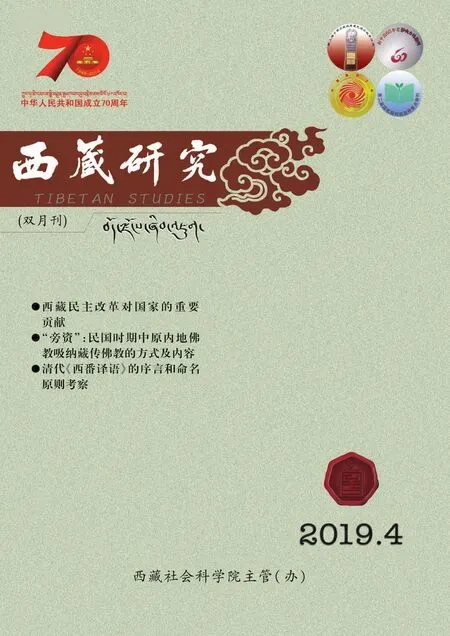炳灵寺第3窟观无量寿经变辨析
赵雪芬 贺延军 曹学文
(甘肃省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甘肃 永靖 731600)
唐朝中期,炳灵寺石窟建设已初具规模,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炳灵寺一带归吐蕃统治,敦煌出土的吐蕃文《编年史》第111条:“至虎年(762年),尚结息与尚悉东赞等越凤林铁桥,率大军攻克临洮军、成州、河州等众多唐廷城堡。”[1]凤林桥在炳灵寺石窟东南500米处的位置,此后,炳灵寺石窟一直处在宋、唃厮啰、西夏等民族政权更替和战乱之中,致使炳灵寺僧侣逃散,宫殿渐坏,佛事衰败。13世纪,蒙元中央集权建立,西藏首次成为元中央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实行“政教合一”的治藏政策。在中央设总制院,由西藏萨迦派八思巴掌管,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明代,仍沿用元代的僧官制度,采用“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藏传佛教在雪域高原兴盛,并迅速向内地传播。炳灵寺位居青藏高原与中原的交接地带,受藏传佛教东传的影响,炳灵寺石窟开始转型,汉僧转为番僧,汉式建筑改为藏式建筑。明成化元年(1465年)“(河州)守镇都阃蒋公玉游窟,像露宇倾,发心修造”[2],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开始兴起,经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不断修建,炳灵寺寺院建筑不断向大寺沟上游、黄河沿岸延伸,出现了“炳灵寺每遇孟夏季冬八日,远近来游及远方番族男妇不可以数计”[3]的繁荣局面。
一、《观无量寿经》的翻译和流行
《观无量寿经》,梵文Amitāyurdhyāna-sūtra,又称《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佛观经》《无量寿观经》《十六观经》,简称《观经》,为大乘佛教经典,与《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合称净土三经。
《观无量寿经》的翻译是净土三经中最晚的一部,但后来居上,在净土信仰中影响巨大。南北朝时期,南朝佛教空前盛行,出现了“都下佛寺五百余所”“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西域三藏法师畺良耶舍远冒沙河,来到建业(南京),在道林寺首译《佛说观无量寿经》一卷。《高僧传》卷三:“畺良耶舍,此云时称,西域人……以(宋)元嘉(424—453年)之初,初至钟山道林精舍,沙门宝志崇其禅法,沙门僧含请译药王药上观及无量寿观。含即笔受。”[4]这是目前有关《观无量寿经》翻译最为详细的记载。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发展至南北朝时期,佛经的汉译本数量已很多,经录开始逐渐完备。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出三藏记集》(梁释僧佑撰),收录了东汉至南朝梁期间的所有佛教经典,《出三藏记集》载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观无量寿经》一卷”[5]。文献只记录了经名,没有交代译者的姓名。隋代沙门法经等撰的《众经目录》中记载“《无量寿观经》一卷,宋元嘉年畺良耶舍于扬州译”[6]。唐代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卷五:“《无量寿观经》一卷(亦云无量寿观经初出见道慧宋齐录及高僧传),《观无量寿经》一卷(第二出与畺良耶舍出者同见《宝唱录》)。”[7]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宝唱录》中收录了《观无量寿经》的两个异译本,一者为畺良耶舍译本,另一译本作者不详,《宝唱录》(梁代宝唱撰)已失佚,其余经录中只收录了畺良耶舍的译本,另一译本的真实性还需商榷。现在流通畺良耶舍的《佛说观无量寿经》译本,梵文本、藏文本已不存。
《观无量寿经》讲述了释迦牟尼佛与众比丘、菩萨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此时王舍城太子阿阇世受恶友教唆,将父王频婆娑罗王幽禁。王后韦提希炒蜜涂身、璎珞盛浆,为国王提供食物,佛弟子目犍连、富楼那为国王说法,国王精神状态良好,阿阇世得知真相后欲弑杀母后,韦提希被幽禁,感到无比绝望,祈求释迦牟尼佛为她指示离开苦难之路,释迦牟尼讲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景象,并介绍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主要方式是“修三福”和“十六观”。“修三福”是前提,“十六观”(日观、水观、地观、宝树观、宝池观、宝楼观、华座观、像观、真身观、观音观、势至观)是途径,通过十六种观想即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在西方净土佛教经典中,《观无量寿经》是一部颇具戏剧性的佛经,以王舍城宫廷政变故事为缘起,大力渲染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景象,西方净土如此美妙,令人心动神移,如何到达,佛陀指示了到达的途径——观想,观日、观水、观地、观树、观佛……进而观整个极乐世界,佛陀嘱咐韦提希及众生“系念谛观”不要放弃,阿弥陀佛在不远处等待你们的到来。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引人入胜。十六观即十六种景象,十六种景象组成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
《观无量寿经》以其“义理深邃,境相胜妙,一心妙观,理事圆融”的特质被信众推崇,佛经译出后,一些高僧大德更加热衷于传播净土信仰,很多名僧为其注疏立说,《观无量寿经》的注疏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净土经典。现存《观无量寿经》注疏从隋至清代有16部之多,隋唐时期达到高峰。隋代沙门慧远撰《观无量寿经义疏》二卷、隋天台智者大师说《观无量寿佛经疏》一卷、隋代胡吉藏撰《观无量寿经义疏》一卷、唐代沙门善导集记《观无量寿佛经疏》四卷、唐代法聪撰《释观无量寿佛经记》一卷,其中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四帖疏》)影响最大,这些注疏也将净土法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高僧皈依净土法门后,宣讲、注疏净土经典,使净土法门的宗义臻于完备,最终成为一大宗派——净土宗。
宋至清代注疏持续不断,有宋代四明沙门知礼述《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六卷、《观无量寿佛经融心解》一卷、宋代释元照述《观无量寿佛经义疏》三卷、宋代戒度述《观无量寿佛经扶新论》一卷、《观无量寿佛经义疏正观记》三卷、明代传灯撰《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图颂》一卷、清代续法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直指疏》一卷、清代彭际清述《观无量寿佛经约论》一卷、清代杨文会撰《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略论》一卷、敦煌本佚名《观无量寿佛经义记》一卷,这些注疏从不同角度对《观无量寿经》进行了解读,为净土信仰不断注入新的理论基础。炳灵寺石窟藏传佛教壁画以尊像为主,经变画较少,现存经变画以西方净土变为主,保存完整,如第70窟西壁《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经变画,藏传佛教净土信仰可见一斑。
二、第3窟西壁壁画
第3窟位于炳灵寺下寺石窟群最南端入口处,为大中型窟。石窟开凿于唐代,窟高3.52米、宽3.40米、深3.10米,平面方形、平顶。窟中心立石雕唐仿木构建筑佛塔一座,南壁上下各开凿一佛龛,内雕佛、菩萨像。明代,窟内壁画被重绘成藏传佛教内容,壁画采用工笔重彩技法。现窟顶壁画大部分脱落,四壁及佛塔壁画保存完整。
第3窟西壁(正壁)呈正方形,是该窟中最重要的位置,壁画从上至下分为3个区域,即顶部、中部、下部。顶部为尊像画,中部为经变画,下部为尊像画,中部是壁画的核心区,该区域从中间一分为二,绘两幅大型的经变画,南侧经变画就是本文讨论的部分(见图1)。
西壁南侧壁画主像为一佛二菩萨像,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背项光外有六挐具。佛背屏外顶部、左右两侧绘三朵盛开的大莲花,花生两茎,莲茎向上下、左右两侧伸展,形成6个莲座,每个莲座上有一坐佛像。壁画上有河流、树木、宫殿,网格纹地面,莲花、荷叶错落有致地点缀其间,地上有幢、伞、瓶等宝物,还有面向河、树、宫殿、佛双手合十跪拜者(见图2)。
图1:第3窟西壁壁画
《观无量寿经》:“而尔时世尊放眉间光。其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还住佛顶。化为金台如须弥山。十方诸佛净妙国土。皆于中现。或有国土七宝合成。复有国土纯是莲花。复有国土如自在天宫。复有国土如颇梨镜。十方国土皆于中现。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严显可观。”[8]
将佛经与壁画比对,佛经中世尊用眉间光示现十方无量世界,壁画中间主像一佛二菩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佛主无量寿佛及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主像顶部、左右两侧坐于莲台上的6尊小佛像,代表其余诸方净土。每朵大莲花中伸出的2根莲茎,曲曲折折托起一座莲座,恰似6座缓缓升起在虚空中的十方净土,下面皈依者双手合十,仰视跪拜佛像,画面立体感十足。国土有七宝、莲花、宫殿等,壁画所展现的内容与佛经描述的情节完全吻合。
《无量寿经》极乐世界环境有精舍、宫殿、树木、七宝莲池、八功德水等,强调众生听到或念诵“无量寿佛”名号或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通过莲花化生即可到达。《阿弥陀经》极乐世界环境有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宝楼阁、七宝池、八功德水、四色莲花、命命鸟、妙音鸟、白鹤等。强调念诵“阿弥陀佛”名号,即可往生极乐世界。《观无量寿经》极乐世界环境中有宝楼、琉璃地、七重行树、八功德水,强调“观想”往生极乐世界。纵观“三经”的极乐世界环境和往生途径,“三经”所描述的环境都很殊胜,但构成要素不尽相同,《观无量寿经》环境中没有七宝莲池。《无量寿经》以持名念佛往生极乐净土,《观无量寿经》进一步发挥了《无量寿经》的净土思想,以观想念佛为实修,两者区别在于实修方式不同。
《观无量寿经》的主要内容为“十六观”。水观:“想见西方一切皆是大水……既见水已当起冰想。见冰映彻作琉璃想。”地观:此想成已。见琉璃地内外映彻。下有金刚七宝金幢。擎琉璃地……琉璃地……楼阁千万百宝合成……是为水想。名第二观……佛告阿难及韦提希。水想成已。名为粗见极乐国地。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不可具说。是为地想。名第三观。”[9]
西壁壁画左上角有一河流,河水清澈,河边一人头戴花冠,上身袒,下着绿裙,手持莲花,双手合十,面向河水跪拜,此人应为“闭目开目”作观想的韦提希。整幅壁画底图为1厘米见方的菱形网格纹,网格内有绿、灰各色宝石组成的莲花纹,网格线条清晰、图案精细、色彩雅致。壁画顶部有2座楼阁,网格纹地面上有宝幢、宝瓶等。此网格纹地应为佛经中的琉璃地,“琉璃地,内外映彻,地以黄金绳杂厕间错,以七宝界分齐分明。”壁画所展现的河水、琉璃地、宝幢、楼阁以及河边观水者的景象,与佛经表述的水观、地观完全吻合。地面绘画工整细致、富丽工巧,画师用细腻的工笔绘画技法极力表现出了极乐世界“琉璃地”的透彻和唯美。
宝树观:“此观宝树。观宝树者。一一观之作七重行树想。一一树高八千由旬。是为树想。其诸宝树七宝花叶无不具足……叶叶相次。于众叶间生诸妙花。花上自然有七宝果……观见树茎枝叶华果。皆令分明。是为树想。名第四观。”[10]
壁画顶部绘一排整齐大树,大树树干粗壮、枝叶茂盛,绿、灰色相间,共7棵,这7棵大树象征着佛经的“七重行树”。树下一人头戴花冠,上身袒、下着裙,双膝跪地、双手合十,为“闭目开目”观想者。
八功德水观:“次当想水。欲想水者。极乐国土有八池水……分为十四支。一一支作七宝色。黄金为渠。渠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一一莲华团圆正等十二由旬……从如意珠王踊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色鸟。和鸣哀雅。常赞念佛念法念僧。是为八功德水想。名第五观”。[10]
壁画上有一条小河,始于右上角止于左下角,河水清清,泛着波澜,水中朵朵莲花盛开,莲叶漂浮在水面上,4只鸳鸯在水中游荡,河边一人面向河水,双手合十,双膝跪地,画面恬静自然,充满田园生活的气息。《观经》“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百宝色鸟”等要素与壁画场景布置一一对应。
宝楼观:“众宝国土。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楼。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作天伎乐。又有乐器悬处虚空。如天宝幢不鼓自鸣。此众音中。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此想成已。名为粗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是为总观想。名第六观。”[10]
壁画顶部左右两侧绘硬山顶楼阁,楼阁有飞檐、斗拱,基座下有飘带,似空中楼阁,这两座楼阁即佛经中的宝楼。观者观至第六观时,已粗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等景象。
花座观:“无量寿佛住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是二大士侍立左右……未来众生。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佛告韦提希。欲观彼佛者。当起想念。于七宝地上作莲花想……此莲花台。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是为花座想。名第七观。”[10]
壁画主像为一佛二菩萨,佛高肉髻,面丰圆,着袒右肩袈裟,双手与腹前做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背项光两侧对称分列六挐具,即大象、狮子、童男、龙女、鲸鱼、大鹏鸟。头光两侧对称绘十身跪拜弟子像。佛两侧侍立二菩萨像,菩萨珠宝、璎珞庄严,一手持花蕾,一手自然下垂,立于束腰莲台上。壁画展现的场景与佛经花座观情节基本一致。
《观无量寿经》将往生西方净土者,因众生“业报”不同,分为三辈,每辈又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往生西方的方式各不相同。壁画顶部宫殿旁边有全开、半开、含苞的莲花,一弟子手持莲蕾、双膝跪在全开的莲花上,应为上辈往生者;一朵莲花半开,应为中辈往生者,一朵莲花含苞待放,应为下辈往生者,寓意明确。
三、小结
炳灵寺石窟藏传佛教壁画中,西方净土思想表现突出,无量寿、阿弥陀尊像及代表西方净土的三佛题材很多,几乎每个藏传佛教洞窟中都有所表现,无量寿经变、阿弥陀经变等大型西方净土经比重大,西方净土信仰在当时颇为流行。
第3窟西壁壁画为观无量寿经变画,画中有明显的“观想”情节,壁画内容与《观无量寿经》表述的情节一一对应。“十六观”从壁画顶部左端为起点,向右端逐次观之,最后观中间主像——西方极乐世界佛主,依次为水观、地观、宝树观、宝楼观、八功德水观、华座观,这些景观最终组合成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共同体。
壁画绘制巧密而精细,构图具有透视效果,立体感强,是藏传佛教壁画中的上乘之作。画中人物主次分明,树木、河流、植物、动物布局疏朗有致,展现出了一个自然和谐充满生活气息的西方佛国净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