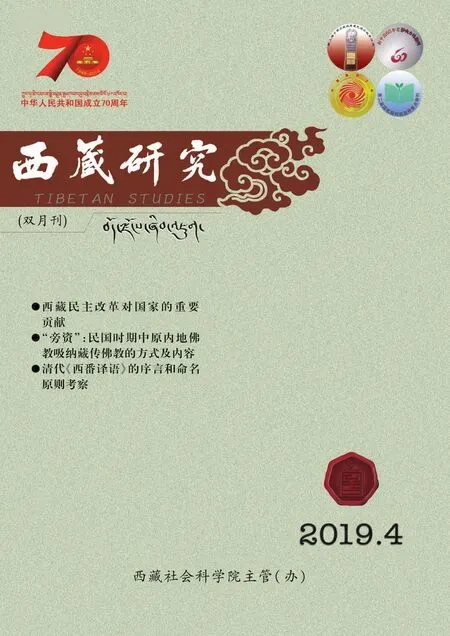俄国藏学家齐比科夫及其藏传佛教著作
何冰琦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一、引言
俄罗斯汉学与西方汉学、东方汉字文化圈共同构成当今国际汉学的三大板块,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1。藏传佛教研究隶属于藏学范畴,藏学是俄罗斯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藏学家是国际藏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俄国藏学萌芽于17世纪末,“有一位叫库利文斯基(П.И.Куль винский)的翻译于1696年在履历中称自己是‘卡尔梅克语、蒙古语和唐古特语翻译。’”[2]直至18世纪20年代在位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阿卜赖寺(Аблайн-хит,早在18世纪初该寺就已经存有藏文的抄本和刻本[3])中发现了藏文抄本后,俄国开始或多或少地对藏文产生了兴趣[4]。此后,俄国学者伊·施密特(Я.И.Шмидт,1779—1847年)等人(1)具体包括奥·科瓦列夫斯基(О.М.Ковалевский,)、梅赛施密特(Д.Г.Мессершмидт,1685—1735年)、格·米勒(Г.Ф.Миллер,1705—1783年)、帕拉斯(П.С.Паллас,1741—1811年)和伊耶里格(И.Ериг,1747—1795年)。搜集到了第一批藏文文献,激起了俄国与欧洲对藏学研究的兴趣(2)阿卜赖寺发现的藏文抄本以单页的形式被运送到彼得堡,彼得一世的图书管理员舒马赫(Шумахер)与欧洲学术界有着广泛联系,他于1722年将抄本的一页寄给了巴黎科学院,委托后者进行科学鉴定及翻译。尽管彼时欧洲已经刊登了众多去过西藏的旅行家的消息,并从1708年开始尝试在尼泊尔和西藏传播天主教,且试图刊登关于传教团活动的消息,然而旅行家们并没有获得对认识藏文有价值的资料,传教团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还没有出版,鲜为人知。分析此页抄本的任务委托给了著名的法国东方学家艾蒂安·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和迈克尔·傅尔蒙(Michael Fourmont)两兄弟,二人幸运地找到了法诺(Giovanni de Fano)的拉丁语——藏语词典手稿,在其帮助下准确地鉴定出抄本上写的是藏文。然而他们并未能借助该词典的手稿给文章标注音标,也未能翻译其字面意义及内涵。在整个18世纪,直到雷慕沙之前,欧洲汉学家一直都在研究阿卜赖寺的藏文抄本,见Востриков А.И.С.Ф.Ольденбург и изучение Тибета//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Том IV.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1935.с.62—64,由此可见俄国发现的藏文手抄本成功吸引了欧洲学者的注意。,为俄国藏学从搜罗资料阶段向科学研究阶段过渡创造了条件。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藏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说进入了繁荣时期(3)该时期涌现出了大量藏学家,其构成复杂,主要包括以王西里(В.П.Васильев,1818—1900年)、希弗涅尔(А.А.Шифнер,1817—1879年)、米纳耶夫(И.П.Минаев,1840—1890年)为代表的学院派藏学家以及以普尔热瓦尔斯基(Н.И.Пржевальский,1839—1888年)为代表的一大批探险者或旅行者。此外还有为沙俄侵略西藏效犬马之劳的政治投机者巴德玛耶夫(П.А.Падмаев,1849—1920年)、德尔智(Агван Доржиев,1853—1938年)和乌里亚诺夫(Дамба Ульянов)等。这些人对西藏的地理、历史、宗教和文化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研究,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色。见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8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轻一代学者又将俄国藏学推向新的高度,其中就包括布里亚特藏学家齐比科夫,“他为俄国的藏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俄国了解西藏最深的一位学者”[5]。
二、生平简介
贡博扎布·齐比科维奇·齐比科夫(Гомбо жаб·Цыбикович·Цыбиков,1873—1930年)于1873年4月生于外贝加尔赤塔县,5岁就跟随父亲学习蒙文,7岁被送入阿金斯科耶教区学校,11岁进入赤塔县男子中学,1893年作为优秀毕业生免费进入托木斯克大学医学系。然而仅上了一个学年他就打算转学东方学,并前往库伦为此做准备。齐比科夫于6月3日从库伦出发,向西直到蒙古西部鄂尔浑河上游的喀尔喀蒙古,6月26日返回库伦。旅行期间他接触了藏语、藏传佛教以及蒙古的风俗与文化,研究了沿途所有的古迹和寺庙,主要包括度母庙(4)齐比科夫详细地记录了寺庙情况,坐落在哈拉河左岸,包括一个中央大殿、4个配殿以及其周围一些藏传佛教僧人居住的小房屋。常住僧人有50人,逢呼拉尔集会可达到500人。详见Цыбиков Г.Ц.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Т.2.О центральном Тибете,Монголии и Бурятии.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1981.c.103。、阿穆尔—巴雅思忽朗图寺(5)阿穆尔—巴雅思忽朗图寺,汉名敕建庆宁寺,北喀尔喀最大的圣地之一,坐落在布隆汗山(Бурун-хан)南麓,在喀尔喀人中间威望很高。修建历经三代,始于康熙,雍正时竣工。寺中供奉的保护神扎木萨朗(Чжамсаран),被视为温都尔格根及其寺庙的保护者。详见Позднеев А.М.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 ы.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ездки в Монголию,исполненной в 1892—1893гг.Т.1.Дневник и маршрут 1892года.СПб.:Тип.Имп.акад.наук,1896.c.24、35。、额尔德尼召(6)当地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建于1586年,坐落在蒙古旧都哈拉和林附近,由阿巴岱汗创建。、大清王庙(温都尔格根庙)、祖苏默等,颇为细致地介绍了各大寺庙的建寺传说、外观及内部布局等。齐比科夫将其旅行见闻记录在考察日记《蒙古之行》中,收录在《齐比科夫著作选》第2卷,于1981年出版。齐比科夫“在库伦的学习十分成功”[6],他于库伦之行归来后即1895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毕业时获一等奖状及金质奖章。自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毕业后,齐比科夫受俄国地理学会委派化装成佛教香客前往西藏进行考察,彼时清政府及西藏噶厦禁止外国人入藏,但生于亚洲各国的佛教徒除外。由于齐比科夫此前就对藏传佛教有所研究,再加上他是布里亚特蒙古人,精通蒙、藏等语言,可以化装成前往西藏朝圣的蒙古人深入西藏,因此他被地理学会选中,受命前往西藏进行秘密的全面考察。1899年11月25日他随骆驼商队从库伦出发,于1900年8月3日来到拉萨,在西藏逗留至1901年9月10日,其间他遍访西藏主要城市和宗教中心,包括大小昭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泽当寺、桑耶寺等,直到1902年5月2日才返回恰克图。此次考察成果丰硕,他不仅在旅途中拍摄了大量照片,还收集了大量佛教经籍和其他书籍,共计333卷藏文刻本,其中包括十分珍贵的藏传佛教文献——“108卷《甘珠尔》和225卷《丹珠尔》,是极其稀有的纳唐版书籍,由印度人、藏族人及其他作者编纂,内容涉及佛教、哲学、历史、医学、逻辑学、语文学”[7]“由于齐比科夫的西藏之行,使得俄国的东方学获得了有关这个古老佛教圣地及其首府的最新资料,从而在俄国和欧洲东方学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5],他所搜集的资料也成为俄国东方学家进行藏学研究包括佛教研究的主要依据,此次考察对俄国的藏传佛教研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得益于此,齐比科夫回国后即被“培养东方政治、工商活动人才”[8]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7)上世纪末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第二大教育中心,被称为“俄罗斯的应用东方学中心”。根据沙皇政府的想法,东方学院应当培养外事部政府官员、指挥部人员、军用以及民用翻译,主要研究的是远东的现代东方语言和国家。东方学院因此而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学中心,在研究远东各国的文化、历史和经济领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东方学院的蒙古和西藏语言及文化研究同齐比科夫紧密相连,自波滋德涅耶夫之后,齐比科夫在这里教授蒙语语言文学,自1907年始他在这里教授藏语……齐比科夫应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藏语研究的首倡者与奠基者。详见Жигмитов Д.Б.Новые данные о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Ц.Цыбикова.//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профессора Г.Ц.Цыбикова.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 статьи.Улан-Удэ:Бурят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76.с.149-150;Цыренов Д.Ц.К оценке научного 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профессора Г.Ц.Цыбикова.//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профессора Г.Ц.Цыбикова.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 статьи.Улан-Удэ:Бурят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76.с.185。聘为讲师,“直到十月革命前他都在这里执教,为东方学院的科学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9]。1917年申请退休后他开始致力于家乡的教育组织工作,1928年受邀前往伊尔库茨克大学执教直至离世。纵观其一生可知,齐比科夫不仅是旅行家,还是“伟大的藏学家、宗教学家、民族学家、蒙古学家、语言学家、布里亚特教育学家”[10]。
三、佛教著作
西藏考察成功归来后,齐比科夫已具备跻身藏学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条件,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藏传佛教的著作。齐比科夫的著作中有着大量关于佛教团体和内部生活的资料,这些资料并不是所有局外人都能得到的,他对所到之处的详细而深刻的描写,甚至单凭其拍摄的大量照片都能使他的著作成为同时代人中的一流著作,其研究至今仍有极大的科学价值与文献价值[11]。
(一)《西藏中部》
1903年5月2日,当《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尚未出版时,齐比科夫就已经根据考察日记写好了西藏之行的先行报告《西藏中部》(О центральном тебете),将西藏之行最为重要的结论都记录在这一报告中[10]30,受到了俄国地理学家和东方学家的高度评价。报告在当年出版,不仅引起了俄国人的关注,还引起了国外人的兴趣,被译成英语于1904年在华盛顿出版[6]。该书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寺庙,作者主要介绍了宗喀巴创建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包括其地理位置、规模、僧侣人数,着重介绍了僧侣的教育(8)齐比科夫在《西藏中部》中认为,藏传佛教寺庙与其说是隐世的苦行僧的避难所,倒不如说是僧人们的学校,其教授范围从文字启蒙到神学知识。任何年龄的人在剃度后都被视为寺庙的一员,根据寺庙的章程接受教育。他们学习的课程主要为神学哲学,包括五大教义,后者主要包括印度班智达编写的教义以及藏译本中的教义。在宗喀巴改革后,各派学者都遵循宗喀巴的学说对这些教义作出了解释。详见Цыбиков Г.Ц.О Центральном Тибете//Известия РГО.Т.39,вып.3.СПб,1903.c.204。及寺庙管理(9)达赖喇嘛为这些寺庙的最高领导者,在甘丹寺设有宗喀巴代理人这一职务,以前由甘丹寺僧人来选举这一职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选举导致的不和使得人们确立了新的任职方法,即由两派当地人轮流选举僧人担任自己所在扎仓的高级职务,任期为6年。十分有趣的是,关于寺庙的管理齐比科夫写道,纪律或整个规章都建立在“对统治者的恐惧”之上,这种恐惧也体现在街面儿上,僧人甚至不敢在街上与达赖喇嘛碰面,在极少数碰面的情况下,僧人应当用布盖住头,躺着一动不动就像死了一样。详见Цыбиков Г.Ц.О Центральном Тибете//Известия РГО.Т.39,вып.3.СПб,1903.c.203—204、216。;二是藏传佛教人物,主要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提及金瓶掣签制度(10)作为西藏中部地区的世俗和宗教首脑,达赖喇嘛负责当地的统治。直至1822年即十世达赖喇嘛选举时,达赖喇嘛的推选仍然由高级喇嘛和预言家任命,然而在选定十世达赖喇嘛时,首次实行了乾隆时期确立的“金瓶掣签”法。将三个按此前方法选定的候选人的名字写在单独的纸条上,此后放入金色的投票箱中,这个箱子先放在释迦牟尼的雕像前,寺中代表就准确选定转世者这件事在箱子旁边做祷告。然后将箱子放入达赖喇嘛的宫殿之中,当着西藏高层统治者和几大主要寺庙代表的面,清王朝任命的驻藏大臣用两根筷子从签中抽出一张,签上的人就成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二大人物,如果说班禅额尔德尼在官方政权上不如达赖喇嘛的话,那么在藏传佛教教徒眼中班禅比他的神圣高得多。班禅比起达赖喇嘛更容易让百姓接近,正因为这一对百姓的感召力,在当地甚至距拉萨更远的地方人们仅将达赖喇嘛视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而非教徒,不论其属于哪一派,都将宗教情感付诸在自己的保护神即班禅身上。详见Цыбиков Г.Ц.О Центральном Тибете//Известия РГО.Т.39,вып.3.СПб,1903.c.211、213。;三是佛教与萨满教(11)笔者直译而来,实际指西藏本土的苯教。的斗争,作者指出“佛教受到西藏统治者的保护理应得到传播,但还是在同萨满教的艰难斗争中做出了让步”(12)详见Цыбиков Г.Ц.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2-е изд.,перераб.-Т.1:Буддист паломник у святынь Тибета.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1991.c.205—206。。
(二)《菩提道次第广论》译注
《菩提道次第广论》(《Лам-рим Чэн-по》)译注是齐比科夫的主要佛学遗产之一,他在1910年的蒙译本序言中写道:“1899年我前往中部西藏考察就是为了了解北传佛教或藏传佛教的理论学说,将宗喀巴的名著《菩提道次第广论》翻译成俄文。”[12]1,他在西藏白居寺(Монастырь Пелкор-Чёде)附近等商队组齐时就学习了宗喀巴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11],回国途中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执教期间他一直在翻译此书。
1.1910年蒙译本
齐比科夫为蒙译本写了一篇长序,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佛教在蒙古的传播史,秉持着“西方国家及其民族受阿拉伯文明和伊斯兰教的影响,而东方国家则受中国文明以及藏传佛教的影响”这一观点,作者主要研究了佛教是如何影响蒙古人的[12]6;第二部分为佛经翻译,作者分析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阿加地区、霍林斯克地区和北京译本,探讨了《甘珠尔》和《丹珠尔》蒙译的原则等。
2.1913年俄译本
作者在序言《宗喀巴及其〈菩提道次第广论〉》(《Цзонхава и его сочинение Лам-Рим Чэн-По》)中指出,蒙古人的全部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都建立在藏传佛教基础之上,他们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都来自于藏传佛教[13]51,齐比科夫介绍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奠基人宗喀巴及其教派对如今蒙古生活体系的影响[13]51,勾勒了西藏藏传佛教发展的总体特点,根据藏文传记文献记述了宗喀巴的生平,详细描写了其研习、传播佛教的整个过程,简要介绍了他所创建的格鲁派及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提及显宗学校研究佛教哲学的新办法、礼拜仪式和圣像画领域的改革。在翻译过程中,作者研究了大量的藏文、蒙文宗教哲学文献,使用了能找到的所有佛教文献,因此其俄译本包含了印度、西藏、蒙古以及中原佛教布道者的珍贵且全面的消息。译文附有内容丰富的注解,且描述了藏文和蒙文版的《甘珠尔》《丹珠尔》中大部分文献的特点,详细解释了具体的宗教哲学术语,就佛教哲学的主要部分做了图书目录,最后解释了各大地理名称。作者在译文中叙述了阿罗汉、辟支佛以及菩萨的主要的佛教教义,为智力水平以及生活习惯不同的信徒讲述了佛教教义的基本情况。
3.《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
《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是齐比科夫最著名的藏学著作,“这部书被国外公认是研究近代西藏历史、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权威性著作之一”[5]。1919年该书由俄国地理学会首次出版(13)《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的出版日期至今仍莫衷一是,这是因为在这本书的封皮上写的是1918年出版,而在扉页上写的是1919年出版。为什么在同一本书的不同页上出现不同日期?想必这本书在1918年就排版了,而校样的审读和装订被耽搁了,于是这本书最终于1919年付梓。详见Жигмитов Д.Б.Новые данные о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Ц.Цыбикова.//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профессора Г.Ц.Цыбикова.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 статьи.Улан-Удэ:Бурят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76.c.152.该书于1981年作为《齐比科夫选集》的第1卷再版,1991年新西伯利又一次出版,1993年我国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献军的汉译版,2011年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出版社再一次出版此书。,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可归纳为佛寺、佛教人物和教义三大部分。一为寺庙,作者介绍了各大佛寺的外观、寺庙管理及僧侣的教育情况,包括土库木苏默寺、马勒桑·尔哈寺、塔尔寺(着重介绍了塔尔寺的扎仓和寺庙管理(14)可分为两部分:宗教管理和世俗管理。堪布是所有僧人的首领,即法台,负责宗教管理。法台由前几任法台的转世活佛中选出,任期3年。世俗权力掌握在三位官员手中,汉语称老爷,即大老爷、二老爷和三老爷,共同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管理寺内所有公有财产、耕地及生活在耕地上的农民。详见Цыбиков Г.Ц.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2-е изд.,перераб.-Т.1:Буддист паломник у святынь Тибета.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1991.c.46、47。)、拉卜楞寺、大小昭寺、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泽当寺、桑耶寺等,详细介绍了拉萨及近郊的寺庙(桑普寺、奇若勒莫伦寺、加东寺和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以及拉萨当地的佛教派别、造像朝拜及宗教活动的场景。二为藏传佛教人物,主要指达赖喇嘛以及班禅额尔德尼,作者颇为细致地介绍了一世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生平、地位及选拔体系(15)关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齐比科夫写道:“在世俗统治者之外,僧侣构成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最有文化修养同时也是贪图权力的人,他们对民众和统治者有着巨大影响。按照僧人的世界观,他们与王公几乎同一个等级。此外,根据藏传佛教教义,达赖喇嘛受戒后就注定了他们的宗旨是“为众生谋福祉”,所以他们理应比自己的弟子们位高一等。他们能够或多或少地捍卫自己的权力和自主性,甚至能让强大的地方当权者服从自己。详见Цыбиков Г.Ц.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2-е изд.,перераб.-Т.1:Буддист паломник у святынь Тибета.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1991.c.132—135.此外,齐比科夫就达赖喇嘛的选拔系统给出了十分准确的定义,将其定性为当地各大政治派别的斗争。详见Семичов Б.В.Г.Ц.Цыбиков-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Тибета.//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профессора Г.Ц.Цыбикова.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 статьи.Улан-Удэ:Бурят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76.с.58。,其中贯穿着西藏的历史及当权者的更替情况(16)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Гэндунь-дуб,1351—1474年)、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Гэндунь-чжямцо,1475—1542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Соднам-чжямцо,1543—1588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Ион-дан-чжямцо,1589—1616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Агван-Лобсан-чжямцо,1617—1682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Чжамбал-чжямцо1758—1804年)、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Лундок-чжямцо1805—1815年)、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Цултим-чямцо,1816—1837年)、十一世达赖喇嘛克珠嘉措(Хайдуб-чжямцо,1839—1855年)、十二世达赖喇嘛成烈嘉措(Приньлай-чямцо,1856—187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Тубдань-чжямцо),作者在论述十世达赖喇嘛时提到了清政府下达的金瓶掣签这一选择达赖喇嘛的方法。详见Цыбиков Г.Ц.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2-е изд.,перераб.-Т.1:Буддист паломник у святынь Тибета.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1991.c.144。;作者认为班禅额尔德尼是现代藏传佛教世界中等级最高的三大藏传佛教领袖之一,他在第十四章集中论述了该寺堪布即一世至六世班禅额尔德尼(17)一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1570—1663年,事实上这里的一世班禅为四世班禅,其前三世为追认的,齐比科夫在书中将其视为一世班禅,因为自他起固始汗授予了班禅称号,笔者注)、二世班禅名叫罗桑益西(1664—1737年或1739年)、三世班禅罗桑贝益西(1738—1780年)、四世班禅丹必尼玛(1781—1834年)、五世班禅丹贝旺秋(1855—1881年)、六世班禅曲吉尼玛(1883—1937年)。详见Цыбиков Г.Ц.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2-е изд.,перераб.-Т.1:Буддист паломник у святынь Тибета.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1991.c.187—188。,较为细致地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三为教义,同前两部分相比,该书对藏传佛教教义涉及并不多,作者简要介绍了格鲁派教义,列举了讲授其教义的“五部大论”:《释量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俱舍论》《戒律本论》[13]。
四、研究动机
(一)国家需要:西藏考察是沙俄侵略我国西藏计划的产物
1.沙俄政府主张利用藏传佛教推行侵略扩张政策
日本藏学家山县初男研究了西藏的历史,指出俄国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其用意有故耳,非真信佛教之故,盖利用僧侣为心腹,因而逞其政略上之手段”[14]283。沙俄政府在向西藏派遣“考察队”多次受挫之后,特别注重利用布里亚特、卡尔梅克蒙古人同西藏的宗教联系渠道,不断派遣人员入藏进行种种不可告人的活动,如齐比科夫即是这样的“秘密考察家”[14]252。对此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升泰曾报告:“蒙古人由草地来礼佛者,络绎不绝。随来人类,颇杂俄人,由北道前来”“俄人又飘忽靡常”[15]12。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俄两国在我国西藏的争夺进入白热化。乌赫托姆斯基(18)乌赫托姆斯基是俄国公爵,尼古拉二世的导师和密友,财政大臣维特的助手,主张利用僧人在亚洲推行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是“华俄道胜银行”首任行长,“东清铁路”董事,《彼得堡新闻》发行人兼主编,著有《论中国事件》(1900年)、《漫谈藏传佛教地区——论英国人进军西藏》(1904年),他曾多次来华活动,如1897年以特使资格率使团来华。参见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39页。作为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主张利用藏传佛教向亚洲推行扩张政策,他强调:“着眼于外交,必须利用我们藏传佛教徒的种族关系和他们对拉萨的精神向往”“在精神上征服和笼络这个藏传佛教地区”[16]3、56—58、128。1898年他将布里亚特僧人德尔智率领的第一个“西藏代表团”引荐给沙皇,代表团建议沙俄政府研究藏传佛教的政治作用,因此齐比科夫的秘密考察着重调查研究藏传佛教。
2.俄国地理学会处于沙俄政府控制之下,其活动具有政治性
大学毕业后齐比科夫成为俄国地理学会的一员,后者实际上受控于沙俄政府(19)会员大都来自军政两界,且十月革命前学会的两任主席都由皇室成员担任(康斯坦丁亲王,1845—1892年;尼古拉·米哈洛维奇亲王,1892—1917年),1846年公布的人员构成名单显示,128名正式会员中有63位等级不同的文官、59位等级不同的军官、1位无官职的院士、1名哲学副博士;在11位准会员中,有7位政府文官、3位大学教授、1名修道士。详见Состав.Записки РГО.СПб.: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т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846.с.1-9.转引自张艳潞《1917年前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第14页。四位副主席中有3位为位高权重的官僚学者(人员构成决定了学会的研究方向与内容,即“首先关注那些尚未被政府研究解决的问题”,故而俄罗斯学者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对无人探索的亚洲中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破译了许多“空白点”,将旅行结果公布于世,齐比科夫也是其中的一员。不仅如此,学会还受沙俄政府的资助,因此可以说地理学会实际上处于沙俄政府控制之下。,其对西藏进行的考察早已超出了纯粹的学术范畴,在他之前的考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受帝俄陆军部、外交部的直接资助和指挥,考察者多为职业军人,为了完成考察任务,多次向藏族民众开枪;二是具有明显的搜集情报性质,规模大,范围广,手段多;三是在从事所谓考察的同时完成政府交派的政治任务,在藏族上层中从事颠覆分裂活动[17]167—169。因此他被地理学会派往西藏考察藏传佛教,实际是为沙俄政府同英国争夺西藏服务,“潜入西藏拉萨,进行‘考察’,窃取了拉萨及其附近的情报,他是最早进入拉萨的俄国间谍之一”[18]59。
3.齐比科夫转学东方学是“巴德玛耶夫计划”的一环
巴德玛耶夫(1851—1920年)是外贝加尔地区的政治活动家,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1893年他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提出了“吞并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巴德玛耶夫计划”,受到沙皇和财政大臣维特的支持。他格外重视西藏,称它为从印度打开亚洲的钥匙:“谁将来统治西藏,谁就能统治青海,包括俄国佛教徒及四川佛教徒的整个佛教世界,就能统治整个中国”[19]132。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他亲自招募布里亚特蒙古人扮作商人和香客派往西藏。在托木斯克他早早就打听到了齐比科夫在学业上的成就、物质上的窘迫,给予其物质资助并建议他“离开医学系,转而研究东方学以及外交活动”[20]152,就这样间接促成了1899—1902年间著名的西藏考察(20)贝加尔国立大学库滋明教授(Кузьмин Ю.В.)提出,巴德玛耶夫和齐比科夫是近亲,巴德玛耶夫的母亲是齐比科夫父亲的妹妹。齐比科夫的父亲将年轻的巴德玛耶夫送到伊尔库茨克,后者对齐比科夫提供物质支持均非偶然。详见Кузьмин Ю.В.П.А.Бадмаев и 《Тибетский вопрос》:характер отношений с Агваном Доржиевым и Гомбожабом Цыбиковым.//В сборнике:Россия и Монголия:нов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д-р экон.наук,доц.В.А.Василенко,канд.экон.наук,ст.науч.Сотрудник А.Ф.Манжигеев.Л.Н.Крайнова(отв.секр.).Иркутск,2015.с.242.。从某种程度上说,齐比科夫转学东方学并前往西藏研究藏传佛教也是“巴德玛耶夫计划”的一环。
(二)个人因素
1.家庭影响
首先,齐比科夫的父亲保证其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古典式教育,为其今后研究藏传佛教打下了基础。父亲在齐比科夫5岁时亲自教他蒙文,2年后将其送入阿加教区学校,还是第一个将儿子送到赤塔中学的。与同乡人相比父亲很睿智,他教儿子的时候并没有灌输藏传佛教的深奥道理,而是进行了俄罗斯——欧洲式的教育(21)此前俄国古典汉学家如王西里、比丘林、巴拉第等人都是精通多种语言的“通才”,他们同时在满学、蒙学、藏学几个领域有不俗的成果。通才式教育是西方古典教育的一种模式,源于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教育精神,俄国因深受欧洲的影响也采用这种教育模式。参见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页。。其次,父亲在齐比科夫转学东方学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听到巴德玛耶夫提出要资助儿子去彼得堡学习时他十分感激,没让儿子说一个字也没问其意见,立刻将儿子送去了库伦[6]。齐比科夫亦坦言:“我遵从了家人和亲戚的意愿,放弃了医学系,在库伦又待了一年时间,于1895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6]最后,父亲始终陪伴并支持着齐比科夫的科研之路。当巴德玛耶夫不再资助齐比科夫时,父亲从阿加草原议会的志愿捐款中划出钱来支持儿子上完大学,齐比科夫得以从巴德玛耶夫的管束中解放出来[6]并继续从事东方学研究。西藏考察前,父亲又陪他一起为前往库伦做最后的行前准备,齐比科夫最终完成了考察藏传佛教的任务。
2.个人经历
受家庭尤其是笃信佛教的父亲影响,齐比科夫很早就开始接触蒙文及佛教。俄国的古典——通才式东方学教育为他今后成长为能同时运用多种语言的藏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首个从赤塔中学毕业的布里亚特人,获银质奖章,因此被巴德玛耶夫看中,并在父亲的影响下转而学习东方学,开始了其藏学研究。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期间,波滋德涅耶夫教授已经将其视为天才给予关注[21],毕业后齐比科夫决定从事科学研究,教授建议他动身前往西藏研究藏语以及“我们并不熟知的库库诺尔(Кукунор即青海湖,笔者注)和唐古特蒙古人”,以便回来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22],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西藏之行,进而推动了其佛教研究。
五、研究意义
(一)首创性
1.齐比科夫是首个深入西藏研究藏传佛教且顺利回国的俄国学者
俄国藏学研究历史悠久,成就斐然,藏传佛教是其重要内容。19世纪下半期以来俄国东方学家视东方人为“宗教的人”,将研究东方宗教作为理解东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根本途径[1]。沙俄东扩为俄国东方学家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提供了便利,因此在藏学研究方面,学者们更加重视从事科学考察活动。齐比科夫的藏传佛教研究成果几乎全部源于其举世闻名的西藏考察,他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的最大功绩在于他是第一个能够深入西藏研究藏传佛教且顺利回国的俄国学者。他根据此次考察撰写了举世闻名的佛教著作,第一次详细介绍了西藏各大佛寺的外观、寺庙管理、僧侣教育情况及主要的藏传佛教人物,为世人揭开了这个佛教圣地的神秘面纱。当时任何一位公开或秘密潜入西藏的外国旅行家都没能像齐比科夫那样自由地接近西藏地区这些宗教、政治和文化中心,并对其进行详尽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等方面的分析与评述[10]71,这使他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研究卫藏及其首府拉萨最富有成果的亚洲东方学家之一。
2.齐比科夫首次将宗喀巴定义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
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俄译本序言里,齐比科夫首次对东方学研究领域内业已形成的定论——宗喀巴是西藏佛教的改革家这一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将宗喀巴称为佛教改革家是不正确的,佛教改革从5世纪左右伴随着大乘佛教和达特罗的传入就早已经开始了”[12]64,因此宗喀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而非改革家,且“在他以前没有任何一个群体也没有任何一种信仰发展到如斯程度”[12]64。这一论点在研究藏传佛教的特征和性质时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应该指出的是:在俄国,从源远流长的佛学角度来研究宗喀巴的宗教活动及其广博的宗教哲学论著的,正始于齐比科夫[10]72。
(二)批判性
奥登堡认为,得益于欧式教育,齐比科夫能够完全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西藏,并在别人只会看一眼的地方仔细观察[23]。他在西藏考察时始终用学者的眼光看待所有他从未见过的事物,因此在反映西藏社会现状的同时也揭露了西藏现实生活中的消极面,他认为“百姓普遍贫穷大多是因为要养活大量的僧侣、地方财政收入有限而且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工业”[13]103,而这种普遍贫穷导致了穷人对富人的崇拜,富人利用金钱使穷人在他们面前低头[13]103。除了批判社会生活外,齐比科夫作为藏传佛教的研究者,其出色之处就在于,他冷静而持批判态度地研究了这一宗教和其在民众、僧侣的日常生活中以及在社会政治中的表现形式[5]71。作者对宗喀巴的教义也持客观批判态度,而且他从中看出了中亚民族文化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宗喀巴的教义使得大部分男性居民追求成为不婚僧侣,而在仅有宗教知识且缺少其他知识普及的情况下,这一教义已经造成了并还在造成世俗教育在藏传佛教徒中的普及度低下、居民人数的减少。”[13]70
(三)延续性
“自从齐比科夫西藏考察之后,俄国及国外藏学在资料积累以及科学研究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推动”[13]28,可见其西藏考察及其佛教著作对俄国乃至世界东方学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且这一影响具有持续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齐比科夫的佛教著作需求量巨大。普巴耶夫在《齐比科夫著作选》第2版的序言中提到,1981年苏联出版的《齐比科夫著作选》第1版印刷了10500册,简直就是一日售罄,就算这样还有很多俄国学者和专家没买到,直至第2版发行之日西伯利亚科学出版社还持续收到了订单。其次,世人对齐比科夫的研究内容愈发兴趣浓厚。国内外对齐比科夫及其佛教研究都十分感兴趣。在俄国这首先体现在“齐比科夫讲座”(22)“齐比科夫讲座”分别于1973年、1977年、1981年和1985年举办了4次。这一学术会议上,该会议出版的著作已经成为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社会科学院的传统,同时它也在藏学、佛学、蒙学和布里亚特学界研究中自成一派。此外,苏联还在阿金自治地方创建了方志博物馆,以齐比科夫的名字命名。国外学者也表现出了对齐比科夫本人及其著作的浓厚兴趣,斯洛伐克著名藏学家约瑟夫·科尔马(Йозеф Колмаш)博士高度评价了齐比科夫,认为他是杰出的西藏研究者,将他的《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翻译成斯洛伐克语并加了大量注解,于1988年在布拉格出版。最后,齐比科夫的藏传佛教研究得到了延续。继齐比科夫的藏学研究之后,藏学家的国际协作大大加强。匈牙利学者定期举办的纪念乔玛(А.Чома,1784—1842年,匈牙利藏学家、佛经翻译家)国际研讨会获得了国际认可;1989年8—9月日本成田佛学研究院开办了藏学研究者国际进修班、1989年我国成都举办第一届西藏《格萨尔》国际研讨会,俄国布里亚特藏学家均获得了参会邀请。这些都表明,国内外学者已经成功地将齐比科夫所献身的事业延续下去[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