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马斯结构主义叙事学视角下戏剧《恋爱的犀牛》分析
袁明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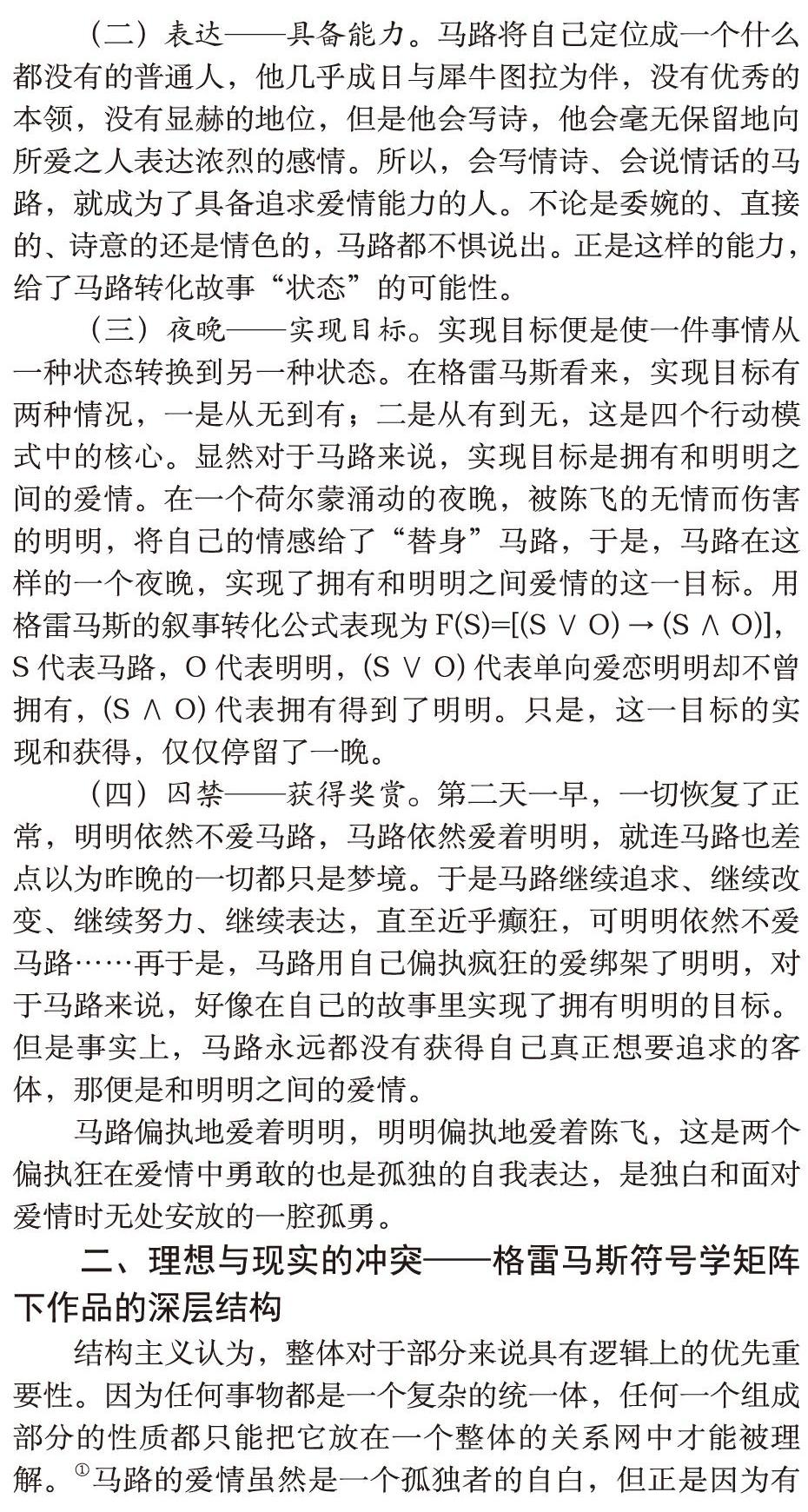

【摘 要】《恋爱的犀牛》这部戏剧作品,是由廖一梅编剧、孟京辉导演,并于1999年首演的一部经典先锋戏剧之作。本文以2018年11月29日在北京蜂巢剧场上演的“空花版”《恋爱的犀牛》为分析对象,借助格雷马斯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叙事学语法,从作品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角色功能所承担的作品价值意义三个方面切入,对这一夸张、荒诞、虚无但又真实的爱情故事进行尝试性分析与解读。
【关键词】格雷马斯;结构主义;《恋爱的犀牛》;作品分析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7-0014-03
2019年是孟京辉戏剧作品《恋爱的犀牛》诞生三十周年,在诞生至今的这三十年里,这部作品常青不衰,不仅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掀起了小剧场戏剧的高潮,更是从2008年在蜂巢剧场上演开始,保持着每年多场的上演频率。除了导演孟京辉先锋独特的创作手法、编剧廖一梅对爱情这一永恒话题的偏执刻画,作品能够跟随时间的推移应变求变之外,《恋爱的犀牛》带给观众对于爱情之外事物的思考也是这部作品能受到无数观众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品的剧情很简单,讲述了一位名叫马路的动物饲养员,爱上了自己的女邻居——一位叫作明明的打字员的故事。但是,故事往往拥有矛盾的关系和冲突的情节才能更吸引人,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最大的矛盾便是女主并不爱男主,女主爱的是另一个叫作陈飞的男人,直到故事的最后,这个事实依然没有改变。
一、独白与勇敢的未果——格雷马斯叙事转化公式下作品的表层结构
在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中,文本内容被分成两个部分:表层的和深层的。表层结构同时也指的是叙事层面上的行动模式,即“产生欲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获得奖赏”四个过程。在这个故事里,马路是故事讲述的主体,不论是对话还是独白,不论是沉默还是高歌,观众都在马路的自我表达和叙述中不断深入到他和她的故事中。但是,笔者并不想把这个故事的女主当成客体,因为对于整个作品来说,这个故事其实是马路的爱情独白,无论明明这一角色出不出现在舞台上,无论明明成不成全这段爱情,马路都是一直在追求自己与明明之间的爱情的,因此在笔者看来,故事的客体是爱情。
(一)初见——产生欲望。主体产生欲望后,才会有行动的动力,因此,欲望是整个故事叙事的源头和动力。对于马路来说,看见这个女邻居的第一眼就无法控制地爱上是不需要理由的,就像马路在戏剧开始和结束时痴痴地说的那样“擦身而过的时候,才知道你在哭,事情就在那时候发生了。”没有任何原因,就这么发生了,只是因为一次擦肩,便在初见时毫无防备地爱上,这是马路产生欲望的开端,也是故事的开始。
(二)表达——具备能力。马路将自己定位成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普通人,他几乎成日与犀牛图拉为伴,没有优秀的本领,没有显赫的地位,但是他会写诗,他会毫无保留地向所爱之人表达浓烈的感情。所以,会写情诗、会说情话的马路,就成为了具备追求爱情能力的人。不论是委婉的、直接的、诗意的还是情色的,马路都不惧说出。正是这样的能力,给了马路转化故事“状态”的可能性。
(三)夜晚——实现目标。实现目标便是使一件事情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在格雷马斯看来,实现目标有两种情况,一是从无到有;二是从有到无,这是四个行动模式中的核心。显然对于马路来说,实现目标是拥有和明明之间的爱情。在一个荷尔蒙涌动的夜晚,被陈飞的无情而伤害的明明,将自己的情感给了“替身”马路,于是,马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实现了拥有和明明之间爱情的这一目标。用格雷马斯的叙事转化公式表现为F(S)=[(S∨O)→(S∧O)],S代表马路,O代表明明,(S∨O)代表单向爱恋明明却不曾拥有,(S∧O)代表拥有得到了明明。只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和获得,仅仅停留了一晚。
(四)囚禁——获得奖赏。第二天一早,一切恢复了正常,明明依然不爱马路,马路依然爱着明明,就连马路也差点以为昨晚的一切都只是梦境。于是马路继续追求、继续改变、继续努力、继续表达,直至近乎癫狂,可明明依然不爱马路……再于是,马路用自己偏执疯狂的爱绑架了明明,对于马路来说,好像在自己的故事里实现了拥有明明的目标。但是事实上,马路永远都没有获得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客体,那便是和明明之间的爱情。
马路偏执地爱着明明,明明偏执地爱着陈飞,这是两个偏执狂在爱情中勇敢的也是孤独的自我表达,是独白和面对爱情时无处安放的一腔孤勇。
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格雷马斯符号学矩阵下作品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具有逻辑上的优先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中才能被理解。①马路的爱情虽然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但正是因为有了明明这一角色的出现才能让爱情这一事物成立,而因为有陈飞这一角色的存在,又让马路的爱情求之不得。所以将马路的爱情放入整体的关系网中,便能更好地理解整个戏剧中马路与明明的纠缠。
格雷马斯提出的“语义方阵”给予了解读文本作品中情节和人物关系的一种模式,也是人們常说的“格雷马斯符号学矩阵”。在这个矩阵里,有着四项基本内容和这四个内容生发出的三种关系。首先,最基本的一对反义关系是A和反A,比如黑与白,大与小;另外还有两对矛盾关系,即A与非A、反A与非反A;除此之外,A与非反A、反A与非A之间又属于第三种蕴含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马路的故事中,自己与自己追求的目标一直处在一种对立的状态。他爱她,她却爱他,这是马路爱情故事中的悲剧。而能和明明在一起才是马路所追求的理想世界,我们可以将其简单总结成“求而得之”,即上图中的“A”;但是理想的另一端便是现实,这个现实则是明明不爱马路,我们可以将其总结成“求而不得”,即上图中的“反A”。那么明明爱陈飞是作品现实中设定存在的,正是这样一个现实导致了马路无法真正得到明明,因此在马路看来,“明明爱陈飞”这样一个事件是非理想的,可以将其总结成“得非所求”,也就是上图中的“非A”。如果按照马路理想的那样去设想,那么明明爱马路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可以总结成“不求而得”,而这种状态是作品现实中存在的对立面,也就是上图中的“非反A”。至此,便可以围绕“理想”与“现实”得出以下这样一个叙事矩阵。
这个矩阵可以清晰地表现出六对、三种不同的关系。首先是两对反义关系:体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作品中表现为马路对于心上人的“求而得之”和“求而不得”;以及“非现实”与“非理想”之间,即马路对于心上人的“不求而得”和“得非所求”。接着是两对矛盾关系:体现在“理想”与“非理想”之间,即“求而得之”和“得非所求”;以及“现实”和“非现实”之间,即“求而不得”和“不求而得”。最后是两对蕴含关系:体现在“理想”与“非现实”之间,即“求而得之”和“不求而得”;以及“现实”与“非理想”之间,即“求而不得”和“得非所求”。
整部作品围绕着这样一个关系网在马路的理想与现实这两极中展开无限情节的可能,在叙事的过程中给予观众以整个矩阵中不同的设想。在六对、三种不同的关系之间,最终以“现实”与“非理想”这二者的蕴含关系呈现出整个戏剧情节的主线,从始至终在主线愈发清晰的过程中,也否定了马路所期望的“理想”,给观众展现了理想与冲突下马路对于所追求爱情的偏执与癫狂。
三、像犀牛一样永不顺从——格雷马斯行动元下作品角色的功能价值
整部作品除了主角马路和明明,以及从未出现但是担任着重要角色功能的陈飞之外,还有牙刷、大仙、黑子、红红、播音员(主持人)莉莉、恋爱教授、犀牛图拉等角色。这些丰富的人物在整部作品的表演性上担任着重要的地位,但在叙事上除了起着旁白和点缀的主要作用外,并没有对马路追求“爱情”的情节发展起到实质性作用。角色是在叙事中承担功能的,因此一部作品的人物可以有很多,但是角色是有限的。格雷马斯在其著作《结构语义学》中论述关于施动者模型的思考时明确了施动者的范畴包括“主体”与“客体”、“发出者”与“接受者”、“辅助者”与“反对者”这几个部分,形成了这样一个角色模式(如图3所示)。
马路是追求明明和爱情的主体,爱情是作品的客体。那么爱情的“发者”则来源于赋予马路一切行为的动力——欲望,而接受这所有一切的“受者”便是马路追求的对象——明明。在所有的施动者中,主体更有自主选择性:辅助者和反对者只是主体本身的行动意志及其想象中阻力的投射,而这些阻力是凶还是吉,则视主体的愿望而定②。因此,陈飞这样一个不断伤害明明、不爱明明的男人成为了马路不断追求爱情的“助手”,因为陈飞越是不爱明明,马路越有机会和理由去追求明明,陈飞越是伤害明明,马路就更愿意要求自己对明明好。相反,明明对于马路来说就成了他追求爱情的“对手”,原因很简单,因为明明爱的根本不是马路。
在笔者分析的图4这样一个角色模型中,马路是主体,陈飞是助手,而明明既是受者也是对手。这样一种看似奇怪的情况并不是不能存在的:格雷马斯在其《结构语义学》中曾举例解释过:一则普通的爱情故事,没有父母的干预最后以结婚收场,在此叙事中,主体同时是接受者,而客体同时是爱情的发生者,四个施动者反向对称,但只混合成两个角色(如图5所示)。因此,明明这个人物重叠了受者和对手的两个施动者角色,使整个角色模式呈现出三者组成的模型。
在这三者带来的角色功能的交织下,即使马路从始至终都受到自己所追求的人的反对和打压,但依然不放弃欲望。就像马路饲养的犀牛图拉一样,即使身边的同伴都已走远,即使生存的环境面临拆除破旧不堪,可犀牛依然不愿意离开这个一直生存的地方,直到死去。即使没有一个人支持,即使这个世界不断在变,马路依然在这个动物园里,只饲养一头犀牛,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只爱一个人。在这样的角色关系所带来的价值功能下,马路对于爱情的执着与癫狂被无限放大、夸张,甚至让观众在马路直接露骨的台词和歌词中感到“害怕”。这也正是编剧和导演所要达到的目的,在近乎绝境的情节走向中,把马路对于爱情的一腔孤勇不断推向极致。
四、结语
在结构主义叙事學的视角下,格雷马斯叙事转化公式和符号学矩阵使作品的表层和深层结构得以浮现:马路这个角色表达出的孤独和勇敢,却最终未能使自己获得渴望的爱情,是作品所讲述的故事主线;而求之不得背后所隐含的理想与现实两极的冲突,在笔者看来是这个作品所蕴含的深层内涵。
《恋爱的犀牛》向观众展现的是一段男女之间未果的爱情,这是一个百分百的爱情悲剧。在故事丰富繁多的人物形象中,马路和明明所承担的另类角色体现出的功能价值,让这两个重要角色显得格格不入又与众不同,他们对于爱情的盲目追求就如同视力极差又不轻易改变的犀牛一样,将一件事情“死磕”到底,绝不转弯。在这个作品中,也许有人看到了马路的勇敢、看到了明明的不幸、看到了是是非非五彩斑斓的现代社会,但笔者更加真切感受到的是作品通过这两个偏执追求爱情的角色而表达出的,在这个时刻变化的世界里依然怀有对美好事物不断追求的信仰与渴望。即使全世界与自己为敌,即使看不到希望和光亮,却依然不忘记自己心中最坚定不移的所盼所期,并且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像马路和他的犀牛一样,永远不顺从。
注释:
①陈建男,吴海清.舞蹈批评方法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126.
②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264.
③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M].蒋梓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259.
参考文献:
[1]刘小妍.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简介及应用[J].法国研究,2003,(1):198-203.
[2]钱翰,黄秀端.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旅行[J].文艺理论研究, 2014, 34(2):190-199.
[3]宫宝荣.戏剧符号学概述[J].中国戏剧,2008,(7):62-64.
[4]吴泓缈.《结构语义学》的启示[J].法国研究,1999,(1):38-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