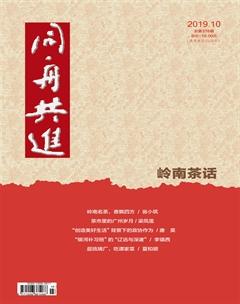“能议是非者”李鸿章
眭达明
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又做过李鸿章幕僚的晚清名家吴汝纶,后来在撰写《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时,曾这样写道:“曾国藩性情坚重,谋定不变,其疏劾李元度,李鸿章尝以去就力争。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吴汝纶所说虽不尽是事实,但在曾国藩幕府工作期间,李鸿章敢于冒犯上司权威,大胆提出反对意见,在所有幕僚中确实比较突出。其中特别让人服其胆识的又有三件事,一是“祁门移军”之争,二是吴汝纶文中写到的,在曾国藩疏劾李元度事件中,能以个人进退坚守自己的立场,三是当面批评曾国藩性格儒缓,缺乏魄力。
“祁门移军”之争
咸丰十年(1860)初,清军江南大营再被太平军一举击溃,苏、浙的形势万分危急,朝廷连下八道命令催促曾国藩率部救援,并授予其两江总督实职。为配合朝廷援苏、援浙的要求,曾国藩把湘军大本营从安徽宿松搬到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祁门县,李鸿章却大不以为然。他说,那个地方像个锅底,兵家把这样的地方称为绝地,如果把大营建在这里,等于自寻死路,从战略上看十分危险,必须赶紧离开。曾国藩不从,李鸿章再三陈说。受李鸿章移军思想的影响,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日渐高涨。
曾国藩执意驻守祁门,主要由下列因素促成:
一是曾国藩认为,祁门地连皖、浙、赣三省,皖南东部又与江苏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目前不仅可阻太平军由浙、赣两省进援安庆之路,力保湘军粮饷重地江西、湖北以及老家湖南的安全,而且将来可为进兵苏南张本。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致澄弟》信中就是这样说的:“余于十五日赴江南,先驻徽郡之祁门,内顾江西之饶州……保江西即所以保湖南也……若此次能保全江西、两湖,则将来仍可克复苏、常。”
二是曾国藩有意做给朝廷看,以表明自己坚决执行朝廷命令的态度。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初七日,曾国藩在《复左宗棠》的信中写道:“弟初奉江督之命,奏明从皖南进兵人吴,旋奉督办皖南之命,又奉江南大帅之命,是江南与皖南,弟之汛地也。”既然如此,怎么能够出尔反尔,离皖南而去呢?
三是曾国藩认为,当此“军心动摇之际”,大营一旦移动,势将造成军民纷乱,出现大溃局面,还不如暂时固守祁门,“以待事机之转”。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写给左宗棠的另一封信中,曾国藩说:“移营之说,此间众口一词。弟思之至熟:此时率鲍(鲍超)赴婺,计已落贼之后;且军心动摇之际,弟若轻动,则军民纷乱,米盐无买,各军皆不方便;不若弟与凯章(张运兰)主守,公(左宗棠)与春霆(鲍超)主战,以待事机之转。”这自然可以视为曾国藩的由衷之言。
也就是说,李鸿章建议移军完全着眼于军事,曾国藩死守祁门则是兼顾政治。在曾国藩看来,军事当然必须服从政治。正因如此,所以不管什么人劝他移军,他都固执不听,说得多了,说不定还会被他嘲笑一顿。
欧阳兆熊的《水窗春呓》卷上就记有这么一条。“文正困于祁门不肯移营,幕中人皆以祁门非应殉节处谏之,文正笑日:‘何根云去常州时,大约左右亦如此说耳。众为默然,无以难也。”
何根云即何桂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太平军兵指常州时,吓破了胆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决心出逃(两江总督府当时驻常州——笔者注)。常州百姓跪在他面前,流泪恳求其留下守城,他不仅不听,反而命令亲兵枪杀十余人。何桂清逃往上海,两年后被清政府处死。
受到曾国藩嘲笑还算客气。有一次,李鸿章再劝曾国藩移军,曾国藩居然十分气愤地公开声称说:“各位要是胆小怕事,都离开好了!”
不久,李鸿章果然因为反对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一事而负气出走。
李鸿章虽然离开了曾国藩幕府,但并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他多次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胡林翼不仅支持李鸿章的主张,而且说李“颇识时务”。
紧接着,曾国荃也从安庆前线派人送来一封“情词恳恻,令人不忍卒读”的信件,用近乎哀求的口气请大哥迅速移军东流或建德。曾国藩读后大为感动,在日记中如是写道:“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孝;读弟此信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友。”
更让曾国藩动心的是,在太平军攻击之下,祁门大营危如累卵,一日数险,有一次太平军前锋距祁门大营仅有十八里,形势岌岌可危,在祁门坐以待毙的曾国藩再次遗嘱后事。全军濒于瓦解之际,曾国藩身边人员“凡前言祁门可屯者”,此时也“皆更请国藩亟去”。
曾国藩这才下定决心,将两江总督衙门从祁门山区搬到长江边上的东流(位于安徽省东至县长江南岸),并对李鸿章高超的战略眼光殊为欣赏。
针尖对麦芒
“祁门移军”之争产生的裂痕尚未弥合,李鸿章与曾国藩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老秘书。早在曾国藩奉命回乡办团练时,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加入了曾国藩幕府,参赞军务,患难相从。在曾国藩众多幕僚中,除劉蓉、郭嵩焘这些老朋友外,就数李元度资历最老了。尤其是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曾国藩几次被人“打落门齿”之时,刘蓉、郭嵩焘等人都不肯出来相助,勉强拉出来后也很快借口离去,王闽运《题铜官感旧图》所写“刘、郭苍黄各顾家,左生(左宗棠)狂笑骂猪耶”,指的就是此事,唯有李元度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与曾国藩同甘共苦度过了七八年艰难岁月。李元度的忠诚和支持,无疑比金子还珍贵,对事业初创时期的曾国藩实在太重要了。
曾国藩不仅得到李元度的坚定支持,而且在曾国藩两次跳水自杀的紧要关头,都是李元度苦苦劝阻,李元度因此称得上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
然而,李元度擅长文笔却缺乏军事本领,曾国藩也深知其并非统军之才,只因自己私情荐举,李元度才被任命为徽宁池太广道即皖南道道员,领兵驻防徽州(今安徽省歙县)。
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在太平军进攻的时候,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陷落,大门洞开,湘军大本营祁门因此丧失防守的前哨阵地,直接暴露在太平军的面前。
李元度乱中逃生后,在浙赣边境游荡,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并不束身待罪,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一气之下,决定具疏严参,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
李鸿章受命撰写弹劾文书,不仅拒绝起草,而且率众坚决反对,理由是李元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曾国藩用人不当。还说李元度“到防不数日,猝遇大敌,守无备之城,又数日而陷,非其罪也”。如果因为李元度“不遽回祁门加以严劾”,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总之,在李鸿章看来,李元度是个典型的读书人,豪言壮语颇多,带兵作战能力较差,不是一位将才。曾国藩也深知李元度的短处,却派他领着一支数量不多且是新招募的部队防守兵家重地徽州,兵败后又要严词纠参,这是毫无道理的。况且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有恩于他,因此,于公于私都不能做得太绝情。
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李元度违令失城之罪如果不究,那么将来人人效法,湘军军纪还如何维持?因而坚持弹劾。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时心急,难免情绪失控。李鸿章来了脾气,说:“如果一定要弹劾,门生不敢起草。”
曾国藩一听,火往上冒,说:“我自己会写。”
李鸿章想不到老师会说出这种绝情的话来,也就无所顧忌地说道:“若是这样的话,门生亦将告辞,因为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只能离恩师而去了。”
正在气头上的曾国藩也失去了冷静,说:“脚在你身上,想走就走!”
如果说“祁门移军”之争还只是停留在工作意见相左的层面上,那么,因李元度事件而产生的分歧和对立,两人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就是明显的意气用事了。
两人已经把话说死,谁都不愿意先服软,李鸿章面前只有一条道可走。不久,他果然负气出走,离开了曾国藩。
当面批评曾国藩
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六日,在他人劝和下,又经曾国藩深情敦促,早已心生悔意的李鸿章返回了曾国藩幕府,曾对他也“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曾国藩十分看重李鸿章的能力,特别重视和珍惜他这个人才,另一方面,正如吴汝纶所说,李鸿章能以个人进退坚守自己立场的刚毅性格,曾国藩也是颇为欣赏的。
然而,重返曾幕后的李鸿章,敢说真话的性格依然故我。李鸿章平生虽然最佩服曾国藩,有时甚至把曾当作神灵一样敬奉,但对其缺点和不足,不仅很少讳饰,而且常常当着曾国藩的面毫不客气地说出来。
重回曾国藩幕府仅三周后的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东流两江总督府后院边乘凉边聊天,当说到曾国藩的短处时,李鸿章脱口而出:“您处理事情比较迟缓,缺乏魄力,不果断。”曾国藩认为李鸿章点到了问题的要害,于是在当天日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与少荃久谈,至二更三点始散。论及余之短处,总是儒(懦)缓,与往年周弢甫所论略同。”
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的“与往年周驶甫所论略同”,是说李鸿章说到的短处,与往年周腾虎指出的一模一样。江苏阳湖人周腾虎也是曾国藩的幕僚,咸丰五年(1855)进入曾国藩幕府后,也很敢于说真话,同样得到了曾国藩的高度肯定和赞赏。如在一篇题为“儒缓”的短文中,对于周腾虎能精准分析和大胆指出自己的性格弱点,曾国藩便给予了充分首肯:‘《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几。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弢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
遗憾的是,曾国藩接触的人物千千万万,但除了周腾虎和李鸿章,再没有人敢当面指出这一点。同时也因为秉性难移,曾国藩的懦缓性格虽经周腾虎和李鸿章当面指出,但最终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与周腾虎一样,李鸿章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说话不会看人眼色,更不会投其所好,阿谀奉承,而是直抒己见,坦诚相待。曾国藩对此恰恰十分欣赏,哪怕李鸿章反对错了也不计较。一个敢于直言,一个胸怀宽广,这就是曾、李二人十分投缘的地方。日后曾国藩选定李鸿章而不是别人做接班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周腾虎也一直得到曾国藩的赏识,遗憾的是,来不及施展才能,他就于同治元年(1862)病逝于上海。这说明,真正干大事业的人是不害怕下属提意见的,即使提错了,只要愿意改正,就是好同事、好部属。成大事者本就应是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和各种个性的人物,具有不同凡响的大气魄和大胸怀。也正是在这种包容异见的氛围当中,曾、李二人诚实坦荡,心无芥蒂,最终携手共进,各自成就了一代伟业。
“敢议是非”的是与非
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不惜与上司争议是非,诚然是一种很不错的品格,但上司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便负气出走,这种行为则有失分寸,让人不敢恭维。
就说李鸿章带头反对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一事。平心而论,错在李鸿章,曾国藩则没有什么不对。李元度弃城逃跑并非小事,曾国藩即使不参他,湘军之外其他官员也会参,与其让别人参,不如自己主动参,否则容易陷入被动,弄不好曾国藩也脱不了干系。
按照清律规定,守城主将应当与城池共存亡,如果弃城逃生而又表现恶劣,是要杀头的。所以清朝官员宁愿自杀,也不敢弃城逃跑,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比徽州早13天失守的宁国,守将周天受死守70余天,屡次击退太平军,后因“援尽粮绝”,军心离散,才“城破身殉”。城破之前,周天受还一面疏散百姓,一面“嘱各将弁带兵勇自南门冲出”,并亲自“策马送之”,自己则“誓以身殉”。“将弁暨道府各官跪请周天受出城,徐图再振”,他也“不肯出城”。周天受的表现就很能说明问题。
李元度虽然罪不至死,但曾国藩执意弹劾他,确有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正因如此,曾国藩后来每当回想此事,总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但又不敢完全断定幕府同僚共同反对的态度是错的。他最苦恼的是,始终找不到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为此,咸丰十年十月初五日,曾国藩特意致信李续宜,向这个向来很有主见又能说掏心窝子话的朋友征求意见:“次青(李元度)处公议稍伸,私情则我实抱歉,不知古人处此,如何而后两尽,请公细思示我。”
李续宜“细思”结果如何,笔者不得而知,曾国藩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肯定,则是毫无疑问的。由此看来,工作当中要完全抛开私情因素的干扰,有时确实非常困难。
明明知道自己没有错而错在对方,曾国藩最后还能不计前嫌地接纳李鸿章并加以重用,这一点足显其胸怀,确实没几个人能做到。
有趣的是,李鸿章后来认识到错误后,对于自己的年轻气盛和意气用事,不仅深感惭愧,而且把它当作身上的一块烂疮疤遮掩起来,容不得他人触碰。
在曾国藩幕府做过八年幕僚的曾氏另一位弟子李榕,在曾国藩死后送了一副挽联,上书:“极赞亦何辞,文为正学,武告成功,百世旗常,更无史笔纷纭日;茹悲还自慰,前佐东征,后随北伐,八年戎幕,犹及师门患难时。”
李榕的下联,本是说自己对恩师曾国藩的去世,虽深感悲痛,但能稍稍自慰的是,不管东征太平军,还是北伐捻军,长达八年时间里,哪怕遭遇再多的艰难困苦,自己都紧随左右,没有因为恩师遇到危难就两脚抹油,借机溜走。没想到,李榕这一“自我表彰”,却无意中揭开了兄长李鸿章的疮疤,李鸿章从此便恨死李榕:“李文忠公见之,颇恨其言。”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可见李鸿章是多么忌讳和羞愧这件事。
(作者系文史学者)
——基于全民健身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