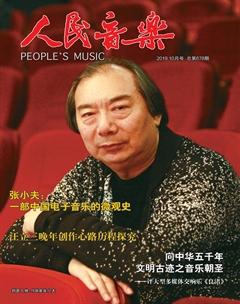“让音乐继续下去”
19年6月24至28日,国际流行音乐研究协会第二十届双年大会(20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opular Music)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ANU)隆重召开。
国际流行音乐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opular Music,IASPM)成立于1981年,由查尔斯·哈姆(Charles Hamm)、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菲利普·塔格(Philip Tagg)等欧美流行音乐学者创建,旨在为流行音乐研究者提供一个国际性、跨学科、跨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目前,该协会已经发展为成员遍布全球、分支机构覆盖十数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同时,也是流行音乐研究领域成立时间最长且唯一具有世界权威性的学术组织。IASPM的学术交流平台主要包括:两年一届的全球大会、各分支机构举办的地区性学术会议、不定期的专题研究会议、学术期刊(IASPM@Journal)、官方网站(http://www.iaspm.net)等,其中,汇聚全球流行音乐研究专家学者、反映流行音乐研究前沿成果及学术发展趋势的双年大会,毫无疑问是本领域最为重头的学术活动。
一、会议概况
本届IASPM大会的组委会在2018年5月发布的发言召集通告中,提出“流行音乐研究中的转向与革命”(Turns and Revolutions in Popular Music Studies)这一会议主题,意在引导流行音乐研究对当下持续变化的流行音乐图景与全球范围内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日益紧缩的局面做出回应,也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回望过去数十年流行音乐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审视近期在表演、后人文主义、空间、超越国界、视觉及其他方面的转向对流行音乐研究的影响,以及本学科未来可能会发生的转向。
组委会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交的三百四十余篇论文,从中遴选出134篇到会发言。此外,大会还开设了16场专题小组讨论、5场全体会议以及若干主题演讲、现场演出、纪录片放映等形式的交流活动。会议历时五天,日程紧凑,内容充实,从多个侧面展示了流行音乐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
134份论文发言以研究内容、角度或方法的差异被划分为37个平行场次,涉及的关键词包括“回望”(3场)、“定位与迁移”“场景与文化”“制作与录音”“数字音乐”“技术”“音乐与政治”(3场)、“种族”“音乐与性别”“抗议”“理论化音乐”“分析声音”“分析歌曲”“音乐学及其他”“感受音乐”“歌迷与名人”“流行音乐与档案的转向”“理解音乐才能”等。学者们以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依托,从多个角度来观察流行音乐,观点新鲜锐利、成果丰富多彩,充分体现出流行音乐研究的跨学科属性。
在16场专题小组讨论中,将议题聚焦于某一国家或地区流行音乐研究的现象尤为突出:中国的电视音乐偶像节目、当代韩国流行音乐的多样性、日本流行音乐的跨国流动、菲律宾的音乐场景与音效创作空间、马来西亚流行音乐的改编、延续和变化(2场)、拉美裔世界的流行音乐等,都成为专场讨论的中心议题。这些由各自国家的学者主导的专场讨论,是对当今世界流行音乐多元化、在地化發展趋势的直接反映。
通过罗列的议题不难看出,亚洲议题在本次大会上成为了热点。近年来,亚洲多个国家的流行音乐有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无论形态还是场景都体现出与欧美流行音乐传统不同的异质文化样貌,不只本土研究者的对这方学术富矿青眼有加,也引来许多欧美学者的关注,相应的研究成果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在这个背景下,一则重磅好消息的到来就水到渠成: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进行的2021年第二十一届IASPM双年大会主办城市竞选中,韩国大邱以44票比14票完胜挪威奥斯陆,申办成功!这是继1997年日本金泽后,亚洲国家第二次获得大会主办权。从会议自由发言中释放出的信息来看,亚洲的流行音乐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K-Pop(韩国流行音乐)在全球音乐产业中影响力的日益增长对此次韩国成功申办助力颇多。
二、成果述要
与会学者带来的研究成果主题丰富、视角各异,相当一部分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姑且借用会议通告中提出的流行音乐研究的六个维度——时间、空间、技术、政治、理论、感情——对其进行分类说明。
时间维度:题为《把音乐带给(博物馆)群众:纳什维尔、西雅图的乡村音乐和邋遢摇滚历史的实物性》的发言,探讨了纳什维尔乡村音乐名人堂、西雅图流行文化展览馆对保存和延续特定体裁的流行音乐遗产和音乐场景的重要意义;《尼尔·杨穿越(时间的和技术的)过去之旅:专辑〈一封家书〉》,对尼尔·杨在2014年专辑《一封家书》中极端的复古制作进行了细致考察,指出其对上世纪40年代的录音棚及早期的机械录音设备和技术的使用,对专辑整体怀旧气质的营造产生的关键作用;《什么是流行音乐史?流行音乐史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追溯了“流行音乐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们来源广泛的学术背景,指明本学科基因中的跨学科属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历史学方法的边缘化问题,并对如何定义“流行音乐史”、音乐史学的方法工具如何应用于流行音乐研究、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流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①
空间维度:《巴黎天空下:在巴西,法语歌曲的记忆与游牧》讨论了法语歌曲和法国音乐家对巴西流行音乐——尤其是情歌——的重要影响;《流行作为艺术、流行作为异域风情:印度尼西亚另类流行音乐艺术跨境流动进入澳大利亚当代“艺术”/表演语境》,对几支印尼另类摇滚乐队在澳大利亚的表演活动进行了追踪,指出一方面这些乐队通过共同的音乐语言和体裁符号与澳大利亚观众相联系,另一方面这些演出的意义围绕着“差异”的新颖性产生,这种新颖的“差异”,即乐队脱离本土场景、并在当代西方艺术的框架下“重新语境化”后的异国情调。②与会学者对空间问题的涉及更多地表现为对各自本土流行音乐的关注,前文已有介绍,不多赘述。
技术维度:题为《与机器一起即兴——以一个表演者的视角观察实时交互》的发言,回顾了一个人类乐手与机器进行实时交互即兴演奏的表演项目, 探讨了“创造力被视为人类本质的最后堡垒”的论断,指出项目实际揭示了“人与机器交互表演中究竟谁为谁服务”这一新的审美困境;《流派相似性基于原产地?Spotify算法推荐系统中空间不平等的表现》的作者指出,Spotify推荐系统的“相关艺术家”功能重现了中欧和东欧极端金属场景的空间隔离,算法设计为,在各自的子流派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乐队最有可能根据流派相似性进行分组,但流派外围的乐队往往会根据其原产地通过Spotify的算法进行配对,算法再现了它们的社会文化空间隔离,这与互联网将缓和线下不平等状态的期望背道而驰,流媒体平台也未能成功扮演“社会均衡器”的角色。③
政治维度:《欧洲电视歌唱大赛中的抗议政治》展示了这项老牌歌唱比赛的发展与“二战”后欧洲政治变革之间的历史关系,重点介绍了冷战结束后赛事组委会关于歌曲涉及环保、性别、反独裁、反战争等内容设置的条例,通过采用限制参赛作品政治内容的规则来达到使比赛去政治化的目的,并提出思考,欧洲电视大赛是否只是反映了欧洲政治变革、抑或也成为了政治变革的催化剂;《发声:政治竞选中的流行音乐成分的变化》探讨了流行音乐在政治竞选中的角色转变,名人站台和音乐陪衬一直是政治企图利用流行音乐文化(和亚文化)吸引力的漫长历史的特征,1997年英国大选中新工党的政治信息与“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的融合是成功的案例,在媒体生态系统全球化、碎片化的背景下,竞选中的音乐成分愈发显现出与“网络迷因”(Internet memes)和“YouTube美学”结合的趋势。④
理论维度:题为《硬连接到软件——朝向代码音乐学》的发言指出,我们当今大量的音乐实践是由软件塑造的,软件提供并限定了音乐的可能性,研究编写代码的人、软件开发的历史和背景,并且在现有的音乐学分析方法和软件及其关键代码研究之间打开通道,是代码音乐学的意涵;《“次要音乐问题”——流行音乐的微妙之处和审美体验》在“传统的音乐分析方法未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流行音乐”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做出推进,提出音响认知微观层面的差异对分析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意义截然不同,这些微妙之处包括微节奏、微音高、运音法(articulation)等,通过微观音响可视化分析,我们会意识到它们在音乐诠释与表达、典型演奏风格的特征、情景音乐记忆、识别和评价音乐等方面的重要意义,这或许将重构分析流行音乐的理论和方法;在研究者纷纷朝向新的研究理论进发的同时,也有学者致力于将流行音乐研究已有的理论成果梳理、总结,以求巩固学科理论基础,例如《流行音乐研究中的和声分析史》等。⑤
感情维度:《“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当感情在流行音乐歌迷圈中变成问题》以美国歌星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政治言论和立场所引起的网络骂战为例,通过列举双方的言语交锋,分析斯威夫特的“粉丝”和“黑子”各自持有的观点背后的感情因素,并进一步探讨“流行”所拥有的政治力量;《音乐与情绪劳动中的身体/情绪管理:朝向律动与社会的理论》指出,自20世纪末以来,以音乐来管理自己身体和情绪的愉悦感的趋势越来越强烈,这一趋势与日常生活中情绪劳动的支配地位有关,作者通过在东京和神户进行的三次(时间跨度20年)问卷调查,试图建立在情绪劳动愈发占
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音乐律动与情绪管理关系的模型。⑥ 三、中国元素
大会的专题小组讨论中,中国议题《中国的电视音乐偶像节目的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TV Music Idol Shows)颇受关注。这个专题小组四位发言人的身份分别为:钱丽娟,来自爱尔兰科克大学;郑雅慧,来自美国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冯应谦,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李春华(Angela Lee),来自澳大利亚“K-Pop学院”演艺公司。当四位文化背景不同、学术背景各异(依次为音乐人类学、作曲技术理论、新闻与传播、金融)的华裔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在中国(大陆)的电视(也包括在线平台)音乐偶像节目时,不但说明节目本身在我国大众文化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文化软实力对世界华人文化圈的广泛辐射。
关于中国的音乐偶像节目,四位发言人展示了迥异的观察角度:钱丽娟的发言《中国的电视音乐比赛:一部观众民族志》,以少数民族歌手参与电视音乐比赛的艺术表现和占比例绝大多数的汉族观众的反馈(问卷调查)为切入点,对这类节目在增进民族国家凝聚力中扮演的角色给予积极评价,并进一步指出,观众通过以多种方式参与节目、表达音乐偏好,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展示了更主动的活力;郑雅慧的发言《音乐作为私密行为:中国的偶像们在港台音乐上的对话》,以电视音乐比赛中华晨宇翻唱周杰伦歌曲《双节棍》和莫文蔚翻唱卢冠廷歌曲《一生所爱》等作品为例,说明偶像选手们在比赛节目中以似乎是建立在自我本真表达基础上的创造性翻唱来激起听众的感情,从而超越对原唱声乐模仿的比赛策略;冯应谦的发言《音乐真人秀在中国:现代性,伪民主或是其他什么?》对“创造101”等在线视频平台的音乐真人秀通过社交媒体技术提供的虚假民主选择进行了批判性地评估,归纳了在线音乐竞赛节目与传统音乐比赛不同制作策略:选择有更多粉丝的参赛者、在选手之间造成更强烈的冲突、制订适合粉丝的赛制并策动他们的情绪、遵循粉丝的喜好,指出在粉丝主导的音乐节目制作中,成功的关键是话语而非音乐;李春华的发言《C-Pop在澳大利亚》介绍了“偶像练习生”等中国的音乐真人秀节目在澳大利亚令人惊讶的影响力,以及她在试图将澳大利亚练习生引入中国演艺界发展时遭遇的困难,她把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国主流社交媒体的差异及与大陆经纪公司合作资源的短缺。
除了关注我国当下的流行音乐场景,也有中国学者的发言着眼于流行音乐研究的基础理论。来自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的赵朴以《披头士歌曲多重文本中的“再平衡”》为题做论文发言,作者试图建立流行音乐分析中的多重文本(Multi-Texts)理论模型、并通过此模型来重新审视披头士歌曲,提出多重文本的“再平衡”是潛藏于披头士歌曲创作中的内在机制,也是披头士歌曲等流行音乐经典作品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流行性的来源。无独有偶,悉尼大学的洁蒂·奥雷根在她的发言《继续钓鱼:分析流行歌曲中的“钩子”》⑦中,提出在流行歌曲中“钩子”(hook,可以理解为歌曲中钩住人听下去的“金句”)很多时候是以“多重钩子”(Multi-Hooks)的状态存在,即塑造“钩子”的不仅是旋律、歌词,还可能涉及音色、编曲、甚至是表演等多个层次的文本,这与赵朴提出的多重文本理论不谋而合。
结 语
在大会闭幕仪式上,IASPM创始人之一、现任主席弗兰考·法布里教授(Prof. Franco Fabbri)除了对本届大会给予高度评价、对会议组织者和承办单位表示由衷感谢之外,还提出了一些建议:“我想要(发言中)多一点音乐。版权部门说,超出10秒的音乐示例是被禁止的,但我们不想听他们的,在播放音乐示例的那一刻,让音乐继续下去吧。还有,我支持我的朋友菲利普·塔格的意见:把音乐纳入音乐研究,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法布里期望的“多一点音乐”,在抱怨版权制度对学术会议中音乐案例的呈现造成限制这个层面容易理解,而后面一句“把音乐纳入音乐研究”则另有深意。对音乐本身的重视程度不足是流行音乐研究领域毋庸讳言的沉疴,菲利普·塔格早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分析流行音乐: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就指出“音乐学的‘内容分析在流行音乐领域中仍旧是一个未开发地带及某种缺失的环节”。⑧如今,IASPM双年大会开到了第二十届,虽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流行音乐形态分析,其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地加深着我们对流行音乐本身的认识,但就本次会议发言情况而言,仍难以作出流行音乐研究中的文本分析与语境研究已经得到平衡发展的判断。塔格、法布里等先行者们提出并践行的“把音乐纳入音乐研究”的倡议,是流行音乐研究未来发展仍需努力的方向。
① 引述的三份发言作者和标题为:Christina Ballico, “Taking music to the (museum) masses: The materiality of the country music and grunge histories in Nashville and Seattle”; Kevin Holm-hudson, “Neil Youngs Journey through the (temporal and technological) past: A Letter Home”; Jacopo Tomatis, “What is Popular Music History?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popular music historiography”.
② 引述的两份发言作者和标题为:Heloísa de A. Duarte Valente, “Sous le ciel de Paris: Memory and nomadism of French song, in Brazil”; Aline Scott-Maxwell, “Pop as art, pop as exotica: cross-border flows of Indonesian alternative popular music acts into Australian contemporary ‘art/performance contexts”.
③ 引述的两份发言作者和标题为:Sean Foran & Toby Gifford, “Improvising with the machine - a performer perspective on real time interaction”; Tamas Tofalvy, “Genre similarity based on country of orig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inequality in Spotify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system”.
④ 引述的两份发言作者和标题为:Dean Vuletic,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Adam Behr, “Sounding off: changes in the popular musical component of political campaigns”.
⑤ 引述的三份发言作者和标题为:Denis Crowdy, “Hardwired to Software - Towards a Code Musicology”; Bernhard Steinbrecher, “Secondary Musical Issues – Musical Nuances and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Popular Music”; Akitsugu Kawamoto, “The History of Harmonic Analysis in Popular Music Studies”.
⑥ 引述的两份发言作者和标题为:Simone Driessen,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when affect becomes problematic in popular music fandom”; Hiroshi Ogawa, “Body/Emotion Management through Music and Emotional Labor : Towards Theory of Groove and Society”.
⑦ Jadey O'Regan, “Keep Fishin: An Analysis of Hooks in Pop Songs”.
⑧ Philip Tagg: “Analysing Popular Music: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opular Music, Vol.1, No. 2 (1982). Reprinted in Richard Middleton, ed.: Reading Pop: Approaches to Textual Analysis in Popular Mus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4.
趙朴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讲师(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