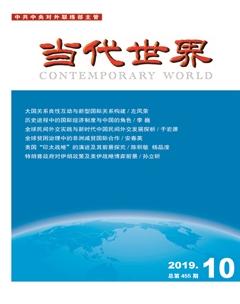全球民间外交实践与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探析
于宏源
【内容提要】民间外交注重通过民间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从而建立超越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人民友谊。这种基于人类文明共同理念的交往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社会基础,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合作奠定了稳固基础。民间外交主体具有人民性和有限性的特征。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民间外交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形式、新特点。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境等各个领域的联系不断加深,中国社会各界也在国家对外交往活动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多元化与网络化日益成为中国民间外交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新时代;民间外交;多元化;网络化
【DOI】10.19422/j.cnki.ddsj.2019.10.003
在當代国际关系中,官方外交在国家外交中起主导作用,民间外交则处于辅助性位置。积极开展灵活的民间外交能有效配合官方外交并弥补其不足。与官方外交相比,民间外交更注重通过民间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信任,进而建立超越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人民友谊,具有更为长远的作用。近年来,全球民间外交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形式、新特点。中国社会各界也在国家对外交往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多元化与网络化成为民间外交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民间外交提出了更高要求。
不断演进的民间外交内涵
明确民间外交的含义是理解这一外交行为及其所发挥作用的基础。目前,民间外交仍缺乏一个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各国研究者采用的表述十分多元,其指代对象既有重合又不尽相同,为学术对话造成一定障碍。例如,在中文文献中,既有“民间外交”的提法,也有“人民外交”的提法,[1]而英文文献的表述则包括“People-to-people Diplomacy”“Citizen Diplomacy”“Civil Diplomacy”“Non-official Diplomacy”“Multi-track Diplomacy”等。[2]二是相关研究领域范畴不断发生变化,增加了区别民间外交与其他非政府外交行为的难度。例如,传统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指“政府向外国公众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的行为”,政府是公共外交行为的主体,民间外交是独立于传统政府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第三种外交形式。[3]然而,近年来公共外交的研究范畴出现明显延伸,[4]两个研究领域又出现交叉重叠,导致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边界模糊。三是相关概念在不同地区的应用不同,其所指代的外交行为存在差异。以“二轨外交”为例,该概念由威廉·戴维森(William Davison)与约瑟夫·蒙特维尔(Joseph Montville)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泛指第一轨道外交(政府官员开展的外交活动)以外的一切国际交往活动,具有非官方(non-official)、非程式化(non-structured)、思想开放(open-minded)、利他主义(altruistic)的特点。[5]根据戴维森与蒙特维尔的定义,“二轨外交”几乎涵盖了“民间外交”的所有内容。针对该问题,达利亚·达萨·凯(Dalia Dassa Kaye)将二轨外交限定为“以问题解决为重点的非官方政策对话,参与者具有某种接近决策圈的渠道”。[6]他进一步指出,不同地区的二轨外交机制在涉及议题、获取的官方支持、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7]
结合以上讨论,可以从两个方向界定民间外交的研究范畴。一是需要区分民间外交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一般性国际交流活动。“外交”必须体现“国家的作用”,即体现国家意志或有国家参与的成分,如有国家的政策指导或资金支持等。[8]因此,民间外交不同于个人或社会团体的一般性国际往来,它具有明确的补充政府外交、促进政府间合作的意图和作用。[9]二是需要明确民间外交的参与主体。民间外交的主体不具有国家外交正式资格,[10]但又往往享有政府支持。民间外交的主体可以是有官方背景的人民团体、地方政府、社会组织、教育机构、新闻媒体和各种民间组织。[11]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将民间外交的概念界定为包含城市外交、二轨外交、三轨外交等多种形式在内的“非官方(中央政府)、非营利性、有组织的一切涉外活动”。
全球民间外交实践的发展
近年来,“治理”理念的发展、国家层面权力的分散以及技术的进步使更多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到国家对外交往活动中来。这些新变化对各国民间外交提出了新要求,全球民间外交实践出现了一些新形式和新特点。在此背景下,多元化与网络化的民间外交主要体现为网络化社会组织的国际活动与全球城市外交两个方面。
一、社会组织网络化和全球民间外交
社会组织网络化是全球民间外交多元化、网络化发展的重要实践之一,其既表现为社会组织自身开展国际活动并形成跨国合作网络,又表现为企业等商业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
第一,各国非政府组织通过跨国社会运动和跨国倡议网络来影响全球治理。跨国倡议网络(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作为以社会活动家为中心、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联合互动为主体的合作架构,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倡议网络通过提出新议题、影响国家政策、建立和传播国际规范来重构世界政治。在民间外交影响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各国非政府组织积极建构与媒体广泛接触的网络。通过与媒体的交流网络,非政府组织能主动发布相关信息,部分信息甚至会使大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面临尴尬境地。媒体还是公布研究成果的渠道,也可以用于吸引群众注意力,或通过大量报道群众集会和抗议等使某个议题公开化,改变公众认知,影响社会舆论。
第二,企业等商业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随着社会组织网络化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凭借其组织形式的弹性和应对战略的灵活性等优势通过网络合作模式将其行动影响力嵌入到全球、地区、国家和次国家等多个层面,提升了治理机制的密度和治理形式的多样性。其中重要表现之一是包括民间团体、城市、企业、基金、商会及智库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跨国非国家行为体数量不断增多,在跨国行动范围、政策游说空间以及网络治理能力上增长迅速,并日益成为民间外交的主体。
二、城市多边和网络化建设中的民间外交
除跨国社会组织网络外,全球治理下民间外交的新发展还体现为城市多边和网络化建设水平的提升。作为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非国家行为体,近年来城市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有较高全球或区域影响力的大都市均开展了一系列多边与网络化建设实践,积极参与多边城市组织。城市外交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外交形态。[12]
以东京的城市民间外交为例,其在发展新型民间外交、城市多边及网络化建设方面值得研究。东京是亚洲重要国际商贸与文化中心,是访日外国游客热门旅游目的地和在日外国人的重要居住地。这为东京开展新型民间外交注入活力,提升了东京与世界的联系紧密度。一是东京將其城市多边与网络化建设嵌入了区域机制中。东京的多边城市外交侧重在亚洲主要都市网(Asian Network of Major Cities 21,ANMC21)框架下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多边城市论坛、主办国际会议等方面。二是东京重视加强同其他区域及国际城市的交流与协作。近年来,东京城市外交活动频繁,市政府代表团在2017—2018年访问巴黎、新加坡、伦敦等城市,与外国政要会面高达98次。通过这些会面,东京逐步建立起其在城市多边网络机制中的中心地位。三是东京重视加强同各国驻日使团的联系。目前,东京定期向外国使团介绍城市规划、公共交通、灾害防备、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政策;与外国使团合作并召开大使年度会议,商讨灾害管理等问题。四是东京积极承办重要国际会议。2019年10月,东京将举办“Urban 20 (U20)市长峰会”,主题包括可持续发展、社会融合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等,旨在通过交流相关经验。五是东京注重提出可能引领潮流的创新性议题与理念。目前,东京已提出“东京都市政府的自动驾驶计划”“东京实现包容社会的倡议”等发展理念与方向,为推动东京城市外交多边及网络化建设方面做出努力。总体而言,东京在城市多边与网络化建设方面起步较早,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展望未来,东京或借助其承办2020年奥运会的契机进一步提升城市多边与网络化建设,谋求在国际事务中更高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巴黎也同样重视推动新型民间外交及城市外交实践的发展。巴黎致力于在国际交往中根据文化交流、体育赛事、国际代表团来访等方面需求,推动与其他国际化城市建立网络化联系。一是从城市发展来看,巴黎倡导发起了多个城市合作平台,联合主办了U20会议;与国际法语协会合作,联合世界221个城市共同推广法语等。二是从国际合作来看,巴黎一直致力于解决经济发展、城市化、文化、气候、人权等方面问题,且每年投入650万欧元,建立了70多个相关合作项目。例如,巴黎积极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自2014年起共投入107.5万欧元用于支持法国非政府组织救助战争受难者、移民和难民。三是从科技合作来看,巴黎邀请了多方专家参与建筑、交通、住房等领域城市建设。四是从文化交流来看,巴黎作为欧洲重要文化中心,已与40多个国际城市开展了机制化文化交流。五是从气候治理来看,巴黎自2007年便开始制定相关计划,以应对气候变化、空气污染、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通过倡导全球城市联盟、积极参与全球前沿议题治理以及加强与世界的科技、文化纽带,巴黎增进了与其他国际城市的网络化联系。城市多边与网络化建设提升了巴黎在国际交往活动中的影响力,从而推动法国民间外交向更多元、更立体的方向发展。
东京、巴黎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都市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建立城市组织、外交平台,加强城市在世界科技合作、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提出创新性议题与理念等方式,不断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这种城市的多边网络化实践,以及城市外交独立性的日益增强,是全球治理下民间外交新发展的重要体现。
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的特征:多元化与网络化
在国际民间交往形式不断创新和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民间外交也逐渐出现了多元化和网络化的双重属性,主要表现在民间外交主体、内容和对象的多元化以及实施方式的网络化。官方外交一般侧重政治领域,而民间外交却可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间外交的主体具有人民性的特征,即以人民为主体,将人民作为工作对象。[13]民间外交主体包括半官方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个人等,活动领域涉及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福利等,形式灵活多样。与官方外交不同,民间外交的交往对象不受国家关系和外交制度的制约。从实施方式看,民间外交出现了网络化等形式创新。民间外交不是通过外交谈判和签订各种条约、协定等来规范双方权利和义务,而是通过不拘形式的平等协商和交流来自愿增进彼此理解和信任,双方合作和交流的手段也没有固定模式。民间外交主体通过网络和多边平台不断推进全球民间互动和友好关系。
第一,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多元化。作为中国外交领域的重要实践之一,民间外交本身与公共外交并非是互斥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外交作为正式外交行为的重要补充,一定程度上另辟蹊径地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建交。当前,随着中国发展与开放程度的提升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入,中国民间外交发展出现外溢现象,即由于非政府行为体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不断密切,中国民间外交由单一政府主导向政府、企业等市场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等社会行为体协作进行转变,中国民间外交的动力机制开始从中央发起、地方配合,向央地互动转变。社会组织成为中国民间外交的主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群团组织是与中国体制相近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友好往来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的对外交往活动逐渐转型,在推动文化和人员交流中作用突出。[14]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中国正面临国际社会的更高期待”。[15]中国不仅需要民间外交主体在重大国际场合以非官方的形式讲述中国政策与行动,传播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人文交流,也需要民间外交主体参与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传播。[16]
第二,由于新时代民间外交主体的多元化,中国民间外交所关注的领域也出现了扩展与外溢。传统民间外交主要围绕政治领域进行,对外交往活动的目标也更多服务于增进外国民众对本国的了解与好感,进而为两国政治关系发展奠定良好民意基础。然而,在当今企业、社会组织乃至个人越来越多参与民间外交的情况下,其所关注的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民间外交议程。企业最关注经济利益,社会组织及个人可能关注社会发展、知识传播、文化交流、环境保护等,这些传统上被视为低政治领域的议题不断进入中国民间外交关注范畴。政治议题不再处于绝对压倒性地位,民间外交议题总体呈多元化发展趋势。
第三,在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中,民间外交网络化的转变体现为城市—企业—社会组织的纽带联系增强。随着外交权力下放以及民间外交中央地方协调模式的发展,地方与城市在民间外交中拥有了更多灵活性与自主权。地方与城市创新能力得到充分调动,其国际交往动力将从传统的旅游“引进来”、贸易“走出去”向旅游、贸易、城市治理经验分享及社会主体驱动等多元动力发展。民间外交愈发呈现出从单向到双向、从双边到多边、从人文到治理、从说服到体验、从活动到机制的特征。同时,民间外交不同行为体间纽带作用的加强也确保了不同民间外交项目间的协调配合与信息分享。民间外交研究机构在其中起到了沟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行为体,在各领域开展民间对外交往活动的桥梁作用。例如,上海运用民间外交的纽带功能,对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建设与民间友好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及日本联谊会以白玉兰奖为纽带,团结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及团体,并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以民促官,以经促政,逐渐增强日本社会对华友好的正能量。2018年,上海承办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各国政府、企业家提供交流合作平台,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上海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改变,中国拓展国家利益的手段更加多元。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国国家总体外交及党的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以来,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开展,民间外交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国家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中国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通过民间外交密切与世界民众之间的联系,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17]总体而言,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有明显的外溢现象,具有多元化与网络化的特征。多元化主要体现在民间外交主体及关注议题与领域的多元化,网络化则表现为多边外交平台的运用以及城市—企业—社会组织的纽带联系增强。
综上所述,新时代中国发展多元化与网络化的民间外交,是中国自身发展与参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必然反映。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生长于中国本土的商业组织与社会组织将显现出巨大活力,中国企业及非政府组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进而发挥其影响力将极大促进中国民间外交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地方自主性与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城市等次国家行为体也将在新时代民间外交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多元化与网络化建设将成为中国未来民间外交的发展方向。首先,中国的民间外交实践对内将进一步与国家总体对外战略协调,而对外则可能进一步嵌入区域及全球重点议题与治理领域之中。其次,企业等市场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及普通民众等社会行为体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相互配合,在不同层次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最后,城市外交将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补充与支持,地方政府将进一步发挥其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与影响。
发展新时代民间外交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18]在借鉴吸收国际民间外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推动民间外交主体、领域多元化以及结构网络化发展,对中国发展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体系而言至关重要。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能源—粮食—水的三位一体安全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6AGJ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丹丹)
[1]刘建平:《中国的民间外交:历史反思与学术规范》,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第25-31页。
[2]张胜军:《新世纪中国民间外交研究:问题、理论和意义》,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第14页;See Seng Tan, “Non-Official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Civil Society or ‘Civil Servi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7, No.3, 2005; James Marshall, “International Affairs: Citizen Diplo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43, No.1, 1949.
[3]韓光明:《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特点分析》,载《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春季号,第65页;张玲、张万洪:《“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民间外交——基于缅甸田野调查的反思》,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30页。
[4] Mark McDowell, “Public Diplomacy at the Crossroads:Definitions and Challenges in an Open Source Era”,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 32, 2008; Geun Lee and Kadir Ayhan, “Why Do We Need Non-State Actors in Public Diplomacy?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Relational, Networked and Collaborative Public Diploma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udies, Vol.22, No.1, 2015.
[5] William D. Davidson and Joseph V. Montville,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 to Freud”, Foreign Policy, No.45 (1981-1982).
[6] Dalia Dassa Kaye, Talking to the Enemy: Track Two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outh Asia, The Hague:Rand Corporation, 2007, p.7.
[7]同[6], pp.11-13。
[8] Mark Mcdowell,“Public diplomacy at the crossroads: definitions and challenges in an open source era”, The Fletcher Forum World Affairs,Vol.32, No.3, 2008, pp.7-15.
[9]张胜军:《新世纪中国民间外交研究:问题、理论和意义》,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第15页。
[10]同[9]。
[11]韩光明:《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特点分析》,载《公共外交季刊》,2012年第9期,第67页。
[12]赵可金, 陈维:《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30页。
[13]蔡拓,吕晓莉:《构建“和谐世界”的民间力量——关注中国民间外交的发展》,载《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第59-64页。
[14]周鑫宇:《全球治理视角下中国民间外交的新动向》,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第32-35页。
[15]孙海泳:《境外非政府组织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及其应对》,载《国际展望》,2018年第1期,第51-69页。
[16]刘建飞:《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基本框架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2期,第4-20页。
[17]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http://www.gov.cn/xinwen/2018-06/23/content_5300807.htm。
[18]李进军:《中国特色民间外交:认识与建议》,载《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第4期,第1-9页、第124页。
7年版,第232-234页。
[4]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p.29-62.
[5] 薛荣久:《入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意义、作用与维护》,载《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10期,第2页。
[6] 王明国:《制度实践与中国的东亚区域治理》,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第107页。
[7] 李巍主编:《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2019):纷争年代的大国经济博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8] 陈文敬:《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及未来发展探析》,载《理论前沿》,2008年第17期,第9页。
[9] Injoo Sohn,“Learning to Co-operate: Chinas Multilateral Approach to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4, Jun. 2008, pp.309-326.
[10] 霍侃、陳立雄:《亚投行渐近》,http://magazine.caixin.com/2014-04-25/100670577.html。
[11] 盛斌、马斌:《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中国的角色》,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16-17页。
[12] 廖凡:《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全球方案与中国立场》,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2期,第43页。
[13]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http://www.pbc.gov.cn/publish/hanglingdao/2950/2010/201009141939040 97315048/20100914193900497315048_.html。
[14] 严双伍、肖兰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演变》,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第88-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