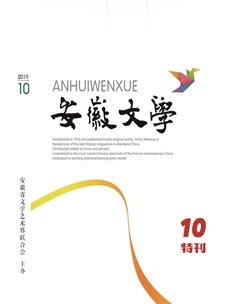唠叨
韦如辉
上
我的妻子刘春花是个教师,我的女儿刘小花是个医生。夹在家庭生活中的我,自然是她们唠叨的对象。
不过,首先声明一点。我对教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没有丝毫的不尊重。相反,我十分尊敬和崇拜这两个职业。从上幼儿园起,我就接受教师的教育,在我的脑海里,教师的美好形象已经根深蒂固,无法用其他的不利影响,撼动他们的地位和作用。而自我出生起,甚至没出生,还在娘胎里,我就受到医生的关爱与呵护。至今,我每年都要造访医院,寻医问药,治疗和调养我日渐衰弱的神经。我写这两个人,纯属聊一聊我的家事,与她们的职业没有绝对的关系,希望没有在不经意中,冒犯众位大神们。
这里需要重点交代我的妻子刘春花和我的女儿刘小花,她们为什么都姓刘,而且名字里都有一个花字?这个事情,是我没跟刘春花办理结婚证前,就议定好的。刘春花的理由简单却充分,她说你已经有了个姓你姓的儿子,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拥有了延续下去的血脉。而我呢,还是单身一个,我不能对不起列祖列宗,给老刘家绝了种,所以今后有了孩子,无论男女都要随刘姓。刘春花是个孤儿,八岁时就没了爹娘,在苦难的岁月里,她一路走来,凸显了她的坚强。我当时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她。做人不能太强势对吧?就是因为强势,我弄丢了我原来的家庭,弄丢了前妻,弄丢了唯一的儿子。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刘春花的要求,还是比较低的,不过分,且合情合理,可以自然而然地接受。女儿出生后,在出生证上,刘春花没有再征求我的意见,就直接把女儿的姓名那一栏,让医生写上了刘小花的名字。我曾满怀疑问地问过她,怎么给孩子起了这么个俗气的名字?她非但不觉得俗气,反倒觉得很得体很有意义。她亲了一口女儿正在皱起的眉头,在其眉心上留下轻轻的唇印,而后仰起头,将一头散乱的头发顺到脑后,如同下过蛋的母鸡一样咯咯笑起来,我是大花,她是小花,这有什么不好吗?这不充分证明你家里长着两朵花吗?你不想一想,你眼睛里和生活里长着两朵花,你不感到喜悦和快乐吗?刘春花一连串的反问,几乎把我的脑袋砸晕了,她不愧为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拥有循循善诱的语言艺术,和对严密逻辑的把握与掌控。
我的苦笑在脸上挤了又挤,终于挤出了一朵不太像花的花儿。而刘春花却把自己的脸庞,弄成了一个大花朵,伴随着花朵的尽情绽放,撒了一地咯咯咯音乐般的笑声。
这里还要说一说我的前妻和儿子。虽然我们曾经有着世界上十分亲近的关系,可是这种关系在几年前就已经千疮百孔了。我的前妻无法忍受当时的家庭生活,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我,她经常唠叨我,不是个有出息的男人!不求上进的男人!看看你周围的男人,哪一个不比你混得好混得强!到现在,你看看你混得算什么?她说的那个现在,是若干年前的事,已经尘封在记忆的深处,一个轻易不能触碰的角落。若干年前,我周围的同学同事,包括跟我十分要好的几个朋友,他们都在自己的人生跑道上,跑出了各自的水平,展示着男人们应有的风采。从政的从政,经商的经商,即便是干个体的,也混得头是头脸是脸的。大家每年至少都要聚会一次,喝酒聊天谈理想,那个做派与张扬,像根针一样,深深刺疼我身体的敏感部位。有一回,我出了个小车祸,车主逃逸,我连医药费都要向朋友们借,真是寒碜透顶了。恨铁不成钢的前妻,对我已经忍受到了极限。她离开我后,凭借着她的美貌与风情,找了个大老板,如今吃香的喝辣的。几次在大街上碰面,我都想主动跟她打个招呼,可她视我如空气一样,让我倍感自讨没趣的苦恼。我的儿子虽然一直随着我姓,身上流淌着我们祖宗的血液,但他对我这个亲生父亲并不待见,除了他读书需要资金支持的那几年,我如期把生活费打到他的银行卡上,之后,他就没跟我联系过,我打电话他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好像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寿终正寝了。他结婚的时候,我得到了小道消息,给他打过去十万块钱,估计他收到了,可能嫌少,也没给我回信息。看看吧,我的人生是多么的失败与不幸。有时候,我觉得活着真没意思,可是又缺乏死的勇气。
当然,我给我结婚的儿子打钱,刘春花并不知道。她如果知道了,她的唠叨肯定如春秋两季天上的雨水一样,细如针线,密织细缝,洋洋洒洒,绵绵不绝。而这笔钱,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小数字,需要我勒紧裤带,再戒烟戒酒甚至疏远一些朋友若干年。
我的女儿刘小花,從小就知道唠叨,不仅当着我的面唠叨,当着刘春花的面唠叨,还无所顾忌地当着她同学的面唠叨。那时,她唠叨的主题,就是我这个当爸爸的太抠门了。每次从幼儿园里蹦跳着出来,只要看到我,嘴巴就噘得像个小油壶。她不喜欢吃咪咪虾条,而我每次都买这种廉价的食物给她吃。我刚才说了,经济上我的“压力山大”,无法承受女儿任意的消费。刘春花怪罪我,你不能给小花买点儿改样的,能多花几个钱?钱可是你的命?如果你的命比你的女儿重要,你就跟你的命过去吧!刘春花的口气,跟我的前妻生气时极为相似,同样使我全身起着鸡皮疙瘩。世上的女人难道都是一种物质做成的?而具有同一种物质所释放出来的功能?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真会扯淡,水是什么,柔弱的象征,水做出来的东西怎么会冰冷如铁。而有一次,刘小花的几个同学,从我和刘小花的身边经过,刘小花的嘴巴正在变成一个可爱的小油壶,那几个同学叽叽喳喳地讪笑着,那个就是刘小花的抠门爸爸吧,就喜欢给刘小花买垃圾食品吃的爸爸。她们几个不谙世事的小朋友,懂得什么?知道生活的艰辛吗?可是,她们的眼神,让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尖利的伤害。
有时,刘春花见我下不了台,也会偶尔安慰我。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往前看,前途是光明的,未来是美好的,面包会有的。她说她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也是在唠叨中度过的。最让她刻骨铭心的唠叨,发生在她第一次恋爱,那时她母亲尽管疾病缠身,而嘴上与心上没有病。刘春花不无动情地回忆,他真是个好小伙子,能吃苦耐劳,对女孩子也百般殷勤,每天上下班,无论风里雨里雪里,无论白天与黑夜,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我下班的路上,陪我走过那段没有路灯且泥泞不堪的路。他真的感动了我,我决心跟他认真地谈一场恋爱,然后找个合适的日子嫁给他。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现我们恋情的,她老人家吃了不小的惊吓,双手狂拍着自己的大腿,哎呀哎呀地叫了一个下午。之后,母亲用一碗鸡蛋面,成功把我锁到黑屋里,死活不许我再见到他,甚至不许我见蓝天和阳光。每当夜晚来临,小伙子在窗户外面学鸟叫,可是我只有用眼泪告诉黑夜,不行,我出不去了,没自由了。母亲坚硬如铁,残忍地告诫我,什么时候反省成功,什么时候去上班。她没经过我的同意,私自到学校帮我办了病假手续。老人家还十分霸道地切断了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她认为那时的任何一丝联系都是十分危险的,都是可能引起爆炸的导火索。就这样,母亲陪着我,整整唠叨了一个半月。就是在那一个半月里,我知道了她的过去,我父亲的过去,还包括我们家族的过去。所有的过去,都包含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听老人的话,吃亏在眼下。还真让她老人家说对了,刘春花继续唠叨着那段她自己和她母亲以及他们家族的历史。那个小伙子,后来由于偷盗,入狱五年。刘春花长长叹了一口气,将两条手臂放在自己的脑后,重重地倚靠在床头上,眼睛里褪去一层暗淡的色泽,从窗外吹进来的风,撩起她的刘海,在她的眼睛与额头之间飘荡。
刘春花无疑给我上了鲜活生动的一课,现身说法,不保留自己的观点和隐私,目的就是让我从女儿唠叨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从而正确面对各种唠叨,并使之堂而皇之。
不能不说,刘春花对我的疏导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着刘小花的唠叨,我习以为常,不以为意。不料,这个事情出现了天大的反转,面对我的冷漠,刘小花反倒不唠叨了,一段时间表现沉默,也没在刘春花面前和她的同学面前,说我一个不字。真是奇了怪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坏事可能变成好事,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世界这个万花筒,处处充满了诡异和变数。
中
刘小花长得真快,在我们的眼前没晃几晃,就长成了个美人胚子,一笑俩酒窝,露两颗小虎牙。初中的那几年,喜欢跟我比个子,只要逮住机会,不论在家里,在校门口,在商场超市,在服务区,还是在景区,或者在公共卫生间外面的洗手盆旁,她都会笑眯眯地站到我跟前,用她的手掌,化作刀子的形状,从她的头顶开始,冷不防地向我的身体横切过来。从我的腰窝开始,而肚子,而肩膀,而脖颈,而耳朵,直到切到我的头顶。经受过每一次的刀切,我不仅不感到疼痛,还感到无比舒服。
我跟刘春花说,咱们的刘小花又升高了。就这样,便打开了刘春花的话匣子。刘春花正在喝稀饭,或者刷锅,或者顶着一头的卷发,或者发微信,或者啃一个快要坏了的苹果。听我这么一说,她都会停下这些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厌其烦地反问我,你光知道说,你可知道她是怎么长高的吗?
我回答,我当然知道,那是岁月的力量,或者说时间的力量。可是我没有沿着刘春花的思路唠叨,因为我已经听惯了她的语气里的各个词语,甚至标点符号,我想借用《焦点访谈》节目的开篇语,用事实说话。我挺了挺自己的身子,意思是告诉她,看看吧,我是多么高大的个子,她刘小花就是伟大的遗传基因的结晶。
刘春花扑哧一下,又扑哧一下,再扑哧一下,在她一下接着一下的扑哧中,她把她嘴里的唾沫,几乎消耗殆尽。她撇了撇嘴,把一丝鄙夷拉到她的嘴角上说,屁!就你,三等残废,还谈什么基因?
真是,我一米七三的身高,竟是三等残废?她刘春花的二等和一等残废,又会是什么样子?
刘春花不顾我的反对,自言自语地说,我每天给刘小花吃的什么?喝的什么?你难道没看到?难道你的眼睛瞎了吗?
我的眼睛没瞎,好好的,一个一点五,另一个还是一点五,在周围人的视力中,我可以算得上神视力了。其实,刘春花给刘小花吃的喝的,都是些普通平常的东西,无非她煮的粥黏一些,煲的汤浓一些,牛肉卤的烂一些,牛奶混搭的多一些。还有,冷热酸甜拿捏的好一些。
刘春花说,这还不够?这就叫科学喂养,合理膳食。嗯,这一点,她说得可能有一定道理,她除了教好自己的学生,投入时间较多的,就是看一些关于营养方面的书籍,对于央视《舌尖上的中国》这个节目,爱到几近疯狂的程度,为了避免我跟她争电视,上卫生间的时候,她也别着遥控器。在刘小花的身上,可以说她用足用活了她的业余学习成果,也用足用活了她的唠叨作料。
刘春花时常端一个青花瓷碗,吹着气,送到刘小花的学习桌子前,小心地说,孩子,喝了吧,对身体有好处。刘小花通常表现得不是太配合,甚至态度很无理,她仍然保持着噘嘴的坏毛病,不!我不饿!有几次,刘小花将放到她面前的碗,无情地推了出去。哎呀,碗里的粥,或者汤,或者羮,天女散花一般撒了一地。刘春花哎呀哎呀地叫一通,没忘了打扫自己亲手制造的战场。
一转脸,刘春花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張开血盆大口,一步步向我走来。哎呀,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她刘小花惹的祸,通常由我这个旁观者付出代价。等刘小花睡熟了,刘春花非要把我戳醒,拽到客厅里,关上严实的门,开始如泣如诉地跟我说话。她通常的第一句都会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这是图的啥?好心当成了驴肝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看看,我可是为她好?可是为了她长身体,今后有个好本钱?我回答,是的,是的。而一般的情况下,只要我连续回答三次是的是的,她就会将目光变成愤怒的刀子,捅向我的淡定与无辜。你老是是的是的,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是在应付我吗?我看你跟你女儿一样,都不是个好东西!其后,我学精明了,当我说到第二次是的是的的时候,再也不说第三次,便岔开话题,表扬表扬她两句。这样,刘春花好像好受多了,心脏跳得缓了,说话的语速也渐渐慢了下来,而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的光线,也在一点点变得明亮起来。我连续打了几个呵欠,她会不耐烦地批评我,算了,算了,睡吧睡吧,看你跟一辈子没睡过觉的样子。
刘小花上高中的时候,已经是校园里数一数二的校花。很自然,刘小花的周围,男孩子像蜜蜂一样飞来飞去。
刘春花告诉我,盯住她,不要放松,别让她迷失了方向,这个时候,她是最容易误入歧途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女孩子不同于男孩子,一旦方向迷失了,青春就会失去本来的光华。
可是,在捉迷藏方面,我再是高手,却怎么能是一群孩子们的对手呢?他们这些孩子们,比我们那个时期接触的新鲜事物多了去了。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何况我不仅不是诸葛亮,甚至连诸葛亮的皮毛也沾不上。哎呀,头疼,我怎么可能是他们一群精灵的对手呢?问题出来了,刘小花意外地怀孕了。
这个好了,捅了马蜂窝,刘春花不依不饶,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得死去活来。
我劝说刘春花,千万别哭了,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咱们的小花还怎么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还怎么活?
刘春花的哭声渐渐小了下去,看来我的劝说起了作用。刘春花把声音藏了起来,并不代表她不难过,也不代表她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她利用三天的时间,不吃不喝不睡,无声地与时间和空间做着对抗。
我带着哭腔说,春花,你喝点水吧?睡会儿觉吧?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我希望刘春花能够振作起来,继续着她的唠叨。如果她真的能够唠叨下去,说明她过去了这道坎。
时间在时间里迈着大步。第四天,刘春花喝了水。第五天,睡了觉。到了第六天,刘春花用一只苍白的手,无力地冲我摆了摆,过来,坐。刘春花的身旁放着一个板凳,仿花梨木,是我们前年在地摊上讨来的。
果然,她准备开始唠叨了。我像只惊喜的猴子一样,一屁股坐到刘春花的身旁,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那个话题的唠叨,一直持续到刘小花考上大学。
值得庆幸的是,刘小花似乎承受外界压力的能力十分强大,她居然在那种环境下,不多浪费一点儿时间,如期进入大学的校门,的确是我和刘春花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这里面,也许本身就有刘春花的唠叨起了作用。也许,刘小花实在忍受不了刘春花的唠叨,决意离开这个环境,才下定决心,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一举成功的。说不定,刘春花的唠叨真的起了作用,这个还真说不定!
离多见少,大多时候,刘春花只有在电话里跟刘小花唠叨。可是,刘春花这边刚起个头,刘小花就急不可耐地把电话掐掉了。这一招,好像踩住了刘春花的尾巴一样,她对着空空的冒着忙音的话筒,哎呀哎呀地叫起来,一双脚扑腾到地板上,咯噔咯噔地响。
刘春花便求救于我,你好好唠叨唠叨你的宝贝女儿吧,别让她再犯错误了。
我回答,好的好的,是的是的。
她马上变脸,什么是的是的?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熊样子?唯唯诺诺,像个男人吗!我刚刚说了一个是的是的,她就受不了了,真是时代不同了,什么都在变。看来,刘春花的脾气与审视社会的标准,也在与时俱进。
下
刘小花外出求学期间,我喜欢到森林公园转一转,美其名曰锻炼,归根到底,是想远离或逃避刘春花的唠叨。
小城的南部新区,刚建成一个上万亩的森林公园,公园里种植了各种杂树,空气质量明显好于嘈杂而拥挤的街道。在这个土地资源稀缺与人口密度较高的平原地區,能够建设这样一个公园,一方面说明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说明城市的建设者们,的确开动了脑筋,下定了决心,可以说干了一件对现代和未来都了不得的事。尤其之于我,现实中直接的受益者,更是激动得不得了。如果再往深处挖一挖,直接的受害者也不是不可能。
去森林公园转一转,顺便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得到无数个类似奖赏的点赞,未免不是个好事、快事、美事。刘春花看到我发的图片,知道我又去森林公园锻炼去了,她很放心,也很无奈,即便是她那个时候再想唠叨,我这个家庭中的唯一对象,还忙着呢不是?她只有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着电视,或者面向阳台,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南方。更南一点的地方,在一个三面环山的一所大学里,刘小花身在其中。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想象,还可以说一个不太道德的臆想,认为这可能也是对刘春花的一种折磨方式吧。可是,渐渐地发现,我还是错了。刘春花一直没有荒废她的唠叨。当我终于挨到时间,回到家里的时候,刘春花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她一手抱着手机,一手忙碌着生活上的琐事,跟别人聊天。有一回,我开门的动静弄大了,可能影响了她聊天的效果,她用另一根手指竖在自己的嘴上,不失时机地冲着我翻了几次白眼。聊完了之后,她冷不丁地问我,锻炼回来了?她说的不是废话吗?我不仅回来了,马上还吃了饭了,还洗了澡了,还看了电视了,还准备上床睡觉了。我知道她一定还想跟我唠叨,而且这个话题才刚起个头。
那是个晚上,严格地说是个傍晚,天不该黑得那么早,只是阴了天,雨水即将来临,定时的路灯,还没有应约亮起来。我匆忙走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回放着乱七八糟的事。比如刘春花,她为什么好唠叨?她的妈妈也不是这样的吧?在我跟她确定关系时,那个百病缠身的老太太已病入膏肓,只用游离的眼神盯着我,并没有唠叨什么。比如刘小花,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甚至连咪咪虾条这个古老的话题,也懒得跟我说了。她跟她的同学们,尤其是长得很帅,又肯在她跟前献殷勤的男同学们,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一辆没长眼睛的小汽车,从我的身后追上了我,并把我弄飞了几丈远。
我住进了医院。一个月,我躺在床上。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我坐在床上。第四个月和第五个月,我时躺时坐在床上,偶尔下来扶在床上。到了半年之后,我虽然可以下床了,但是更为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医生说,我的听力受到撞击后,曾经一度消失,但回归本来的可能性也消失了。不得不佩服,这个医生是个高明的医生,有着高明的医术,他说得一点儿没错,尽管他摘下了他一直戴着的口罩,把说话的声音放到最大,我还是没有听到,他到底跟我的妻子刘春花和我的女儿刘小花说的是什么?我一点儿也听不到,只是,从她们母女惊讶的口型里,我读懂了大事不妙。
我的世界里没有声音,只有图像。朋友们来病房里看我,对着我的耳朵喊,伙计,咋样了?我之所以这样断定他们这样说,一个是从他们的口型上,另一个从我们之间称呼的习惯上,还有一个就是从他们脑袋无奈地摆动中。平时,他们几乎不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只在我的身份证和档案里躺着,他们只叫我伙计,伙计长伙计短的,蛮亲切的,比叫某某某要敞亮得多。
刘春花跟刘小花只要一照面,就不停地说着话儿。她们说什么?有没有说我的坏话?我睁大眼睛,发挥着想象,捕捉着她们的表情。有时候,她们会扭过头来,冲痴痴的我笑一笑。有时候看都不看,觉得戒备我简直是多余的,她们的话语无所顾忌地进行着。我心想,也好,母女俩能这样唠叨一辈子,不能说就是一件不好的事儿。
那些日子里,我身体固然是痛苦的,而心里也算是快乐的。我想起许多过去的往事,往事中刘春花与刘小花这样和谐相处,还是不多见的。阿弥陀佛,但愿时光静好,人聚不散,且行且珍惜吧。
冬天来临时,一场北风一场寒。下了雪,刘春花炖了一只老母鸡,刘小花递给我一碗刚出锅的鸡汤。我美美地喝了一口,哎呀哎呀地叫起来。刘小花慌了神,歇斯底里地问了句,爸,烫吗?我回答说,嗯,烫,真烫,哎呀呀!
刘小花高兴坏了,从屋里跑到小区院子里,把我能听见说话的消息,告诉给了在那里做义工的刘春花。刘春花急不可耐地拽住一把扫帚,一路哭喊着回到屋里,用疑惑的语气看着我问,真的可以听到说话了?
我点了点头,不争气的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弄花了泛着瓷光的脸庞。
刘春花快走两步,一把抱住我的头,哎呀哎呀地叫,太好了太好了,老天爷终于开眼了。我的脑袋钻在刘春花的怀里,汲取着她身体的温度,一种别样的奶香味儿钻进鼻孔里,呀呀呀,好闻,好味道,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幸福来得真快啊。
刘小花说,这下可好了,爸爸又可以陪你说话了。刘小花看着刘春花,不无兴奋的样子。刘小花整天陪着我,其实是在陪着刘春花唠叨,我可以听到说话了,刘春花的唠叨对象便恢复了以前的我,对于她们可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然而,事情并没有刘春花想得那么好。
刘小花本来要留下来工作的,在我能听见声音之后,她改变了主意,坚持出去闯一闯。她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刘小花背着背包,拎着行李,临出门,回头喊我,爸爸,想我,打电话哦。刘小花伸出大拇指和无名指,在自己耳边晃了晃,作打电话状。远处,高铁的鸣笛声穿过河流、树林与田野,悠扬而清脆。
刘春花跟我说了好多想说没说的话,说的最多的是刘小花。她也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嫉妒恨,她告诉我刘小花对我可好了。比如,做饭、洗衣服、买菜、打扫卫生,诸如此类的家务活,原来刘小花不做,也不会做,更不愿意做。可是,自从你出车祸,好了,世界改变了,一切都变了,她什么家务都做,而且越做越好,常常抢着争着做,老天爷,真是开眼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刘春花喜欢说老天爷三个字,老天爷是刘春花的救世主。
我听了很高兴,眼泪在眼眶里把持不住,顺着脸颊肆意流淌。我喃喃地说,老天爷。
刘春花恢复了本来的样子,开始喋喋不休。说,你看,咱们的刘小花刚发的信息。你看,这道菜的颜色咋样?你看,天晴了,云散了,真蓝啊。小区的那个保安知道吧,就是那个胖子,昨天摔了一跤,差一点儿没爬起来。你看,老天爷格外开恩,我们的好日子才开个头哩……
我点点头,嗯了又嗯。不知怎么了,我觉得很疲惫,懒得再说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有时用鼻音,也感到有点费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