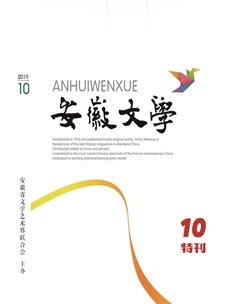二十载追风高速人
朱冬云
1978年的老高剛刚8岁,瘦而高,肩膀薄而利,总是弯着腰,一副总要往前跑的样子,他跟小伙伴们一起给在生产队上工的父母打下手,用板车运石子,挖淤泥给猪圈沤肥,用铲子整饬田埂,风里阳光里,一颗心被吹的空空荡荡。
40年后,老高依旧清晰地记得那一个夜晚。那晚,破旧的收音机里电流的沙沙声和主播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在院子里浮浮沉沉,父亲笔直坐院子正中,母亲紧攥围裙斜靠着厨房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这些字飘在小院的空气里又钝钝地落在胸膛。晚上起夜路过院子,发现父亲低头用袖子抹了脸,锋利的肩胛骨在半明半暗的黑暗里孤独地耸动。老高怔怔地看着这些,乡邻嘴里关于知识分子爷爷的只言片语从心头羽毛般掠过,他有一点当时还不能理解的酸楚的惆怅。
田野里长大的孩子,缺衣少穿、饥肠辘辘都可以忍受,只要日子有希望,而不管这希望有多么渺茫多么稀薄。现在,复制粘贴的日子升起了光,父亲原本空洞的眼眶里升起了一簇簇火苗,在煤油灯下给他缝补棉袄的母亲,穿针引线的间隙也总爱浅笑盈盈地看着他。就连以前总是沉默着像一棵老树的爷爷,也褪去了倦怠、失望、痛苦等元素组成的表情。有天黄昏,他在草垛子上给爷爷掏耳朵,爷爷歪头咧嘴,贪婪地看着村口的大榆树。久经风霜的老榆树枝干被闪电劈得两头空,半大孩子的胳膊可以从这头伸到那头,可依旧不认命地向高处、向两侧伸展着稀稀落落的枝丫。爷爷用目光缓慢地抚摸它,两侧嘴角向上牵动,像主动请缨孤身深入威虎山的杨子荣临走的那一回眸。40年后,已经是老高的他终于可以恰如其分的概括出那一回眸中感情色彩:悲壮、不屈和一些被埋藏的很深的委屈。当时,他看了一眼瘦如飞蓬的爷爷,又看了一眼瘦骨伶仃的老树,鼻尖开始泛红,他扭过头,一颗种子在心里悄悄发了芽。
1989年的3月,小高参军部队所在的城市春色已经很浓郁了。当兵出身的爷爷给他注入了参军的绿色基因,这个春天他像一粒漂泊的种子被时代的风从江淮大地刮到了上海这块繁华富饶的土地上,一种对未知世界强烈的新鲜感让他暂时放下了思乡的情绪,可总有一种东西牵引着他。有时,他半夜醒来坐在床上,恍惚还能听见母亲纳鞋底时,丝线和顶针摩擦的声音。但是,只要透过窗户看到大院内高杆灯远而利的光,心里就一哆嗦,知道已经是远离故乡了。下雪的时候,他和战友一起清扫积雪,想起和小伙伴雪地里撒野的时光,眼睛一热,手一摸,就湿漉漉的。小高是个优秀的士兵,遵守纪律,反应敏捷,天生具有黏合和重建关系的本领,只是与他皮实外表反差很大的是,他有一颗过于恋家而敏感的心。于是,退伍后他顺理成章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小城。
夏季的汊涧镇上高悬着一轮让人心烦意乱的毒日,烘烤着乱哄哄的人群。在究竟要不要拆除205国道控制红线内的违章搭建的猪圈这个问题上,路政员小高与猪圈的主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皖苏交界的边远小镇,居民都是宗亲式聚居在一起,不一会猪圈主人就叫来一群人,他们气势汹汹,像憋足了气的气球,拔开气门芯就能上天,叫嚷着“谁只要动了猪圈,今天就吃不了兜着走”。闷热的如同一口热锅倒扣的小镇上,炒熟的热豆子一样亢奋的人群中,小高掏出路产路权宣传册试图递给猪圈主人,手才伸出半截就被不知来自哪个方向的手打落。他蹲下身,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掸去灰尘,不急不恼地再度递给对方。看小高年纪轻却蛮沉得住气,“包围圈”这才松动了一下。一阵风吹过,小高吸了口气,定了定神,重新跟村民普及起了路产路权法律法规。这时,一个声音插进来:“我们不知道什么路权不路权的,猪圈是我们自己辛苦建的,想拆,没门!”小高望过去,一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年轻后生,光个膀子,上衣随意搭在肩膀上,见小高望过去,目光钉子似的扎向他。小高朝他一笑,善意和友好通过细微的面部表情反映给对方,对方却像戳破了皮球,羞惭的低下头去,迅速淹没在乱糟糟的人群中。
当天,小高解决完第五起路产路权纠纷,迎着瑰丽的落日往公路局走,一双眼睛被炫目的阳光刺得一阵乱眨,几乎就要流泪。但是他踏在205国道的水泥路上的脚步是笃定的,这种是知道一小部分命运谜底的笃定,就在迎着阳光的这一刻,父亲的希冀,母亲的微笑,爷爷的悲壮背后的心灵密码,他一瞬间全部破解了。
小高刚刚到公路局报道时,坐的是几十人的大巴车,车辆在205国道上颠簸来颠簸去,一群人像被使劲摇晃的火柴盒里的火柴,一会倒在左边一会倒在右边,小高的心就配合着左摇右晃的节奏,一下子提了上来,又一下子落了下去。上上下下的,一路上就没有安生过。听客车驾驶员说,这条连接皖苏的大动脉,刚建成时路况是很好的,水泥路厚实平滑,车轮轧上去没有一点声音,可“跑得车多了,路就不经用了”,时间一长,路面就坑坑洼洼。这些道听途说浮光掠影般的印象式了解,在成为天长公路局路政员后,小高很快进行了更正和补充——205国道站可不仅仅是路况差这一个硬茬子。
由于路况差,交通事故就多,救援任务就重;由于是一级收费公路,冲卡逃费的现象特别频繁;由于法律意识差,民风彪悍野蛮,征缴双方关系极差,205国道站新上班的收费员总会在老员工的特地嘱咐下备一些简单的防身工具。
每天早上6点,路政员小高起床,6点半小高就与同事一起上路巡查所辖路面,清理路面的碎石垃圾,协助交警处理交通事故,拆除韭菜一样此起彼伏,一茬茬冒出来的违章搭建,配合公路局直管的205国道站处理收费纠纷,夜里还要进行夜巡。每到恶劣天气或者路况不好的地段,巡查只能靠脚力,一天下来,大约要走2个小时,两三个月就会穿破一双鞋。
有时他们还会和那个时代盛行的港片一样上演雨夜追车的戏码。秋夜雨寒,一辆小车撞弯205国道收费站的收费栏杆后子弹一样射向前方,司机开出一截后,笑着将手伸出窗外,食指朝天勾了勾。这让道口的同事既无措又气愤。接到通知的小高和一位年长的同事赶紧前往拦截,雨脚密集的前路上,小车一会往左,一会往右,在不算宽的道路上不停变道。有时还故意放慢速度等小高他们追上来,眼看距离差不多了,再猛踩油门“呲溜”一声往前驶出老远。当小高、同事和江苏的同行将小车司机拦在皖苏交界的潘家花园站时,年轻气盛的司机双手叉腰一脸不屑:“不就是要钱吗,喏,给你!”“你冲卡逃费你还有理了?”同样年轻的小高一股气直往脑门冲,一只脚刚刚踏出去,同事就拉了拉他的制服袖子,澄澈的眼光定定地看着他,静静地说着“不”,小高探寻地看向他,慢慢地收回了脚。
回單位的路上,同事慢腾腾地开口:“做路政工作,有时候要急,有时候急不得,发生事故了,要急,讲究一个快速高效;有收费纠纷时,要慢,讲究一个有理有据,年轻人要懂得控制情绪,老百姓不理解咱事业单位的,认为咱们吃皇粮不干事,咱们这些跑在最前面的就更要做好形象工作了。”一番话说得小高低下了头。在从小高蜕变为老高的这个过程中,这次谈话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句话的每一个停顿,每一个音节,每一个音调变化,小高都记得清楚。这种对公路事业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帮他平稳度过了入职10年后的那次考验。
1998年,安徽省高管局正式从事业单位变为企业,当时已经被市公路局委派为205国道站负责人的老高与这所收费站一起打包转至了省高速集团。他也从有事业编制的“公家人”变为了给企业打工的“打工仔”。接下来是一系列艰难的身份认同。那一段日子,为了避免听到各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吃瓜言论,老高下班后总喜欢在205国道上走一走,反刍消化掉这一变故对自己的影响。
散了一个星期的步,老高发觉205国道这条路早已与自己血肉相连。这条路上一厘一寸的裂缝、一丝一毫的变化,都会在他棕黑色的脸上得到相应的反馈,不是惊奇地瞪大眼睛,就是为难地皱紧眉头,或者那犁沟似的皱纹,因为欣喜而舒展得如龙须菊一样。干吧!反正无论身份如何变化,守一条路,捧一颗心,做一些事的权利是不会被剥夺的。
2008年那场大雪来临的时候,小高已经成为了老高。凌晨4点,刚刚在雪线上奋战了一夜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的老高就收到了监控中心的出勤通知,被困在205国道上的一辆客车内有一个病重的孩子急需就医。时间就是生命,老高和同事利落地给路产车辆装上防滑链,在雪地里艰难地开路,由于雪太大,雨刷不起作用,前挡风玻璃不一会就被雪积满,老高手拿抹布,右手伸出窗外不停地擦拭,不一会,伸出去的半边身子就僵了。等到他们赶到被困客车的地点,才发现情况更加严重,半岁大的孩子,脸色青紫,呼吸微弱,眼眶肿成了一只大桃子,原本圆溜溜的眼睛被卡在了桃子中间,已经不能灵活转动,眼角不时流出黄色的脓水……“这孩子情况不妙啊”,身为父亲的老高心里喟叹一声,立马从哭的六神无主的母亲手里抱过孩子,一步跨下客车。“快开车”他冲同事大喊,随即往最近的医院赶去。
“幸亏你们送的及时,再晚一点孩子可能就要失明了”,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脱下手套,扭头看向守在重症监护室外的孩子母亲。听到这话,年轻的母亲腿一软,鱼一样从监护室外的椅子上滑下来。老高和同事立马把她扶起来,她朝老高和同事投来感激的一瞥,嘴角抽动,几番欲言又止,老高把她按在座位上,微笑着摆了摆手,将和同事一起凑的几百块钱塞给孩子母亲,对挣扎要起身的母亲摇了摇头,又笑了笑,随后消失在医院空荡荡的走廊里,他实在太累了。
路产员是高速公路上最辛苦的工种之一,单调枯燥,危险繁重,毫无乐趣可言,但是老高做的有滋有味。在上路巡查的间隙,他极目四望,高速两边的绿化树蓊蓊郁郁,像燃烧的绿色的火,一阵风吹来,一群蒲公英升上天空,飞过山川河流,飞过童年少年,顺着时代的风向,只是飞,就是美,就是梦想。
每当这种时候,他就感觉心里还有股熊熊燃烧的火,就感觉到岁月还没有完全寂灭他的雄心,那些随着岁月起皱松弛下来的“未来”“将要”等诸如此类抽象的字眼又重新在心里活过来,实实的,满满的,塞满胸膛。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