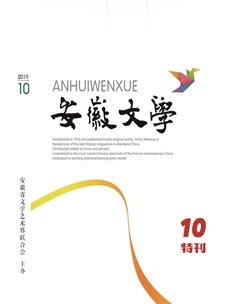秋题三章
林如玉
一
无从摆脱对秋的迷醉。我沿着她渐渐幽深的方向,一路徜徉。
梧叶覆地,百鸟远徙。小径上,纵是落叶与鞋子缱绻,生出好听的窸窣声,这个夜晚,我也不想让心情涂上一丝萧杀的色彩,让“静女其姝”般的秋被什么淹没。于是,我决定向灯光最火热的地方走,去呼吸那里的热空气。
“千年古县”全椒城真的越来越大,我怎么走,都好像仍在圆心徘徊。这几年,以“美丽”为基调的发展号子格外铿锵,像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涟漪应声向四方漾开。
去每年正月十六都牵动着中央和地方媒体神经的太平桥看看吗?那里灯光是够灿亮的。听说夜幕甫降,宽阔的桥面、堤面,还有两旁的广场上,市民就辐辏而至,他们在驳杂而欢腾的鼓乐声里,各自秘密地把酿造的丰收醇醪端出来。不论国标舞的典雅,还是广场舞的恣肆;不论黄梅调的奔放,还是庐剧腔的沉抑,清脆的拍子响彻襄河南北,幸福的腰肢随着心情一起轻松律动。
以襄河为墨池,把地砖当成天设的纸格,娱乐第一的地书家们登场也很吸睛。他们在乐声里逸兴遄飞,笔走真草隶篆,力道里尽是龙腾虎跃,忘我地奢侈着偌大的“净皮宣”……
太平桥若是不老的君子,他压抑了多少个寒来暑往,多少次朝代更迭?他背负了太多的传说和祈盼!当梦想成真时,他知道,多遭磨难的先人们的苗裔没有理由不载歌载舞,不把酒言欢,只是倏忽间,人间恍若天上,天上又逊色于今夜。
由是,我想起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当时,位于汴京的宋廷已是内外交困,画中的繁华和祥和,掺入了多少臆想,终不得而知。即便它描绘真实,那不过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与这里一年比一年热闹的“正月十六走太平”比起来,不知寒酸了几重?
立于桥上,放眼隐约可见莽莽苍苍的南屏山。想象着山之巅,笔峰塔此时如塑金身,巍然耸立,是何等的气派!而塔下,新近来了一班文墨男女,就着灯光,或心摹手追“兰亭”“寒食”,或作起散文、小说和诗歌,闲雅如曲水流觞之戏、赤壁舟中之谈。夜风也浩然,当它阵阵拂过,似曾斑驳的千年文脉又历历可见了。
若是白天,转个身,吴敬梓家的祖居地也可尽收眼底。如果说,襄河是一滴饱满的墨,它在纸上洇开来,那么,那片文化厚土就是纸面上颜色最深的一块。若能挨到今日,吴老先生自不必为完成《儒林外史》这鸿篇巨制而背井离乡,更不必举家食粥,绕城暖足,客死扬州。当然,当他满面红光,把如椽之笔端得稳稳的,也许写出的是一部盛世赞歌。
二
去我们县城的政务中心开会、办事,去新城市广场购物、赴宴,去城南靠近高铁站的某个小区拜访朋友,对我这个居于城东的市民来说,无异于一趟远游,就像当年去逛南京新街口,总是害怕自己衣着土气,配不上环境,会贻人笑柄。
其实,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这些让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城市,我也曾逗留过。那时,我喜欢呆呆地仰望镶着玻璃幕墙、豪华得晃眼的凌云高楼,喜欢车子在迷宫一样的高架桥上疾驰时目眩的感觉,喜欢在宫殿般富丽的商厦里对中外顶尖品牌的衣服过眼瘾,也喜欢让目光流连于公园里由千花百草组成的一块块花圃,艳羡的眼神,不啻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短短几个春秋,变戏法似的,都市的光怪陆离纷纷移植到了我们全椒城南。
中秋前,亲戚家乔迁,我去上礼,吃喜宴。骑车至城南的高楼丛林里,我才发现那个名字很西洋的小区似乎在跟我捉迷藏,一时不知其踪。因为那一片挤挤挨挨,全是高档楼盘,里面都植有名贵树木,辟有郁郁葱葱的花圃,有的还设计了假山、喷泉,我怎么都不能从它们内里辨清谁是谁。
好歹我也在县城待了二十多年,算是资深市民了,而亲戚是从乡下来的,为了找到他的居所而打电话向他“求解”,会很失面子。逡巡之际,还是一位从奔驰车上下来的小伙子热情地给我指了路。
我言谢时,小伙子冲我理解地笑了笑,说,这块儿路是很绕人,小区大门也够隐蔽的,不过你可以开手机导航。我连连点头,心里却抵触得坚决,难道我在自己“家门口”,还要那玩意儿帮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真的不敢细想,我会在朝夕为伴的县城里迷路。
发生了那次囧事,我就不失时机地去逛逛城南。在深圳打拼多年,现已在区块链领域成就斐然的老同学回乡来看我,我把晚餐安排在城南一家土菜馆。一桌子的家乡味,勾起了他对年少时苦涩生活的咀嚼,而在知己面前,他竟不顾如今的身份,大快朵颐起来。
膳毕,我陪着微醺的他,在店铺密布、霓虹竞艳的大街上闲逛,最后进茶楼接着叙旧。谈话间,他对近年家乡的华丽转身发了一大通感慨,并蓦地抓住我的手,说,你可以帮我在这附近物色一套房子吗?看我一脸纳闷,他表情更加郑重地说,我想等我老了,就回来住,这里舒适,应该不比深圳差多少。
三
天气转凉,我数邀母亲来全椒城小住,她老人家都坚辞。绝非我态度不诚恳,来了后会有所顾忌,原因很简单,其一就是,她待在乡下诸事更方便。
人越老越恋旧,越不愿轻舍故土,况且母亲已上八旬,腿脚不够灵便了。城里车来车往,动辄爬高上低,对她是种折磨。而且在乡下,每餐可吃自种的蔬菜,菜的品种、生熟、咸淡,饭的软硬,都贴合她的所好,她无需为谁而默默迁就。乡间环境单纯而静谧,她出门就有村邻陪说话,时光也会走得了无痕迹。
自村里土地流转,哥嫂进城谋事,儿孙满堂且领着高龄补贴的母亲,就彻底终结了农人一辈子都在土地上劳作的宿命,一个人留守故宅,享她的清福。准点起床、吃饭,饭后散步一里,每周去村医务室量血压和心率,她生活悠闲,有规律得像个退休老干部。
只有我能琢磨出,她老人家不稀罕去城里生活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现今的家乡十字镇百子村真的秀美无匹,她若想看风景,何须舍近求远?绿野环村,路是柏油铺的,晚上照明有光伏路灯,灯下的广场舞比城里更新潮,百子庵的灿然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难怪同学Y君怂恿我和他一道回去买套房子,还调侃说,那也算是叶落归根。
可是入秋后,曾随政协领导到乡下就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做调研,发现了更多好去处。车驶入石沛镇荣鸿现代农业示范园,就如同进入一片神秘地带。在花海的中央,随意点缀着池沼和苇丛,水畔嵌有小旅店,还有设施先进的球馆。尤其是在大墅镇龙山“无聊栖地”,商家稍加改造、装点,寻常农家小院这只土鸡,居然摇身变成了金凤凰。外表依然是瓦顶、砖墙、不规则的院落,而探身进去,会眼睛一亮,里面像宾馆和小酒吧,装饰风格恬淡而温馨。这个本该让乡村景致凋零的季节,没想到会带给我别样的惊喜,而我所见的,可能还只是豹之一斑。
照此下去,乡村会成什么样呢?现在,我也弄不清到了暮年,頤养之所该定在城里,还是乡村了。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