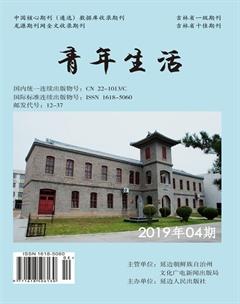曹禺笔下瑞珏与曾思懿的婚姻对照
杨雨晴
摘 要:曹禺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和其创作的小说《北京人》都以家族叙事为视角,分别讲述了二十世纪初高家和曾家两个大家族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中的两个女性人物,瑞珏和曾思懿,一个温柔,一个泼辣,她们两人本应毫无交集,但在作家的笔下,她们的婚姻生活出现了相似的运行轨道。她们都屈从于封建包办婚姻,并深受封建婚姻的禁锢,最终不可避免地落得悲剧的命运。
关键词:瑞珏;曾思懿;性格;夫妻关系;悲剧
曹禺的作品几乎都是对旧中国社会问题的反应,并且无一例外的对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女性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关注。他的诸多作品,都以女性的悲剧命运为情感主基调,塑造出一个个形象饱满、极富个性和感染力的女性人物。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性情刚烈、自我强烈舒张的繁漪、花金子等形象,也可以看到温柔贤淑、默默奉献自我的瑞珏等形象,还可以看到泼辣刁蛮、咄咄逼人的曾思懿等形象。她们的性格不尽相同,但这些女性逃不掉的悲剧命运,使两部都作品笼罩在悲剧色彩之下。
一、瑞珏与曾思懿的性格——贤妻与毒妇
两人性格的差异巨大,甚至是两个极端。在曹禺改编的《家》中,瑞珏是一个带有美好品质的温婉女性形象,甚至在某些程度上,与《北京人》中的愫方有些相像。曹禺在瑞珏身上给予了自己对女性的美好愿望和期待。
因封建长辈的包办,瑞珏与陌生的觉新结合,通过新婚之夜瑞珏的内心独白,就可以窥见这位女子心性的纯洁。“只要他真,真是好!女儿会交给他”[1]当觉新转过头来看她时,她“侧过脸,含羞,紧张”[1]“为甚么一见面,就觉着这样投缘?”[2]……内心独白过后,作者安排了几位孩子“听新房”的插曲,瑞珏帮忙给五弟穿鞋,温柔的叫醒在床下睡着的六弟,这样温厚的品格扣动了觉新的心扉,也融化了隔在两人中间的坚冰。婚后的瑞珏自是十分贤惠,第二幕第一景中写道,瑞珏“望着觉新总是那样诚挚地期待着什么”[3],她在家庭生活中,抚爱弟幼,孝敬长辈,表现得贤淑温婉,豁达大量。她不顾陈姨太的嫉恨和冷言冷眼,悉心服侍照顾高老太爷。为了爱,觉新看的书,瑞珏都看;为了爱,在兵荒马乱中,她坚持陪觉新守在前院;为了爱,她忍痛到城外去分娩,让觉新少受长辈的刁难。作者对瑞珏身上这些高洁情操和传统美德的描写,使得这个平凡的女子形象变得格外崇高,也使得瑞珏这一形象更加远离现实。可以说,瑞珏这个形象完全是曹禺“男性”理想观对女性的心理期待,这样极具传统美的瑞珏,其实承载的是作家“男性”期待中女性追问爱情的理想范式。
与瑞珏的美好不同,在《北京人》中,曾思懿从头至尾都扮演了一个“毒妇”的角色。曾思懿作为曾家的大奶奶,是曾家真正的当家人,家中的大小事,事无巨细都要她亲自批示,甚至整部《北京人》就是以曾思懿的出场为开始。文本一开头就说曾思懿“自命知书达礼,精明干练,整天满脸堆着笑容,心里却藏着刀,虚伪,自私,多话,从来不知自省。平素以为自己既慷慨又大方,而周围的人都是谋害她的狼鼠。嘴头上总嚷着‘谦忍为怀,而心中无时不在打算占人的便宜,处处思量着“不能栽了跟头”[4]。从这几句简短而又精准的描述中,曾思懿的“毒妇”形象就已经展现了出来。在剧本中,无论是曾思懿的处事方式还是她与其他人物的对话,无不体现了她的这些特点。对曾皓,她心中充满的是对金钱的算计,表面上的尊敬,只是想逼出曾皓手中数额所剩无几的银行卡。对儿媳妇瑞贞,封建家长制的高人一等使她完全卸下伪装,“滚!死人,你怎么不死啊!”[5]尖锐的话语将她的刀剑之心暴露无遗。对文清和愫方,她是残忍的,她摸清了所有人的性格,所以当她在曾皓面前提出让两人结合的想法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的“一片好意”,既会让自己显得很大度,又不会让自己有所损失。她这拙劣的小伎俩明眼人都明白,只不过她面对的恰好是两个懦弱的人,这点小伎俩才成了“精明的算计”,她也因此落得了“坏女人”的形象。
二、各自的夫妻關系——撇不开的“第三者”
高觉新爱着梅芬,曾文清爱着愫方。无论是觉新与梅,还是文清和愫方,从早年就在心里埋下了青梅竹马的种子,虽然觉新与文清都屈服在封建包办的婚姻之下,但这四人都割舍不下从幼年到青年的感情,以至瑞珏和曾思懿嫁过来之后都必须面对她们与梅和愫方交往。在《家》中,觉新与梅不是每天见面,再加上瑞珏的贤惠,生活算是幸福美满。但《北京人》中,文清与愫方常年低头不见抬头见,两人长期的情感压抑,经思懿性格的催化,造成了三人之间关系的“病态”。
瑞珏的心是善良的,虽知丈夫心系梅表妹,倾心与她交谈,发自内心的同情她怜惜她,两个女人的和谐减轻了觉新的负罪感和痛苦。在第二幕第三景梅芬要走时,瑞珏“羞赧”“深厚”地对梅芬说:“我真恨不得把什么都给了你,只要你能快活一点,他——他也能快活一点。”[1]她甚至想把海儿交给梅,回自己娘家,自己在心灵上承担一切痛苦,来成全觉新和梅,“我看他苦,我的心都痛了啊!”“我是真爱他,真是说不出的那样爱,那样爱啊!”[1]瑞迁向梅倾吐衷肠,情真意切,哀婉动人,句句都感人肺腑。 它把瑞珏善良无私、纯洁高尚的心灵世界,和无法排解的内心苦痛,真切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瑞珏对觉新爱的深沉,爱的纯挚,以致忘我无私。梅芬上轿离开时,“瑞珏悲哀地望着觉新凄恻的脸”[1],觉新不快乐,她也觉得不快乐,甚至她还会自责是因为自己才造成了觉新与梅的不快乐,梅芬病重的消息传来,瑞珏流着泪并哀痛地对觉慧说“是我害的梅表妹”。因为爱的太深太重,她对丈夫的爱远远超越了对自己生命欲求的关怀,她愁的是他的愁,喜的是他的喜,担心的是他的担心,痛苦的是他的痛苦,丈夫就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以致深情成了她的负担。瑞珏去城外分娩经过梅芬的坟墓,而她本身,也正在向着死亡靠近……女性的隐忍压抑被美化为善解人意,女性的委曲求全被升华为贤淑体贴,这个故事的确有些温暖动人。但这两个女人因为对觉新深沉的爱和性情的善良,都成为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作者通过瑞珏与梅芬的悲剧,发出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控诉。
在北平的曾家,曾思懿处处讽刺、压制着愫方,话里话外都能听出她对愫方的敌意。虽然思懿“毒”,但没有女人是不渴望爱的。从剧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曾文清对曾思懿的冷漠,曾思懿这样一个聪明的人是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的。她深知丈夫对自己没有爱,所以她心里一直存在着失去丈夫的恐惧,封建传统礼教在她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以夫为天”的思想,所以她拼尽全力想要维护这场没有爱且十分压抑的婚姻。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曾思懿是曾家的核心人物,但在曾府分崩离析的表面之下, 文清、愫方、瑞贞、曾霆构成了一个以愫方为中心的情感圈,他们之间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互相安慰,如文清与愫方,愫方与瑞贞,而唯有曾思懿高处不胜寒。丈夫躲着她,儿子躲着她,在偌大一个曾府里, 她游离于家庭感情的秩序之外。对于她来说,被排斥在主体秩序之外,使她丧失了主体身份,使她充满了失落的焦虑,深藏着被驱逐的恐惧,并随时渴望确证自身的存在。对于曾思懿来说,这种恐惧的最大来源莫过于愫方的威胁。愫方与丈夫文清之间的感情早就不证自明,曾思懿对于愫方的冷嘲热讽,逼着文清当面还给愫方的信,实际上不是对于文清感情的挽回,因为文清的冷漠早已使她认识到了这场婚姻没有丝毫爱的成分,她需要通过这种“泼辣”的方式在其他人心目中凸显自己的地位,她的这些所作所为,也正成了她“毒”的证据。曾思懿是可悲的,她想拥有爱,所以通过“算计”的办法来争取爱,但她这样做的后果,却是把爱的人逐渐从自己身边挤走了。
三、两人的悲剧命运的成因
(一)自身都为未想过反抗
在面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时候,她们都选择了接受。与其相似,瑞贞与曾霆也是这样的结合。但作为下一代的青年,瑞贞没有屈服在压抑的大家庭里,勇敢地选择了出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不值得她留恋,既然如此,又何必要留下来耗费生命。
瑞珏接触到了新的思想潮流,渐渐对一些新事物产生了兴趣,她看新书,学者用白话文写日记,并用自己的积蓄资助觉慧等青年人办进步刊物。她在牢笼般的封建大家庭中, 悄悄地呼吸着新时代的新鲜空气,甚至渐渐萌生了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热切向往。但可惜的是,她本质上还是一个封建旧家庭培养出来的女性,遵从“三从四德”,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她信守着她母亲灌输给她的“一个女人一辈子生儿育女、吃苦受难,都是应该的”[1]的旧观念。纵然性格中悄悄产生了些新的因素, 这不足以使她产生一种企图冲破封建桎梏的性格力量。她因为觉新和梅而痛苦,她的善良让她把这种痛苦归因到自己身上,她想过退出这场婚姻,但那只是为了让觉新和梅能够摆脱痛苦,活得快活一点。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压抑在自己、压抑在所有人身上的,其实是罪恶的旧社会。所以瑞珏最终还是凄惨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在杜鹃声中走进高家的洞房,最后又在杜鹃的啼叫声中悲惨死在了高家的旧屋中。
曾思懿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旧家长似的女性,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她没有接触过新思潮,毫无一丝进步思想可言,她感觉到了这个家庭的衰落,她想努力拯救,但她依赖的办法依没有走出旧封建的圈子。曾思懿在那个时代,无可例外的成为了父权的受害者和维护者,她坚定地守着旧社会的“ 礼数”,指望着用封建礼教来重整这个家庭,因为她想抓住且能抓住的只有封建礼教这个对她来说就是一切的“救命稻草”。身为悲剧的承受者却浑然不觉,甚至于为再一次成为施暴者而沾沾自喜,最终也只能成为维护旧社会中的一个干瘪的符号而已。社会的不断进步证明了封建社会终会灭亡,男权意识下等待她的最终只能是作茧自缚。
(二)封建礼教的残害
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而言,若要建立起门当户对的婚姻关系,首先就是门第观念,其次是家族财产,婚姻关系是两者的搭配或势力的联合。对于双方而言,爱情在婚姻关系中微乎其微甚至毫无半点。婚姻顺理成章的打上了无爱的标签,家也成为了禁锢爱的樊笼。这样的封建婚姻,无疑是造成旧时代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瑞珏与曾思懿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
瑞珏平和地接受了长辈们为她包办的婚姻, 没有像繁漪、花金子那样的反抗和不满, 并以自己的善良和宽容赢得了丈夫的“爱”,婚后她们心灵相通,产生了感情, 互相爱恋,他们是一对应该得到幸福的好人。曹禺在瑞珏临死前的这场戏里, 着力表现了她对觉新的深挚的爱以及她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 在瑞珏生产时,因为封建家庭的压力,觉新不能守候在她身旁,甚至到了垂死时,她也只怕惹起丈夫的伤心和担心丈夫没人照顾,生命垂危之际,瑞珏依然顾不上考虑自己的安危,也没有一丝青春生命面临死亡时该有的惊惧、痛苦,一如既往地替丈夫的生存考虑,安慰觉新“不过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1],鼓舞觉新在自己死后勇敢地去追求新生活。如曹禺所说,“她应该很好地活着, 却被封建礼教无辜地断送了生命。”他们处在封建婚姻制下所遭遇的不幸,也正是一些善良的青年男女在封建社会里所遭到的悲剧的命运。
曾思懿虽然“毒”,但她又何尝不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曾文清和愫方之间自由爱情的失败,并不是曾思懿一手造成的,但是她却为两人的爱情悲剧承担了众多非议和诟病。在这个充满悲剧的婚姻中,曾文清除了企图逃避就是消极抵抗,相反,曾思懿为了维系自己的婚姻尽了最大的努力,无论是逼迫丈夫退回愫方的“情书”,还是在策划愫方出嫁时斥责丈夫,都是她煞费苦心地想要用夫权秩序和伦理纲常维系这个四分五裂、濒临毁灭的封建家庭的圆满。曾文清对曾思懿的无爱的漠视是一种无形的磨砺,使得曾思懿的灵魂走向麻木,使她整日沉浸在猜忌和报复的情绪之中,内心趋于难以抑制的疯狂,性情也变得越来越乖戾阴毒。她被人们不断指责的险恶性格是在不幸的婚姻状况下形成的,这是她的悲哀,是封建婚姻造就的悲哀,这是整个社会的错,并不是她个人的错。
婚姻是座围城,她们在懵懂中被推入了围城,在无意识中将自己禁锢在了围城里,在无意识中一步步走向了毁灭。处在封建婚姻这座围城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无法避免走向悲剧的结局,但她们都是无辜的,无论是瑞珏还是曾思懿。她们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她们同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个女人一样,只是想过平静安稳的日子,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大家族的衰落注定了她们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幸福和爱情遭到狂暴的摧残, 黑暗的封建势力是青春和一切美好事物的死敌,她们是衰败下去的旧家庭的女人,这种衰败不单属于家族的而属于时代,所以她们注定要去陪葬,她们注定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参考文献:
[1]曹禺.《家》[M].曹禺戏剧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曹禺.《北京人》[M].曹禺戏剧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3]廖全京.曹禺:在《北京人》和《家》中走向潜沉[A].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C].上海:中国戏剧家协会.2011.
[4]茜萍.关于《北京人》[N].曹禺研究资料(下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5]何其芳.关于《家》[Z].曹禺研究资料(下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6]李天济.论剧作《家》中的人物创造[N].曹禺研究资料(下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