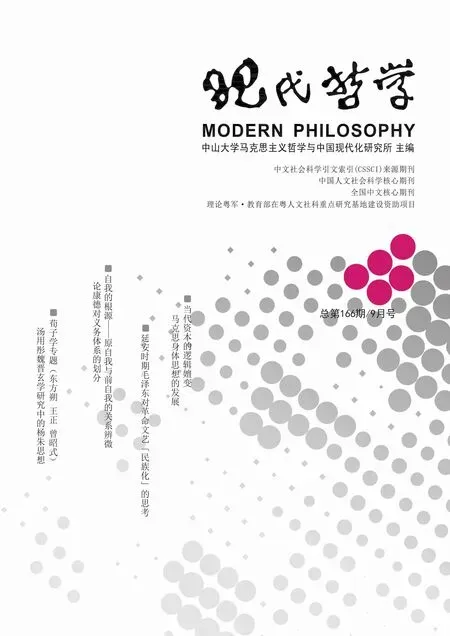卢梭与作为哲学问题的自恋
汪 炜
对卢梭来说,自恋首先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具生殖力和形态学特征的概念。从语义学和词源学的角度来看,自恋或那喀索斯主义(narcissisme,或德语的narzissmus)一词起源于Narcisse(那喀索斯)(1)如无特别说明或需要,文中凡涉及西文的专有名词均依循法文拼法。此外,本文中卢梭著作引文均出自伽利马出版社“七星文丛”版《卢梭著作全集》(uvres complètes, sous la direction de 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 Paris :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9-1995),以下简称《全集》,将直接在引文后的括号里标明卷数和页码;本文中卢梭书信引文均出自拉尔夫·利(R. A. Leigh)主编的52卷本《卢梭书信全集》(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Genève : Institut et Musée Voltaire, puis Oxford : The Voltaire Foundation, 1965-1998),以下简称《书信》,将直接在引文后的括号里依次标明信件编号、卷数和页码。所有引文均为作者自己的译文。。它既是一个总遭遇到误解(contre-sens,反意义)的忧郁而深刻的神话故事中的虚构人物,也是植物学对石蒜科中某一属植物的分类学命名(2)卢梭在其《植物学通信》中错将水仙花认作百合科植物。在此,本文更加关注的是其所谓的植物学“趣味”以及伴随他一生的这种科学和哲学实践活动。。这两个名称既在一系列神话学和伦理学话语中相互勾连,又同时在其共同的意义起源中找到更加丰富而多样的谱系学。Narcisse源于希腊语narkè(“入睡”),因为“人们认为水仙花具有麻醉催眠的效用”(3)Dictionnaire universel françois et latin, ou Dictionnaire de Trévoux, tome IV, Paris: Julien-Michel Gandouin, 1732, p.23.。在此意义上,普鲁塔克赞成索福克勒斯的说法,即Narcisse是地狱之神头顶上的皇冠(4)Plutarque, uvres morales de Plutarque, tome III, traduites du grec par Ricard, Paris: Lefèvre, et Charpentier, 1844, p.251.。而在那个神话故事中,Narcisse当然还与一种知识空间和目光拓扑学的原型相关,我们可以将其同《斐多篇》中的某些著名篇章(99c-d)联系起来。
这些问题都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在同一个概念中获得其自身的特定位置,并导致了一系列持续至今的哲学效应。在卢梭之前,这并不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卢梭很早就估计到这个概念所蕴含的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也充分意识到这种估计本身所可能具有的局限性。他以一种启蒙时代所特有的、源自蒙田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和写作方式,将这个概念及其问题或明或暗地显露于其作为一名“反哲学家”(5)斯塔罗宾斯基敏锐地注意到,卢梭既是“哲学家”,也是“反哲学家”。Jean Starobinski, Jean-Jacques Rousseau. La transparence et l’obstacle, Paris: Gallimard, 1971, p.9.的哲学体系之中;他通过不断的评估和重审,赋予这一问题和哲学本身新的维度和风格,并注定要因此忍受那些来自“先生们”(Messieurs)和“人们”(Hommes)的误解乃至诽谤,直至今日(6)伏尔泰认为,卢梭是无知愚昧和倒退回动物式的自然状态的赞颂者(《书信》317,卷3,第157页);狄德罗则认为卢梭的著作都是“片断和散块”拼凑出来的(《全集》第2卷,第317页)。至今仍有人否认卢梭的哲学家资格,认为他只是一个偏执而谵妄的文学家或艺术家。而卢梭自称是一个梦想家或艺术家,并不愿成为人们眼中那种抱着美丽假设来陈列各种体系的哲学家(《全集》第4卷,第941页) 。。这种不断评估和重审的运动,开始于卢梭18岁那年以这个概念为名而创作的独幕喜剧《那喀索斯或自恋者》(7)卢梭在1753年此剧发表时所附的序言中说自己18岁那年创作了该剧。尽管他后来在《忏悔录》中承认自己说谎,他其实是在尚贝里居住期间(1732-1740)创作了该剧,不过他仍然强调自己创作时的年龄没有超22岁。无论如何,这部剧作可以说是卢梭最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思想动力的源泉。《全集》第1卷,第120、1290页。,并因此而提前在哲学中打破了其意义复杂性的沉默,明确提出这一哲学问题,然后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下简称“第二篇《论文》”)《爱弥儿》《忏悔录》等作品中隐秘嵌入此问题,直至最后在一个充满了现代性的文本《遐思录》中重新建构了自我:“我的生存”(mon existence)。或许卢梭已展现了这个问题的全部面向与可能,同时清查了这一问题进行自我调整和转换的几乎所有的层级、帧率和剖面,不论是《社会契约论》中的极端解决方案,还是《忏悔录》中源自一种主体性疯狂的申辩。卢梭既是生活在18世纪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也是生活在我们之中的现代人。
因而,要理解自恋问题(或者说那喀索斯主义)的复杂性及其在卢梭哲学中的位置,首先需要追溯和限定这个问题,然后从其派生的歧义概念入手,在它们的混淆与分化中达至一种清醒状态。
一
关于自恋,除了人们在日常用语所表达的模糊而流行的(世俗的)含义之外,还有一种明确而异常复杂、棘手的意义。根据前者,自恋是一种对于自身的偏爱或者沾沾自喜的倾向。对这种倾向的尝试性解释有两条途径:一是源自19世纪末的心理学,在20世纪初受到一群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关注;与此相关,二是对欧洲19世纪的浪荡主义(dandysme)所采取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不过,作为当时一种社会姿态的浪荡主义有其深刻的伦理学和哲学背景,它很可能与这里所说的“自恋”或那喀索斯主义问题相关。加缪(Albert Camus)认为“浪荡主义是一种弱化的苦行”,而浪荡子的口号就是“在一面镜子前生和死”(8)Albert Camus, L’Homme révolté, Paris: Gallimard, 1951, p.72.,这正是一个那喀索斯所是或应是的现代化身。
因此,不论是哪条途径,自恋的世俗含义都应以另一种关于它的明确意义作为基本前提。这种意义渗透到我们的语言和肉体,每当我们以为自己彻底摆脱了它,或者我们用五花八门的源自其不同面向和层次的次生概念来伪装它时,它总会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或者暂时无法理解的方式在我们面前重现。这种明确而复杂的意义直接处于心理学和哲学研究的前线。在心理学方面,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让我们颇受启发。他首先将自恋作为处于自体性欲和对象性欲之间的中介性的性进化阶段,在这个阶段,自我(Ich)被建构为在自体性欲阶段尚未形成的一个统一体,它是聚集着力比多的巨大的储藏室,因此自恋在统一的自我人格的形成方面具有必然而本质的强制性作用。在《图腾与禁忌》中,他甚至认为即使具有自我人格的成年人的力比多已经转向了对于外部对象的选择,但是人们仍然无法摆脱自恋,因此自恋力比多是对于人类的自私或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的无意识说明,即其所说的“自恋是自私的力比多补充”(9)Sigmund Freud, Introduction à la psychanalyse (1917), Le Narcissisme, l’amour de soi, dirigée par Bela Grunberger et Janine Chasseguet-Smirgel, Paris: Sand & Tchou, 1997, p.56.。从1914年开始,弗洛伊德进一步将自恋与人的整个存在相联系,而不仅认为它是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他区分了两种自恋:自恋首先是对自我的力比多“投注”(Besetzung),即原发性自恋,主要指儿童在选择外部对象之前将自己作为性欲对象;其次是继发性自恋,即通过与母亲的关系的内化,向外部投注的对象力比多折返回自身。通过这种力比多的一元论,弗洛伊德试图直接阐明自恋及其意义的深层心理结构,进而以此对自我和个体乃至人类文化的形成做出某种哲学式的解释。这种解释与卢梭关于自恋(amour-propre)与自爱(amour de soi)的区分具有非常明显的“对称性”(10)本文将卢梭的重要概念amour-propre翻译为“自恋”,而没有采用通行的中文译法“自尊”“虚荣”“骄傲”等。关于这个概念的哲学内涵及其中文译法的初步探讨,以及卢梭和弗洛伊德的概念区分之间的“对称性”,参见汪炜:《如何理解卢梭的基本概念amour-propre?》,《哲学动态》2015年第10期。。不过,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早已超越了精神分析学领域。
首先是理论解释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弗洛伊德预设了实在与经验之间的连续性,从而停留在对心理现象本身的描述、归纳和分析,忽略了从自我到对象、个体到一般性这一过程的曲折性和巨大裂痕,放弃了对于扎根于物质世界中的普遍性结构的探求。这或许是吉拉德·埃德尔曼(Gerald M. Edelman)称弗洛伊德是一个“属性的二元论者”(11)Gerald M. Edelman, Bright Air, Brilliant Fi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12.的原因(相对于笛卡尔的实体的二元论而言)。尽管弗洛伊德对自恋力比多的无意识结构的把握试图超越经验认识和反思语言的封闭性而达至某种科学的客观性,但这种结构显然仍是停留于心理沙地之上的海市蜃楼,并没有逃脱时间性神话的掌控。即使他在1914年出版的《自恋导论》中提出了自我理想(Ichideal)这一概念,后期甚至将它与超我(über-Ich)等同起来(参见1923年出版的《自我与超我》),从而将其视为一种独立于自我之外、对自我具有一定主导作用或者向自我提供一种具有有效性的理想化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个体性的还是集体性的——可它仍然固守于一种心理内部的投注现象。从哲学上说,弗洛伊德依循的还是一条“主宰着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哲学的主体-客体关联性的道路”(12)Maurice Merleau-Ponty, Signes, Paris: Gallimard, 1960, p.155.。
与此相应的是弗洛伊德在方法论上的还原主义。这个问题从他开始关注自恋问题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从对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童年的研究(参见1910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对童年的一个回忆》)开始,弗洛伊德就将自恋与同性恋的成因联系在一起:将自身作为性欲对象的结果是产生了对自身生殖器官的兴趣,随后便会发展为对于拥有同类器官的同性的欲求。这种还原论式的解释模式从此时开始就已经成形,其基本特征是作为力比多的不变的“先验”原则的设定,以及一种垂直式的简化的时间演化图式,最后是着迷于对若干关联区域的、泾渭分明的大区分,消除了这种区分内部或者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增殖可能。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就批评精神分析学对自恋问题的研究缺乏辩证法的维度(13)Gaston Bachelard, L’Eau et les rêves : Essai sur l’imagination de la matière, Paris: José Corti, 1942, p.31.。
对精神分析学在自恋(那喀索斯主义)问题上的处理方式进行简要的回顾是必要的。一方面,它直接面对着关于自恋的明确而复杂的意义本身,因而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也是潜藏在哲学话语中不断重现的问题,是精神分析学、人类学和某种哲学发生重合的话语空间。因而,精神分析学所遇到的上述那些问题,或许同样是某类哲学所遭遇到的问题。然而,与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不同,长久以来,这类哲学都把上述问题当作某类心照不宣的概念而加以阐明和运用,尽管它们总是或明或暗地遭遇着,但前者总是躲避着后者,几乎不愿费心思去直接谈论后者。近来,我们才在一种源于启蒙时代的、被中断了的“现代的”哲学姿态中看到了思想与上述问题的正面交锋。
与在精神分析学中的情况相仿,自恋首先也是一种哲学的神经官能症,它长期以来建立于某种基本的大区分之上,以及对这种区分之间的连续性的哥特式信念,不论这种信念是依靠反思或是直观,还是某种意志或欲望的作用而得以实现。人与世界、文化与自然、个体与普遍、经验与实在的关系,总是陷入一种被强加的、简单而直接的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对应结构之中,而这种结构又总是以观看者的视线为主导,这种视线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内在性的、呈现于自身的观看。因此,自恋或者那喀索斯主义问题就是对这样一种视线和影像的迷恋,对一种目击者和叙述者式的姿态,即一切经验的现象学姿态的固守。这种哲学中的那喀索斯主义从那个古老的神话中分离并歪曲了一些元素。这些元素既是赢得个体性的必要的重返,也是固守其中的危险。因为它与自我意识的起源和现实世界中的个人身份或同一性相连,然而这往往会转化成一种危险和契机。
当那喀索斯明白那湖中的影像就是他自身的时候,他对这种悖论发出感叹:“我已然发觉我即是它,我的影像不会将我欺瞒;我在对自身的爱中燃烧:那折磨着我的火焰亦由我自己点燃。”(奥维德《变形记》:463-464)(14)本文中奥维德的引文均出自Ovid, Metamorphoses, Books I-VII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84。本文引用的所有古代作家(如奥维德、柏拉图、塞涅卡等)的引文,均只标明出处及罗布古典丛书中的对应边码,所有引文均为作者据此版本的译文。因此,影像不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表象,它一方面向自我揭示了真理,另一方面又以某种悖论的方式与一个自身融合:“我从我这里获得的占有物却使我无法占有我自身。”(奥维德《变形记》:466)对这个自身-影像的爱想要将我与我自身联合起来,想要在我的整体性中重新找到我自己,但如果不通过迂回的弯路,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个体与自身无法重逢的悲剧意味着与自身结合的渴望需要我们先远离自身:“我希望我之所爱远离于我。”(奥维德《变形记》:468)在普罗提诺的阐释中,我在那自我的影像中要去辨别和认识的其实是一个极限他者的极远方的形象,是一个在最高处隐匿自身的外在的神明。因此,正如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所说,“普罗提诺是这样一个转折的开端:影像不再被定义为对表象的模仿,而是作为对本质的表现……每一个个体灵魂的命运都在这镜子模型引起的两个极点中间演出。或者说灵魂置身于散发光线的源泉中,也就是说在它自身中,它保持朝向存在和太一的太阳,它凝视着这太阳,它在这目光中与太阳联合,与太阳混淆起来”(15)Jean-Pierre Vernant, uvres, II, Paris: Seuil, 2007, p.1424.。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或者自我的存在经由分裂与多元化的途径,经由看与被看被交互性地、“自然地双重化”(16)Gaston Bachelard, L’Eau et les rêves : Essai sur l’imagination de la matière, Paris: José Corti, 1942, p.34.,最终统一在一种普遍性之中。
那喀索斯最终未能直接践行这一分裂与融合的普遍化道路,然而他的死亡也并未真正导致弗洛伊德所得出的破坏性的“死亡冲动”(Todestriebe)的危险。相反,正如这个神话本身以及后来在卢梭的思想和实践中所看到的,那喀索斯用他那“沸腾的鲜血”(《全集》第1卷,第1083页)滋养了一片与其同名的植物,这既是一种“变形”、转换或重生,也是一种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所说的应和(correspondance)。如果剔除了普罗提诺对那喀索斯神话的阐释背后的新柏拉图主义成分,那么或许可以得出这种变形或重生的基本原理:那喀索斯主义的问题既不再关乎某种理念或实体,也不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问题,或者说已不再是一种关于主客体的关系和自身对自身在场的问题。它是嵌有一种交换进程的客观性的普遍条件或结构,在这种匿名的、非人的客观化过程中,个体与文化才能真正找到它的自身或nature(自然、本性)。因此,那喀索斯的神话既展现了一种必要性的危险,也暗示了一种脱险的方案。这就如同缪塞(Alfred de Musset)笔下的那只被套夹困住的狐狸一样,只有不断啃噬那只被夹住的脚,才能求得逃脱(17)Alfred de Musset, 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73, p.19.。那喀索斯神话所蕴含的这种辩证的潜力需要在艰难而长期的哲学行动中被重新找到,卢梭或许就是自觉采取这种行动的第一人,因为他是“这种根本的客观化的伟大发明者”(18)Claude Lévi-Strauss,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Deux, Paris : Plon, 1973, p.49.。
二
这种艰难的哲学行动有其自身发展的基本曲线或者史前史,通过简要回顾,可以揭示这条逃脱之路以及卢梭在其中所处的位置。通过尝试使那喀索斯主义这一问题的“外延和内涵多样化……把它导出其起源地之外;将其视为样式,或者反过来,为其寻找到某种样式”,我们将重新发现那喀索斯主义或自恋问题与我们所关注的那些哲学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且将“通过诸种规整化的变换而逐步赋予其一种形式的功能”(19)Georges Canguilhem, étud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Paris: Vrin, 1968, p.206.。
在那喀索斯的神话故事结束之时,在镜子被采纳为一种话语范式和一种基本的哲学工具的时刻,那喀索斯主义或自恋这个问题就第一次出现了。柏拉图和塞涅卡是这种自恋问题的重要代表。在柏拉图那里,问题在于要建构一种正当的关乎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自己的影像(参见柏拉图《斐多篇》:99,以及《智者篇》:265)。塞涅卡则讲述了一个叫做沃斯提乌斯·瓜德拉(Hostius Quadra)的放荡成性的贵族奴隶主利用镜子对人体的夸张影像来满足一己私欲的故事(参见塞涅卡《自然问题》:I,16.1-16.9)(20)本文中塞涅卡的引文均出自Seneca, Naturales Quaestion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71。所有引文均为作者自己的译文。,并随后得出结论:镜子的发明是为了认识自身,获得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给予我们看见自身的机会”(塞涅卡《自然问题》:I,17.4),不过这不是为了沉迷于自身的影像,否则,我们就会“受到自己对自己的爱的折磨”(塞涅卡《自然问题》:IVA,2)。塞涅卡马上又用一个对应结构的句子,说明这种爱其实就是一种自负和欲望。在这里,已经可以隐约看见卢梭日后处理自恋问题的思路雏形(21)卢梭对柏拉图和塞涅卡都深有研究,他也亲自翻译过柏拉图和塞涅卡的著作和一些残篇。参见《全集》第5卷收录的翻译作品,以及Léon Herrmann, Jean-Jacques Rousseau, traducteur de Sénèque, in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Jean-Jacques Rousseau, tome 13, Genève: Librairie Jullien, 1920-1921, pp.215-224.。
对于塞涅卡来说,如何把镜子运用为一种陈述的范式,来呈现关于实在世界的恰当的影像,但同时又并不会在这影像或陈述中看见主导这一影像或陈述的主体形象,这是自恋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里,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和道德哲学与斯多亚主义接合起来,他在《论基督导师》中提出如何构想一种可以不带任何欲念的语言教学法,即要剔除那种希望自己被看见、被喜爱或是可以将某种好处占为己有的欲望(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I,8)。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原先被基督教的否定自我的姿态所遮蔽的自恋问题重现于哲学当中。然而,此时的它已不再只是一个道德的或伦理的问题,而是以构成性的方式在那充当某种主体性的实体及其责任的哲学姿态中发挥作用。人及其文化开始试图摆脱对某种超人类的神圣的或自然的观念秩序的依附,因为真理、德性、正义乃至人的地位不再由这些秩序所决定。个体重新被一种对于自身的欲望所主导,他开始要求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22)Descartes, uvres et lettres, 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3, p.168.。问题不再是依附某种外在的权威,而是要以真理之名肯定自我。卢梭说他的行为准则“是自然用不可擦除的文字刻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们行为的一切道德性都在我们自己对它的判断中”(《全集》第4卷,第594、600页)。康德正是在卢梭的这种感召之下于1784年回答了何为启蒙的问题:Sapereaude,即自己要有勇气去运用自身的智力!尽管康德曾长期把卢梭看作是伦理学中的牛顿,然而正是从康德出发,我们今天才重新建构了卢梭的哲学形象。对于康德的先验哲学来说,“一个人不是从对象出发,而是从建构他自己的思想主体的可能性系统而开始的,他是他自己思想能力的发动者”(23)Immanuel Kant, Opus postumum, translated by Eckart Förster and Michael Ros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7.。先验哲学是自己规定自己的体系,只有脱离了形而上学的先天综合知识才打开进入到先验哲学的道路。这一点异常重要,因为正是通过某种半熟的批判哲学的风格,卢梭与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与从启蒙时代延续至今的那种那喀索斯主义哲学之间的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才能够得到恰当理解,我们也在这种理解中提早地看到了某种构成性的、先验的和非那喀索斯主义的主体性这一艰难问题,以及对建立那不可逾越的壁垒从而完全废黜一种个体姿态的追求。正是在这里,卢梭默默超出了伦理学的范围——也许他本身并不知情——对那喀索斯主义或者自恋问题在近代的主体性形式的形成起到了悖论性的中介作用。
卢梭或许是从蒙田那里获得这种辩证的力量,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说:“道出这一切的不是卢梭,而是蒙田!”(《全集》第3卷,第86页)。对于蒙田来说:不再是通过镜子,而是利用自身来让每个他者都能看见他自己的面孔。这种重新折返回自身的运动的本质,是不停地探问自我得以构成的那些条件。在卢梭之前,蒙田就与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主流保持着一种辩证的距离,他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材料包含进他的怀疑之中,既是反哲学和神学的,也是对一种绝对个体的神经官能症的软化:“是否有一种既存在于我也存在于所有人之中的自然力量,而这力量使我们能够承认我们朝向正义和真理的努力具有一种积极的含义和一种内在的价值?”(24)Léon Brunschvicg, Descartes et Pascal, lecteurs de Montaigne, Neuchatel: La Baconnière, 1942, p.96.蒙田的问题得到了笛卡尔和帕斯卡尔的关注,两人以不同的方式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而它们也都在卢梭那里重新得到考察和转换。
笛卡尔在《方法谈》第三部分启用了“一套临时的伦理规范”来回答自恋问题,尤其是第三条准则:“除了我们的思想以外,任何事物都不是完全地在我们的力量范围之内的。”(25)Descartes, loc. cit., p.142.这个回答是为了避免一种犹豫不决而下的决心,始终处于一种临时的决心范围之内,并且期待能有更好的回答方式。因此,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回答,它向我们抛出了一系列关于自恋的未有定论的方面。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其中两点:第一,笛卡尔主义的认识论划分。在这种划分中,数学模型分离出一种说话和判断的类型,而陈述本身在这类型中是被贬低的。自恋问题现在在一种判断的哲学姿态中获得其地位。不过,此后一旦欧几里得的几何模式发生了动摇,各种笛卡尔主义者们就不得不忧心于“科学的危机”,并寻求一种陈旧的、排中性的概念作为自己的最后避难所。第二点与第一点紧密相关。在出版《第一哲学沉思集》后不久,笛卡尔在现代意义上论述《论灵魂的激情》,格外关注其中的意志问题。他对灵魂之激情的首要定义,即所谓的宽宏(générosité)显然是一剂对自恋的伦理解毒剂,它同日后的积极的浪荡主义姿态密切相关,即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所讲述的一种震惊力量:它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可是没有什么能让它感到震惊。
笛卡尔的问题当然受到了17世纪的伦理学家们的重视,譬如拉罗希福寇(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和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这是一种正在建构当中的现代哲学,它从一开始就将哲学问题中的激情层面与其社会层面联结起来,这是我们始终都不应忘记的,它构成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卢梭问题的动力之一。更有意思的是,这一阶段的一些语法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态度,与伦理学家们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一拍即合。阿尔诺(Antoine Arnauld)和尼科尔(Pierre Nicole)将笛卡尔问题的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把在作为逻辑和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说话和写作(当然也包括绘画)中对于第一人称的节省不仅仅看作是一种语言策略上的要求,更是一种伦理和宗教的要求:“为了不让我们的对话者产生误解,以及不使他们对我们想要说服他们接受的真理产生反感,我们可以加以注意的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尽可能少地因为谈论自我而激起他们的妒忌和猜疑,并向他们展现可能跟他们相关的对象。”(26)Antoine Arnauld et Pierre Nicole, La Logique ou l’art de penser, Paris: Gallimard, 1992 (1662), p.250.这种思想显然受到了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深刻启发:“自我是可憎的……然而我憎恶它是因为它是不正当的,而且它使自己成为全体的中心。”(27)Blaise Pascal, uvres complètes, tome II, édition présenée, établie et annotée par Michel Le Guern, Paris :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2000, p.763.不过,这里所说的可憎的自我(moi)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个主体或实体。“唯一真实的美德就是憎恶自身,这是由于我们因自身的贪欲而是可憎的;这美德在于寻找一个真正可爱的存在者,从而去爱慕他。但是由于我们无法爱那在我们之外的事物,故而应当去爱一个在我们之中且不是我们的存在者。”(28)Blaise Pascal, loc. cit., p.755.因而,自我之所以是可憎的,是由于其对自身的一种不正当的爱。解决自恋问题不在于消除那个自我,而是要去管治这种不正当的爱,或者说,通过弄清楚什么才是它真正的“自身”,从而在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中而导向那正当的爱;反之,只有爱能将我们引向真正的自我认识,它是赋予我们的思想和意志以活力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尔-罗瓦雅尔语言学派清楚地表明,这种语言学的节省原则正是为了避免陷入不正当的爱,即自恋(amour-propre)的困境。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的许多重要作家并没有将amour-propre与amour de soi(或amour de soi-même)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情感。拉罗希福寇在《箴言录》中对amour-propre极为赞扬,提到十多次,而谈到amour de soi则不过一次而已。卢梭在读完《箴言录》后称它是一本“让人心灰意冷和不愉快的书”(《全集》第1卷,第112页)。伏尔泰说它是“一种所有人都有的自然情感;它更接近于自负,而不是罪恶……说自爱(amour de nous-mêmes)是我们的所有情感和行动的基础的那些人在印度、西班牙以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是很有道理的:这就好比我们不需要写些什么来向人们证明他们都具有一张脸孔一样,也不需要向他们证明他们都具有自恋(amour-propre)的情感。这自恋是我们保存自己的工具;它就好像种族延续的工具一样”(29)Voltaire, uvres de Voltaire, tome XXVI, Paris: Lefèvre, et Werdet et Lequien Fils, 1829, pp.274-275.。伏尔泰将amour-propre看作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永恒联系,并可以导致互惠性和对他人的仁慈。显然,伏尔泰在对它的使用上与amour de soi没有什么区别。
这里,便出现了卢梭处理自恋问题的一个关键的门槛。卢梭追随了奥古斯丁的路线(30)这里可以看出奥古斯丁主义者帕斯卡尔通过波尔-罗瓦雅尔学派而对卢梭产生的重大影响。,由此amour-propre和amour de soi就不再是同义词。对于后者来说,它与后来弗洛伊德所说的Selbstliebe显然有着根本的不同;而对前者来说,其内涵超出了一种纯粹道德的领域,伦理学的意义只是它所产生的一个效果。它与自恋问题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早就说过:“对自身的爱是一切有理性的活动的原则。这不是自我主义:有生命的存在者生来如此,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身。”(31)Pierre-Maxime Schuhl éd., Les Stoïciens, tome II, trad. émile Bréhier, Paris: Gallimard, 1962, p.853.因此,本文将amour-propre译为“自恋”,amour de soi则译为“自爱”。卢梭在第二篇《论文》的第十五个注释中对两者的分别作出了那段著名的论述:
不应该混淆自恋和自爱,这是两种在本性和其效果方面都极为不同的激情。自爱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它使得所有的动物都关注于对自身的保存,并且在人类那里受到理性的引导和同情心的调节从而产生出人性和美德。自恋则只是一种相对的、人工的情感,它诞生于社会之中,并使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重视胜过其他任何人,它还引起人们互相做出所有的恶行来,它是荣誉心的真正源泉。(《全集》第3卷,第219页)
冉森派和波尔-罗瓦雅尔学派对卢梭的影响,特别是阿尔诺和尼科尔在逻辑学中对amour-propre的公开批判,还表现在这种将判断、逻辑和伦理学联系起来的倾向将我们带到一种哲学的核心地带,这种哲学伴随着启蒙时代的哲学氛围同18世纪被推到前台的一种政治和意志主体一同发展出来:“奴才!去跟你的主子说,是人民的意志让我们坐在这里,只有武力才能迫使我们离开。”(32)在1789年6月23日举行的一场全国三级会议中,国王仪典总管德勒-布雷泽侯爵要求第三等级离开会议大厅,来自艾克斯-普罗旺斯的第三等级代表米哈博伯爵回应道:“奴才!去跟你的主子说,是人民要求我们坐在这里,只有武力才能迫使我们离开。”米哈博伯爵的这句著名回应的准确表达到底是什么,历来有很多种说法,不过差别不大。(Edmond Dubois-Cranté, Analyse de la Re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G. Charpentier, 1885, p.23.)政治问题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境遇,但是当一种不同的人类秩序出现时,它就关系到一种主体性的问题了。这种主体性问题不再被作为面对着世界的秩序而得到界定,而是面对着一种被分享的意志。
三

不论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政治方案,还是其《忏悔录》(或者王尔德[Oscar Wilde]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心理学和伦理学技术,由于这一根本哲学问题在其中的缺席,它们的失败将被一种重复出现的那喀索斯主义的时针所标示出来,而它同时标示出不断伴随着所有哲学的日程表:不是放弃主体性问题,因为主体性的蕴含是本质的,我们无法摆脱这种牵连,但它不是一种实体性的条件,而只是一种哲学活动的特征。伦理学谴责利己主义,政治学谴责对不合法权力的占有。自恋则是一种对自我的着迷,产生自另一种秩序,某种越轨失常的哲学姿态,但这绝不是对一种哲学要求的否定。由此,便提出一种对主体性进行更新的哲学要求。从这个角度重新阅读卢梭及其问题的丰富性,需要对自恋或那喀索斯主义这个扭结重新采取哲学行动,并将这一哲学行动铭刻在一种现代化的“实证主义”之中。
自爱在卢梭那里跟一种自我保存的本能相关,它可以通过同情心(pitié)的调节或扩展而超越个体,延伸至同类乃至所有生命形式。自恋则使个体将自身放在绝对高于他者的位置之上;它制造社会分化,催生虚假的道德价值和文明秩序。通过区分自恋和自爱,卢梭一方面宣告个体性的无罪,另一方面又将个体与物种、自然与文明、感性与理性的问题提上日程:自爱是自然的,而当社会状态下的人无法避免地将自身与其同类比较时,自爱就堕落为了自恋(《全集》第4卷,第492—493页)。
因此,卢梭对自恋问题的关注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伦理学以及个人主义的心理学的范围,走向一种无限广阔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考察。尽管我们无法否认卢梭著作中那强大的伦理学修辞,但更应该看到存在于这种伦理学之下的根本关切与基础原则。
在我看来,人类的一切知识中最有用也最不完善的知识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注释二),而我敢说单单德尔斐斯神庙上的那句铭文就含有比那些伦理学家们的所有巨著都更加重要且更加艰深的训诫。(《全集》第3卷,第122页)
在这段话的“注释二”中,卢梭引用了被他视为真正哲学家的布丰(Buffon)的著作《自然史》中的一个段落,从而将那句哲学开端的古希腊箴言与一种新生的人类科学等同起来,将他的伦理学考察与一种哲学认识论联系起来,并将后者奠定为“人文科学的真实原则和道德的唯一可能的基础”(33)Claude Lévi-Strauss, loc. cit., pp.55-56.。因而,思考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问题的人类学方法,也是一种试图重新把握感觉和理智、个体与普遍之间关联性的哲学工作,因为“这是我们不能返回的原初的谎言”(34)Maurice Merleau-Ponty,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Paris: Gallimard, 1964, p.75.。这种过渡和关联性与卢梭说的自爱这种情感密切相关。这种方法或工作将揭示另一种建构主体性的感知逻辑,它不再隶属于一种反思的模式,而这种感知逻辑展现出一种新的可理解性的图式或结构。这种可理解性的图式既不能被绘制为我们与影像的模拟的-自恋的关系,正如普罗提诺对那喀索斯神话的阐释所否定的那样,也不能通过那经典哲学式的描述姿态而被捕捉。对卢梭来说,更为重要的或许还是这种可理解性的图式让我们避免了对于当代社会及其中的人进行一种简单的伦理学的或短视的思考,揭示出个体与世界、我们的理智与感性、实在和经验在一种物质性的载体上的丰富而多变的交换模式,揭示出我们的生活和文明的虚拟形式与可能性。应该看到,卢梭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所采取的是一条中间的道路。
正如前面分析那喀索斯的神话时所预先说明的那样,卢梭的问题已经不仅限于自恋或者那喀索斯主义,而是牵涉到由最初的自恋与自爱的区分所引起的上述整个问题链效应。因而,我们其实不应该称其为自恋或者那喀索斯主义问题,不仅是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就呈现出来的这个极具生殖力和形态学特征的概念本身所包含的那些丰富的问题,它那远远超出了自恋或者那喀索斯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即从神话到道德、从指称到去指称、从哲学到植物学、从生到死的循环及其与一切修辞法保持审慎距离的歧义性和暧昧性;也不只是由于卢梭早年所创作的那部被我们视作其思想之动力源泉的喜剧《那喀索斯或自恋者》,以一种哲学和“反哲学”的方式直接发掘了潜藏在那个古希腊神话中的危险和逃脱的意义——那只缪塞笔下的被套夹困住的狐狸,而这个意义或许过早地预示了卢梭日后所面临的那一系列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领域;还因为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在卢梭那里的自恋与自爱的关键性区分以及其整个理论和实践效应,将让我们重新赋予那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以现代的目光和新的面孔:也许,我们不应该再去问“我是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保留地赞成和同情德里达的如下期待,尽管我们所要求的应该远多于一种友爱的政治学和任何可能重新落入危险的他者(或绝对他者)的伦理学:“不存在那种那喀索斯主义和那种非那喀索斯主义;存在着的是一些或多或少宽容的、慷慨的、敞开的、延展的那喀索斯主义,而被我们称作那种非那喀索斯主义的东西一般来说不过是一种更为殷勤而友好的那喀索斯主义的结构,而且它向着作为他者的他者的经验而敞开。我相信,如果没有一种那喀索斯主义的重新属归化的运动,与他者的关系就会被绝对地摧毁,就会被预先摧毁殆尽”(35)Jacques Derrida, Points de suspension, choisis et présentés par Elisabeth Weber, Paris: Galilée, 1992, p.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