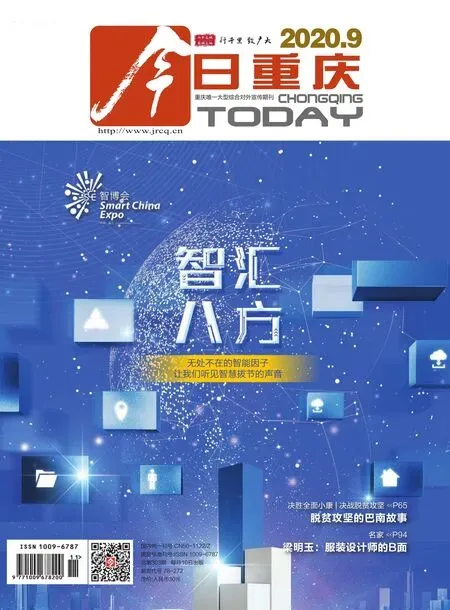一个村庄的一字之差
文 图| 杨棚飞 李相博
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群山莽莽,沟壑纵横,是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之地。
在诗人眼里,这是“巴山夜雨涨秋池”的绝美丽景,也是“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壮阔雄奇。而对于祖祖辈辈居住在大巴山的山民来说,这满眼满目的大山,无异于道道枷锁,锁住了身、锁紧了眼、锁死了心。“与世隔绝”带来了“愚昧”,也落下了世世代代拔不掉的“穷根”。
上世纪80 年代末,四川日报一位记者翻山越岭走进龙田乡仓房村,记录下触目惊心的贫困状况:在这个距离城口县城仅7 公里的山村,家家户户居住的竟是“‘棒棒’一围,茅草一盖”就是一间房的“排肋房子”,甚至是“茅草一堆、薄膜一盖”就是一间屋的“窝招蓬蓬”。记者同当地人交流,发现了一个更令人揪心的事实,当地人九成以上是文盲,不少人因没有文化和长期无人交流,竟已不大会说话,一张口就是啊呀哦的,就像哑巴和傻子……这名记者后来写了一篇名为《“愚人村”的悲哀》的报道,“愚人村”这个名字不胫而走,成为秦巴山区教育短缺的一个缩影。
而如今,经过30 多年不断发展教育,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曾经“声名远播”的“愚人村”,走出了38 名大学生。他们怀揣着梦想,插上了“翅膀”飞出了大山,仓房村不仅不再“愚昧”,还成了新时代的“育人村”。
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两座山,两个村,几代人,因一个老师,摘掉了“愚人”这顶帽子,改变了当地孩子们的面貌,照亮了他们走出大山的路

山高谷深的仓房村冲破大山的阻隔,走出愚昧,“愚人村”成了“育人村”

如今的仓房小学得益于爱心企业的捐赠,于2017 年建成。学校两边山上有两个村子,仓房村与四湾村
在大山播下知识的种子Sow the Seeds of Knowledge in the Mountains
在仓房,说起教育,不得不提陈申福。
立秋虽已过了半月,城口县却依然酷热难耐,连晴高温让人不敢出门。当走进龙田乡仓房村,见到陈申福时,老人正汗流浃背地在吃一碗泡面,桌子上放着一张被汗水濡湿的体检表。
随行的村干部告诉记者,听说有记者要了解村子教育发展的情况,一大早就进城办事的陈老师马不停蹄赶回了家,连饭也没来得及吃。
说起村子里的教育,扎根村里30 多年、教出300多名学生的陈申福感慨万千。
“在上世纪80 年代以前,整个村子基本都是文盲,能认识几个字就是了不起的‘文化人’。”陈申福说,村子里直到1965 年才有了第一所“学校”。而所谓的“学校”,也只不过是一间四处漏风的“排肋房子”,只有几个学生,唯一的一名教师是外村请来的,仅有初中文化,即使是这名老师,没过多久也受不了离开了。没有办法,村里只有四处求人,只要有点文化都“来者不拒”,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老师能待上两年,“我在村里读了5 年小学,老师换了五六个。”
这深深刺痛了陈申福,1984 年,作为村里的第一个高中生,25 岁的陈申福在打了几年散工后,回乡成为仓房一小唯一的一名老师, 这一待就是35 年。
陈申福刚“上任”便遇到了“拦路虎”:由于原有代课教师水平实在有限,学校12 名学生在百分制的考试中,平均成绩竟然只有2.5 分。
困难没有让陈申福丧失信心,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起早贪黑认真备课,根据学生情况针对性制定教学计划,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学生最低成绩都有68.5 分,最高90 多分,甚至超过了乡中心小学的水平。陈申福“一炮而红”,原来让孩子在家做活路的村民,也纷纷将孩子送来读书,班里的学生一下子达到了60 多人。
可拦路虎不止一个。“我接手学校的时候,教室还是20 多年前修的一间‘排肋房子’。”不仅四处漏风,而且“外面下大雨,屋头下小雨”,没过两年,便摇摇晃晃,学生安全都无法保障。在老支书杨正云的号召下,村里筹资筹劳,东家出两根梁,西家凑两片瓦,你负责挖土,我上山开石,全村花一年时间修起了两间夯土瓦房,一用便是30 年!
到了2017 年,政府出资修建了一所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学校,教室宽敞明亮,教学设施一应俱全,食堂、活动室、图书室等原来想都不敢想的设施设备全部配齐。陈老师笑着说:“相比于以前,现在这些娃娃读书真的是享福哦!”
陈申福前前后后教出了300 多名学生,其中包含20多名大学生,这成了他最自豪的事情。这位乡村教师30多年在仓房撒下的“教育种子”,如今结出了累累硕果。他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只有徒弟超过了师傅,我才是真的师傅。”
今年上半年,60 岁的陈申福正式退休,但他放不下课堂,义无反顾接受了县教育局的退休教师返聘,那张被汗水濡湿的体检表,便是他为返聘而做的准备。

原先在山上,由于办学条件有限,一间老木屋就是一所学校。如今学校的条件已大为改观
贫困户飞出“金凤凰”“Golden Phoenix” from Impoverished Family
由于大巴山的阻隔,城口自古不是“诗书传家”之地,民间俗语称“明无举人,清无进士”。曾经,能靠着一亩三分地让一家人吃饱,就是山民们最大的满足。至于读书,从来不是大家重视的问题,“读书不读书,都是坐‘山川’,最后还是种庄稼。”
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有了年轻的仓房人走出大山、走进城市,但都是外出卖力打工,挣钱才是第一位的。
陈申福在教书的头几年,经常发现有学生没来上课,一问,多半是家长把孩子带出打工去了。邓光友便是其中之一,由于连每学期9 毛8 分钱的学费都出不起,一家四兄弟没一人读书。陈申福想法设法为他们垫上学费,可仅仅读了两个月,四兄弟就集体辍学:两个跟父亲出门打工,另外两个跟母亲在家里种地。陈申福费尽口舌,没能劝回四兄弟。
但也有例外。王良兴这个朴实的农家汉子,就一门心思要送孩子读书,靠知识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最终,他家3 个孩子,先后考上重庆师范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成为村里读书“不得了”的家庭。
而一个大山里连吃饱都要靠“老天爷赏脸”的贫困家庭,要供出3 个大学生,这其中的辛酸,只有王良兴自己知道。
为了挣够读书钱,王良兴曾以烧炭为业。“上山砍树、打窑、烧炭,要从9 月份一直干到来年2 月。”王良兴说,一过10 月,山上就下雪,气温降到零下10 多度。雪积了半个腰身,人还要拖着一捆捆柴,连滚带爬往前赶,满身是汗。
3 天一窑炭,只能挣40 多块钱,这点收入还是入不敷出。其余日子里,王良兴还要钻小煤窑挖煤、上山采中药材……。采到了药、挖到了山货,还得翻过海拔1000 多米的大山,走到县城售卖,“到县城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公里,但不通公路的时候,一来一回翻山越岭就得一天。”为了第一时间将山货药材换成钱,王良兴经常半夜就打起火把出门,下午才能赶到县城,等卖完东西,又得半路打起火把才能回家。
最难的是在2007 年。为了筹措读书钱,王良兴到高燕镇打零工,意外身受重伤,不仅欠下了两万多的医药费,还必须休息三个月。孩子们看到父亲身受重伤的样子,哭着说自己不读书了,王良兴第一次对孩子发了火:“你晓得啥子?不读书,穷一辈子吗?哪个都不要再提不读书的事!我就是去讨口,这书也必须读!”
而今,大儿子王全友在西安工作,二女儿王全练考到重庆师范大学城口附属实验中学当教师,小儿子王全富也考上了县税务局的公务员,这三只“金凤凰”真正飞出了大山。
可喜的是,近年来,村民们对教育也空前重视起来,大家纷纷认识到只有读书才能断掉穷根。他们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要送孩子读书!现在的仓房,不仅不需要教师挨家挨户动员读书,有的家长还将孩子送到县城甚至是重庆城去读书。
“文化人”回乡反哺桑梓“The Educated” Return Hometown to Benefit Native People
故土难离,仓房村人对于家乡,更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许多靠读书走出穷山窝的孩子,学成之后又义无反顾回到家乡。他们说:“我们仓房背了这么多年‘愚人村’的帽子,我们就是要回来摘掉这顶不好听的‘帽子’。”
杨德陆便是其中一个,从小在村中长大,看着乡亲们年复一年过着穷日子,他心里十分难受。
2004 年,杨德陆高中毕业参军,成了村里的骄傲。
“复员后,当时有好多条路可以走。”尽管杨德陆完全可以在城里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却义无反顾地回到仓房,当上一名村干部。“从小看着村里人受穷,现在我读书、当兵,见过了一些世面,学到了一些知识,我要用好这些东西,带着大家一起奔一奔好日子。”
当村干部不仅收入比不上城里,而且还辛苦。但杨德陆始终抱着最初的愿望,一直没有放弃。
时间一晃,十年过去,仓房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先是道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3 公里长的蹇家湾隧道贯通,打破大山对仓房村几百年的围困,从仓房出行到县城,由原来的半天缩短到只要20 来分钟;四通八达的通组道路爬满了任河两岸的两片大山,村民出行正式告别了爬坡上坎、翻山越岭的时代,也不再“晴天一脚灰,雨天一身泥”。同时,通往陕西省紫阳县的省道也从仓房经过,通车后仓房村将一举成为连接城口县西部片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变化的还有住房。2015 年,新一轮精准扶贫伊始,乡、村两级20 多名干部通过走村串户摸情况,了解到群众最迫切的民生需求,除了教育,就是住房。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仓房已有20 多户贫困户住上了新房,其他有条件的村民纷纷开始自建房屋。而今的仓房村,再不见“排肋房子”“窝招蓬蓬”,随处可见的是一栋栋“小洋楼”。
扶贫产业在杨德陆和村乡干部们大力推动下,也取得了极大成效。原来的仓房村,村民守着“一亩三分地”苦磨苦做,依靠“洋芋、玉米、番薯”这“三大坨”,一家人往往连吃饱都成问题。杨德陆等人四处取经,引导大家培育观赏苗木,养起了中蜂、山地鸡、生猪,还组织村民建立起了集体经济组织,到年底,仓房村人就能实现历史上第一次入股分红。
“我一定要带着乡亲们拔掉这个‘穷根’,未来的仓房,一定会很美好。”对于未来,杨德陆信心满满,充满希望。
回乡的不只是杨德陆,现在的仓房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回乡的大学生,村里的产业带头人也是当年的学生。依靠知识和苦干,曾经的“愚人村”成了真正的“育人村”,从这里走出的“文化人”,正为仓房村“插上翅膀”,走向幸福和希望。

手把手地教孩子写字。陈申福改变了许许多多山村孩子的命运

由于学生分散路远,学校下午两点半就下课,好让学生们在天黑前能够到家。陈申福也会把孩子们一一送出校门,目送孩子们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