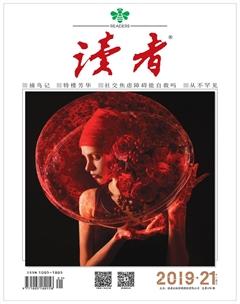社交焦虑障碍能自救吗
卡生
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数据,美国成人中有1500万人(约7%)有社交焦虑障碍。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龄是13岁,75%的患者首次出现症状的年龄在8岁至15岁,终生患病率高达13.3%。可见社交焦虑障碍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从豆瓣到QQ群,不少民间自发的互助小组散布于网络,那么,这种心理疾病是否可以通过自救得以改善或者自愈呢?
社交焦虑障碍症自救者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将原来“社交恐惧”的诊断词条修订为“社交焦虑障碍”。这个微小的改变,反映出精神医学界对这种精神障碍由浅到深的认识过程。书中写道:“对于社交场合有明显的、不合理的恐惧;暴露于社交场合中会感到强烈的焦虑,担心别人对自己做出负面评价;回避社交场合,如果无法回避,就变得非常紧张。症状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即可被诊断为社交焦虑障碍。”

我是通过豆瓣的“社交焦虑障碍互助小组”找到潘真的,类似的小组大概有15个,人数最多的小组大概有2.5万个成员。我给几乎所有互助小组的活动发起者发了“豆邮”,少数几个回复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潘真大学时读的是西方哲学。她说,学这么偏门的学科就是想避开社交。每天上课之外的时间,全都在图书馆和书打交道,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如果不出差错,她一生将从事学术方面的研究。大四毕业那年,家人为她安排了一次相亲。那天,潘真坐在餐厅角落,不敢抬头看对方一眼,对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到,回答越是语无伦次,她越感到恐惧,多少次她想重整旗鼓恢复理智,最后竟然联想出对方一定认为自己有精神疾病。她没有撑住,匆匆离开餐厅。回到宿舍,潘真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胆怯的行为,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耻。
之后,潘真开始在图书馆里查阅与社交焦虑障碍相关的书籍,恐惧、焦虑、完美主义倾向、恶意揣测、自我的过度评价和羞耻感,她当天的每一种行为都在社交焦虑障碍的症状栏里。
她回忆了一下过往和异性交往的过程。从小学到大学,她所有的同桌均为女生,她从来没有想过和男同学说话,即使有异性和她聊天,她也从来没有用正眼看过对方。
我在查阅社交焦虑障碍症的资料时,看到一种特殊的社交焦虑障碍症,叫异性社交焦虑障碍。潘真告诉我,为了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属于社交焦虑障碍的范畴,她使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做了自查。艾森克人格問卷是由英国心理学家H.J.艾森克编制的一种自陈量表。艾森克提出三个维度人格类型学说,对于测试社交焦虑障碍人格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测得的结果与多种心理学实验研究结果十分接近。潘真的测试倾向符合社交焦虑障碍症患者内向性与神经质的个性。
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数据,美国成人中有1500万人(约7%)有社交焦虑障碍。可见社交焦虑障碍症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心理疾病,并非某个人特有的隐疾。这种心理疾病是否可以通过自救获得改善或者自愈呢?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系且对社交焦虑障碍症研究多年的心理咨询师覃宇辉向我解释:“如果由于后天因素,如社交受挫、防御以及缺乏自信引起的轻、中度社交焦虑障碍,可以尝试从认知、行为层面进行干预。”
在排除病理性社交焦虑障碍后,潘真开始了漫长且艰难的“自救行动”。潘真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找到了恐惧异性的端倪。她回忆说:“记得我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看电视,只要有男女亲吻的镜头,我妈就会让我捂住眼睛;为了不让我早恋,父母告诉我的班主任,不允许我的同桌是异性;初中时,我收到过一封情书,我妈跟疯了一样暴跳如雷,不仅烧了情书,还把事情闹到学校……”这种对异性的阻隔与切断,让潘真仿佛生活在一个缺乏异性的真空空间。
大学期间,她研究了各类克服社交焦虑障碍的方法,例如森田疗法、系统脱敏疗法以及刺激的暴露疗法之后,她对森田疗法的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森田疗法的核心思想讲究“顺其自然,为所当为”,鼓励患者怀着顺其自然的心态,接受消极的体验和不良的症状。更重要的是,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森田正马曾经的患病诱因与她的极为相似。同是出生在严苛的家庭,家庭压力像是一枚安静的“核弹”,最终在日常生活中爆炸了。
这个疗法听上去很抽象,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有一些具体办法的。潘真开始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根据她内在人格的敏感、自省、安静,她尝试了冥想和瑜伽,并试图与异性说话。哪怕仅仅从“你好”“再见”开始。她告诉我,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她说完就跑,一口气跑回宿舍,才发现自己的双手浸满了汗水。
互助之难
做一个互助群的想法,潘真已经酝酿了两年。她说:“我当年非常清楚那种困局,犹如进入一片泥沼地,想要挣脱,却越陷越深。互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到那些并非病理性的轻、中度患者。”
最早,潘真在豆瓣组建的互助群里发布了一条消息,宣布社交焦虑障碍线下互助小组成立,愿意参加的人可以识别她的二维码进群。据潘真回忆,一天的时间就有30多人自主入群,他们基本上都是默默入群。当潘真热情地表示欢迎时,对方的表现也显得不太积极。“其实有很多所谓的社交焦虑障碍群,大家都只是线上讨论得火热,一旦涉及线下的社交,群里就会显得十分沉闷。”
第一次互助的时间和地址公布后,有5个人报名参加,但真正抵达现场的只有一人。唯一的互助者便是她现在的花店合伙人高丽林。初见高丽林时,潘真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1.75米的高个儿姑娘,蜷缩在一个角落不敢正眼看人,拳头紧紧地握着,似乎下一秒无法忍受时就要从现场逃离。后来高丽林告诉我,那天她做了3个小时的心理建设才出门,最后是一个声音反复在脑海中出现:如果要逃,又何必想要救自己呢?
潘真想起去年看过的一本书《芬兰人的噩梦》,她和高丽林分享了这个故事。“芬兰人的白日梦:一辆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一部只有自己的电梯,一种不需要打扰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打扰的生活……”这让处于紧张状态下的高丽林感到放松。她慢慢向潘真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是某家旅游公司的行政人员,她最大的恐惧是在公共场合汇报工作进度。即使那些数据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但只要站在台上,她脑海里便是一片空白。在一次上级领导视察工作的大会上,高丽林拿着手稿的手在发抖,声音已经变调,可想而知那一次汇报是多么惨不忍睹,因为说错了很多重要的数据,她最终被点名批评,差一点丢了工作。
覃宇辉告诉我:“焦虑障碍分为特定对象恐惧症、社交焦虑障碍、场所恐惧症、广泛性焦虑障碍等。像高丽林的恐惧便是对某个特定情景或场合的恐惧。只要他们不面对所恐惧的场景,别人是看不出他们患有焦虑障碍的。”
第二次线下互助,潘真只约了高丽林。她觉得高丽林现在的状态适合一对一突破,因为她是在公共场合才有恐惧。这一次高丽林放松了许多,她告诉潘真自己患上这种心理疾病的原因。“我上小学的时候,被班主任当众羞辱过。因为我回答不上来一道题目,她用非常粗鄙的语言侮辱了我,我还落得一个难听的绰号,只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就能听到同学们在背后小声喊我的绰号。”在社交焦虑障碍的形成过程中,曾经的“社交受挫”是重要的成因之一。之后每周,潘真都会约高丽林吃饭,让她大声朗读自己写的日记,或是找一个会议室让她演练平常汇报的文稿。反复几次练习后,高丽林的表达顺畅了许多,这超出了潘真的预期。
社交焦虑障碍症患者可以互助吗
社交焦虑障碍症患者线下互助真的可以做吗?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潘真的脑海中。加拿大圣·约瑟夫卫生保健研究所焦虑症治疗与研究中心主任马丁·M.安东尼所写的《羞涩与社交焦虑》一书中,曾提到过社交焦虑障碍治疗方式中团体疗法的优势。“团体疗法使患者有机会认识其他有相同问题的人,这样患者既可以从其他人的失败和成功中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患有此病的人。团体治疗给患者提供机会,让他们接触参与暴露和角色扮演的其他患者,对治疗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
就此,我向覃宇辉咨询了社交焦虑障碍线下互助的可行性。他说:“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社交焦虑障碍症,互助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很关键,如果方式不当,极易激活焦虑感,导致病情加重。”
覃宇辉跟我详细讲述了在治疗社交焦虑障碍时使用的暴露疗法、系统脱敏法,这也是目前西方国家主流的治疗手段,能有效地控制社交焦虑障碍者的病情。对来访者深度了解之后,医生会专门制定一套符合其产生社交焦虑障碍的刺激等级。一般来说,刺激分为15个等级。通过鼓励患者进入让他感到恐惧的情景,接受1级刺激适应后再进行更深度的2级刺激,以此类推。在持续的刺激下,患者会发现虽然感到异常恐惧和害怕,但他们所恐惧的灾难并未出现,最终使患者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
潘真的自救过程让她对社交焦虑障碍的起因和治疗方式有了一定的认知。在社交互助群里,她每天都会发送关于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报告,让每个人正视自己的问题。在确定线下互助人选之前,她会公布每一次线下活动的主题。潘真的主题活动分成动静两类:一類是阅读会和观影会;另一类是瑜伽或冥想。最后留给大家一些时间,表达当天的感受。
覃宇辉说,目前还没有全国范围内的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调查。但是综合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焦虑障碍的患病率很高,年患病率为2.6%~7.9%。由于国人对该病症普遍认识不足,大量病患被轻描淡写地认为是“胆小、内向”而未受到重视,导致对病患数量的估计趋于保守。
潘真告诉我,在她主办的20多期活动里,共有22名线上成员参加,其中有8人多次参加。她说:“我不知道我究竟能帮助多少人,这就像是黑暗中的灯塔,给予一定的指引总归是好的。”
(本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凡 客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4期,本刊节选,辛 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