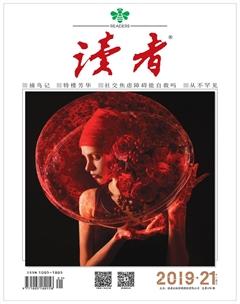一杯看剑气
朱天文
荷西在门前种树,种好了,三毛忽然笑起来,道:“荷西,树是有脸的呢。”种好的树,又挖出来重新种了。
今天早晨,我把桌上的两颗椰子放在水龙头下冲洗,想起三毛的话,将两颗椰子整了整方向。看看,果然是一脸喜滋滋地迎着人笑哩。
知道三毛,是从“联副”刊登的《中国饭店》开始;认识三毛,却是在《联合报》小说奖颁奖典礼上。这期间,1977年,三毛曾写过一封长信给天心。三毛向来不主动写信给别人,那次因为读了《击壤歌》,晚上睡不着觉,踱来踱去踱了一夜,隔天就寄了十美金来,附上只有一句话的短笺。她原以为天心不过一笑置之,岂知天心亦是喜欢她的。自那时起,只晓得天涯海角有个三毛,隔着千重山万重山,偶尔才从报章杂志上捎来天边的一朵白云。一种牵挂,而好像连牵挂也说不上的,便只是两地闲情,都共在一个日光星辰下吧。
然后就是荷西去世。三毛回来了。
我们也不去信,也不打电话,冷漠得像是连起码的人情都没有了。只因为一番痛惜珍重之意,竟连惊动也不敢,便是一句半句安慰的话,都是冒犯了。
在《联合报》的颁奖典礼上,出乎意料地遇见三毛,是天心先发现的。我们赶紧跑到她面前,天心才说一声“我是天心”,眼泪就哗哗地流了满面。颁奖过程中,三毛隔着一条通道坐在我们斜前方,晓得我们在看她,偶尔回过脸来望一下,我的心口就像给抽了一鞭。她全身穿黑,裙子底下是马靴,头发中分披肩,露出一张苍白的小脸,脂粉不施,只画了眼圈,整个人像是只剩下一息意志。方才匆匆地拉了拉手,纤纤一握,她是一个晨昏就瘦了多少?

每次唱《橄榄树》,三毛作的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杳远苍茫的调子,令人泫然泪下,像天起了凉风,而日影飞去。
三毛头一回来我们家,就像这样,从那辽远的画梦里走了出来。那晚天气奇冷,三毛素来披在肩上的头发扎成了两束,像个印第安女孩。一进门,我们就称赞她好看,她笑说是头发脏了,梳这样的发式可以遮丑,又低下头来,拨给我们看,中分线的发根都花白了。我们看得心惊,她却是半分无可奈何,半分像是对她自己开了一个调皮的玩笑。
她坐在沙发上,牛仔工装裤,衬着灯笼大袖蓝布衫、白短袜、包头凉鞋,一副小男孩打扮。初看的时候,人很憔悴,讲着话就渐渐眼睛也亮了,肤色也明净了,一派神采飞扬,竟是看不出年龄的。讲到荷西的死,她的眼泪只是静静地流下,痛,是更真切更深沉的。眼泪一滴一滴都是穿石的,像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又像娥皇女英的泪洒斑竹。至今数千年,那潇湘水深,苍梧山高,存在于世世代代的怀思里,似绣进历史的织锦,从未有过死亡。
三毛道:“我还是想死。找到荷西的时候,我想好了,从岸边一直走,一直走,走进海里,跟他一起去了。可是那时爸爸妈妈正好赶来——他们在岛上,赶来荷西出事的岛要乘飞机,可飞机票一直买不到,我先来的,他们后来的。爸爸妈妈远远地跑过来,我茫茫然地回过头,妈妈还好,爸爸整个人都崩溃了——我总算没有去。后来回到台北,有姐姐弟弟,我想可以去了……爸爸恨我呀!如果我去了,爸爸说,要一生一世和那个杀死我女儿的人为仇,来世变鬼也要报仇到底!好好笑,我说,爹爹,杀死你女儿的是你亲生的女儿自己,不是别人。爹爹说,那么那个人便不是我女儿,我跟她不共戴天,来生一辈子报仇!想死啊,活着没有意思。我说,爹爹,你们太残酷、太自私了……结果你们看,我就成这个样子了。像袭人,爱宝玉爱得那样,几次要死,后来还不是嫁了蒋玉菡,简直是讽刺……”
此时此刻,我已觉得荷西的死不再重要。“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眼前是三毛本人啊。她只管在那里说生说死,好比她恼了造化小儿,在天地面前不甘心、不服气,撒泼耍赖,不惜豁出去了。
三毛实在强大。而且她天才的性情,使她即使在这样悲痛的境遇里,也仍然没有一点晦暗。她讲到荷西可爱又可怜的地方,泪痕犹在,却哈哈大笑了起来。三毛说:“那次读到天文写的,和天心等车吃苦味巧克力的事,就和荷西去买了一大板巧克力要寄给你们,可是那时候天气好热,怕化了,便收在冰箱里存着。谁知道,要寄给你们的巧克力,竟被荷西偷吃掉一大块啦!”
明儿写了一幅字,我拿给三毛看。他写的是:“道旁杏花一树明,照山照水夫妻行。长亭买酒郎斟妾,妾惜金钱郎惜情。”三毛嚷起来:“这幅字该是给我的呀。妾惜金钱郎惜情,是我嘛,总是我在算钱。啊,我们岛上种的全是杏花呢……那回我和荷西在山上看花,满山的杏花,雪白雪白的!我们坐在树下,惆怅得不知怎么才好,好像只有死掉……”
荷西属兔,三毛是荷西年轻的妻,也是姐姐。这样一对姐弟、夫妻,海角天涯地创建了自己的家。也許因为沙漠漫漫的天、漫漫的沙和漫漫的人情世景,也许因为三毛的纯真和她的喜欢,把爱情叫作恩情,总让我想起那是天地之初的一男一女,当时连世界都还未形成。他们离开伊甸园,来到一处不知名的山崖水边,那日色水纹,田舍待耕,桑园待植,就这般兴致勃勃地做起了衣裳器皿、宫室舟车。
三毛自己不知,她道:“朱老师要我做天下人——我不要做天下人,我是最自私的了。”
她岂知我也是最自私的人呢。但是有一个林黛玉,她才是世间第一自私的人。
林黛玉种种的小心眼儿,说话故意冤枉贾宝玉,动不动就伤心流泪。最大的私意,莫过于她对宝玉说:“我为的是我的心。”林黛玉的一生其实也不是为了情,她是为了求证一件最真实的东西,是求证她自己吗?她把自己置于不可选择的绝境,如渡天河,渡不渡得过去,就此一搏了。她对宝玉的绝不迁就、绝不委屈,亦是对自己的绝不妥协。
我喜欢古诗所言“日月光华,弘于一人”。比方做三三的大事,到底什么才叫三三大事,怎样做才算是做?写文章是做,唱歌、演讲、座谈也是做,捆书、送书、装订、寄书、卖书、贴海报、算账,都是做,但所有的这些也都不是做。大事,其实更像宝玉黛玉相见,顿时立地皆真。因为有他,只觉世上的万事万物历历在目,一桩一桩皆宛转归于自己,是这样的亲切贴心可感激。为了他,亦即为了天下人;见到他,亦即见到了天下人。所以英雄美人的私意,是他自己的,同时也是天下的,且那实在是亲到了极点,真到了极点。
却不知三毛此生此世,也有为求证一件东西的吗?我想是有的。
她讲起她的生平,几次三番恋爱,每一次都爱得那样深痛,毫无保留,像是把自己掷于炉中冶炼,烧啊烧啊。天心惊叹道:“三毛呀,怎么样的一个人,能那样子燃烧自己,像烧不尽似的!”
的确,三毛的一生,如行走于悬崖峭壁之上。好几次,她都险险地要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了,换成别人,本质差了一点点的,恐怕就会堕入黯淡悲惨的境遇。比起我们,她是经过了人世的大寒大暑来的,然而她的明丽纯真、阳光和热情,一如初出茅庐,竟像是她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未曾发生过。
三毛比一比她的手臂,道:“这里,现在穿长袖看不见,有一条大疤,很多年前的事了……”说着又是眼睛一亮,满是顽皮的神气,“可是不伤心,身体的伤,一点儿伤不到心。”
六年之后,她再去西班牙,荷西要娶她为妻,她跟荷西本来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也是为报荷西的知遇之恩。那个破碎的身体、冰冷的心,一念之间仿佛豁然开朗,又是一个全然簇新的人,全然清纯的心,完完整整地给了荷西。她与荷西婚后才开始恋爱,一年比一年好,好到最后一年,好到不能再好,就像是那满山满谷的杏花开遍,只有痛快地落它一个白雪纷飞,还给了天地不仁去吧。
因此,我们对三毛不说安慰的话,因为本来这世界是不能给她安慰的。因此,荷西的死,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一句话:“父啊,成了。”“成了”,成了什么呢?那要问三毛,她求证的是什么呢?
我们也去教堂,人不多,讲道的时候小孩子跑来跑去,倒像是星期日大家来串门子。
三毛那天穿着马靴,白布裙,黑毛衣,披着长发,我们并排坐在长椅上,有时低声讲讲身上的衣饰。三毛的装束看起来很时髦,纯棉或纯布的料子,手染花色,有一种自然本色的风味。同样的装扮,于别人穿着便是刻意修饰,在她却是最自然不过,并且三毛的裙子是她自己做的。
她有一只皮镂背袋,每回出门都用它,铜棕色的镂花,好似埃及的出土古物,朴拙大方,非常好看。这样的一只背袋是路边一个嬉皮士给她做的,她用了五年,那色泽、式样和气味就像三毛本人。而我们身边有个天心,穿的、用的、喜爱的都跟三毛很像。三毛有件地摊上买来的黑底奶油黄小花布袄,天心爱得要命,也去买了一件。后来天心在颁奖典礼上穿时,三毛大吃一惊,咬定天心把它偷了去,虽然她知道自己那件衣服正挂在衣柜里。
离开教堂,十几个人去吃馅饼、玉米粥、羊杂汤,大家吃得高兴,三毛感叹道:“荷西在就好了。荷西也喜欢吃馅饼,他还爱吃汤圆。有一回不知在哪里吃了,回来要我做给他吃,又不晓得叫什么,光会说,小皮球呀,白的小皮球呀,里面包着甜甜的东西的呀。我又没做过汤圆,试着做,这样,搓个球球,挖一个洞,塞些豆沙进去,然后黏上盖子,谁知煮一煮,盖子都飘走了,散成一锅稀里糊涂的什么东西……”说着哈哈地笑了起来。
过两天是荷西百日,我们邀三毛来家里过,三毛一高兴,嚷嚷道:“发红包呀,新年发红包,小孩子每人一个红包。”见她这样的意气焕发,一天好似一天,真是叫人欣喜。此刻,街上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风吹过灰茫茫的天空。三毛的靴子敲在红砖道上,她的衣摆随风扑扑地飞着。行走在午后满是异国情调的敦化南路,三毛变得很少讲话了。我们亦无言,走啊走啊,也没有目的地,心中真是不知要从何想起,单单感觉着无边无际的远风迎面刮来,灰色的、钝滞的、大大的,无边无际的风。三毛说:“荷西的死是死了两个人,而我的活,亦是活了两个人。”
三毛的恋爱观即人生观。她信上就写过:“婚姻,是太好太好了,但愿有一天你们也能结婚、成家,做那个男人的女人。”王老师替三毛看八字,说她是癸水多情,好比流水一泻千里,所以她的一生总是在付出、付出,不断地付出。三毛笑道:“好啊,能够付出,真是最幸福的事情了。”果然是这样的,也只有年轻、青春的生命,才能够这样一直付出吧。
如果我们对三毛有所苛求,便是在于这个付给的对象了吧。因為青春的燃烧仍然是要能够结晶的,如果燃烧得只剩下一堆灰烬,那就是天地间最大的憾恨,天也不能原谅的。
从初见三毛至今,也有三四个月了。这三四个月,人世的高山大海,像是波澜不惊,只见上次三毛在后院走走的时候,爬山虎的枯藤,如今都绿叶覆荫了。难道岁月只是在草儿花儿身上见到踪迹的吗?不由得人要恨起三毛,问一问她:“你可也是有心的呢?”
三毛终究不能留居台湾。她就像天边的一颗流萤,在夏夜里遥遥隐隐地闪烁着。她本来是陈伯伯、陈妈妈家的混世魔王,他们前辈子欠了她的,她今生来讨,讨完了,就重返太虚灵河畔归位。但我更喜欢虬髯客最后对李靖所说的:“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东南相贺。”言讫,与其妻从一奴,乘马而去,数步,遂不复见。
此后十年,或者不必十年,让我们在大漠、草原再见吧。那时,大家仍然年轻,依旧爱笑,就痛痛快快玩他一个日月昆仑,直到化为尘,化为飞烟。
三毛,一杯看剑气,二杯生分别,三杯上马去!
(素 平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一书,本刊节选,沈 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