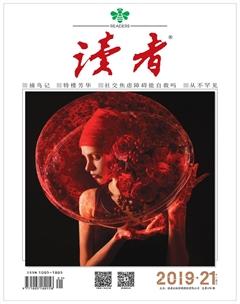特楼芳华
孙文晔

特楼
1954年,在今天的中关村东区建起了一批住宅楼,其中三栋三层小楼,总共48户,因其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最好,安排高级知识分子居住,而被称为“特楼”。
这三座灰砖、黑瓦、朱红色木窗格的小楼,就是现在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
李佩屈就当“村官”
1955年11月,钱学森一家落户到14号楼201室。
走进钱家,最显眼的是一架三角钢琴。特楼中不少家庭有钢琴,可是有三角钢琴的却寥寥无几。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夫人蒋英的结婚礼物。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曾扣押过此琴,经过一番波折,他才要了回来。路过14号楼,如果运气好,就能听到蒋英那优美的琴声和动人的歌声。
钱学森安家时,中关村到处是林立的脚手架和刚刚开挖的地基,而他也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打地基”——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规划”,确定了我国重点发展的学科和项目,钱学森作为综合组组长,用他的远见卓识,把当时还非常神秘的计算机、导弹、原子能等列入其中。“两弹一星”甚至“神舟飞船”的发展,都由此打下基础。
“向科学进军”的蓝图铺展开来,钱学森急不可待地致信康奈尔大学的郭永怀,邀请他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信中还提到了两家在特楼的住房:“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好了,去办公室只需步行5分钟,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有了钱学森的前车之鉴,郭永怀为了顺利回国,烧掉了自己的论文手稿和笔记。同船的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则受到美国的严格审查,以至船晚开了两个小时。同船的两家人,后来在特楼又成了邻居。
出任力学所副所长后,郭永怀一家入住13号楼。他的夫人李佩,本来被安排到中科院外事局工作,但为了就近照顾丈夫和5岁的女儿,就在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办公室当起了副主任。
年轻时的李佩非常漂亮,作为西南联大、康奈尔大学的高才生,屈就当个“村官”,实在是大材小用。不过正是她的热心肠和高超的沟通才能,才让在中关村的日子有滋有味起来。
特楼刚建成时,周围仍是荒郊,配套设施稀少。在李佩的组织下,吕叔湘的夫人、赵忠尧的夫人、赵九章的夫人、邓叔群的夫人、梁树权的夫人组成了“家属委员会”,许多有关生活的事,如卫生、学习、安全、子女教育……都由她们操持。这个全部由院士夫人组成的家属委员会,开社区自治的风气之先。
对妈妈们来说,孩子的教育是头等大事。在各方努力下,中关村建起了幼儿园,还对名副其实的乡村小学——保福寺小学,加以改造。现在名气很大的中关村第一、二、三小学都脱胎于此。科学家给小学生上课的传统,也是那时李佩开创的。
为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李佩还请一位退休后住在女婿家的沈大夫建起医务室。这个女婿就是“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院士。直到1960年建立了中关村医院,中关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才有了很大改善。
科学家们对环境卫生和公益活动都很重视。那时,每周都有这样一个傍晚,平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科学家们,全家一道出现在楼前,不是聚会,而是出来打扫卫生、美化环境。这些学富五车的大科学家或包着头,或戴着口罩,或戴着袖套,打扮得“灰头土脸”的,来到楼前,或拿着扫帚,或挥着铁锹,或浇水,或撮土,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特楼周围的环境大为改观。13号楼前一片重瓣桃花,每年春天争相吐艳;14号楼前是一个花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关村一街的路口还建了一座“福利楼”,里面有餐厅、理发室、乒乓球室等便民设施。卖原版书的外文书亭和用篆字做招牌的餐厅,都让这里显得与众不同。
现在成了“网红”店的中关村茶点部,是由李佩向中科院提议,北京市政府特批的,专营西式糕点。为确保口味正宗,还把天津起士林西餐厅的井德旺请来担任主厨。那个年代物资紧缺,连用点黄油都得盖几道章,这里却特别舍得下料。不但科学家爱这一口儿,上岁数的老北京人也会想起这么句话:老莫的蛋糕,新侨的面包,中关村的西点。
名字最有趣的要数“四不要”礼堂。之所以叫“四不要”,是“不要砖头,不要钢筋,不要木头,不要水泥”,全部用预制块构件盖成,连暖气都是陶瓷的。别看礼堂音响效果不佳,来演出的都是大腕儿,梅兰芳去世前的绝唱就在这里。
这些待遇看似优厚,但相较于科学家们放弃的,实在不值一提。
汪德昭在巴黎的居所,有大得可以开音乐会的客厅,和飘着玫瑰香的花园;李佩在康奈尔大学旁边的家,风景绝佳,是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独幢别墅;张文裕和王承书有两辆私家车,因为归心似箭,来不及变卖,干脆都送了人;杨承宗回国之前,刚接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年薪55.5万法郎的聘书。

1952 年8 月,郭永懷、李佩和郭芹,在美国的家门前合影
特楼的黄金十年
在特楼,即使是国宝级的泰斗,也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
在儿子钱思进眼里,父亲钱三强是科学家,更是一位好爷爷。在楼后的小副食店门口,他每天按时排队领取牛奶,一直到最后一次住院前;当女儿女婿不在家时,他常坐在床边给孙辈们讲故事,孩子睡熟之后,再继续他的工作。
他们虽然不讲行政等级,但同事间的称呼还是大有学问的。被称作“老师”的人,一定德高望重,比如赵忠尧,一来他以前是清华教授,二来很多科学家都是他的学生。赵忠尧的学生钱三强和王淦昌则被称为“公”,即钱公、王公。也有被称作“先生”的,如何泽慧等。
钱三强的书房里挂着“从牛到爱”几个大字,外人常常不明所以。原来,这4个字是即将进入清华大学时,他的父亲钱玄同送他的。钱玄同说:“学物理嘛,就要向牛顿和爱因斯坦学习,做出成就来;其二嘛,学习就要像牛那样苦干,渐入佳境后,就会爱上这门学科。”
《中国植物志》的主编林镕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午饭都是包子——他去食堂排队总有人让位,他故意晚去,学生又把饭端到办公室。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他夏天吃凉包子,冬天把包子放在暖气上,以至大家都知道“林伯母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蒸包子”。
1955年,选聘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时,柳大纲先生曾经两次提出,把自己从候选名单中去掉,原因是“不够资格”。何泽慧在回答“您被选为院士后有什么感想”的问题时,以她特有的率真和质朴说:“我才不稀罕什么院士呢!”
三座特楼里,有好几对夫妻科学家,有的还是上下级关系。陈世骧和谢蕴贞都在昆虫所工作,陈世骧任所长,留法归来的夫人谢蕴贞一直是六级副研究员,没有得到提升。陈世骧向孩子解释:“我也觉得亏待了你妈,但是当了所长,自己的事就不能多想,这样才能使人信服。”童第周的夫人叶毓芬直至去世仍是副教授,也是因为有童第周这个“顶头上司”。
这么多“最強大脑”聚在一处,最大的好处是随时随地可以“头脑风暴”。
郭永怀和汪德昭住楼上楼下,他们的夫人也是旧识,一次聊天时说起铀235的分离问题,研究声学的汪德昭在既有方法之外,另辟蹊径,提出用超声波进行分离。力学和声学两个学科就在谈笑中有了交集。
走的走,搬的搬
特楼里这种温馨而忙碌的气氛,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打破了。
在14号楼时,钱学森主持研制的“东风一号”导弹冲天而起。为了方便他的工作,也为了加强安保,聂荣臻亲自安排了航天部大院中的一栋小楼,让钱学森搬家。
自从1960年10月搬出特楼,钱学森就再没挪过窝。2009年,钱学森去世后,前去吊唁的媒体记者惊讶地发现,“副国级”的科学家竟然住在不到100平方米的住房里,小小的门厅,最多只能站4个人。不是国家不给钱学森分房,而是他执意“不脱离群众”。
聂荣臻的远见,间接保护了钱学森。“文革”中,童第周等被赶出特楼,仍住在特楼的,住房也大多被占用。本来五居室的格局,住进了另外三四家,一个厨房摆着5个灶,一到早上就抢厕所,自然极不方便。李佩为了让郭永怀的副手林鸿荪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就主动请林鸿荪和他的夫人杨友住到了自己家。
无论待遇如何,只要还能工作,特楼里的科学家就能找到乐趣。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全国激动万分的时刻,核武功臣杨承宗却在家里睡大觉。原来二机部的领导怕这些专家长期超负荷工作,承受不了突来的欢乐,就在前一天晚上拉着他们看电影。电影放了一部又一部,直到半夜,才把核武功臣们送回家,算是缓冲了一下。
声学研究所所长汪德昭一度被安排扫厕所。在这种境况下,他仍有心开玩笑,还写了“请垂直入射”的纸条贴在马桶上。得知他们研制的某国防水声设施发生故障后,他和前去维修的人约定暗号,如果修好了,就发电“母病已愈”,否则就是“母病危”。
1968年12月5日,特楼里的气氛雪上加霜。郭永怀从青海基地乘机回京,飞机在北京机场不幸失事。当领导把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也未发一言,就站在阳台上,久久望向远方。此后,人们也没听她提起过“老郭的死”,只是有时见她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十年浩劫之后,特楼也铅华落尽,本就十分朴素的灰砖墙斑驳破损,原来鲜艳的红色窗框,油漆剥落。门前那一片桃花源似的美丽景致,因为盖研究生楼和宿舍楼,已不复存在。始终保留的,只剩花坛里一棵孤独的雪松,据说是郭沫若和钱三强一起栽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科院建起了新的高档住宅,让老院士们搬出已成“大杂院”的特楼。这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好不容易可以做学问了,谁愿意耽误时间搬家装修啊。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楼里走的走,搬的搬,50年代的老住户越来越少,居住条件也越来越落后于时代。1994年冬,杨家雷回国探亲,发现楼里的暖气不热。却见老爹杨承宗掀起穿在外面的大棉袄,指着腰间的宽布带说:“这是我的发明,可以保持身体暖和。”这一年,杨承宗已83岁。
1999年国庆节前夕,“两弹一星”功勋奖颁奖,在特楼里住过的6位科学家获奖,但为研制核武做出重大贡献的杨承宗,却不是获奖者。有人为杨老感到不公,可他只是带着爽朗的笑声答道:“事情做出来就好。”
进入21世纪,特楼里的住户已经换了几批,但有几个“钉子户”,就是不肯走。
中科院曾经几番动员,钱三强与何泽慧都执意不搬,他们甚至想出一个不成立的拒迁理由,说新楼离图书馆远,不方便。实际上,新楼离图书馆更近些。
1992年5月底,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元帅。为了准备发言稿,钱三强前一天晚上在书房里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到深夜,第二天,他又坚持听完所有人的讲话才回家休息。当天晚上,钱三强心脏病发作,一个月后去世。
自钱三强去世后,家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不论是卧室还是书房,何泽慧都尽可能地保持着钱三强生前的样子。无论谁劝她搬家,都会被她顶回去:“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
直到今天,钱家的书房仍保持原样——写字台上,台历的日期还定格在30年前;书桌边,是何泽慧最喜欢的旧藤椅。只是,墙上挂着的照片,多了一张。
坚决不搬的还有中科院的“寿星院士”贝时璋,他不仅不换房,连保姆也是几十年都没换过的“李妈”。走进他家,就像到了“旧物陈列馆”,还能找到1954年迁到北京时公家配发的家具。2009年10月29日,106岁的贝先生在睡梦里安详辞世。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家里和6位研究人员谈创新。
随着100岁的杨承宗、106岁的贝时璋、97岁的何泽慧相继离去,连二代子弟也过了花甲之年或出国或搬家,住在特樓里的老一辈只剩下李佩一位。
这里是科学院的根
商业大潮涌起,中关村寸土寸金,特楼也愈发“相形见绌”,拆除的传闻不绝于耳。
可李佩怎么舍得离开这里呢?她的花在这儿,阳台在这儿,钢琴在这儿,和郭永怀相恋时画的画也在这儿。离休后,李佩为了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重新投身社区建设。在中关村,仅她义务组织、主持的系列知识讲座就有600余场。提起拆迁,她就说:“你们看看窗外楼前那些树吧,是我搬过来之前种的,现在已经是50年树龄的大树了。”
2016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李楠看到《湍流卷不走的先生》一文,被李佩的故事打动,对颇有些年岁的特楼和那些掌故也上了心。
李楠实地探访科源社区,令她唏嘘不已的是,由于多年疏于管理,当年建筑质量特别好的特楼,早已没有了昔日的荣光,外墙坑坑洼洼,内墙斑驳污秽,楼前的花园和小路也是一片残败。虽然李佩还住在楼里,但有些五居室已经被大拆大改,彻底沦为“群租房”,安全隐患不少。
2017年1月,李佩先生走了,享年99岁,但她的影响力,似乎仍在冥冥之中保护着特楼。
旅美作家王丹红写出一系列纪念文章,让更多人知道了李佩未了的心愿;在2017年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李楠发表论文,推荐将科源社区的23栋建筑整体列入历史建筑;作为中科院子弟,边东子是特楼的老住户,他仍在多方寻访资料,完善着人们对特楼的回忆。
2019年6月底,特楼等429处建筑被公示为北京首批历史建筑。
“怎么恢复特楼的活力还得多方协商。”李楠说,历史建筑保护和文物保护不一样,讲究的是“让历史在当代生活环境中存活下来”,因此可以一边保护一边利用。这为特楼的未来拓宽了思路。
“老科学家们的作风、品格、精神应当被传承下去,但精神要有载体,要由物质来反映和表现。那么多年发生了那么多事,若能放到一起,足够建一个博物馆的。”边东子又翻出李佩当年亲笔写下的保留特楼的呼吁信:“中关村这几幢楼是众多为科教兴邦建立功勋的科学家的故居,历史不应忘记他们,不应忘记他们当年孜孜不倦、埋头书案的生活环境,使后代年轻人在高楼大厦群中看到师祖辈当年艰苦朴素的创业心境,未始没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在这封信上联合署名的,有特楼的住户,也有其他的名人、学者,包括中科院的一批院士。
(朱权利摘自《北京日报》2019年8月27日,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