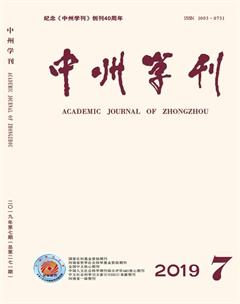立人·立德·立国: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张宝明 李帅
摘要:以“新人”为突破口,通过“新道德”的换血,从而达到“新国家”的目的,乃是五四先驱的一个基本逻辑构成。将“心身薄弱”的“纨绔子弟”改造成“心身两全”的“朴茂青年”也就成了五四先驱最初追求的“立人”目标。所谓“心身两全”,就是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当《新青年》“主撰”意识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后,“德育”便作为不二的启蒙法门被给予了超负荷的重托。至此,五四先驱的“立人”目标已由原先的“心身两全”变成了“以德为主”。要“立国”,须先“立人”,而“立人”的路径则是“立德”。他们的这种以“新道德”的换血来造就新国民、新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古代的“修身治国之道”可谓如出一辙,其中无不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陈独秀;《新青年》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7-0120-06
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是绕不开的主题。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看,这一联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历史的实际选择。就《新青年》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一精神事件而言,它如同一个“宝葫芦”,究竟其中“卖的什么药”,则是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应该予以深究的命题之一。如果说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之说,那么时至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则有了一个全新的“三立”概念:“立人”“立德”“立国”。在那个不破不立的时代,究竟何“立”之有?立什么、如何立、为谁立,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被学术界以切块或打包的形式涉及过。尤其是关于“立人”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是众口一词,诸如“人的发现”“个人本位主义”“人道主义”等等“人”字当头的概念、名词抑或思潮不一而足。①再如“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之标语口号下的“立国”目标更是被广泛的认可,并为学界同仁所津津乐道。②如果说“立人”与“立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定论,那么本文的立意就不再是在这两点上打转转,而是要通过对“如何立”的解读与诠释,来厘清多年来我们习以为常甚至一笔带过的“立德”路径之逶迤曲折。至少在笔者看来,以“新人”(“新青年”)为突破口,通过“新道德”(“新伦理”)的换血,从而达到“新国家”(“新社会”)的目的,乃是新文化人或说“新青年知识群体”的一个基本逻辑构成。在此,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被牵出:“立德”之“德”在新旧道德(伦理)大换血的转换过程中呈现出的多重纠结与缠绕如何厘清?进一步说,西方舶来的那些“新知”何以在这“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根底中都一股脑儿地沦落为道德的奴婢?最后,新文化同人在反对“伦理政治”③的设计中不知不觉地中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计:不但西学的所有内容都成为伦理道德的囊中之物,而且一种新型的伦理政治范式也在悄然酝酿。在文化运动的背后,却是借文化之名进行的一场全盘的“立德”演绎,这个“德”不但将诸如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德先生”都拉进无所不包的“德”之网格,而且还将那些与伦理无关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赛先生”也囊括其中。
地归结为伦理问题的同时,我们看到,新文化人的所有努力在所谓的文化革命、思想革命、伦理革命背后,就又变成了九九归一之途:新道德造血。不言而喻,为“新国家”,须造“新青年”,而“新青年”的骨血则是他们口中念念不忘的“新道德”。当“人”再次成为集体、国家、社会的手段后,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治范式也就呼之欲出了。
一、立人:以“新青年”为标杆的时代主体
说到立人,一个耳熟能详的发刊词足以将五四那一代人的初心表白透彻:“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④对象是“青年”,而且是以“改造”“辅导”为主业,这已经透露出“青年”与“新青年”之区别。经过“改造”“辅导”后的“新青年”究竟是如何一番面貌呢?
回到《新青年》主撰的原初立意,不外乎身心两全的设计。用我们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即是“德、智、体”的三全或说三好式青年。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伊始之际,“德”“智”“体”三者在五四思想先驱那里并没有严格的权重勘定,只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以及思考的深入,才有了后来的以“德”为主体并将“智”一锅煮的“伦理”“觉悟”。
所谓身心两全的立意,无非是说心力与体力的有机统一。这时的“德”“智”有意无意间融通,与“体”并驾齐驱。这从主撰对“新青年”形象与气质的塑造上可以窥见一斑。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虽然多次说到“修养”和“人格”,但对青年人应有的身体素质之诉求也历历可见:“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⑤在这里,虽然心理、精神因素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陈独秀已经意识到封建传统对国人尤其是对青年的不良影響,于是便有了《新青年》杂志上以《新青年》为题的直截了当:“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何以故?原来:“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⑥现状堪忧,那“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陈独秀认为:“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⑦所谓的“做官发财”的思想,显然不是主撰心目中新青年应有的追求,而是戕害青年的科举时代余毒。
不难看出,上述陈独秀所论无不蕴含着对传统教育方法不够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反思。于是也就有了呼之欲出的针对“新青年”的教育方针:在“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之外,一个振聋发聩的方针更是一语中的——“兽性主义”。这兽性主义教育方针完全是一种体力的教化:“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而《新青年》主张塑造的“新青年”则是一种旧貌换新颜的范儿:“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细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穷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这一系列的反问和诘难充满了挑战性,根源在于主撰陈独秀认为“遍于国中”的“纨绔子弟”是难以“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的,新时代所需要的是“朴茂青年”。⑧
一个细节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尽管我们今天习惯于说“身心”健康、“德智体”等语词结构,但是在五四先驱者那里,“心身薄弱”一词却也暴露出他们对“心”看得更重一些。这也是日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心”(德智)倾斜的原因。不过,“心”“身”并重的“改造”布局也是新文化运动伊始时期的历史真实。这从接踵而来的读者来信以及主撰的用稿原则上也可见其端倪。1916年9月,一位名为程师葛的读者来信咨询“德、智、体”诸问题,主撰以“知之为知之”的心态予以作答。其中,回信中对“军国主义”的讨论尤其吸人眼球。从“勇武可钦”的西人性格中找资源,而对军国主义又模棱两可,这多少反映出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思想吊诡与两难。
正是因为倡导者的思想导向,才有了一系列有关国民性尤其是青年改造的文章。这些启蒙文论,尽管不一定是严谨的科学论文,但是对当时舆论环境的营造却至关重要。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可算是充分理解了编辑的意图并能投其所好的幸运之作。要知道,背靠北京大学的《新青年》会聚了一批海归以及学养深厚的教授和博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投稿的结果几乎就是石沉大海,除非作为边角料的读者来信才有用以填窗补洞的可能性。这位署名“二十八画生”的作者不是别人,乃是尚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这位雄姿英发的后生俨然以科学的态度解读体育在国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将“智识有愚暗,无不知自卫其生者”作为“释体育”的立论前提。作者开宗明义:“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⑨寥寥数语,已经将文章主旨与主撰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关于“不知科学”之“浅化之民”的描述如出一辙地流布出来,更与《今日之教育方针》中有关“兽性主义”的导向珠联璧合。
总之,在五四那一代人心中,只有“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才有可能实现“根本之救亡”⑩。至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的出发点,最终的归宿还是要落脚于国家的事权上:“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二、立德:“德、智、体”三位关系的演绎
辛亥革命以降,民主共和一直是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样一个新型政体之所以受到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追捧,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是一个与封建皇权专制根本不同的五族共和的民主制度。当然,对一个被“伦理”之桎梏缠身达数千年之久的政治体制来说,要想从此挣脱出来,可谓困难重重。道德理想的天朝梦如同缧绁一般萦绕在国民脑际,这也是陈独秀之所以“敢断言”中国国民之觉悟关键在于“伦理的觉悟”之底线的根本缘故。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时不时地伴随着复古与回潮。尽管天朝梦屡屡破灭,尽管道德理想王国一再覆灭,但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雄心烈火却从没有被浇灭过。当我们看到陈独秀等一代先驱去挑战那“伦理”的“底线”时,我们在对他们的艰难选择充满敬意的同时,也为他们的那股韧劲儿捏了一把汗。要知道,“伦理觉悟”的底线既充满了“善的脆弱性”,也挟带着步步惊心的所谓的“启蒙的冒险”。在这里,我们且撇开凡此种种的逶迤曲折,但以主撰那字里行间流布的意识乃至潜意识成分为例,就足以领略到潜藏并驻存心间的意识危机。通过“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这句话,我们发现,在“思想”和“修养”并驾齐驱的背后流露的则是一种“思想修养”观念。上文提及的那篇《一九一六年》几乎全文都是在讲自该年伊始一举刷新修养、品德的位格之事。在于中西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中,作者的文字诉求无非是“新青年”何以“新”。而其标准也无外乎摒弃“怯懦苟安”转而“好勇斗狠”、“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而养成“自由自尊之人格”。一言以蔽之,“独立自主之人格”乃是针对“奴隶道德”的一种不二选择。就此而言,这一思维逻辑很容易将启蒙的路径引向道德至上的窠臼。
这一隐形基因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回到中国五四时期的语境,本身就在“修养”和“人格”上立意的《新青年》自然更容易借坡下驴。尤其是在“金心异”同志的千呼万呼下周树人、周作人等纷纷加盟这一群体之后,看看那位被主撰引以为豪并以“听将令”为要的鲁迅之所作所为,就可以明白一二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是作者留日期间受到仙台幻灯片事件刺激之后形成的观念,也是他“弃医从文”的根本动因。用文学来改造国民性并培育新人的初衷,构成了那一代“新青年”同人的心声。从鲁迅之反传统伦理“吃人”的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一代思想先驱的爱恨情仇最终都化作了伦理的轴心:或批判式的揭露“弊病”,或同情式的“人道”,或救济苍生式的“博爱”,不一而足。
这里,我们不妨以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立论为例,看看其所立之人的原委。本来,就周作人思想革命的立意来说,很是具有原教旨启蒙的意味:他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简单的“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如果说,前者的“慈善主义”是出自人性本能的“恻隐之心”,那么后者所说的“人间本位主义”则是具有一定宗教情怀并顺应人性的“人道主义”。“讲人道,爱人类”乃是这个“主义”的核心观念,“利己而又利他”更是其“博爱”意念的全部:“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不难看出,“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乃是其通篇的立意。
道德观念,在人文传统中本来就有很高的权重,加之又是近亲关系,要在二者之间给出个楚河汉界谈何容易?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五四先驱自觉不自觉地将自我启蒙的理念挂靠在了伦理、道德的战车上。撇开那一时代的诸如同情人力车夫遭遇的诗歌《人力车夫》,李大钊的以“平民”“贫民”“庶民”等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关键词也时常跃然纸上,尤其是配合《新青年》文学改良与革命呼声的应运之作《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更是将俄罗斯人道、博爱的特色文学视为至宝予以推介:“凡夫博爱同情、慈善亲切、优待行旅、矜悯细民种种精神,皆为俄人之特色,亦即俄罗斯文学之特色。故俄罗斯文学直可谓为人道主义之文学,博爱之文学。”文学观念如此,思想观念、文化观念也无不充斥着建立在平等、博爱意念基础上的伦理色彩。连“一战”的胜利和俄国革命的胜利都是“道义”的胜利:是“人道的警钟”的回响,也是“公理”战胜了“强权”。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先是一股脑儿地将思想的“股份”都投资到了“精神”的权益上,对前期一度热衷的“体育”已经视为烟云。当愚昧、无知、颟顸成为亟待“启蒙”并“觉悟”的代名词后,一个与启蒙难分难解的问题便顺理成章地浮出了水面:毕竟,“觉悟”与“启蒙”这一“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公开”行为并不尽然相同。进一步说,虽然启蒙与觉悟二者“均强调个人自觉性的提升突破,对自省、反思等能力与感触的增强”以及“均着重自由幅度的扩张”,但是“‘启蒙不能只是指拥有理智或理性,亦在于有勇气‘不经别人的引导以运用理智,从中显露个人的成熟与独立”,同时“‘觉悟带有较强烈的主观及神秘色彩,可与‘启蒙所强调的客观科学理性背道而驰”,因此“启蒙”与“理性”不即不离,而“理性”与“觉悟”却若即若离。若是“启蒙”与“觉悟”相提并论,就“意味在启蒙运动中,理性以外的因素可能有的作用与冲击”。尤其是当“勇气”等诸因素被作为美德加以夸大,而“理智”等“独立思考”的能力被忽略的时候,“德”及其相关伦理要素很容易被作为启蒙的不二法门委以超负荷的重托。
三、立国:当家国情怀成为最大的道德
可以说,五四先驱当年“改造青年”的路径是“立德树人”的逻辑,追究原因在于主撰陈独秀认为中国之所以会“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因此,由“立德”而“立国”的逻辑就成为无论怎样的“灌输”,即使是“打鸡血”一般的兴奋剂输入方法都不为过。这一点,我们不是在那一代人饥不择食的“兽性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方针中领略过了吗?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论述历历在目,主撰陈独秀的直白更是一针见血:“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这也是陈独秀何以在创刊号开门见山地说出下面这段话的理由:“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这与他在“社告”中的发刊词一脉相承:“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这个“辅导青年”也好,改造国民也罢,无非是用自以为是的所谓新道德、新伦理、新文化来塑造未来国家的新主人。一句“修身治国之道”道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傳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我们看到,这一情怀在古代士大夫那里固然坚不可摧,就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即使是在那些学贯中西的海归派新型知识分子那里也是每每呼之欲出。在严复那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固然是德智体的雏形,就是梁启超那笼而统之的“新民说”也无不贯穿着浓浓的传统淑世情怀。这也是笔者将其概括为“新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根本依据。
以伦理的大换血贯彻启蒙大众的理念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旧瓶”烙印。这“人格”与“国格”的关系,之前我们已经引述过。而“个人之人格”与“国家之人格”的关系还在于这么一个逻辑:“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陈独秀立国逻辑之设计的理由还在于其对近代以来文明冲突的研判:“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伦理政治”本来就是一个怪胎,而招致这个怪胎的罪魁祸首乃是被复制了几千年的“三纲五常”之伦理道德。作者将文明冲突分为“学术”“政治”“伦理”三个层次,并细说了何以要在此时此刻拿下“最后”一轮的缘由:“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这里已经说得再明确不过了:“自由、平等、独立”乃“西洋之道德政治”。这样的理解必将给新文化运动一个南辕北辙的答案或说结果。
如果说作为主撰的陈独秀的理解还处于一个就事论事的阶段,那么接踵而来的“同志”的出现则可谓后来居上了。一个基本的理论遵循还在这里: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建立为每一位拥有国族身份的公民提供了具有深沉家国情怀的归属感。而且正是从这种归属感里,我们找到了道德伦理与国家政治的脐带。爱国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正是这一归属感的内化与外化的双重表现。列宁那句“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就是对这一归属感的根本表达。从数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的心路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殉君”“殉国”“殉道”者的那种将“星空”与“道德法则”奉若神明的心态。屈原因忧心楚国国运而自投汨罗江,文天祥因殉节宋室社稷而壮写“留取丹心”的正气之歌。这不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实写照吗?这“家事国事天下事”有着说不尽的“匹夫有责”情结。千百年凝结的人文传统,即使是在中西文明冲突与交汇的近代历史中,也依然可见其蛛丝马迹:梁巨川与王国维的先后自绝,不是对未来“会不会好”的答案诉求,而是对千年道统的依恋与追寻,这恰恰是道德意义上的心理归属占据了上风。
回到我们上面所说的“同志”,以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为例,如果说以上的士大夫群体的殉难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超越,那么他的“青春”则是鲜明的为国奋斗的“责任”人生,“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在《“今”》一文中,他将一切寄托于当下(未来):“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这是一个心理年轮的超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他呼吁国人“打破”并超越“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矛盾生活”,力求“脱去二重负担”,“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这也是之后我们将要看到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中作者一再强调超越过去和当下,全心致力于“第三种文明”、聆听“人道的”钟声、拥抱“自由的曙光”、迎接“赤旗的世界”的根本之所在。不言而喻,如果说士大夫是在传统之“来龙”上追寻回家的路,那么五四那一代人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在一张新裁就的白纸上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以把握未来的“去脉”。
无论是用传统的箴言表达——“立德立功立言”,还是用今天的话来叙述——“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我们都可以这样概括先哲的情怀:传统的文化、西方的文明都已经成为过去,“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在20世纪的那一时刻必将是超越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走向,因为它是人类“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这个“新精神”既具有伦理淑世的普遍性,又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法则。正是在这一逻辑构架下,《新青年》知识群体从引领文化运动到参与社会运动,从研究“学说”到倾心“主义”,从运动社会到孕育政党,一个新型之现代中国呼之欲出。
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立人”“立德”“立国”,不同于传统的“三立”之间并列关系,五四时期的“三立”则是一种由“立人”(通过“立德”的路径)而“立国”的逻辑关系。即“立人”目标逐渐由原先的“心身两全”变成了“以德为主”。要“立国”,须先“立人”,而“立人”的路径则是“立德”。他们的这种以“新道德”的换血来造就新国民、新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古代的“修身治国之道”可谓如出一辙,其中无不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注释
①关于五四时期“立人”问题的研究论著有:张宝明的《由立人而立国——论陈独秀五四文化道德思想》(《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曾锋的《“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生存观》(《兰州学刊》2009年第2期),张先飞的《五四理想“人”的发现与初期新文学主题、形态的确立》(《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杨国强的《论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第9期、第10期连载)等等。②关于五四时期“立国”问题的研究论著有:沈淑瑜的《略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救亡主旨的深化与发展——兼评“文化断裂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董涛的《五四救亡与启蒙关系我见》(《晋阳学刊》2000年第3期),李新宇的《高一涵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家理念》(《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傅正的《经“救亡”而实现的“启蒙”——以《新青年》的变化为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6期)等等。③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④陈独秀:《通信·答王庸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⑤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⑥⑦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⑧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⑨二十八画生:《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⑩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15日。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修订版序言》(修订版),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页。君特·格拉斯,哈罗·齐默尔曼:《启蒙的冒险——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对话·前言》,周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沈尹默和胡适均以“人力车夫”为题在《新青年》上发表过诗歌(见《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此外,鲁迅的《一件小事》一文也赞扬了人力车夫的伟大。李大钊:《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2页。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陈独秀:《发刊词》,《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陈海文:《启蒙论: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0、29、97—98页。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一文中提倡“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刘叔雅在《军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一文中倡导以军国主义改变中国当时武风不振的局面。陈独秀:《袁世凯复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严复:《原强》,《国闻报汇编》1903年6月。张宝明:《启蒙,启蒙:启蒙的两难——我为什么不是一个道德形而上主义者》,《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陈独秀:《通信·答常乃惪》,《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8页。康德曾深深感慨:“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7页。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李大钊:《“今”》,《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