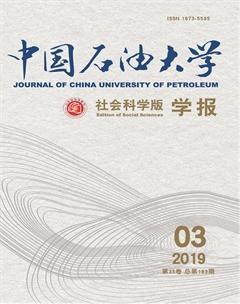重构与再定义:个体与社交媒体幸福观的互动
庄美连



摘要:社交媒体凸显了个体的主体性,使个体能自由言说,获得“可见性”,并赋予个体新的思考内容。通过以王宝强离婚事件为经验材料,对个体与社交媒体在幸福观上的互动进行考察发现,在社交媒体上,用户个体自我、个体相
互之间、个体与社交媒体之间等都存在竞争、冲突、顺应和同化等不同程度的互动。在竞争、冲突中,个体的幸福观得以“可见”,影响了社交媒体对幸福观的呈现;与此同时,社交媒体通过构筑信息环境等手段改变、更新了个体的认知图式,进而实现对个体幸福观的建构。通过对情境的定义,个体与社交媒体的幸福观都实现了重构和再定义。
关键词:个体;社交媒体;幸福观;互动;王宝强离婚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2;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3-0088-08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允许自主撰写、分享、沟通的社交媒体与人们的关系越发紧密。一方面,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日渐渗透进个体的日常生活,人们与媒介的接触点越发扩散,媒介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认知、态度甚至行为;另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自我表达和自主话语能力的社交媒体也让个体技术赋权,与媒介互动越发频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因此,是媒介影响了人们的认知,还是个体影响了媒介的建构,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样地,在对“何为美好人生”的幸福观问题上,社交媒体与个体之间,是前者对幸福观的建构影响了后者的认知,还是后者对幸福的思考影响了前者的呈现?两者之间有何关联?这些问题就是本文的研究所在。
一、缺位的主体:被建构的幸福观
幸福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话题,幸福观是人们对什么是幸福、如何追求幸福等问题所持的系统观念。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对其进行了多维度、多学科的研究。随着技术的更新和媒介的发展,幸福也被引入了传播学研究领域,学者主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即媒介拥有对幸福感的客观影响和媒介内容对幸福感的主观塑造)对媒介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1]媒介与幸福观之间的关系主要属于主观方面。
培养理论认为,媒介再现现实,同时也影响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影响和建构着我们的现实观。对媒介与幸福观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延续了培养理论的研究传统,认为媒体对幸福观起着形塑和建构的作用。1987年,Marsha L. Rlchins对电视广告的研究得出结论:电视广告暴露与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关联,对受众的幸福观有形塑的作用,受众越多接触电视广告,其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越强。[2]这种形塑作用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媒介。姚君喜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幸福感的认知评价有明显的建构和影响作用,尤其是以报纸为主的传统印刷媒体。[3]
之后,学者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就媒介对幸福观的建构作用和方式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如张梦霞对《中国青年报》关于幸福话题的内容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青年报》在生产新闻的过程中以隐含话语偏向的方式向广大青年构建了中国式幸福观,并在幸福这一值得人们永久探讨的话题上,实现了其作为机关报和社会公器的双重身份的融合。[4]与此同时,在对个体的幸福观的呈现方面,媒体大都采用群像式呈现,个体缺乏辨识性,千人一面,在媒体上往往是面目模糊的“他们”,如张玲玲等人对1961—2012 年拍摄的四部中外纪实影像进行内容分析后认为,这些影像建构了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中西方迥异的幸福观,其中《幸福在哪里》和《你幸福吗》表明了中国式 “幸福观”的主要特征:“家庭”是幸福的“动力源”,“子女”是幸福的“发动机”。[5]
随着媒介对幸福观影响的深入,部分学者进而探讨媒介内容对幸福感和幸福观的影响机制。如袁爱清利用焦点小组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表明,媒介之所以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幸福感,主要是以满足其需求为基础,其中认知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6]郑恩、龚瑶等人则通过综合研究提出了媒介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三种路径:对媒介内容的主动使用与满足、构建参照系、影响观念认同。[7]
在塑造象征性现实、影响受众主观现实和幸福观方面,传统媒体展示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然而,如姚锦云所言,效果研究的传统使得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媒介对使用者影响的层面,而使用者对媒介的影响层面,亦即媒介使用者的主体性被忽视。[8]8幸福观是对“何为美好人生”的一整套信念、价值、态度及行为意向的体认,人作为具有自主意识和能动创造性的个体,在受外在环境影响的同时,更具有主体的内涵,在选择何种幸福观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在传统媒体阶段,媒体的版面、时段等受限,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理念使得媒介使用者只能以受众的面貌出现,缺乏与媒介互动、表达自我的渠道和工具,媒介使用者的主体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致使其在对幸福观的体认和追求这个本应最具发言权的问题上缺位、失语;而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的社交媒体的出现则为展现个体的幸福观、凸显人的主体性,从根本上改变个体在媒介面前被动、主体缺位的局面提供了可能。
二、凸显主体性:社交媒体对个体的意义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也称社会化媒体。关于其定义,国内外学者各有侧重,莫衷一是。田丽、胡璇梳理了其起源和发展脉络,认为社交媒体是以互动为基础,允许个人或组织进行内容的创造和交换,依附并能够建立、扩大和巩固关系网络的一种网络社会组织形态。[9]彭兰将其定义为“互联网上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10]。不管何种定义,社交媒体是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允许用户进行自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具有UGC(用户生成内容)的属性这一本质是不变的。换言之,它既是用户表达和交互的工具,又是承载用户生成的内容的平台,其对凸显个体主体性有重大意义。
首先,作为工具的社交媒体,能够使个体技术赋权,自由表达与交互进而获得“可见性”。“可见性”是丹尼尔·戴扬提出的概念,指能否被他人注意,能否被他人看见。当注意力达到一定规模时,就获得了可见性。戴扬认为,是否可见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其包括三种权利:被看见的权利、以自己定义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赋予他人可见性的权利。[11]139一直以来,媒体是提供信息、生产现实、达成共识的功能性机构,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实际上就是对事物或个体可见性的赋予或剥夺,都在影响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知觉与印象,指引着受众的注意力。面对力量庞大的传媒,受众只是被动的存在,对于关注什么、是否被关注,受众往往缺乏主动权,处于可见性被剥夺的状态。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则使用户掌握了回应和对抗传统媒体的工具,他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写日志、发视频等传播信息的活动,使自己有机会被他人注意、被他人看见。他们对自己发布的信息具有控制权,可以对接收对象进行设置,可以决定信息是某些人可见还是全部人可见,还可以决定向他人是展示三天信息还是展示半年信息。同样地,他们还可以通过搜索、评论、点赞、转发等行为让某些人、某些事成为热搜,获得关注度,赋予他人可见性。如此,面对拥有强大传播力的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赋予的可见性实际上使个体掌握了话语权,拥有了自我设置議程的能力。
麦克卢汉曾言“媒介即讯息”,强调媒介形式对我们思维、行为方式的影响。哈罗德·英尼斯则进一步提出,新的传播技术在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的同时,也给予了我们新的思考内容。社交媒体对个体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其作为一种工具为个体提供了绕开大众媒介而获得可见性的一种可能,创造了可以自由言说的个体性主体,还体现为其为用户提供了“一种用于交流讯息和观点的网络”和展现自我的平台,并给予我们新的思考内容。以幸福感为例,用户在社交平台上所展示的内容与传统媒体不同。传统媒体重宏观上的信息呈现,侧重政府作为主体的行为以及偏重成就报道,[12]往往遵循一定的媒体框架;用户发布的信息则没有既定的选择框架,最为丰富充沛的是个体情感和社会关系层面上真切细腻的情感[13]。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为用户大范围充分暴露现实中敏感议题提供了空间,使得多样化的议题开始超越大众媒介的选择性框架而暴露在公共视野中,成为公共领域中的议题。[14]所谓见多识广,社交媒体上个体自由发布的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内容,拓宽了个体的视野,并与传统媒体上的信息一同构筑了个体的拟态环境,赋予了我们新的思考内容,成为我们进行决策的重要信息依据。
社交媒体作为个体进行互动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工具、实现信息及时迅速且公开传播的平台,兼具社交属性和媒体属性,其主角不再是媒体的运营者,而是千千万万的用户。社交媒体赋予了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千千万万的用户构成了庞大的基础网络,他们创造内容也传播内容,使社交媒体成为建立在人际传播基础架构上的大众媒体,个体主体性凸显。此时,社交媒体平台上呈现的幸福观已不再由某一媒体单独建构,而是千千万万的用户与用户、用户与平台之间不断互动、博弈的结果。因此,社交媒体背景下,媒介与幸福观研究要从以往的狭隘视角中抽身出来,应充分考虑到媒介特性和个体主体性。[8]8本文以王宝强离婚事件为例,围绕社交媒体及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探讨和争论,据此探讨社交媒体与个体幸福观之间的互动。
三、王宝强离婚事件中个体与社交媒体幸福观的互动
2019年1月17日,王宝强与马蓉的财产划分完成,离婚案司法程序全部终结,长达两年多的离婚事件终于尘埃落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此事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了广泛热议,事件及相关当事人几度登上热搜榜,讨论主题从单纯的明星婚姻、家庭延伸到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涉及经济、法律、家庭、传统伦理等各个方面。在沸沸扬扬的围观与讨论中,从宣泄情绪到表露态度,从陈述事实到表达意见,网民们纷纷利用社交媒体,以跟帖评論、点赞、微博留言、转发、投票等方式进行发声,将自身对幸福的理解和思考投射到平台上,多方互动,建构了多样化的幸福图景和多元化的幸福观。其中,在社交媒体这个平台上,用户个体自我、个体相互之间、个体与社交媒体之间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互动。
“互”是交替、相互的意思,“动”指使起作用或变化。“互动”就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等通过语言或其他手段传播信息而发生相互依赖性行为的过程。它是一种最基本、最普遍的日常生活现象。美国芝加哥学派的R·E·帕克和E·W·伯吉斯认为,互动是一个过程,他们主张把“互动过程”分为竞争、冲突、顺应、同化四个不同的阶段。[15]综观始于婚姻、家庭,关涉事业、朋友、经济等多个维度的王宝强离婚事件,社交媒体用户围绕着不同的幸福观相互之间所进行的交流、冲突、认同和融合的过程,与上述互动过程是基本吻合的。
(一)竞争:表达与展现
竞争指的是一个系统中各个部分为获得稀少资源所进行的斗争。反映在社交媒体上,竞争即是不同事件、观点为获得可见性而进行的斗争。与其他热点事件起源于个体的微博发文相仿,王宝强离婚事件中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同幸福观间的互动始于2016年8月14日凌晨王宝强在微博上公开的《离婚声明》。这份声明使凌晨的社交媒体平台瞬间热闹起来,个体纷纷利用手中工具在社交媒体这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态度、展示自己的观点。根据微指数数据,8月14—18日,“王宝强离婚”微指数高于当时正在举行的“奥运会”微指数。该阶段,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可归结为三类。第一类是与事件当事人进行虚拟对话,对王宝强的该条微博进行评论或转发,或是到马蓉微博留言,直接输出自我对幸福的理解,如陈晋38066评论称“做人不能太霍顿 娶妻不能叫马蓉 用人不能用宋喆”。第二类是发微博或朋友圈,根据自己的认知图式来理解该事件,如Tracy随喜发微博称:“一方总是妥协的婚姻迟早会出问题。”行者_木子也感慨:“再美的爱情也禁不起背叛!”此类用户多是借王宝强离婚事件来表达或佐证自己早已认定的观点,进行自我展示和自我言说。第三类则是针对该事件进行自我互动,基本遵循“我早就觉得他们的婚姻有问题+证据”和“天哪,这不是真的+祝福王宝强”两种互动模式。
戴扬认为,媒体是通过展现(monstration)使事物获得关注度、赋予事物可见性的机构。展现什么,不展现什么,向谁展现,以何种方式进行展现,这些都是简单而重要的问题。[11]146因此,王宝强离婚事件中,不管是虚拟对话,还是自我展示,抑或是自我互动,都是个体在社交媒体上所进行的展现,这种展现形成了一定的观点并使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可见性。有人感慨“金钱未必能买来幸福”,有人宣称“娶妻当娶贤,不要找美女当老婆”,更有人探讨新时代学历、价值观等方面的门当户对……不同观点在同一平台展现,即是对受众注意力的一种竞争。这些对何为幸福、幸福包含的要素的讨论在社交媒体上都获得了不少的注意力,各方形成了竞争态势。其中,点赞是最有效也是最直观的一种竞争方式,评论区中经常可见的“同意的赞我”“赞我送我上热搜”等言语即是竞争各方扩大声势的一种手段。微博评论中的热门评论代表了一定时期内的主流意见,实际上也是各方竞争的结果:意见获得了最大的可见性。
(二)冲突:互动与影响
冲突是彼此相互联系和传播的单元之间的竞争。根据帕克的观点,“传播”被限定为有效的传播,即当两个或更多的个体心灵相遇时所发生的活动可以彼此相互影响。在王宝强离婚事件中,不同幸福观间的冲突几乎与竞争同步发生。在各方竞争的众声喧哗中,网络上迅速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派抨击马蓉对婚姻不忠诚并对其进行道德审判,感慨“宝宝心里苦”;另一派则认为王宝强的做法伤害了父母和孩子,质疑其侵犯了隐私。这两种观点在批判婚外情,认为家庭美满、婚姻幸福就是幸福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在如何实现幸福方面却存在分歧。前者从儒、道等集体主义传统文化出发,秉持“社会取向的幸福观”,即个人存在于社会关系中,并具有一定的角色和地位,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追求幸福应注重角色责任,[16]21倾向于认为破坏家庭、婚姻的言行是对自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破坏,都应得到惩罚;后者则依从欧美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坚持“个人取向幸福观”,即个体是独立自主的存在,是行动的主宰者,强调对幸福应采取个人负责和直接追求的态度,[16]20倾向于认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成败必须完全由个体自己来承担,不应牵扯到父母和孩子。媒体人士曹林称这种冲突为“精英与大众彻底地撕裂和决裂”[17]。双方唇枪舌战,互相攻讦,冲突从微博蔓延到微信,从个体发展到群体。
冲突首先在微博中的个体间发生,微博的@功能能使对话具体到个人,让竞争和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增加。《离婚声明》博文下的几百万条评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网友间的对话构成的。这些对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持不同幸福观的网友间@来@去的直接对话。持“个人取向幸福观”者批评王宝强不该公开离婚声明,持“社会取向幸福观”者立即就回应“结婚要普天同庆,离婚为什么不能公开声明?”;前者质疑王宝强的做法“太不男人了”,后者马上就以潘粤明和董洁的事件进行回复。微博成为个体自由言说和讨论的“公共领域”,本属于王宝强个体的私人事件逐渐公共化,私人领域有演化成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趋势。[18]总体而言,事件初期,微博中占主流的是对马蓉的道德审判,网民们以群体形象出现,用成千上万的评论、转发、点赞表达着愤慨。
“新闻后的跟帖和微博留言是大众的武器,精英是不屑于跟帖评论,而是通过有表达门槛的长文章和自媒体来表达系统的观点。”[17]当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到内容生产和信息发布的流程中,这些分散、独立的信息源就构成了一个扁平且多元化的信息互联网络,彻底颠覆了传统大众媒介中心化、集中式的傳播路径。与此相反的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再中心化过程。与普通网民依靠数量优势形成声势大相径庭,网络意见领袖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生产的文本往往能引起强烈的情感共振,提出的见解对大众具有导向作用。王宝强离婚事件中,相较于持社会取向幸福观并谴责马蓉没有尽到妻子、母亲的责任而对其进行道德审判的个体是普通网民占多数,而持“体面解决、各自安好”个人取向幸福观的个体却不乏掌握着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因此,很快,微博上个体的冲突就蔓延到其他媒体或自媒体平台。其中,廖保平在“沸腾”微信公众号发表的《吊打奸夫淫妇,王宝强还迷恋农耕时代的价值观》和新浪新闻发表的评论《王宝强离婚声明:乡鄙野夫的野蛮复仇》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将不同幸福观间的冲突推到了高潮。所谓人以群分,社交媒体建构的是一种价值观传播[19],它对持相似价值观的人具有聚合的作用。因此,本来聚集于微博的个体冲突蔓延转移到以微信公众号为主的自媒体平台的同时,冲突的主体也从原先的个体扩大到以微信公众号为主的自媒体平台所代表的粉丝群体。冲突的蔓延转移实际上也是社交媒体时代热点事件微博发端、传统媒体跟进、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加温的传播路径的一个体现。
(三)顺应:深化与补充
顺应与同化都属于个体或群体对环境的调试过程。顺应指的是人类通过形成新的行为习惯或改变原有的行为习惯以适应环境需要的过程。它往往发生在冲突停止之时,是对竞争冲突结果的一种适应,其种类有妥协、和解、容忍等。如果说竞争和冲突是个体利用社交媒体这一互动交流的工具输出自身的幸福观,那么,顺应和同化则是作为承载用户生成内容的平台的社交媒体对个体幸福观的形塑和建构。王宝强离婚事件在全民热烈讨论一段时间尤其是一审宣判后,两派对立观点间的冲突也趋于缓和,然而,对于个体而言,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即顺应才刚刚开始。
个体的顺应主要体现在改变已有的认知图式以理解新刺激。认知图式是“过去反应或过去经验的一种积极组织”[20],是人脑对信息客体的认知方式,其主要作用在于构建主体对客观事件的解释框架。[21]认知图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个体必须深化或扩充已有的认知图式,因此,认知图式具有可塑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赋予了个体新的思考内容,实际上是向个体提供了解读客观事物的框架,以利于个体构建新的认知图式来顺应环境。很多自媒体,尤其是微信公众号,纷纷从自身的定位和目标受众出发,对王宝强离婚事件中涉及的幸福要素进行分析。如秦小明的《王宝强离婚启示:动态平衡的关系才能走到最后》强调真正可以长久维系的婚姻关系应该是夫妻双方一直处于动态的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状态;也有人从《爸爸去哪儿》中分析了王宝强家的家庭相处模式,认为一个幸福的家庭中爸爸居于什么地位至关重要;等等。这些内容包含了“个人取向幸福观”中强调自我应独立自主,个人的幸福应通过积极主动的驾驭环境如不断提升自我、戮力改变外在环境来达成等内涵。而2018年6月22日马蓉接受新浪娱乐独家采访中言及的为了孩子选择隐忍王宝强的家暴等注重母亲的责任的言论与“社会取向幸福观”中强调个体的角色责任和义务暗合。2018年6月29日马蓉在微博@金耳朵兔子发布的《为了孩子,我请求你做一个有温度的父亲!》一文中多次强调王宝强的父亲身份,实际上也暗含了“社会取向幸福观”中幸福与个人肩负的责任息息相关,它是经由包容互依的自我会同和谐融入环境来达成的等观点。艾英戈和金德通过研究认为,媒体报道在影响大众形成政治意见方面主要是通过铺垫效果起作用的,即“通过唤起对某些问题的注意,并忽略另外一些问题,影响了观众对政府、总统、政治和公职候选人进行评价的标准”[22]。铺垫效果主要影响了人们的态度权重,主要以激活或引起人们注意那些被大众传媒强调的议题,并改变人们心目中该议题的重要性程度的方式起作用。[23]王宝强离婚事件中,个体,尤其是持“社会取向幸福观”且对该事件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婚姻层次上并对马蓉进行道德审判的个体,在接触自媒体的这些分析后,会倾向于以夫妻双方是否维持动态平衡的关系为标准来判断一段婚姻是否幸福,以爸爸是否与其他家人同等重要来评价一个家庭是否幸福,其更关注个体的幸福。持“个人取向幸福观”的个体在了解了马蓉的采访和发文后,观点虽然未必受其影响,但角色责任在个人幸福观中的权重这一议题则会受到关注。经过这些环节,个体关于幸福要素的认知得到扩充,对于幸福的评价标准会有所调整,认知图式得以深化,其为后续理解乃至接受对立方的观点提供了基本的理解框架。
(四)同化:过滤与改造
皮亚杰认为,人类智慧的本质就是适应。[24]生物学上的适应包括顺应和同化两种。顺应是改变已有图式来更好地理解新刺激,同化则是根据已有图式解释新的刺激。换言之,顺应是深化、构建认知图式,同化则是利用深化或构建的认知图式来解释新情境。
认知图式构建了个体对客观事物的解释框架,为我们理解新的认识对象提供了模板。如果个体的认知图式处于“休眠”状态,同化首先必须激活个体的潜在认知图式。激活的过程,也就是理解、解释的过程。社交媒体构筑的拟态环境在激活个体认知图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环境建构是媒介化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的信息在获得可见性的过程中,实际上为其他用户提供了一个认知“蓝本”,即拟态环境。与传统意义的拟态环境不同的是,此时的拟态环境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共同构筑的,而非大众传播媒介。刘京林指出,媒介信息可以通过背景介绍、解释性内容及综合信息等帮助受者激活认知图式。[25]在王宝强离婚事件中,谴责、谩骂马蓉的一方以提供事件背景或解释性的材料为主,如有网友在王宝强微博评论中称曾“撞见宋喆马蓉亲密同游”,也有人提及《爸爸去哪儿》中马蓉和女儿对王宝强呼来喝去缺乏基本的尊重和爱等,这些信息激活了个体幸福观中家人和谐、相爱地相处是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认知图式;抨击王宝强的一方则主要以综合分析的形式,指出王宝强和马蓉两人在学历、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暗含门当户对才能幸福的幸福观。背景材料通过对相关内容的介绍帮助个体了解信息所反映的人的某种行为产生的原因,综合分析则增强了个体认知图式的有序化。在社交媒体上这些解释性材料信息的帮助下,个体的潜在认知图式从潜意识进入显意识,并自动填补认知主体认知结构中的缺失部分,这一过程的完成表示主体对信息的认知和理解。评论中常见的“同意楼主观点”“太有道理了”等语句实际上也是个体认知图式被激活后的反应。
个体认知图式被激活之后,接下来就是对输入的刺激进行过滤和改造的过程。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恩斯的模型认为,为减少信息成本,人们倾向于从头脑相似的人那里获取信息。[26]“头脑相似的人”即为认知图式相同或接近的人。受既有认知图式的影响,同化可能使个体对接触的信息进行过滤,更容易接受协调性信息,而过滤或屏蔽与己相斥的信息,其结果可能出现“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甚至是群体极化。此种情况在圈层分化相对严重的微信传播中尤为明显,同一个微信公众号平台的粉丝的评论往往非常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间虽然也以评论、点赞等方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互动,但其认知图式即幸福观仅仅停留在互相印证和补充阶段,其变化不大。同化的另一个过程是对接触到的信息进行改造以纳入既有的认知图式。人在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做直接的反射性反應前,多数情况下会首先审视和考虑这些信息,或定义这些信息,进而根据自己的定义来理解和对待它们。这就是托马斯所言的“情境定义”[27]74。情境定义的结果是个体和社交媒体上的幸福观都实现了重构和再定义。
四、互动对幸福观的重构与再定义
托马斯认为,互动过程由对情境的定义决定,即个人或群体依据对所处客观环境的主观认识和界定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中涉及人类行为特有的解释、选择、判断等主观心理活动。情境定义的结果是对个人和整个社会价值观、幸福观的重构和再定义。
“情境定义”所强调的是人类意识“内化”外部刺激的独特过程和功能。[27]74因此,对个人来说,互动是一个人价值观、人格重塑的过程。王宝强离婚事件中,最初,针对马蓉的行为,冲突双方中持“社会取向幸福观”的一方将其定义为“恶意背叛婚姻”,故进行谴责与谩骂等道德审判;另一方则将其定义为“婚姻的失败”,故呼吁“依然以人性的态度,对待曾经在一起的生活伙伴”。人的认识是主客体在相互作用中通过顺应于物和同化于己而完成的。如前所述,为顺应之后事态的发展,个体改变或构建了认知图式。事件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和沉淀,2018年6月22日在二审判决前马蓉接受新浪娱乐独家专访。在经历了竞争、冲突之后的顺应环节后,尤其是对该事件有了相应的解读框架,此时社交媒体用户对其的反应与此前的一边倒大相径庭。在@新浪娱乐该条新闻的下方评论中,尽管仍有谩骂和冲突,但@楽语茶的评论“可以看出离婚前两人的确出现问题了,详情各有各的说法,冷暖自知不想站队。离婚是两败俱伤的事,希望尽快协商解决,让孩子不受影响,身心健康成长”成为最热门的评论,获得了1 747条回复和互动,也是评论区的主流观点。很显然,经历过之前的认知图式的改变,在解读马蓉的专访时,很多人对王宝强离婚事件的情境定义发生了改变,倾向于将其仅仅定义为持“个人取向幸福观”者所言的“离婚”,并在其中加入了“社会取向幸福观”一再强调的个体植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中所应承担的角色责任:让孩子不受影响,健康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所经历的解释、选择、判断等主观心理活动会逐渐影响其整个生活和价值观,使其发生悄然改变。换言之,个体的认知图式一旦改变,影响的不仅仅是其当下对某个事件的看法,而是接下来人生的一系列重要事项。因此,在托马斯看来,不仅具体行为依赖情境定义,而且渐渐地一生的策略和个性都会遵循一系列这样的定义。[28]幸福观亦如是。
对社会而言,互动使不同的个体进行交流和共享,由此可能导致一种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幸福观。H·布鲁默指出,我们根据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采取行动,而意义是社会互动的结果。[29]“情境定义”的过程是社会互动的过程,也是人类“给予意义”的过程。然而,由于事件的复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在初始阶段,一个事件的社会情境的定义即意义往往不是很清楚,通过不断的互动其意义才可能明晰,个体才可以领会期待和被期待。在王宝强离婚事件中,在竞争和冲突阶段,“社会取向幸福观”将该事件视为离婚事件,从婚姻角度出发,对王宝强和马蓉的定义是丈夫和妻子,“个人取向幸福观”则从个体对幸福的追求出发,将该事件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对王、马两人身份的定义是拥有隐私权的男人和女人。随着事件的发展和讨论的深入,明星的光环褪去,“为孩子着想”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尤其是马蓉接受新浪娱乐专访时一再强调其母亲身份,王、马作为父亲、母亲的身份慢慢凸显。经过一系列的竞争、冲突、顺应、同化,至该案件所有司法程序结束,大多数人对该事件的定义重新回归为普通的离婚事件,对王、马二者的身份也逐渐清晰、一致,将其定义成拥有多重身份的完整的男人和女人。王宝强离婚事件情境定义的完成,表明社会上对于该事件共享定义的形成,也意味着大众在该事件上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形成。
共享定义指导着我们的行动。托马斯定理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30]换言之,主观印象和理解可以反射到生活中,成为真实生活的投影机。人们的情境定义一经确定,相应的客观行为也就随之产生,尤其是一种定义得到社会成员某种程度的认可或成为社会共同定义后,情况更是如此。[31]如人们关于婚姻中双方保持“势均力敌”才能长久幸福的认知。情境定义的趋于一致,实质上为内在价值观的一致奠定了基础。经过竞争、冲突、顺应、同化四个阶段,社交媒体与个体对王宝强离婚事件的情境定义趋于一致,实际上是在何为幸福、幸福包含的要素等方面从分裂逐渐趋于一致,在此过程中,不管是秉承传统观念的大众,还是坚持现代理念的精英,抑或是社交媒体平台,其幸福观均实现了重构、再定义。
五、结语
陈龙认为,随着社交媒体转帖、互动书写等的盛行,网民议事从广场模式转向议事厅模式,实时互动的议事共同体取代了虚拟的想象共同体,体现了理想的交往行动特征,是公共空间的一种重构。[32]社交媒体的工具属性使网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塑造了一大批实时互动的议事共同体,其平台属性则重构了公共空间,使各种观点尽呈其间、竞争碰撞。在“何为美好人生”的幸福观问题上,对于普通网民而言,社交媒体为其提供了表达和展现的工具,个体作为互动和影响的主体出现,其幸福观有了展现的平台,并在其间竞争、冲突,获得了“可见性”;
同时,社交媒体还通过以信息铺垫深化补充认知图式、以拟态环境构筑影响主
观现实、以框架设置提供解读模板等方式建构和形塑了网民的幸福观。
对于社交媒体而言,个体投射其间的思考和理解不仅仅是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其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影响了其对幸福观的呈现。个体与社交媒体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互动。
个体和社交媒体间的这种互动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对话双方不应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对话”主体间具有平等性。[33]
同时,这种互动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个体以社交媒体为工具和平台输出自身的幸福观进行竞争、冲突,输出的幸福观在成为社交媒体的重要内容和信息来源的同时,也成为个体的拟态环境,形塑和构建了个体关于幸福的认知图式。经过顺应于物、同化于己,个体新的幸福观又在社交媒体上展现……如此循环往复,在不断的竞争、冲突、顺应和同化的互动过程中,通过对情境的定义,个体幸福观得到了重构和再定义;通过交流和共享,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幸福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享定义。具体言之,经过社交媒体上的一系列互动,不管是持“社会取向幸福观”的个体,还是持“个人取向幸福观”的网民,他们两者自身、相互之间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其幸福观最终趋于一致:在传统文化占主导的语境中,“人”的意义根植于社会关系和人际交流,幸福与个人肩负的责任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在履行自身角色责任和义务的前提下,个人的幸福应通过积极主动地驾驭环境如不断提升自我、戮力改变外在环境等来达成。
参考文献:
[1] 韦路.媒介能使我们感到更幸福吗——媒介与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J].当代传播,2010(4):16-18.
[2] Marsha L Rlchins. Media, Materialism and Human Happiness[J].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1987(1):352-356.
[3] 姚君喜.大众传媒与社会公众的幸福感[J].当代传播,2006(4):10-13.
[4] 张梦霞.新闻生产与神话的诞生——《中国青年报》对幸福话语的建构[D].湘潭:湘潭大学,2015.
[5] 张玲玲,张欣,张书成.纪实影像如何建构中国式“幸福观”——对四部中外纪实影像作品的内容分析[J].现代传播,2013(11):91-95.
[6] 袁爱清.社会转型期媒介对人类幸福的建构与影响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4.
[7] 郑恩,龚瑶.新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1):56-64.
[8] 姚锦云.从幸福感到幸福观——媒介与幸福研究的新进路[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1).
[9] 田麗,胡璇.社会化媒体概念的起源与发展[J].新闻与写作,2013(9):27-29.
[10] 彭兰.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
[11] Dayan D. Conquering Visibility, Conferring Visibility:Visibility Seekers and Media Performa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3(7).
[12] 廖卫民,钱毓英.民生新闻传播与社会幸福感评估——基于浙江省媒体语料库的实证分析[J].当代传播,2012(3):21-25.
[13] 何明,廖卫民.城市幸福感与媒介微传播:基于微博样本对“幸福大连”的实证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31-138.
[14] 孙玮,李梦颖.“可见性”:社会化媒体与公共领域——以占海特“异地高考”事件为例[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37-44.
[15] 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83.
[16] 陆洛.华人的幸福观与幸福感[J].心理学应用探索,2007(1).
[17] 曹林: 面對王宝强, 精英与大众彻底地撕裂和决裂[EB/OL].(2016-08-15)[2019-01-18].http://s3.uczzd.cn/webview/news?app=uc-iflow&aid=8007491574158795269&cid=100&zzd_from=uc-iflow&uc_param_str=dndsfrvesvntnwpfgi&recoid=&rd_type=share&sp_gz=0&pagetype=share&btifl=100.
[18] 张朋华,靖鸣.私人事件传播中不同媒体议程设置的博弈——以“王宝强离婚事件”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6(12):15-19.
[19] 张洪忠.社交媒体的关系重构:从社会属性传播到价值观传播[J].教育传媒研究,2016(3):28-30.
[20] Anderson J R.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M].San Francisco:Freeman,1980:3.
[21] 童清艳.超越传媒——揭开媒介影响受众的面纱[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34.
[22] Iyengar S, Kinder D R. News that Matters: Television and American Opinion[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134.
[23] 林功成,李莹.铺垫效果研究:发展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3(7):62-69.
[24] 章洁.大众传媒心理学教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63.
[25] 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63.
[26] 郭履腾.网络人际传播场景中的表情图像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7.
[27] 芮必峰.人类理解与人际传播——从“情境定义”看托马斯的传播思想[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6).
[28] W·I·托马斯.不适应的少女[M].钱军,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37.
[29] 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8.
[30] W·D·珀杜,等.西方社会学——人物·学派·思想[M].贾春增,李强,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298.
[31] 朱芮黎.人际交往取向的空间性比较——论中国人交往模式的差序性[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08.
[32] 陈龙.转帖、书写互动与社交媒体的“议事共同体”重构[J].国际新闻界,2015(10):6-17.
[33] 谢晓默,陈少平,吕蓉蓉.互动论视角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5):24-27.
责任编辑:赵 玲
Abstract: Social media highlights the individuals subjectivity which guarantees the individual free speech and visibility and offers new thoughts to the individual.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media on the view of happiness based on the divorce case of Wang Baoqiang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raction on social media, such as competition, conflict, compliance, and assimi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himself,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and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media. The view of happiness of the individual can be visible in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which influences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view of happiness on social media.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media changes and renews the cognitive schema of the individual by constructing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n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the view of happiness of the individual. Through the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both the views of happiness of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media are reconstructed and redefined.
Key words: individual; social media; the view of happiness; interaction; the divorce case of Wang Baoqiang
——评《当代中国青年幸福观及其培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