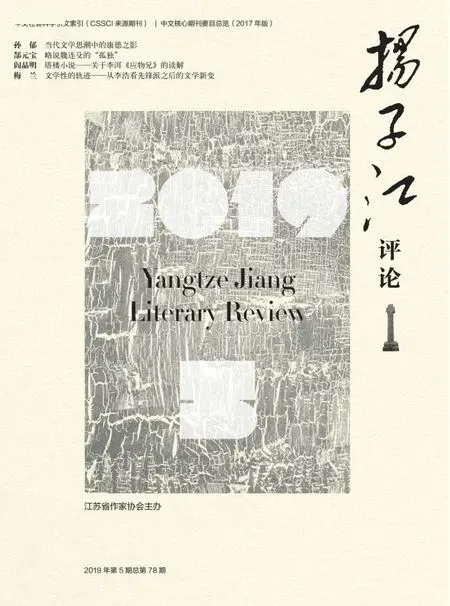略说魏连殳的“孤独”
郜元宝
鲁迅小说《孤独者》主人公魏连殳的故事很简单,他正是鲁迅《呐喊·自序》所谓“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魏家先前境况尚可,但魏连殳父母死后,只剩下他跟很早守寡的祖母相依为命,后来甚至只能依靠祖母做针线活来维持生计。
在祖母操持下(大概总还有一点家底吧),魏连殳进了“洋学堂”,毕业后在离家一百多里的S城中学当历史教员,因常写文章,“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触犯了S城的人,被校长辞退,丢掉饭碗 。
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际,他只好放弃原则,做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从世俗眼光看,他获得了再度风光。但在他自己,这毕竟是违心之举,必须整天做不愿做的事,整天跟心里不喜欢的各色人等虚与委蛇,还要不断忍受内心的自我谴责。这就造成极大的精神苦闷,很快就生病去世了。按照他“从堂兄弟”(同一曾祖不同祖父的同辈男子互称,简称“从兄弟”)的说法,“正在年富力强,前程无限的时候,竟遽尔‘作古’了”。
正如题目所示,魏连殳的精神苦闷主要是“孤独”。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首先,可以从魏连殳跟“故乡”的关系来理解他的“孤独”。
魏连殳的故乡“寒石山”是个封闭落后的山村。小说的时间背景已经是1920年代,但“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全山村中,只有连殳是出外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所谓“异类”,就是小说另一处所说的“‘吃洋教’的‘新党’”,当时专门用来骂那些不参加科举考试而去“学洋务”的人,因为他们“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呐喊·自序》)。
在辛亥革命前,“未庄”的无业游民阿Q骂魏连殳这些“异类”是“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在不知道是辛亥之前抑或之后的《祝福》中,鲁四老爷对这样的“新党”,哪怕是本家侄儿,也要当面指桑骂槐地加以攻击,所谓“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呐喊·自序》《阿Q正传》《祝福》所说的情况,正是“寒石山”村民对魏连殳的态度。
但他们同时又“妒羡”魏连殳,“说他挣得许多钱”。这就恰如应该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故乡》中豆腐西施对“我”的编排:“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大轿,还说不阔?”看来,在政治和文化上贬低一个人,并不妨碍“寒石山”村民从经济收入的角度“妒羡”此人。这里的逻辑颇堪玩味。或者,正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已经将一个人踩在脚下,这才更加“妒羡”其人的收入颇丰,因为觉得他还不配?或者因为“妒羡”其人收入颇丰,就更加要从政治文化上拼命加以贬低,以便最终使他的经济收入也不再值得“妒羡”?
总之,小说开头这一段似乎不经意的叙述告诉读者,魏连殳和“寒石山”村民之间,尽管表面上也许还客客气气,骨子里差不多却早已势不两立了。在这种关系中,“寒石山”村民可谓占尽优势,而魏连殳则立于相当凶险的境地,——他不仅在政治文化上遭歧视,被厌恶,还在经济收入上受到普遍的“妒羡”。
小说接着写魏连殳从S城回家,给老祖母办丧事。本家亲戚们趁机搬出一大堆关于丧礼的陈规旧套,逼其就范。他们原以为魏连殳既是“‘吃洋教’的‘新党’”,肯定不从,“两面的争斗,大约总是要开始的,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不料连殳只冷冷地说了四个字:“都可以的”,一切照办了。这就令主事的和围观者们大感意外。
通常以为这个细节是说,新派人物魏连殳并不像“寒石山”村民想象的那样,完全抛弃了旧的文化习俗。旧文化旧习俗的许多内容,新文化都能包容。说新文化不认祖宗成法,那是对新文化的污名化和妖魔化。
这样解释也有道理,但小说重心并不在此。作者通过这个细节,其实是想表现魏连殳在精神上与“故乡”的隔膜与对立。在魏连殳的童年记忆里,“寒石山”是否算得上“我的美丽的故乡”,小说没有交代,但成人之后的魏连殳一定像《故乡》中那位卖了祖传老屋的“我”一样,对故乡“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
精神上,魏连殳跟“寒石山”村民们本来就势不两立,现在相依为命的祖母又过世了,他跟“故乡”仅存的精神纽带更是彻底断绝。魏连殳的肉身虽然暂时回到“故乡”,精神上却完全是一个局外人,无可无不可,随人摆布也无所谓了。
果然祖母死后,魏连殳跟“故乡”再无实质性联系。到死为止,魏连殳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当魏连殳的“从堂兄弟”“十三大爷”为了霸占他在“寒石山”的旧宅,假惺惺地要把侄儿过继给他时,他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当着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面,大骂这一大一小“都不像人”!
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魏连殳对“故乡”的态度的决绝。他真正成了一个在精神上没有“故乡”的人。
这是造成魏连殳“孤独”的第一个原因,也是他的“孤独”的第一种表现,即不再有精神上的“故乡”。他的灵魂从此只能到处飘荡,沦为《野草·墓碣文》所说的那种没有归宿的孤独的“游魂”。
2
失去精神“故乡”而导致的孤独,并非魏连殳一人所有,乃是为了追求现代文明而背井离乡结果精神上再也回不到故乡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心境。
但魏连殳的“孤独”还有一项特殊内容,就是他对唯一的亲人老祖母既深深依恋又感到异常隔膜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使他始终无法跨越跟至亲者之间那一道情感鸿沟,由此失去了来自至亲者的情感慰藉,成为一个亲情匮乏的孤独者。
魏连殳很早就父母双亡。父亲去世后,本家亲戚们为了合伙抢夺他的房产,竟然逼迫小小年纪的他在字据上画押,弄得他大哭不止。所以魏连殳自幼就是被家庭和家族抛弃的孤儿,很早就看到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亲人之间残酷的争斗。命运为他保留的最后一个亲情的避风港,就是让他跟唯一的亲人老祖母相依为命。这情形就很像由蜀汉入西晋的李密在《陈情表》中所描述的,“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但两相比较,魏连殳更惨。李密后来毕竟成家立业,儿女成行,魏连殳则终身未娶,当然更无子息,真正是李密所说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再说李密祖母是亲生的,魏连殳祖母却是祖父的续弦,父亲的继母。李密只提到他的祖母年迈多病,没说精神上有什么问题。魏连殳的祖母却因为不是祖父的原配,又未生养一男半女,而且很早就守寡,所以她在魏家的地位极其尴尬,差不多等于一个低贱的仆佣。她活在魏家唯一的理由,就是把并非亲生的小孙子拉扯成人。这种生活养成了她极端沉默而孤僻的性格,时刻提防着周围一切人,不肯多说一句话。在魏连殳的童年记忆中,祖母“终日终年的做针线,机器似的”。她爱魏连殳这个从小一手带大的孙子,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爱,“无论我怎样高兴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她欢笑,常使我觉得冷冷地,和别人的祖母们有些不同”。魏连殳也爱祖母,却总觉得缺乏交流,彼此有一种说不出的隔膜。他工作之后,固然一领薪水就立即寄给祖母,“一日也不拖延”,但祖孙二人之间仍然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实际上,魏连殳“从略知世事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
小说中的“我”批评魏连殳,不应该“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魏连殳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说,躲在“独头茧”里不跟人交流的,并非他一个。祖母一辈子就是“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魏连殳的祖母首先就是不折不扣的“孤独者”。唯一的亲人尚且如此,由这位亲人一手抚养大的魏连殳,怎能不也是一个“孤独者”呢?
总之,魏连殳很早就从他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祖母身上感染了人生在世那份深深的“孤独”。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这就不奇怪,小说为何要浓墨重彩地描写在祖母大殓结束之时,当着本家亲戚们的面始终不肯掉一滴眼泪的魏连殳,竟会突然嚎啕大哭——
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咷,铁塔似的动也不动。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
对于这次看似反常的痛哭流涕,魏连殳自己对“我”解释说,“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意思是说,既然老祖母跟他一样都是“孤独者”,那他就不妨在哭老祖母时,顺便也为自己将来同样孤独的死“豫先”哭一场,反正到他死时,不会有谁再来为他而哭了。
魏连殳和老祖母是精神上有“遗传”关系的两代“孤独者”。鲁迅这样描写祖孙两代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经历的人生的“孤独”,跟李密《陈情表》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在描写孤独之苦的程度上,鲁迅超过了李密。李密写的是幼年时和祖母相依为命、共同感知、可以相互扶持的孤独,魏连殳和祖母当然也有面对村民和族人时共同感受的那一份孤独,但小说着重描写的乃是他和祖母之间彼此隔膜因而在精神上无法相互沟通、相互扶持、必须各自面对的孤独。
《陈情表》是写给君王的,在表达真情实感和终极诉求时,必须做到极致的委婉和得体。这是它的魅力所在。《孤独者》写得也很委婉而得体,但毕竟是给一般读者看的小说,可以更加无所顾忌地诉说作为表奏的《陈情表》不便诉说的更多真相。围绕“孤独”这个主题,从《陈情表》到《孤独者》,有一条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有序演变的轨迹。
总之魏连殳既失去了精神的“故乡”,还雪上加霜,缺乏亲情的慰藉。他一上场,就是这样一个双重的孤独者。
3
失去精神上的“故乡”,跟唯一的亲人又有说不出的隔膜和疏远,这是造成魏连殳一生“孤独”的心理基础,而他后来在社会上的遭遇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孤独”。具体来说,就是魏连殳在小说描写的S城的生活,最后将他的“孤独”推向了极致。
鲁迅小说和杂文中经常出现“S城”。这是以鲁迅故乡绍兴拼音的首字母来取名的,但鲁迅不肯点明“S城”就是绍兴。在写于比《孤独者》更早一年的杂文《论照相之类》中,鲁迅还故意说,“所谓S城者,我不说他的真名字,何以不说之故,也不说”。其实“不说”的理由,在别处还是有所解释的,就是不想把文学作品写得太“专化”,而想让读者可以“活用”(《答<戏>周刊编者信》)。“S城”的原型或许是绍兴,可一旦写进杂文和小说,就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不再局限于真实生活中绍兴这一地了。和杂文一样,小说《孤独者》也想将魏连殳工作的S城写成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如前所述,魏连殳并不满足于仅仅在S城中学担任历史教员,他经常写文章,“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他的议论跟他平时说话一样,“往往颇奇警”,即独特而深刻,而且“没有顾忌”,比如“常常说家庭应该破坏”。这就容易触犯众怒,被目为“异类”,陷入孤独。为什么?因为“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
所以魏连殳是满腔热忱,关心社会,却不被社会理解,以至于到处碰壁。魏连殳在S城的坎坷命运,正如他在“寒石山”的遭遇一样,就是这样被注定了的。尽管他是从“寒石山”和S城走出去的,在外面或许总要自称“寒石山人”或“S城人”,但现在既然又从外面回到了“寒石山”和S城,那就必然会因为眼界和意见相左,而饱受自己故乡“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衰落之邦,好不容易培养出若干俊秀之士,因为不合衰落的胃口,就只能“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这似乎也是某种历史的必然,而魏连殳就做了这种必然的牺牲品。
这里不妨简单说一说S城和“寒石山”的关系。两地之间的距离,“旱道一百里,水道七十里”,但既然魏连殳可以每月给祖母寄钱,邮路应该早就开通,说不定也有《风波》里航船七斤那样的“出场人物”,每天来往于城乡之间。总之“寒石山”和S城还是可以互通声息的,像S城的《学理七日报》《学理闲谭》以及隔壁山阳县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之类的新闻报纸,说不定也会流传到“寒石山”的有钱人家。S城人知道魏连殳在“寒石山”的所作所为,“寒石山”人知道魏连殳在S城的事,也就毫不奇怪了。在舆论上,这城乡两地早已连成一气,“寒石山”人以魏连殳为“异类”,为“‘吃洋教’的‘新党’”,S城人又何尝不是这么看魏连殳的呢?他在荒僻的“寒石山”不宜乱说乱动,在表面上似乎稍微开化一点的S城,难道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魏连殳当然知道这些,所以他有时也懂得掩盖一下自己的热心肠。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经常忍不住又要流露出来,结果他“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喜欢管别人的闲事”。这种忽冷忽热的脾气,令不熟悉他的人望而生畏;而他一旦被人摸清了底细,又很容易上当受骗。
比如魏连殳的那班似乎很能谈得来的青年朋友,就都是摸清了他的底细,摸透了他的脾气,跑到他这里来混吃混喝的。这些年轻人也算是受到了“五四”新文化的熏陶,身上不免都带有一些新文化的气息。比如他们因为读过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就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零余者”,喜欢“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表面上看来,似乎很能够和魏连殳同命相怜,其实不然。
鲁迅这样写,当然不是嘲笑郁达夫及其小说集《沉沦》。《沉沦》1921年出版,1922年周作人就发表评论文章,驳斥社会上对《沉沦》的攻击,高度肯定《沉沦》的成就。文章出自周作人之手,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鲁迅的意见。《孤独者》写于1925年10月,而鲁迅早在1923年2月就在北京的家中与郁达夫见了面,两人从此一直保持亲密关系。小说《孤独者》提到《沉沦》,主要是看不惯用《沉沦》做幌子来装模作样的文艺青年。他们只是感受到新文化的一点皮毛,对魏连殳这样的新文化第一代倡导者和实践者并无真正的理解和同情。以魏连殳的见事之明,他何尝不晓得这些青年的底细,但即便如此,他对这些青年人还是十分喜爱,十分宽容,始终待若上宾,从来不觉得厌烦的。
然而等到魏连殳被中学校辞退,在金钱上一向不注意积蓄的他,顿时就窘迫起来,昔日那些围着他打转的“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很快跑得无影无踪。魏连殳过去总是高朋满座的客厅,后来就变成无人光顾的“冬天的公园”了。
这是写魏连殳在“新青年”中感到的“孤独”。
小说还花了不少笔墨,写魏连殳虽然自己没孩子,却非常喜欢房东家“四个男女孩子”。在叙述者“我”看来,这些孩子“大的八九岁,小的四五岁,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的可以”。不仅如此,他们还“总是互相争吵,打翻碗碟,硬讨点心,乱得人头昏。但连殳一见他们,却再也不像平时那样的冷冷的了,看的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只要有他们在,魏连殳的眼睛里就“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他还耐心地开导对孩子的天性有所怀疑的“我”,说“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这不仅是“救救孩子”的思想,也是魏连殳热爱中国、希望它好起来的一份真挚情感。因为“我”不肯被他说服,继续怀疑孩子的天性,魏连殳甚至“气忿”了,三个多月不再理“我”。
但魏连殳后来还是跟“我”和解了,因为他告诉“我”,“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这是三个多月前创作的《野草·颓败线的颤动》的一幕,鲁迅把它又用在这里了。
总之,给魏连殳造成伤害、带来失望的,往往就是他所敬重的青年,和他所宝贝的孩子。离开这些青年和孩子,他只能又躲进那可怕的“独头茧”里去了。
当然最令他痛苦,使他彻底陷入孤独和自我封闭的,还是他最后因生活所逼,放弃原则,向社会屈服,做了军阀杜师长的幕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已经真的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胜利”是从世俗角度说的,“失败”是对照自己一直坚持的做人准则说的。这种矛盾和痛苦,他无人可以诉说,因为每天与之周旋的只是那些“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他在这样的热闹中当然倍感孤独,千言万语,只能闷在肚子里,一个人慢慢消化。
魏连殳在写给“我”的信中,还提到一个神秘的人。他说“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这人是谁?小说一笔带过,此外并无任何交待。
也许,这就是魏连殳的祖母,她当然愿意孙子长命百岁,而她自己也确实活得很艰难。但小说明明又说魏连殳的祖母是得了痢疾而老死的,而且“享寿也不小了”,谈不上“被敌人诱杀了”。
也许,这是魏连殳的没有出场的异性爱人,魏连殳就是为了她而终生未娶。
也许,是号称要给魏连殳找工作却一直没有结果的“我”。在魏连殳看来,“我”出于同情,愿他多活几天,而且魏连殳担心,“我”恐怕跟他一样,也到处碰壁,几乎就“活不下去”。但他怀疑“我”跟他“究竟不是一路的”,“我”迟早要跟这个社会同流合污,这在魏连殳的眼里也就等于死了,等于被《我之节烈观》所谓“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谋杀了:正如他自己一样。他从一个“议论颇奇警”的人变成《学理七日报》上的那些无聊的诗文所恭维的“连殳先生”、“连殳顾问”,不就等于从活人变成了死人吗?
但这些都是推测。这个神秘的人是谁不重要,读者知道他或她是魏连殳唯一挂念的人就够了。这人一“死”,魏连殳就觉得可以不必再为理想而活了。从今往后,他活着不是为了所爱,倒是为了所憎,“偏要为不愿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联系鲁迅在《坟·题记》中类似的表述,魏连殳这句话的意思就并不难理解——
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魏连殳活到这个份上,当然不是他所愿意的。他做杜师长顾问,也并没有跟他们沆瀣一气,为非作歹。但他那忽冷忽热的脾气确实更加古怪了(他变得更加挥霍无度了;他一改过去的谦逊恭敬,竟然称也是寡妇的房东老太太为“老家伙”,居高临下地赏她点东西;他送给孩子们礼物时,甚至恶作剧地要他们“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但是,古怪的魏连殳不会真的去伤害别人,更不会像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的“工人绥惠略夫”,因为爱人,结果变成憎恶一切人,疯狂地报复全社会。魏连殳没有变成向一切人开枪扫射的“工人绥惠略夫”,他只是在孤独的煎熬中,暗暗地伤害他自己。
鲁迅在杂文《忆韦素园君》中说,“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魏连殳的死,就是一个“认真”的“孤独者”慢慢“啮碎了自己的心”的结果。
4
纵观魏连殳的一生,最初“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这使他特别留心察看“世人的真面目”,从而养成冷峻、孤傲而忧伤的性格。此后竭全家之力走出“故乡”,进“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具备了一定的新思想,不料这就竟然是他不久便隔断与“故乡”的精神联系的起因。尽管魏连殳是以内心的决绝代替了外在的冲突,但他对于“故乡”的这种无声的告别如此彻底,以至于在他的意识中竟从未片刻闪现过“我的美丽的故乡”的回忆。
他由此成了失去“故乡”的孤独的“游魂”,这其中又包括他对同样是“孤独者”的唯一的亲人的永难消除的隔膜与疏远。带着这样的经历和心性走进教育界的魏连殳,自然是以真率与热忱换来冷漠和倾轧,最后甚至丢了饭碗。
在这过程中,他还失去了对于青年、少年和孩童的爱的信念,也几乎没有找到一个同志和爱人。在彻底的失败中,他孤注一掷,隐身官场,试图像史涓生那样,“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先导”。他这样做,是想努力“活下去”。但他并不能真的“遗忘和说谎”。他终于还是一块“火的冰”。他只能在全然陌生、全然隔膜、全然厌恶、全然孤独的官场中沉沦,慢慢地“啮碎了自己的心”,“冻灭”了他的“火的冰”。
从魏连殳的结局,大概就可以看出《狂人日记》小序所谓“狂人”后来痊愈、“赴某地候补矣”的一种可能吧。
《孤独者》和它的姊妹篇《在酒楼上》一样,都采取了未完成、开放式结尾。《在酒楼上》的“我”离开牢骚满腹、穷困潦倒的吕纬甫,“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我”为何感到“爽快”?因为终于告别了吕纬甫这个喋喋不休的倒霉的朋友?还是觉得自己可以不至于重蹈他的覆辙?这似乎都很难说。
被魏连殳怀疑为“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叙述者“我”,在见证了不算朋友的朋友的奇怪的“大殓”之后,一个人走在月光中,这里有一段经典的描写:
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里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
问题是“我”果真觉得自己“冲出”了魏连殳的阴影,“心地就轻松起来”了吗?魏连殳何以会变成“孤独者”,从小说的前后叙述大致可以看出原委。但魏连殳为何非要一步步陷入绝境,他是否也可以从“孤独者”的处境“冲出”?对这一点,小说并无丝毫的暗示与启迪,因此这样的结尾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毋宁说只是表达了“我”的一种愿望而已。“我”不想变成魏连殳第二。但“我”的结局如何,又岂能仅仅取决于“我”的主观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