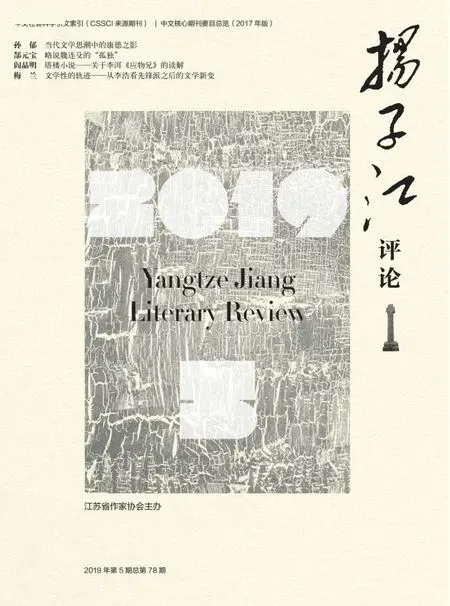残酷青春背后的人性审判
——读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齐 红
台湾女作家林奕含的长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主人公房思琪被家教老师李国华长期性侵,终因不堪承受心理压力,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而小说的作者林奕含也因类似经历留下的阴影,一直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在小说出版两个多月后(2017年4月),于家中卧室自缢身亡,青春、美丽、爱与写作全部在26岁的年纪戛然而止。
的确如一些评论者所言,林奕含以她杰出的文学才华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这其中最具震撼力和冲击力的就是性暴力给女性带来的重创和阴影。我在阅读中情不自禁地联系着现实事件,本能地将批判词汇抛向加害者,对受害者则生发无尽的惋惜和心痛。但是,如果我们回归理性,仔细梳理小说中主人公的心理历程,你会发现,如上简单的道德评判已经不足以显示悲剧的本质,更令人心痛的事实是,我们在“施暴”与“受害”这个特殊的关系场域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波荡。房思琪的悲剧是各种力量加持、不断让恶与失控发展壮大并走向极端的悲剧,这个加持力量中也包括房思琪本人。具体地说,这个小说绝不只是关于男性、老师、家长、社会的审判,还有对房思琪本人的审视,以及作者林奕含的自审,在这个意义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显示出它更为出色的一面——它想要努力抵达的,是一场更彻底的、关于人性的大审判。
一、青春到底有多残酷?
林奕含自杀前8天曾接受台湾一家媒体的采访,留下了一段15分钟左右、阐释这部小说的视频,其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这个观点听起来虽有些夸张,但以房思琪为个案,却带有相当普遍性的、已曝光或被遮蔽的性暴力行为,的确构成了少女们“残酷青春”中最具杀伤力的记忆。而对于“文艺少女”房思琪而言,她的青春之“残酷”意味则更发人深思。
首先,作为一个极具文学天赋、聪颖敏感的女孩,房思琪在被侵犯和强暴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理性审视的企图和努力,这个特点必定会让她感受更多、内心更痛、伤口更深。
从十三岁开始遭遇语文家教老师的性侵与控制,直到十八岁考大学前精神崩溃住进医院,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房思琪一面一次次被老师带进公寓、小旅馆、私人别墅,一面不断回想并记录下所有那些混乱、不堪、罪恶、羞耻与疼痛。她的日记本因此成为集感性的情绪渲泻与理性的人性分析于一体的奇特文本。
一个施暴者和一个受害者之间通常存在着“权力”的悬殊与不对等,而“权力”落差包含诸多内容:力量强弱,地位高下,年龄长幼,财富多少,资源多寡……在与房思琪的关系中,李国华无疑占尽优势。三十七岁的年龄差,家教老师,父母信赖和感恩的好邻居……李国华身上的这些“关键词”使得受害者完全无力与之进行任何意义上的抗衡,主动性,掌控权,身体力量,道德强势……房思琪一开始就注定极其弱势。第一次有如恶梦,所有的本能反抗都变得微弱无力,房思琪甚至分不清是恐惧、讶异、震惊、慌乱,几乎是不由分说地,她在日记中记录道:“他硬生生地将我翻面。”
在无力改变事实的前提下,房思琪必须为自己找到一条承受、忍受强暴的借口——她不断说服自己,让自己“爱上”老师,只有爱,才可以缓解与此相关的罪恶和羞耻感,她需要这种关系中有“爱”的成份:“我要爱老师,否则太痛苦了。”因为“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是可以的。不是么?”日记呈现出房思琪作为一个受害者默认强暴行为的心理逻辑,但日后她又用红色字体在日记旁边作出了如下批注:“为什么是我不会?为什么不是我不要?为什么不是你不可以?”(《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第24页。以下出自小说的引文均只标注页码)
畏惧、羞耻、压力、“爱”的幻觉、自我说服、自我麻醉……所有如房思琪一样有过被性侵经历的女孩一再默认并忍受暴力的实施可能都无外乎这些心理,以至于这些创伤体验越积越多,最后让她们不堪重负:“她身体里的伤口,像一道巨大的崖缝,隔开她和所有其他人。”房思琪的精神渐渐出了问题:健忘、记忆断片、失眠严重,睡着的时候也全是恶梦:梦里的自己总是被侵犯、被强暴,“从十三岁到十八岁,五年,两千个晚上,一模一样的梦。”(第83页)如心理学专家所说:性暴力、性虐待是最容易导致抑郁的创伤——压力与抑郁断送了房思琪的青春。整个过程中,她所有的沉重都无处倾诉,“日记”就是唯一的倾听者,我们在日记中看到了一个时而感性、时而又用惊人的理性自我剖析的少女,她的青春之舞因疼痛、扭曲而呈现出骇人的面目。
其次,对于一个沉迷文艺的女孩儿来说,青春呈现出更具“残酷”意味的一点在于,房思琪不断赋予这场扭曲关系以“文艺”的迷人面纱,使得她自己无比痛苦却又不断沉沦、内心排斥却又不断进入,终至于嗜毒成“瘾”——这也让一个文艺老男人对一个文艺少女的强暴与践踏显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影。
在李国华不断得逞的性暴力实施过程中,“文学”、“博学”、语辞美感对痴迷文艺的房思琪构成了巨大的蛊惑。两位少女最初确立信任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这是“一个整篇背诵《长恨歌》的人”,接下来的交流、交往中,李国华更是借助自己非同一般语言修辞能力展示着个人的“魅力”,导致房思琪不由自主地在这些话语中迷失、迷乱。侵犯、暴力、占有在李国华这里统统被他用语言艺术包装成了“爱”:“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小天使”,“你能责备我的爱吗?”“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师节礼物”……夸奖房思琪的作文是:“我从不背学生的作文,但是刚刚我真的在你的身上尝到了天堂。”看着淋雨后的房思琪说:你现在是曹衣带水,我就是吴带当风。(第58-67页)……
“话语”成功实施了“诱奸”,房思琪在“不堪”中沐浴着文艺之“美”。
即使是不那么“文艺”的晓奇,也在李国华的“甜言蜜语”中最后沦陷,死心踏地地“爱”上了老师:“你是从刀子般的月亮和针头般的星星那里掉下来的吗?你为什么这么晚到?我下辈子一定娶你,赶不及地娶你走,你不要再这么晚来了好不好?……”类似的话语重复多遍以后,晓奇不仅接受了这种性关系,而且还在被抛弃之后哭诉着请求复合,表达着自己专一不二的爱情——一个青春少女的可怜、可悲令人心痛。
比晓奇更“文艺”的房思琪自然中毒更深。李国华抓住了房思琪的这一弱点,在实施话语诱奸方面可谓老谋深算:“告诉她她是他混沌中年的一个莹白的希望,先让她粉碎在话语里……让她在话语里感到长大,再让她的灵魂欺骗她的身体。”(第43页)
诗、诗意、文艺性为性暴力做出了浪漫的伪装,房思琪变得甚至有些离不开这种关系了:她在可以不去李国华家的时候主动送上门去:“隔天她还是下楼……”(第56页)、“隔天还是拿一篇作文下楼……”(第66页),约定时间未到之时,坐在咖啡厅的房思琪甚至有隐隐的期待和等待……
这个“主动”性中包含着一个文艺少女复杂的人性状态:一方面,语辞本身确有一种审美的诱惑力,在房思琪的社交圈内,有能力与她进行文艺对话的只有两人:伊纹和李国华。而前者有家庭之困,房思琪只有不断走向后者;另一方面,这个文艺少女在潜意识里把这种特殊关系——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当成自己阅历、体验文艺的一种渠道或方式,她不断走向李国华是对这种“恶”与“痛”体验的主动猎取与积累——怕着,又沉迷着,生命因此变得可怕却丰富。就像林奕含在小说中的剖析:“没有人看得到她对倒错、错乱、乱伦的爱情,有一种属于语言,最下等的迷恋。她身为一个漂亮女生,在身为老师的秘密的之前。”(第105页)这种“错乱”、“混乱”导致房思琪的青春在其“残酷”性中包含了更为复杂和耐人寻味的质地。
二、“身体”究竟意味着什么?
确切地说,我想经由林奕含的小说梳理并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施暴”与“受虐”引发的男女关系中,“身体”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意味?
传统女性的“身体”意识与身体主张基本可以用三个词汇去描述:压抑、被动、沉默,那些贞德女教中出现的“身体”故事与身体行为多半综合着暴力因素与“他者”主张:断臂名志、取血调羹、自杀守节……女性对身体的“处置”看起来是“自我”的,实质完全是传统道德教化下的“不由自主”。
所以,女权主义理论家们一度孜孜以求的,就是一种“唤醒”的努力——唤醒女性对于身体的感知、意识、觉悟,并由此生成对自我身体的正确与自愿主张。吉尔伯特和古芭说:女性写作者必须努力杀死那些别人创造出来的“天使”和“怪物”,说出“我”究竟是什么,埃莱娜·西苏说:“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归根结底,这些女性主义理论、批评和创作者们想要共同完成的,是对女性“沉重肉身”及其真相的认知与呈现。
因为“女性和身体的奴役曾连接在一起,那么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的联系是合乎逻辑也合乎历史的”。但在通往解放的道路上,“身体”的意味与意义在女性书写中一直显得茫然、嘈杂,充满困扰。
较为集中且具有冲击力的“身体书写”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私小说”领域。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陈染在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中也表现过“性侵”题材。加害者与被害者同样是师生关系:班主任T老师对主人公倪拗拗先是语言与态度的“暴力”、“贬抑”,后是身体上的侵犯:抚摸、拥抱、亲吻直至强暴。于小学和高中时的倪拗拗而言,所有这些行为都带着令人恐惧并恶心的进犯性质,但在被强迫的过程中,她惊讶地发现了“身体”的秘密:“他的姿势是一道闪电,使她吃惊,使她疼痛,使她发现自己身体上还有着另外一个她不知道的嘴唇在呼吸和呻吟,……他冲进了她身体内部的虚无之中,打断了她的模糊的沉睡,他把它丢进她生命的沟底。”(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对身体的侵犯是可怕的、极具侮辱感的,但这暗黑体验中划出的一道闪电却是“肉身”的苏醒。在陈染、林白们的笔下,这具“身体”是熟悉的,但它又如此陌生,夹杂着它本身的张力和欲望,尤其是当这种生理的愿望首先经由一个压迫者和性侵者来实现时,痛苦、纠结、矛盾、奇怪的困扰和沉重的负罪感同时产生。
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倪拗拗而言,“身体”是“禁忌”,但也正在突破“禁忌”,并被她们用作反叛的载体和工具。她对T老师毫无爱意可言,T带给她的记忆也都仅仅指向恐惧、压抑与沉重。在遭遇性侵的过程中,倪拗拗最初只能在内心深处用语言和想象向T老师复仇:大声说出“私部”,以“抚摸”去反抗抚摸——但一切仅止于幻觉。长大以后倪拗拗发现了T老师对自己的“爱意”,看到他被折磨出“疼痛般”的样子,怜悯与快意同时产生。借他实现身体的“经验”,并以这具“被魔鬼的快乐所支配的肉体”完成对T老师的驾驭和复仇,是她潜意识中对身体的定位。
于女性书写者而言,“身体”从来不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物质属性的“肉身”,而是一直综合着精神的属性:出于认知,出于反叛,即使是出于工具性的需要。唯一的问题在于,这种“身体”书写被消费社会和市场利用,常常被单纯解读为一种“符号”而已。
与男性不同的是,身体的原罪感在女性这里从未消失过。大学期间遇见自己喜欢的男生尹楠,收到表白的倪拗拗有些自惭形秽:“你不了解。你不知道我曾在欲望面前多么的无耻。”同样的,三十年后,房思琪的反应与倪拗拗有着惊人的相似:“你要一个好男生接受我这样的女生——就连我自己也接受不了自己?”(第106页)
于女性而言,“身体”与欲望仍带有罪恶标记——房思琪是如此,她最好的朋友刘怡婷是如此(知晓秘密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好恶心!”),林奕含也是如此(她本人的美好婚姻未能让她超越和解脱)。但在李国华那里,罪恶感几乎没有,即使偶尔出现,也可以轻松地被成就感、满足感以及罪名转嫁快速消解。他往来于台北(工作)和高雄(家庭)之间,在外越是混乱放纵,在家越是对老婆和女儿宠爱有加。小说分析他的心理是:“老婆是稻壳,思琪是软香的熟米,是主食,在台北的思琪越是粘他,他越是要回高雄送礼物,不是抵消罪恶感,他只是太快乐了。”(第136页)事情暴露之后,在妻子面前,李国华更是虚伪、猥琐地将所有罪责推到了女孩子身上,洗白自己:“是她在诱惑我,我没能自控……”眼泪、悔恨、自残的举动,足以让同样具有女性身体原罪意识的妻子相信并原谅这个男人的行为。房思琪疯掉以后,另一个花季少女又等在房间里,李国华永远不缺他想要的女孩,而房思琪尽管特别,也不会成为他停留的驿站。法律奈何不得他,道德又没有对他构成压力,李国华们可以继续横行于世。
综合着历史的、现实的各类因素,“身体”在女性这里呈现出物质与精神、符号与意义、保守与激进、传统与现代的混杂意指,而观念的嘈杂导致女性的自我把控与价值判断也变得矛盾、混乱、游移,以至于在被侵犯的过程中,作为女性的当事人经常在施暴与做爱,占有与施予,纵欲与逍遥之间边界模糊、迷惑摇摆,这种混乱无形中将自己推向了更严酷的处境。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不止一个情节和细节表现出女性的这种游移与摇摆:房思琪问李国华“她之于他究竟是什么呢”?后者回答是“千夫所指”。背负着“千夫所指”在大街上牵住自己的手,房思琪脑海里突然冒出“天地为证”一类的句子,但身体上是老师的印记,手背上有老师的手形,“千夫所指”可以被置换成“千目所视”、“千刀万剐”——语辞的变换间,房思琪之于这种关系的价值取向及内心迷乱可见一斑。
倪拗拗和房思琪最后都患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症,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暴力侵犯状态下的“身体”,女性仍然无计可施,又缺乏深度的探究和理性的认知,从而面临着无可逃脱的割裂感?
三、心灵该如何得到救赎?
美与爱、诗与歌、自由与幸福、女性和男性……世间的许多美好是否还在?能否纯粹?如何获得和抵达?最终,我在林奕含的小说中读到的,是对如上问题的追问,以及追问后不可救治的幻灭感。
房思琪在爱情故事中看到了悲观与绝望。在所有人眼里,许伊纹和钱一维的爱情与婚姻更像是一场完美的童话:前者光是坐在那里就是一本“迷你言情小说的封面”,“美得飘飘欲仙”,并且,热爱文学和阅读,比较文学专业在读博士,学养与气质都是一流;后者拥有无可挑剔的家世与背景,同样“端到哪里都赏心悦目”的外貌,美国式的绅士派头却又毫不自大……但就是这个“笑起来满脸涟漪”、“看着他眼睛就感觉他会承诺你一座乐园”的男人,竟会在婚后不久便开始家暴,把柔弱、文静的许伊纹打得遍体鳞伤。虽然也会在妻子怀孕后表示悔过,但终究本性难移,又一次暴力殴打令伊纹失去了腹中的孩子,也彻底葬送了两人的感情。伊纹的内心在婚姻中被毁坏得千疮百孔,难以修补。
房思琪在家教老师那里看到了社会的阴暗与污秽。这些灵魂的工程师们,面对着压力之下补习功课的女孩子们,脑海里掠过的念头却是如何占有、怎样俘获。“来者不拒”的英文老师嘲讽“几年不换”的物理老师,即将“大满贯”的数学老师在数字上比拼着英文老师,语文老师李国华则沉醉并得意于自己“诗性的诱奸”,认为其中包含别人不能理解的“美感”:“英文老师不会明白李国华第一次听说有女生自杀时那歌舞升平的感觉。心里头清平调的海啸。”(第45页)他们各自假“补习功课”之名,行占有狎邪之实,“家教老师”的形象在房思琪眼中全面沦陷,他们就是一群没有廉耻、不断寻找猎物的自私、猥琐的中年男。
房思琪同样在亲朋好友那里感受到了孤独、拒绝与距离。父母、密友、老师……房思琪试图伸向他们的求助之手统统缩了回来,只是稍稍谈及这个话题,她听到的就是讶异、不齿和反感。晓奇父母的态度基本上代表了所有中国式家长:你跟这种人乱伦;你伤害别人家庭,你跟一个老男人性交,你以为还嫁得出去?!(第173页)伊纹觉察到了问题,她“隐约感觉思琪在掩盖某种惨伤,某种大到她自己也一眼望之不尽的料疮。可是问不出来……伊纹才感觉思琪对这个梦幻中的创伤已经认命了。”(第140页)在只有两个人的车上,沉默良久的房思琪最后还是表示“没办法讲”。隔绝、孤独、自闭、自我承受与消化——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精神的崩溃几乎是一种必然。
这就是房思琪眼中的世界,无可逃脱的世界,她在电话中向伊纹哭诉道:“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我好失望……这个世界,或是生活、命运,或叫它神,或无论叫它什么,它好差劲……”当她住进精神病院后,好友怡婷发现她在日记中曾记录过这样的想法:“其实我第一次想到死的时候就死了,人生如衣物,如此容易被剥夺。”(第182-184页)向死之意早已滋生,并且会不断蔓延,但究竟该对谁发出指控呢?房思琪不无悲哀地想:也许我才是所有人中最邪恶的一个。
在酷爱文艺的房思琪、伊纹这里,她们曾经寄希望于用书籍完成心灵的自我救赎。“书”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频繁出现的一个意象。房思琪、伊纹、刘怡婷的家里都有大量的藏书,前两者的收藏、阅读与品味更是非常高端,一度她们聚会的快乐与享受就是朗读经典:按年代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可以脱口而出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名字,一起爱菲茨杰拉德,用莎士比亚擦掉眼泪和不快……房思琪的梦想是“当作家”,她一度认为书写可以找回“主导权”,当写下来的时候,“生活就像一本日记本一样容易放下”(第167页)。
但在具体的日常现实面前,房思琪和伊纹的救赎梦想遭遇了惨败。仅就降临的残酷“身体”现实(性侵和家暴)而言,所有来自于阅读和书写的救赎都显得苍白、无力、无用了。
小说最后的场面是,一众邻居又在聚餐:围坐的是圆桌,体会的是圆满,一屋子充斥着欢乐祥和。三个不在场的女性(房思琪、刘怡婷、许伊纹)仍是他们的谈资,只是那些毁灭和创伤在他们嘴里都是不屑、轻薄和嘲讽——错在她们自己,“读文学读到发疯”是怪不了别人的——某种意义上,这个场景是对文学救赎意义的再次消解。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堪称杰出,可惜林奕含本人却没能借助文学和写作超越伤痛,获得救赎。这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生出更多疼痛和遗憾。林奕含虽然离开了,但她的作品会永远存在:我相信,在她无法完成自我拯救的地方,会有人借助她的书写走出黑暗。
【注释】
①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李银河、冯唐等关于本书的推荐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3页。
②《台湾作家林奕含生前最后的采访完整版视频曝光》,https://v.qq.com/x/page/u0501etqr2s.html
③祝卓宏:《林奕含自杀了,梅莉为何活了下来》,《健康报》2017年9月8号006版。
④[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页。
⑤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⑥[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