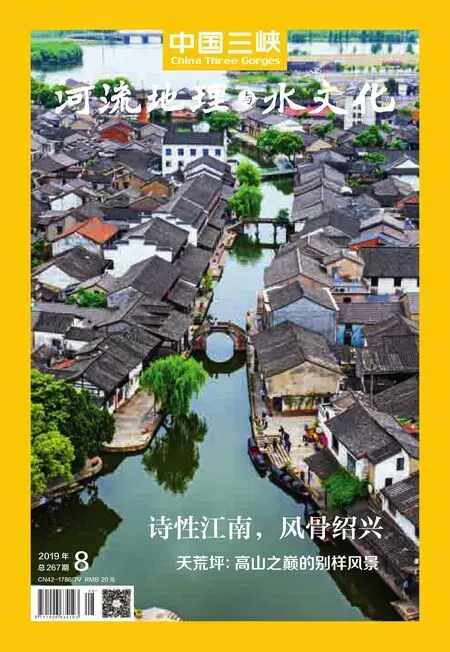外余祥
◎ 文 | 伍绍东 手绘 | 刘宁 编辑 | 孙钰芳

1
余祥,李顶武,张博也,饶之美,朱奇武……我故乡的这些村庄,全都是祖宗的名字。以祖宗为名,村子就有了生命;以开发商为名,小区终究是商品。
回头看,我好像对自己的村庄,很不熟悉。我甚至不知道它存在了多少年。说来奇怪,离我们很近的两个村庄,我居然一直没去过,一个叫柯如竹,一个叫李能俊。
那些村庄,一个比一个美。南方雨水充足,地里随便挖个坑,就会形成池塘。一个村庄,至少有一方大池塘,因为,女人必须早晨洗衣服,小孩夏天必须游泳,男人年底必须摸鱼过年。
回想自己这四十年,城市里二十年的岁月,几乎没什么珍贵的记忆,显得荒芜而粗糙。相反,那遥远的农村生活,却弥足珍贵,意味深长。
起初,我的全部世界,就是我的村子,边界是村外的自留地。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自留地里摘菜,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心爱的花碗丢在地里了,哭着喊着要去寻回。
家里外墙有一半是青砖,有一半是土墙。我爱土墙,因为春天可以在墙上掏蜜蜂。蜜蜂喜爱钻洞。四岁的我是个中高手,会提前准备好用完的雪花膏瓶,里面放些油菜花,再折一截细细的杨树枝,就可以掏蜜蜂啦!
其实不是掏,是挠。力道要轻柔,蜜蜂觉得痒了,就会吱吱叫,往外扑腾,这时候,我的雪花膏瓶子早准备在洞口了。
2
余祥、李顶武、张博也、饶之美、朱奇武、刘桂、柯如竹、李能俊……故乡这些村子的名字特别美,可见祖先一定特别美。
事实上,这些村子也特别美,池塘,麦田,油菜地,乡间小路,橘子树,意杨树,大江在侧,简直是天赐的家园。
土话里,村子不叫村,叫垸,念湾,意思是弯弯曲曲的村子,比如外余祥垸,弯弯曲曲卧在两条大坝之间。垸,不是水之弯,而是土之弯。安东尼奥·高迪说,直线是人为的,曲线才是上帝的,大概说的就是村子吧。垸,从第一位祖先定居,建造房子,繁衍后代,再分家建造房子,依着大地的纹理,弯弯曲曲地生长。这样的垸是活灵活现的。
传说余祥公是第一祖,祥公的某位儿子翻过坝,开创了另一座垸,人称坝外余祥,简称外余祥。我就生长于外余祥。二祖生四子,成为本垸村民的主要发源,人称“老四家”。老四家后裔,在村里是有地位、有权势的。
我的父亲是外姓,母亲是本姓。因此我家总有一种处于边缘的感觉。本姓人觉得我家是外姓,但若回到我早逝的祖父的故乡——梅川伍家楼,又认为我是外地人。因为这种边缘的感觉,我读书的时候,找到了一位知己,即思想家以撒·伯林,俄罗斯人说他是德国人,德国人说他是犹太人,去了英国,英国人又说他来自敌对阵营——苏联,伯林说自己常常活在边缘。
3
我喜欢那些自然而然长出来的东西。比如村庄的名字。
刘伯温说我们广济县“八百年前一堆沙,八百年后千万家,再八百年后沙还沙”,之所以是沙,是因为广济县以前属于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有巨大的沧浪湖,又叫沧海(如今只剩武山湖、太平湖等剩山残水了)。嗯,就是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地方。后来水渐消,湖渐退,露出沙地。有那么古早古早的几个人,李能俊,余祥,柯如竹,刘桂等一伙人,来到长江和大湖之间的沙地,开荒种地,筑屋围院,结婚生子。儿子长大成人了,就得分家,在老屋附近,顺着地势再盖几栋。村庄弯弯曲曲得可爱,小路也弯弯曲曲得令人销魂,村庄,就这样开始成长了。为了纪念父亲,过路人问起村子名字,此地就以父之名称呼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有些村庄的名字,可能是路人给起的。比如二里半村,估计是路人问地里种庄稼的村民:“这地方到叶家垴有多远啊?”“二里半。”
有些村庄村口有棵大樟树,村子就叫樟树下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很美好的事。
4
在《纳尼亚传奇》第一季里,一开始能通过魔衣橱进入纳尼亚世界的,只有最小的露西。我小时候的村庄,其丰饶其奇幻,不亚于纳尼亚。可是现在,我再也进不去了。
如果你家有孩子,你会悲哀地发现,孩子上小学的时候,甚像纳尼亚人;而一过十二岁,他(她)就再也进不去魔衣柜了。

那时候晚上有满天的星星!并非杂乱无章的,我记得那些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后来得了近视,我再也看不清星星了。
黄广大堤两边斜坡上,野草丛生,蝴蝶和蜜蜂飞行其间。我拿着父亲的一本《广济中草药》,去草丛里找草药:八根草,灯笼草,野豌豆,薄荷草,紫苏……父亲给我总结:百草都是药。
我在雨后会特别忙。一是去池塘的洗衣板底下捞螺蛳,一是在门前雨水冲出来的沟里建造大坝,一是到树上捡树油。树油像琥珀,形状各异,我拿树油在桌子上摆造型。
小时候我们像猴子一样在树上爬来爬去。前年我在师大秋水湖边看到一棵树,其形状甚好,一下子,久违的爬树的欲望被勾起,我抱着就想往上窜,不料硬是登不了一毫米。
5
小时候,故乡方圆几里地太过于丰富,我常常在外面玩得流连忘返:开春去河边放野火,夏天在树丛间打仗,秋天躲到橘树林里捉迷藏,冬天跑雪地里寻野兔,常常会听到母亲的呼唤:“东尔——细弟——”不管情愿不情愿,我得回家。
有一年大三回家,爱云的姨(湖北武穴方言,姨就是母亲)得病走了。爱云跟我一般大,已经出嫁。妹妹亚云小一些,在放声痛哭。母亲叹气说:“以后,亚尔放学回来就没有姨叫了。”
母亲的话如在昨日。如今我回老家,也没有姨叫了。
后来读书读到《人间词话》,静安先生说:《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
我会在上班的路上,起风的时候,用陈琴老师的调子唱《蒹葭》,就仿佛被唤起。那调子仿佛是小时候母亲的呼唤:“东尔——细弟——”
什么是艺术教育?《蒹葭》即是。杨老师在《斯文》课里讲述道:艺术家截取人间万象的某个片段,让你停顿一下,风人深致一下,短暂地拥有了摩耶之幕之外的视野。
“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莫去追问《蒹葭》是写爱情,写政治,还是写求才不得,等等,《蒹葭》就是村庄里母亲那一声呼唤。
6
我大概在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带娃。
大舅有三个儿子,我有三个表哥。细表哥结婚后,大舅舒了一口气,似乎人生任务完成了一半,接着就开始为他还没出生的孙子想名字。大舅掐指一算,估计会有五个孙子、两个孙女。

大舅掐指算的时候,已经给孙子们起好了名字,叫“开建新中国”,孙女不那么重要,是后来临时起的名字,一个叫春燕,一个叫露。春燕者,余家新燕啄春泥;露者,颇像小林一茶的俳句: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
后来的故事,居然完全按照大舅的计划发生着。对此事,我一生都百思不得其解。
我奶奶身体一直不好,又嗜好打麻雀牌,据说是个中高手,忙,所以没怎么带我。我是外婆、表哥和表姐带大的。雪娥表姐疼我,总往我家跑,老远就喊“东东哥哥”。姐说唱的声音,像“东东格格”,煞是好听,姐还带我跟她一起上学,她把我藏课桌底下,她站起来回答老师提问,我在底下看各种各样的脚。
所以,带着报恩的心态,五个表侄出生后,我哥和我就开始帮忙带娃。我哥上初中忙,后来我就主带。
7
故乡的长江边上,有一片天然沙滩,因为偏离城镇,罕有人至。以前天气好的时候,我带大侄女兰兰和她的小伙伴,在黄广大堤上散步,最远会走到这片沙滩。后来,二侄女和小侄子先后降临世间,我依然带他们去这里,一片堪比普吉岛的天然沙滩。
兰兰会缠着我问问题。孩子总是喜欢纠缠不休:要么喜欢一样东西,不停地说“再来一次吧”;要么不停地提问,仿佛天眼大开。比如兰兰一到黄广大堤上,看到蓝天白云,会问:
细爸爸,天为什么是蓝色的?
看到绿树成荫,会问:
细爸爸,树为什么是绿色的?

到沙滩上,我告诉她眼前的滔滔江水,名字叫长江。兰兰望了会儿,说:
细爸爸,你得告诉我长江整个的样子。
这让我停顿了一下,因为她的神态,有点像“桐叶封弟”里那个弟弟问他哥哥的样子。他哥哥是周成王,很庄重地告诉弟弟:“弟问何为朋友之交。朋友之交,乃生死之交。”
于是我拿起一根树枝,在沙滩上给兰兰画长江的样子:源头的沱沱河,沿着横断山脉的金沙江,被玉龙雪山强阻后掉头向北,拥抱着众蜀山,接纳众蜀水,然后即从巴峡穿巫峡,然后到武汉,到我们眼前……
那年大概是2003年前后,兰兰四五岁。如今,已经快十年没见兰兰了。愿这头犟牛一切都好。
8
二侄女青青也是一头犟牛。小时候好哭,哭得我一度担心会哭背过去,没法哄的那种。脾气躁起来,会急得额头出汗,至今依然如此。
老羊村长曾经做了一本书,请人翻译的,叫《一生的忠告》,是一位英国外交官给他儿子一生的忠告。其中头一条忠告是:清晰地表达你自己。
为了让二侄女能学会清晰地表达自己,我跟她玩角色扮演游戏,说:“以后,你当老师,我当学生。”
她太开心了,立马把家里墙壁当黑板,搬来桌椅,还有模有样叫来她闺蜜当助教,满座小朋友、大朋友必须双手后剪,青老师这才开讲《咏柳》,逐字解读。
六年级时候,她喜欢英语。我说:“青老师,你给我用英语讲个故事呗。”青老师大喜,自己一边手舞足蹈地表演,一边用英文诵读《仙度瑞拉》:“Long long ago,far far away,there's a girl named Cinderella……”
野地里,百草皆是玩具。两只狗尾巴草,可以制作成小提琴,青青则在小提琴上别出心裁地放一朵花——夜来香。
9
我带小侄子似乎没有费什么心,虽然他是我们家第一个男孩子,要传宗接代的,金贵。他一出生,我压力顿时小了。
我不费心,是因为小侄子天生就乐观、大气、舍得出力气。我似乎没见他小气过,什么吃的用的玩的,他都乐于与人分享。我父亲以前劈柴的时候,累了,四五岁的侄子看到了会说:“我来。”抡起柴刀就开干,舍得力气。他又总是笑呵呵的,似乎就没过哭脸。我父亲走的那天,他还在棺木边跑来跑去,哈哈大笑,不知道悲伤也没有恐惧。那年他六岁。

我小时候,父亲是一个多暴戾的人啊:我曾因为赖尿,被他提起双脚、倒过来打;我侄儿侄女出生后,父亲是一个多温柔的人啊:他最疼侄子,几乎每天开三轮车接送侄子,带他去散步,去地里摘菜,有求必应,想买什么就给零钱。
起初我教侄子踢足球,他似乎兴趣一般;教篮球,可是没有篮;教乒乓球,他似乎一下子有了兴趣;教跑步,跟他一起比赛跑,故意跑他后面追不上他,侄子就开心啦,爱上了跑步,后来在小学运动会,他跑步获了奖。
这孩子从小做事就有模样,搭房子,就像个房子;堆沙雕城堡,就像个城堡。我甚喜欢。
“你要想得人爱,先得可爱。”
如今他已经一米七二,身高超过我了,我若回家,还好意思拥抱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