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个人体验与重构
——甘茂华文化散文集《这方水土》解读
■桑大鹏 肖四新
作者单位:桑大鹏,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肖四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文化不仅是群体的,更是个体的。个体在对文化群像的领悟与理解中注入个人意志,使之向个人生成,文化就在这种与个体的互动中打上鲜明的个人印记,成为具有个体特色的微观意义系统。甘茂华文化散文集《这方水土》可视作文化个体化的一个样本。文本表明,具有鲜明地域和种族特色的巴文化不仅被作者目击、领悟、记录,更在此种领悟中以自己体验达到文化的个体性重构。
一、相遇是宿命
作者出生于鄂西恩施,青年时代随知青上山下乡活动(1967年)被下放到江西,五年之后又迁徙到山西,又十五年之后回到出生地恩施,之后定居宜昌。在外地漂泊二十余年,其间身份叠经变化:农民、工人、编辑、银行干部、作家、词作家。但无论何种身份,都无法斩断作家的怀乡之思。文本处处是这种深情款款的文字:
“清江不仅给了我们吃的喝的,而且还给了我们用的玩的。我在清江边筛过沙,挑过石头,苦力换来的钱,买过书本,也买过玻璃球。夏天里,清江是天然游泳池。游过对岸,在五峰山脚下有一处冰凉的山泉。用小桶盛满泉水,双手推托着游回来,再提回家,一家人泡西瓜吃,其乐也融融。”
此种文字置于文本固有的语境中,其实不能仅仅理解为情感的发舒,或作家童年记忆的叙事,而是对某种召唤的回应,是与某种从不主动出场而又无处不在的精神的相遇,笔者将此种精神命名为“乡愁”。
作家从故乡出发,二十余年后又回到祖居地,这是一种个人命运的文化隐喻:无论漂泊的时空范围多长多远,故乡的文化之根正如手中的风筝线,始终牵引着漂游的灵魂,时间愈久,地域愈广,牵引力就愈发坚韧,怀乡之思终于显现为不可遏止的回乡冲动,乡愁展现为现实行动,回到祖居地表面看来是个性的选择,本质是对地域与种族文化的追寻与祭奠,是某种宿命式的“回归”。正如作者自白:
难道是巧合吗?上天让我分两次看了三峡的上半截和下半截,是故意吊我的胃口,还是冥冥中另有安排?反正离开家乡鄂西去江西当知青,心情十分沉郁,谁知知青这辈子是个什么结果呢?……人们在告别她的时候,才发觉这条文明大峡谷蕴含的历史文化的上千年记忆,是无法忘却也是无法复制的。
这是对于“宿命”的认知与领悟,甚或是某种“欣然认命”。正如作者所说:“这条文明大峡谷蕴含的历史文化的上千年记忆,是无法忘却也是无法复制的”。当领悟到这种宿命之后,作家的行为变得更为自觉:自觉打量武落钟离山、清江画廊、摆手舞、腊猪蹄、包谷酒;自觉认知祖居地的文化意义;自觉进入祖先文化的深度体验;自觉留住行将灭失的文化旧影。最后,所有自觉凝聚为一种设想:作家要创造一种富有个性化特征的文化系统,作为对祖先、对过往的心仪与祭奠。
二、相看两不厌
人与自然,构成对象化的双方,正是双方的看、关注、打量,构成了互相接纳的基础。站在自然立场看人,一座山峦、一条河流、一片瓦砾沿着人的文化气息走进其精神深处;站在人的立场看自然,澄明的目光使自然的文化精神醒目、鲜明而活跃起来。“看”,使自然的精神气质趋于明朗、鲜活。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方水土》就描述了一个人与山水、历史、故乡互相观待而各自活跃的过程。
庙背后黄牛岩顶那四座灰白色山壁,被阳光照得晃眼。在大江高崖衬托下,黄陵庙显得威严而又尊贵,不仅气势凌人,而且伟岸壮观。我眼睛一亮,在心里呼唤:大禹,别来无恙?……它脚踏滚滚波涛,弓身低头,两只犄角直朝峡岩撞去,仿佛刹那间便会爆发出雷霆万钧之力,使人联想到黄牛助禹开峡的雄奇形象。
可以看出,正是作者的“看”,黄陵庙的伟岸、雄奇、壮观、气势凌人等精神特质一时鲜明起来,向知音、向同类精神、向熟悉的文化气质之生动显发。“我眼睛一亮”,隐喻了一种内心的洞开与敞亮,基于此种敞亮,“我”得以与祖先对话而进入无数年日的时间旅程,领悟历史并对黄牛岩、黄陵庙全面悦纳,黄陵庙也因“我”的悦纳而凸显其意义的“整全”。
“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视觉行为,此中不仅有对对象的召唤,还有对其精神的领悟与理解,更有对主体自我的反思,主体在这种精神的反复回流中获得充实与成长。
每次在长江上独立船头凝眸三峡时,我总是感到了一种诗人的襟怀,一种船工的性情,一种虔诚的宗教般的渴望,让我刻骨铭心……从宜昌到巴东一段,恰恰是三峡长卷中的精彩部分,每次经过这段水路,看峡谷峡江,总觉得百看不厌,还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从恍如隔世、似曾相识中领悟一种宗教情怀,正是现在的“我”与某种失落已久的恒久意义的遇合,“我”因此种遇合而有一种获得感:获得当下的领悟与充实。三峡也因“我”的获得而领有了饱胀的意义,此意义溢出三峡的地域限制,成为一个意义饱满的文化符号。
可以看出,作者与祖居地的互“看”达到了两种效果:一者使三峡故地的文化意义由隐蔽而敞开,向人、人类敞亮起来;二者是主体自身因地域之历史文化意义的领悟而获得个人宿命式的回归。人与祖居地就如此互相悦纳、彼此促进,共同成长。但富于意志的主体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看”,他还要进入符号意义的重构。
三、时空的个人印记
在主体与祖居地的彼此观待、互相悦纳之中,主体不仅领悟种族文化的核心意义,更在这种领悟中烙上自我的印记,开始文化的个体性重构。
“雨天的吊脚楼群,像唐代的《竹枝词》,乡情土韵,牵动着父老乡亲的心。这时我们看一眼清江,如龙、如凤、风里来、浪里去,便有了一种襟怀摇曳的感觉。”
主体以“我们”——类化的“我”打量吊脚楼,发现吊脚楼玲珑秀美,具有刘禹锡竹枝词的诗意。是不是所有个体观待吊脚楼都像竹枝词呢?显然不是。故此,吊脚楼之富有竹枝词的多情就是主体的个人印记了,是吊脚楼的符号意义之向主体的独有启示。循此余思,笔者可将主体在“襟怀摇曳”之思中看清江如龙凤般的动感,视作个人的图腾意识与清江妖娆之姿的遇合。
个人印记还在主体少小时的点滴记忆之中:
“那时恩施还没有自来水,居家用水都靠家人从清江河挑回来。也有专靠挑水卖的人,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我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去清江河挑水,直到把水缸灌满为止。沿着北门河坎上的一道斜坡走下去,在河滩上等候跳板。因为跳板像极了略宽的长条板凳,一头搭在岸边,一头伸向水深处,只容得下一个人来回走动。你要想吃到干净的水,就必须等前面的人下了跳板后你再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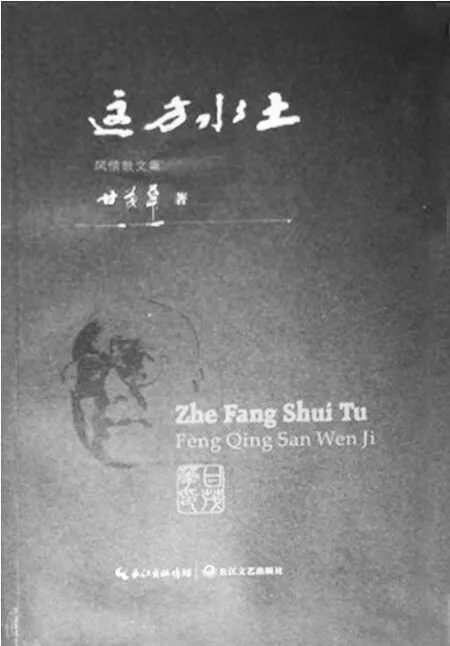
《这方水土》
“挑水”是特殊地域环境中的特殊生活方式,“我”对挑水的自身经历加强了对地域特征的亲身体验,“我”的体验顺势印入地域的独特性中,从此成为浪游灵魂对故乡的特殊记忆,并构建“我”对他乡风物的前见与理解,这种前见式理解把我更深地引入与故乡精神的浑整统一。
“听着清江冬日的低语,我们听见了清江深处黄钟大吕般的的旋律。清江的历史文化,流水一样缱绻柔情,唤醒了冬眠的山魂,绽开了人性的花朵。清江河是向王天子的一支牛角吹出来的,是巴人部落古老的迁徙歌唱出来的,是男女翩跹跳摆手舞跳出来的……”
此中,作者将感知角度从视觉转为听觉。听,是一种更深的感知,是将对象纳入内心的凝神内省,是深远而宁静的忘我之知,因而是物我合一的精神凝练。在这种凝练中,主体灵魂破茧而出,看到了部落迁徙、舞姿翩跹;听到了向王天子的牛角呜呜;悟到了缱绻柔情、人性花朵与醒来的山魂。于是我们可以说,此种文化意味带着主体感知的个人印记。
由于个人灵魂印记印入祖居地,于是故乡风物就领有了人的生命。
潮涨潮落、山高山低、雷鸣电闪、呐喊挣扎等等具有生命迹象的风物动态都因呼应着向王天子和“我”的引领而发生,随着主体的性灵节奏而舞动,本质是人之生命的借以呈现。如果说在物我观待、“互看”中还能悟出山水的自身生命,那么此中故乡风物却是打上了人的生命印记。
不仅如此,领有人之生命的故乡风物还灵动地向广大延伸,流入更广更大的人文之海,故乡风物在不同“前见”的解读中展现出多重意蕴:
历史学家或民族学家眼中,由此寻觅到几千年前消失在三峡黄金洞里、尚武喜舞的巴人的悬棺铜剑;作家或艺术家,在此倾听到传说中生长在土司山寨里、原汁原汤的土里巴人的情歌巫歌;便又有哲人怀着淡淡的忧伤,来此寻觅精神的乐园。感叹:适彼乐土!
当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作家,艺术家,哲人关注同样一方水土时,他们各自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意义。这一方水土就是一面镜像,映现出千千万万的心影。我们何尝不能将此理解为同一种生命与无数个体性的遇合、从而带有个人印记的万千新生命之发生?
四、何以忧怀?
甘茂华文化散文的审美风格表层看来有忧郁、伤怀的基调。《鄂西风情录》如是;《山那边是海》如是;乃至《这方水土》亦复如是。亦即,此种忧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直至如今似乎始终挥之不去。甘茂华能因腾格尔的豪放而鼓舞,能自作“山里的女人喊太阳”而壮歌。但其散文却无法不流露伤怀。因何而伤?大约因某种必然的逝去而痛惜。作者有足够的理由忧伤:三峡是作者的精神故乡,是灵魂的始源地与回归地,而现代化的经济运作却使故乡向历史的深部渐行渐远,“故乡”随移民而流散,某种文化的“原力”正被现代化所稀释。作者虽怀着顶礼膜拜的心情朝礼故乡,但一路上反复遭遇伤逝,因而悲从中来,忧伤不可遏止。
作者能做的就是记下故乡印记的原汁原味、原汤原水,记下山水人文的粗粝与野蛮,记下自己沉重的乡愁,并将自我生命注入故乡风物之中,使之获得个体性的永生。而关注与描述首先表现为一种自觉:
“现在是时候了,我要把自己体验到的三峡,告诉我的读者朋友。哪怕是粗线条的勾勒,也要把它素描出来。我知道我的笔力太弱,无法尽述我的心情。但再弱的笔一沾上三峡的色彩,它就有了或多或少的美感。”
但描述的自觉终究敌不过伤逝的沉重:
“数千年承载三峡文明的主要地区将淹没在水面下,上百万人举家迁徙,又让我们不禁发出留住千古三峡的概叹。”
作者牵挂的是故乡百姓因移民远离故土、散处四方而导致文化的灭失;父老乡亲异乡生存之艰难;方言、乡音、民歌等种种图腾的堙没。这一切无法不使人忧伤。伤怀的心情驱使笔致具有挽歌之音:
“我们都曾记得哑巴艄公肚子里有数不清的故事,可如今,竟和数不清的岁月一道沉默了。这沉默协调着默契的心声,而那一弯飞虹却负不起过多的心事。唱啊唱,唱不过杜鹃飞过的叮咛。峡啊峡,留不住你深深浅浅的身影,留不住你汩汩滔滔的脚步。无人知晓,这平静下的暗流,有多急,有多深。而冷冷的钟乳石,正冷冷地注视着,这尘世间的天阴天晴、花开花落、月圆月缺。她说,那边是石拱桥,连接千年往事……”
以此挽歌巡历哑巴艄公、身影脚步、花开花落、短笛牧歌,故乡的人、事都进入凝神内省之中,进入伤怀的往事追忆之中,即将“逝去”的时间使故人故物都被烙上某种忧伤的“宁思”,从而具有了某种“禅悟”意味:
“我又想起这次在乐平里邂逅的那个清纯如水的姑娘……她的容颜和身材就是一枝站在家乡的端阳花,朴素中透着诗人的灵气……雨水顺着她乌黑的头发像露珠一样流成一串儿,清秀的脸上写满了脉脉的温情。我想她应该属于正宗的屈原的诗族诗裔,是她的光脚板踩出了一行又一行散发乡土气息的诗句。”
至此,作者以对土家姑娘入丝入微的内观而获得古典诗意的超越性感悟,打灭了伤逝的悲切,在平静的心境中接受更广大的意义:屈原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人类的,是故,屈原的文化符号意义更为恒久。这种“接受”无疑更具理性意味。
五、无喜无悲入涅槃
涅槃,是佛法的专有概念,对应汉语的不生不灭、无喜无悲以及没有时间标尺的“永恒”。佛,因看透并经历了轮回的一切悲喜剧,至入涅槃时已无喜无悲。本文当然只是“借用”涅槃概念,用其无喜无悲之意。佛的无喜无悲虽以“寂照”、“无为”为本,但并不排除祂能够感应轮回众生的一切生机,或其无喜无悲之中本身就充满生意。
前文已述及,甘茂华文化散文表层看似伤怀,但观其文本行至深处,其实无喜无悲。作者意识到,红尘滚滚,人世巨变,“一切在历史过程之中发生的东西都将在历史过程之中消亡”(马克思语)。故迷人的三峡人文无论其如何特异,如何牵动人的挚念,消逝都是必然的。更何况在今日叠遭巨变。故伤怀、挽歌并不能留住行将逝去的旧影。与其如此,不如对峡江文化进行理性的省思,接受更广大的意义。这种“理性的自觉”在其后期文化散文中更加明显:
“穿越巴山楚水,探寻苍茫的历史风雨,诵读鲜活的现实诗篇,心中笼罩着一片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迈气概。我知道,这不仅是神奇山水带给我的真实感受,而且更是建设者的精神风貌,如一道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我的内心世界。一路走来,正是巴山楚水不知不觉地滋润我的情怀。我因此深深的理解了跋涉蜀道的艰难和价值。这些人生风景将陪伴我继续去探寻诗和远方。”
可以看出,作者虽叙述文字气韵生动,虽仍然向往诗和远方,但理性的痕迹俨然。重要的是,文字一如既往的带着“我”的痕迹,带着鲜明的“个体性”。于是笔者试作如是理解:既然无法阻止地域与种族文化向历史深部渐行渐远的的必然趋势,则何妨从伤怀之中超脱出来作理性静观?而作者以理性审视故乡所获具的更广大的文化意义、带着鲜明的文化哲学与美学的个体性、达到了无悲无喜的涅槃之境。
六、结语
要描绘、勾画出一个种族、地域的文化面相,散文是最便利的方式。如果用小说,因小说文体的核心使命是刻画性格,地域种族的文化资源都用之于性格的刻画,当性格立体式地凸显时,文化信息因被片面地使用,其意义走向狭窄。只有散文,具有表达的自由和散点透视的方便。甘茂华使用散文,表达的自由使其在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山水与人文之间自由穿行,而散点透视又得以描绘出土家文化的全方位、多侧面、立体感,并不失时机地将个人体验带入意义的认读之中,创造了一种具有个体性特征的文化符号系统,最后在无悲无喜的理性静观之中将种族的文化意义带向人类意义。这正是甘茂华文化散文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