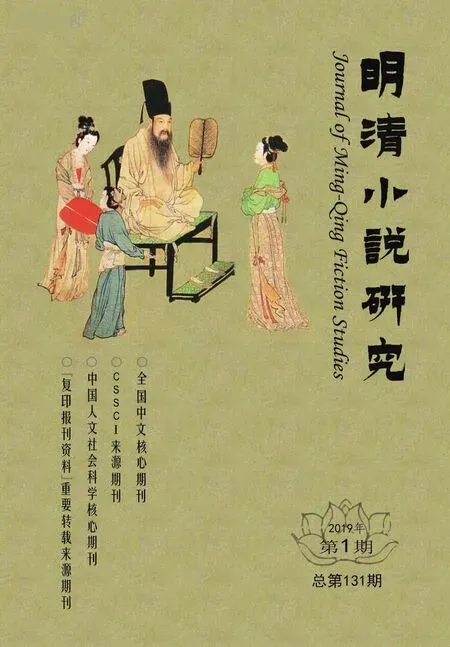《金瓶梅》在法国
——试论雷威安对《金瓶梅》的翻译与研究*
· ·
内容提要 雷威安是法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金瓶梅》研究专家。《金瓶梅》在法国历经一百多年的翻译旅程,最终得以出版问世,雷威安功不可没。他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论著在世界汉学界均有较大影响,而《金瓶梅》的研究最具特色,影响也最广。国内对法国《金瓶梅》一波三折的翻译出版史知之甚少,其中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文学接受与艺术审美的因素,有关雷威安《金瓶梅》的研究成果也鲜为人知。本文对此进行细致的研读和分析,以补缺我国有关法国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成就的不足。同时,为中国《金瓶梅》学术研究引入新的声音,为促进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国际对话提供具体而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和理论依据。
雷威安(André Lévy)是法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金瓶梅》研究专家。他1925年11月24日出生于天津,是一名法国钟表匠的儿子。1937年他离开天津返回法国,在凡尔赛、马赛、克勒蒙费朗度过中学时光,1945年开始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修读文学与东方学,并在索邦大学学习汉语、日语、印地语和梵语,从此与东方语言结缘,毕业后在河内、京都和香港的法语学校任教,进一步接触和研读东方文化,1969年回国后进入法国高校工作,从此,开始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雷威安将自己的关注点定位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中国白话文学、明清小说和历代话本。在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他首先从翻译着手,自20世纪70年代起便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这其中包括《凌濛初:狐女之爱》(1970)、《西山一窟鬼:12—14世纪的七个中国故事》(1972)、《金瓶梅词话》全译本(1985)、《西游记》全译本(1991)、《古代中国的爱情与死亡故事》(1992)、《孔子》(1993)、《不了情》(1993)、《聊斋志异》选译本(1996)、《一片情》(1996)、《欢喜冤家》(1997)、《中国古典爱情诗百首》(1997)、《牡丹亭》(1998)、《中国古代神奇故事》(1998)、《爱与仇》(1998)、《欲望之镜》(1999)、《素女妙论》(2000)、《孟子》(2003),译著颇为丰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法国对中国现代社会与生活了解需求的加深,尽管雷威安已是75岁高龄,但他开始转向中国现当代作品的翻译,并很快出版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迷园》(2003),《台北人》(2004)、《邯郸记》(2007)、《乌鸦》(2012)等多部作品。雷威安除了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外,他还同时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早在1971年便出版了专门论著《中国长短篇小说之研究》,之后每隔十年他都会推出一部研究专著,如《十七世纪中国白话短篇小说》(1981)、《中国古代和传统文学》(1991),此外,他还主编了《中国文学词典》(2000)。雷威安的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和研究论著在世界汉学界均有较大影响,而其中《金瓶梅》的研究最具特色,影响也最广。
然而,我国国内目前仅有对雷威安《金瓶梅》研究的个别成果分析,大都基于“《金瓶梅》法译本导言”和“中国十七世纪通俗短篇小说”两文,而且内容主要限于对其研究的总体评价。笔者有幸在法国留学期间发现了有关雷威安《金瓶梅》翻译和出版的许多全新史料及其鲜为人知的一些研究成果,本文对此进行细致的研读和分析,一方面补缺我国有关雷威安及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为中国《金瓶梅》学术研究引入新的声音,为促进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国际对话提供具体而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和理论依据。
一、《金瓶梅》漫长曲折的法国翻译之旅
法国最早出现有关《金瓶梅》的信息是在1816年出版的《赏与罚》中。法国汉学家让-皮埃尔·阿贝尔-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第一次提及《金瓶梅》,他指出:“从《金瓶梅》这部著名的小说中,人们也可以汲取对社会风俗的有益的经验。虽然有人说它的淫秽内容比腐败的罗马帝国及现代欧洲的所有黄色作品都要严重,然而正确地说,它在色情描写方面是赶不上这些作品的。”①1862年埃尔韦·德·圣-德尼侯爵(Hervey de Saint-Denys)出版《唐诗》,他在序言中曾以“风俗小说”提到《金瓶梅》,并说他已选译了《金瓶梅》的若干章节,准备刊行,遗憾的是,他的译本并未问世。但无论如何,这应该是法国最早对《金瓶梅》的介绍了。
真正《金瓶梅》最早的法译片断是由法国的中国戏曲研究家、翻译家安托万-皮埃尔-路易·巴赞(Antoine-Pierre-Louis Bazin)翻译的,他选译的内容为原书第一回《武松与金莲的故事》,收入1853年法国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一书。然而,直到1912年《金瓶梅》的第一部节译本方才问世,由法国汉学家、翻译家乔治·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翻译,名为《金莲:中国小说选》,由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联合出版社出版。该本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节译,尽管未能体现《金瓶梅》的全貌,但译本达294页,可谓是《金瓶梅》在法国译介的一次飞跃。同时,莫朗在译本《序言》中写道:“《金瓶梅》与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一样有趣”②,这个译本主要保留的是原书中对性的描写。这期间,侨居法国的中国学者吴益泰亦译有《金瓶梅》的片断,收入他的译著《中国小说》(巴黎韦加出版社,1933年),由于是与其他中国小说一起出版的合集,没有单行本,故知者甚少,影响有限。
其后,让-皮埃尔·波雷(Jean-Pierre Porret)的节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始末》出版,全书共两卷,1949年由巴黎居伊勒普拉出版社出版第一卷,1953年出版第一卷修改本,但因遭法国官方查禁,直至1967年禁令取消后才将两卷出齐。1962年,由约瑟夫·马丹·鲍尔(Josef Martin Bauer)与赫尔曼·海斯(Hermann Hesse)等合译的另一节译本由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出版,名为《金瓶梅·帷幕后的女人》。然而,波雷和鲍尔等人法文节译本都是根据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的德文节译本转译而来。而库恩是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国明清小说翻译家,他的德文节译本《金瓶梅》根据《第一奇书》翻译而来,题名《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全书分四十九章(920页),1930年由莱比锡岛社初版,后多次再版,除上文所提的法文译本外,英国、瑞典、芬兰、匈牙利、荷兰的节译本也大多是根据库恩版转译而来。虽然库恩的译本在欧洲颇有影响,但它也使《金瓶梅》在欧洲沦为一部下流书,长期被放在淫秽小说类书架之上。正如法国比较文学教授、汉学家热内·艾田蒲(RenéEtiemble)所说:“把这部小说看成是黄色小说显然是由已发行上万册的多种欧洲语版本所引起的,这些译本都执意删去这部名著存在的基础,而只强调下流的情节,更糟的是,这些糟粕几乎全是效法于库恩的猥亵译文,因为他的译本使《金瓶梅》沦为一部下流书,从而将一副完整的、由繁荣而衰落的文化图景变成了一些轻佻的、令人憎恶且支离破碎的画面。”③这样一来,就不难想象波雷和库恩译本内容的倾向性和片面性了。
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一项选译东方国家文化名著、编成一套“东方知识丛书”的决议,同时决定这套丛书交由巴黎权威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负责此项工作的是法兰西院士、作家罗歇·卡约(Roger Caillois)和艾田蒲教授,他们计划将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唐人传奇》《聊斋志异》等列入丛书,其中《金瓶梅》的译者是由艾田蒲推荐的安德烈·雷威安。从起意组织翻译《金瓶梅》法语全译本到译本付梓出版,这期间长达36年之久。据艾田蒲回忆:“1949年我从埃及归来,边翻译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的《金钞》,边着手撰写《兰波的传说》,之后拜读了波雷由库恩的德文节译本转译的法译本《金瓶梅》后发现,这只是库恩的编译小说,它所删除的部分正是这部风俗小说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这是一部丝毫未加粉饰的明朝末年中国社会的风俗画。八年后,当我在中国逗留期间(这一时期正是所谓‘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从中国权威人士那里得知,这部‘淫书’(甚至在‘百花齐放’年代,它也不幸被冠以此名)将在内部发行,并且他们已答应到时送我一套,但最终我也未能如愿收到。因此,我不得不向日本出版界订购五卷本的中文原著(1963年)。从那时起,我就制定计划,要向法国读者们奉献一部完整的、忠于原文的法文译本。自1965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1966年我就一切可行的方案向伽利玛出版社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在此我不再细说报告的具体内容了,重要的是我终于找到了一位称职的译者。我作为评审委员会成员参加了他的论文答辩,其论文题目是《十七世纪的白话小说:中国文学叙事体的兴衰》。那是1974年1月11日的事。法国汉学家谭霞客(Jacques Dars)极为推崇他的论文,并已看出这位学生将来会是一位‘大师’,我当时就想到最终把《金瓶梅》献给我们的人将会是他。”④
经过七年的辛勤努力,雷威安的法文全译本《金瓶梅词话》(FleurenFioled’Or)于1985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并被纳入在法国享有盛誉的“七星文库”(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之中。雷威安说:“翻译这部长篇巨著,困难不少,有如在茫茫大海上航行,随时都有可能触到暗礁,葬身鱼腹。我力求字斟句酌,传出作者的妙笔神韵,保持原著的娱乐性。”⑤《金瓶梅词话》法文全译本共2756页,分上下两册,附崇祯年间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木刻绣像插图200幅,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金瓶梅》全译本,出版后在法国和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欧洲许多著名学者和重要报刊编辑均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纷纷撰文,一方面称赞法语译文的高超,一方面也跳脱出《金瓶梅》是“色情小说”的评价,从文学、文化和社会学的角度重新看待这部经典作品。此书的出版受到新闻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学院派汉学界的态度则多少有些战战兢兢。法国汉学家克洛德·罗阿(Claud Roy)在1985年5月20日的《新观察家》(第1072期)上写了题为《被肆虐的一角》一文,指出:“《金瓶梅》从它问世的那天起,既使中国读者难堪,又使他们着迷。文人学者不知如何对付这部令人心悸的杰作,对付这部巨型的色情与商务编史……各政权及检查机构在这只黑色羔羊面前表现得犹豫不决,但不知他们的恐惧、犹豫从何而来,或者是由于书中那萨德式的毫不在乎的色情性,或者是由于那副描绘对黄金与性极度贪欲的社会图画所表现的冷酷的残暴性。”⑥这位汉学家说的是《金瓶梅》在中国的遭遇,实际上也是对《金瓶梅》传入欧洲的命运的真实概括。也正如我国学者钱林森教授在他的《中国文学在法国》一书中所说:“《金瓶梅》的确是一部不名誉的书,在故乡,不消说,人们提起它来总要和‘淫’字连起来,因而谈《金》色变;在异乡,它也未能落得一个好名声,人们称它为来自东方的‘黑色羔羊’,难以驾驭。它在西流中,有着不平常的遭遇。事实上,从19世纪初,这只‘黑色羔羊’闯入法国和西欧文学界,就一直令当局者、汉学界左右为难,欲禁不能,欲弃不舍。因此,引进工作也就长期处于犹豫、提防、否定、肯定之间摇摆。”⑦这种状况,一直要到雷威安的法文全译本《金瓶梅词话》面世之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可见,雷威安选择和承担翻译《金瓶梅》所具有的突破性眼光和勇气,及其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评价和审美能力。
雷威安的《金瓶梅》法文全译本以日本影印的《金瓶梅词话》(1617年版)五册本原著为底本,同时参考了英、德、日、俄、法等多种译本后完成。为使译文能够准确地表达原意,雷威安对原书中的诗词、歇后语作了仔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阅读了大量相关的研究著作,特别是日本学者的研究著作。
从1816年第一条《金瓶梅》注释的出现到1985年法文全译本的出版,《金瓶梅》在法国经历了170年的翻译旅程,雷威安的法文全译本《金瓶梅词话》是翻译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也是集大成者,虽然已出版30余年,但不断再版,因深受读者喜爱,于2004年加入Folio口袋书系列以小开本发行,这充分说明雷威安译本的忠实性、可读性、权威性和所具有的生命力,他不仅为法国读者提供了最可信赖的版本,同时也为法国乃至西方学界《金瓶梅》研究的开展,赋予新的推动力。
二、雷威安视域中的《金瓶梅》
雷威安的《金瓶梅词话》法文全译本不仅填补了法国《金瓶梅》全译本的空白,为读者带来了忠实且优美的译本,还洗刷了《金瓶梅》在法国长期以来被当作色情文学的污名,充分体现了《金瓶梅》风俗小说的全貌。此外,他在《金瓶梅》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近二十载,有多篇论文发表,还出版专著,多次参加国际《金瓶梅》学术会议,提出了众多颇有建树的观点。然而,目前国内仅有对雷威安《金瓶梅》翻译与研究成果的个别论文或著作的介绍,主要是对雷威安《金瓶梅》法译本的导言、序的研究,评论大都肯定了该法译本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与权威性,称其为法译《金瓶梅》中的代表作,但对雷威安的《金瓶梅》研究鲜有提及,对其研究观点的引用多出自他的“《金瓶梅》法译本导言”、“《金瓶梅》法译本序”、《中国十七世纪通俗短篇小说》结论部分,以及《评〈金瓶梅〉的艺术》和《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接受——法国著名汉学家雷威安一席谈》。然而,经笔者大量查询和认真仔细地研读后发现,实际上,雷威安有关《金瓶梅》的研究论著十分丰富,研究问题和内容涉猎细微而深入。
早在雷威安《金瓶梅》全译本出版之前的1979年,他便发表了第一篇论文《〈金瓶梅〉初刻版本年代商榷》。他认为初刻本年代以万历四十五年(1617)较为可信,至于《金瓶梅》是否有过已经失传的刊刻于万历三十八、九年(1610、1611)的版本,这一问题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不必匆忙下结论。该论文1979年4月被收入英文版《中国文学评论集》,1980年4月由周昭明翻译,载于《中外文学》第8卷第12期,并被收入《〈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雷威安在文中就《金瓶梅》是初刻于万历三十八、九年还是万历四十五年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以往大多中国文学史都模糊其词,将初刻时间说成“万历年间”,时间涵盖了1573至1619近半个世纪,然而文学研究的时间问题的重要性古今如一,六年之差已经关系重大。因此,他重提这个问题就变得掷地有声。雷威安提出,假设存在失传的早期刻本非但不必要,而且在有关记述中也找不到佐证。他认为《金瓶梅》初刻本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并提出三点证据论证没有万历三十八、九年初刻本的存在。雷威安1979年发表的《〈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就已经使人刮目相看。
《评〈金瓶梅〉的艺术》(1981年)是他的第二篇相关研究论文,载于美国《Chinese Literature》杂志1981年第一期,后由白黎翻译,刊登在《文学研究动态》1984年第10期上,这篇文章是雷威安为香港著名学者孙述宇教授的《〈金瓶梅〉的艺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一书所写的书评。雷威安认为《金瓶梅》的遭遇是自相矛盾的,它在“五四”时期曾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现代体裁的长篇小说,是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珍品,但依旧留有“淫秽小说”的恶名,在香港、台湾和大陆都属禁忌,当时《金瓶梅》的研究主要在日本、美国和英国。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金瓶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香港开始能买到未删节版的《金瓶梅》。孙述宇的《〈金瓶梅〉的艺术》在台湾出版也证明台湾重新开放了对《金瓶梅》的研究,大陆从1979年起也陆续有关于《金瓶梅》的文章发表。孙述宇强调《金瓶梅》是写日常生活细微情节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对生活各个方面的观察研究,塑造了使人难以遗忘的完美人物形象。孙述宇的贡献在于他站在读者的立场而非历史学者的立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论点可与夏志清的观点互为补充。夏志清试图揭示西方读者对《金瓶梅》的过分赞扬,而孙述宇则是向中国公众说明《金瓶梅》为什么以及怎样被忽视、被曲解和不被承认。
第三篇论文《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载于台湾《中外文学》1981年10卷第3期。雷威安在文中重点介绍了魏子云的《〈金瓶梅〉探原》一书,认为这是“一本尚未为众人所知但却非常有意义的卓越尝试,他对研究《金瓶梅》的方法有很大贡献,就是我们称之的‘外在研究’,这是二十年前韩南教授提出后一直未再受人重视的方法”⑧。这一观点在中国大陆出现得更晚,可以说,雷威安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学术交流的桥梁和使者。雷威安认为,魏子云的学术研究审慎而有趣,他有将“每块石头都要翻过来加以检查”的态度,其目的是抛弃原有的外在证据(《金瓶梅》原稿形成于1596年或更早,刻印成书在1610年),他在其中提出令人激赏的结论:《金瓶梅》写作的最早年代应该是1621年,即天启时代的开始,同时也更正了他之前在《〈金瓶梅〉初刻版本年代商榷》一文中认为《金瓶梅》写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观点。此外,雷威安就魏子云书中论点的重要性做了思考,并认为虽然有很多证据表明《金瓶梅》的手抄本原本未被发现或遗失,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它们真实存在过。雷威安以魏子云的《〈金瓶梅〉探原》为主线,主要讨论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期间穿插对张竹坡、姚灵犀、鸟居久靖等人观点的评述,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魏子云的观点,但他认为魏子云以审慎的研究态度提出研究《金瓶梅》的新方法,并有推翻旧说的勇气和毅力,非常令人钦佩。从中可以看出,雷威安的研究视野并没有局限在法国国内,他密切关注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在学术研究和翻译研究等诸多方面与台湾有着长期的交流和交往,他的研究不但促进了法国金学与国际的交流,也推动了中国金学研究的发展。
1981年雷威安的研究专著《十七世纪中国白话短篇小说》(LeConteenLanguevulgaireduXVIIesiècle)于巴黎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多认为这部论著从文化视角对《金瓶梅》以艺术审视,认为《金瓶梅》决不是“淫书”,而是一部描写社会风情、表现都市风貌的“奇书”。似乎这是一部有关《金瓶梅》的著作,但经笔者仔细阅读后发现,其实它是一部雷威安对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专论,而非《金瓶梅》研究。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话本的文体,简介其中的代表作;第二章从文化角度探讨了白话短篇小说如何从口头、非文学与文学材料中汲取养分,编者如何注意到这些古代话本并进行编辑刊印以及话本的流行与17世纪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章分节讨论《三言》《拍案惊奇》《今古奇观》《西湖二集》《豆棚闲话》与《西湖佳话》,研究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17世纪,白话短篇小说兴盛的意义何在。因此,显然《金瓶梅》作为长篇小说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所以我国学者将他的这本著作作为《金瓶梅》的研究文献有失偏颇。
1983年5月,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举办《金瓶梅》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印第安那大学与金赛研究所联合主办,欧阳桢主持,与会人员有夏志清、雷威安、韩南(Patrick DewesHanan)、孙述宇、芮效卫(David Roy)、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浦安迪(Andrew Plaks)、马泰来、郑培凯、陆大伟、史梅蕊(Marie Scott)等,会议成果结集成《〈金瓶梅〉西方论文集》(1987年),由徐朔方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编者也希望通过美国学术期刊《Chinese Literature》将该书介绍给西方学术界,于是《Chinese Literature》便于1986年第8卷刊登了系列论文,围绕《金瓶梅》展开讨论,其中包括雷威安的“Perspectives on the Jin Ping Mei——Comments and Reminiscences of a Participant in the Jin Ping Mei Conference”。他在文中介绍了学术讨论会的基本情况,并对会上的各方观点和文章进行评述。会议的主题是“禁书:在古代中国和当代美国”,会上共讨论了四个主要问题:1.成书与作者问题;2.宗教与哲学视角下的《金瓶梅》;3.如何评价作为虚构叙事的《金瓶梅》;4.《金瓶梅》留给后世的遗产。与会者共提交了12篇论文,其中5篇后来结集出版,其余7篇或因作者即将出版专著,或因有些作者认为还有修改的余地,并未一起出版。
在“Perspectives on the Jin Ping Mei——Comments and Reminiscences of a Participant in the Jin Ping Mei Conference”一文中,雷威安以下几个观点值得关注:1.很难说彼得·拉什顿(Piter Rushton)的论文配得上它的“领导地位”,虽然人们可能认为他的论述广博庞杂;2.对于《金瓶梅》是否是色情作品,他的观点是,一本内容欠佳的好书比起内容不好的烂书更糟糕;3.现代的“作者”概念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古典小说;4.柯丽德对儒家经典和宋元理学很感兴趣,她对小说的叙述结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析了“叙事学”如何与宗教和哲学观点密切交织;5.浦安迪主要研究《金瓶梅》崇祯本,分析古代对《金瓶梅》的传统评价以及《金瓶梅》对后世小说的影响;6.史梅蕊认为要想掌握人类行为与其后果间的微妙关系,花园是个可以抓住小说核心的意象;7.还有几篇文章,如维多利亚·卡斯(Victoria Cass)的“《金瓶梅》中的末世论:道教模式”、马泰来的“谢肇淛《金瓶梅》后记研究”是近年来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马泰来的后记也值得被全文翻译。
1985年《金瓶梅词话》法文全译本出版,艾田蒲为其专门作序,雷威安也为此书写了导言,“序言”和“导言”无疑都是高水平的研究论著。艾田蒲在肯定《金瓶梅》的历史意义的同时,特别联系欧洲的社会状况肯定了《金瓶梅》的现实意义,可谓独具慧眼,见地不凡。雷威安在“导言”中介绍了《金瓶梅》译本在欧洲的流变,并阐明自己的翻译策略与观点。
自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徐州召开以来,国内外各类学术研讨会密集召开。1989年6月中旬在徐州召开的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雷威安提交论文《〈金瓶梅词话〉53、54回的秘密》。他认为从谢肇淛的跋文可以猜到五十三回到五十七回以外会有一些文章是“补以入刻”的,十卷本和二十卷本的五十三、五十四回中,文章共同处不多,十卷本的这两回比二十卷本长二三倍,两个版本的色情描写语言如此接近不会是偶然。此外,1992年6月在山东枣庄市峄城区举行了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雷威安向大会赠送了自己的《金瓶梅词话》法文全译本,德国汉学家祁拔兄弟(Kibats)的两位女儿将祁拔兄弟花费数十年心血译成的新版《金瓶梅》德文全译五卷本作为礼物送给大会。可以说,法文和德文全译本的出版推动《金瓶梅》的学术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994年雷威安主编的《中国文学词典》(DictionnairedeLittératurechinoise)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由他执笔的《金瓶梅》词条足足占据四页篇幅。雷威安在介绍该书的基本情况后,重点介绍了“成书之谜”与“禁书”两个方面。
纵观雷威安的《金瓶梅》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成书时间与作者问题的关注,这也是中国以及国际“金学”研究一直以来的热点与难点。虽然他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无法与国内“百家争鸣”的热烈局面相比拟,但他以“外来者”的视角,纵观国内外“金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庞杂的史料抽丝剥茧,以严谨的逻辑分析与论证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答案(毕竟成书与作者问题依旧是未解之谜),但他无疑为国内学界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观点和方法。此外,雷威安多次重申不应把《金瓶梅》放在“淫秽小说”之列,他充分肯定《金瓶梅》对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重要影响以及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以一位严谨的译者、研究者、文化传播者的使命,努力扭转大众对这部现实主义巨著的误解。
三、结论
《金瓶梅》在法国从一开始的注释、节译、转译再到最后全译本的问世,经历了近两百年的翻译旅程。雷威安经过七年辛勤耕耘、翻译的《金瓶梅词话》最终于1985年出版,这部全译本因其完整性、忠实性与可读性被纳入法国最富盛名的“七星文库”,历经三十年依旧不断再版,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该译本不仅第一次让法国读者读到了原汁原味的《金瓶梅》,也以其忠实完整的译文为这部在法国长期带着“淫秽小说”帽子的作品正了名。与此同时,这一漫长的翻译过程不但说明法国读者希望了解中国故事与生活的愿望,也证明这部作品在法国具有的长久生命力。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法国几代翻译家孜孜不倦、艰苦卓绝的精神,同时也侧面反映出法国汉学界从娱乐性翻译到学院派研究式翻译的发展过程,从一知半解的小心求证走向考据详实的新论点、新成果不断出现的过程。
雷威安耗时七年翻译完成了《金瓶梅》全译本的翻译,并持续研究了二十年。他认为文学既不是对社会简单的反映,亦非意识形态卑微的仆人,白话文学这一体裁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期的特殊风貌,他的白话文学研究为中国文学研究在法国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他首先一再强调不应该把《金瓶梅》视为色情作品,因为把探讨邪恶的作品视为邪恶文学显然是荒谬的,色情描写是否不同程度地触犯了读者的廉耻心或羞涩感,进而讨论查禁是否必要,那是政治问题。从文学角度看,应该研究有关的篇章段落是否写得精彩、独特,是否写得实在。在这一点上,雷威安认为与大部分同类作品相比,《金瓶梅》都应该得到更高评价。《金瓶梅》虽有不足之处,但是从文笔风格到整体布局,从描写的精炼细腻,到探讨人类生存状况问题之深刻,它都不容置疑地称得上是一部杰作。从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研究者一直忽略的一点是,《金瓶梅》是中国小说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它是否由一人写成还无法定论,但“在它的带动下,才有了后来迥然不同的《红楼梦》。如果把《金瓶梅》从中国文学史中抹去,那么,中国文学就不会有今天的面貌了”⑨。
综上所述,雷威安对《金瓶梅》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国读者而言,他是《金瓶梅》最权威的译者,他担负着为普通读者介绍这部作品的责任,因此在他的《中国古代与传统文学》以及《中国文学词典》中有对《金瓶梅》内容、作者与时代背景的详细阐述。作为译者,雷威安多次在访谈中谈到译者身份、翻译策略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困难。作为《金瓶梅》的推广者,他在研究的同时不忘常常在论文中提及《金瓶梅》所遭受的贬低与误解,他认为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读者多半还是将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珍品视为色情文学,不论是政府还是读者都不愿正视它的文学与社会价值,这种遭遇是自相矛盾且极其不公的。对法国汉学界而言,雷威安主要关注《金瓶梅》的作者与成书两个问题,这也是中国以及国际“金学”研究一直以来的热点与难点。对国际“金学”界而言,雷威安是名副其实的法国“金学”代言人,他长期关注国内外的“金学”研究,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中国大陆、港台,美国,日本学者保持密切的交流与往来,是学术交流的桥梁和使者。雷威安以扎实的考据功底与严密的逻辑思维,写出一篇篇高质量的文章,他涉猎甚广,在点评他人著作时常常旁征博引,贯通中西。正是因为雷威安与美国、日本和中国保持长期的学术交流,他的学术研究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正是因为他踏实、严谨、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以及在“金学”领域的长期努力使得其研究成果在世界汉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大陆的“金学”研究从80年代起开始腾飞,这正是雷威安金学研究成果最多的十年,他以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和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写成一系列论文,在成书年代、小说作者、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上都为当时的大陆“金学”带来了新鲜的视角和更加学术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雷威安的研究不仅将法国的《金瓶梅》研究水平提高到了新的阶段,也通过不断的国际学术对话,使法国的《金瓶梅》研究处于世界前列。他不仅推动了法国《金瓶梅》研究的发展,也通过学术交流助力了中国80年代《金瓶梅》研究的大发展,为中国《金瓶梅》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声音。
注释:
①⑤⑦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3、189页。
② 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LotusD'or:romanadaptéduchinois,Paris:Eugène Fasquelle ,1912,pp.xl.
③ 钱林森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戏剧和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④ André Lévy,trans.FleurenFioled’Or,Paris:Gallimard,1985,pp.xi.
⑥ Claud Roy,“Le coin ravagé”, Le nouvelObservateur,1985,Vol.1072,pp. 30-31.
⑧ [法]安德烈·雷威安《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中外文学》1981年第3期。
⑨ [法]安德烈·雷威安、钱林森著,傅绍梅译《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接受——法国著名汉学家雷威安一席谈》,《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冬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