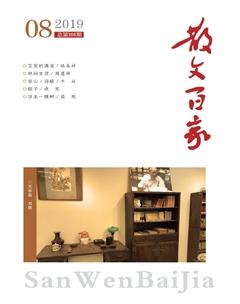浮来一棵树
简默
我执拗地相信,眼前这棵银杏树与记忆中那棵银杏树,一定有着某种亲密而必然的联系。
四十多年前,黔南沙包堡镇东机厂宿舍区20号楼的一套筒子房里,住着我们一家。在楼后,隔着一道高过一楼的围墙,挺立着一棵银杏树,四下就这一棵树,这叫它看上去孤零零的。它粗壮的树干如孕妇的腰身,枝干散漫而收拢有度,我们六七个小伙伴,手拉手围起一个圈,才能环抱住它。它浓荫密布的树下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坐在它爆出地面的老树根上,阳光倾泻如瀑,穿过枝叶花花点点地打在我们头上、肩头。黔南的天气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有时玩着玩着,山那边还出着太阳,树这边却突然下雨了,我们慌忙往树中央靠了靠,树撑开它的枝叶,像一把伞,替我们挡住雨水,但地面上潜伏的潮湿与霉烂,被雨水唤醒了,翻身纷纷往上涌来,呛得我们直皱眉头。
春天来了,我们在树下仰着脖子,等待大孩子爬上去摘一枚枚树叶扔给我们,我们将那扇形叶子对折成小鸟,一手捏着叶,一手扯着茎,仿佛一只大雁在不停地扇动翅膀,细微如发的气流淌来淌去;渐入秋季,秋风秋雨至,吹落黄金叶,铺满一地,层层叠叠,我们拾了洗净晾干,夹在书里,一整本书,夹了一个不长的秋天,随手翻翻就到了尽头。这是一棵野树,没人管它,听任它站在这儿自生自灭,也没人站出来认领它,荒野中的它享受不到此待遇。谁都可以扛着长长的竹竿,打树上结的果,没有人出面制止,但一般没人这样做,也不值得。累累果实摩肩接踵,悬挂枝头,被风扫荡,被雨痛击,相互追赶着坠落,滚入银杏叶铺成的眠床,深深浅浅地埋入时光中,也被漫不经心的脚步带到四方。银杏果外面包着一层皮和浆肉,成熟了几近透明,搓破沾到手上,味道不好闻,就着自来水管,哗哗地冲上半天才能洗净。我们用石块砸开壳,剥出里面的果仁,嘗着又苦又涩。
我们家住在二楼,恰好与这棵树的下半身齐平,它自由舒展的枝叶,从厨房开始,一路平行掠过我们家卧室。我站在厨房和卧室的窗前,就可以探手扯过树枝,摘上头的绿叶、黄叶和果实。有时忘记关窗了,刮风了,下起了阵雨,将黄金一样耀眼的叶子纷纷吹入厨房和卧室,湿漉漉地贴在地下和床上,像栖落一地一床的黄蝴蝶。
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家外,我都亲密接触着这棵树,它和我一样,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无拘无束、顺应自然地成长。每天早晨,我躺在床上,醒来第一眼看见的便是它,我亲热地向它问声早安,它摇摇枝叶,算是问候我了;到了夜晚,我躺在床上,临睡前最后一眼看见的也是它,我礼貌地向它道声晚安,它耸耸双肩,权作响应我了。我已拿它当我们家中的一员,它可以是我远方从未谋面的爷爷,也可以是我朝夕相处的老朋友,我愿意将我的心里话,包括那些藏在宝葫芦里的秘密,毫无保留地讲给它听,我知道它会洗耳恭听,会替我保守那些秘密,还会迎着风儿拍着巴掌鼓励我大胆地说下去。它默默地见证着我的成长,与我一同分享着一年又一年青黄相接的记忆,因此它完全有资格对我说“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对此我心服口服,感恩它日日夜夜的深情陪伴。当我回忆起我的童年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由它出发,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童年。
牢牢地扎根在记忆中的这棵树,是我童年的生命树,也是我成长之路上的消息树。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从它开始,我钟爱上了树木,尤爱大树和古树。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在腾格里沙漠边缘,在荔波群山簇拥的少数民族寨子,在跟随护林员徒步护林途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寻找着大树和古树,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着有无大树和古树。这当中有惊喜,看见一棵大树或古树,尽管我瘦弱的手臂拥抱不过来它,但我仍然尽可能地伸出手臂抱抱它,就像久别的儿子重逢了父亲,我是在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向它致敬,也向人类的生命之根致敬。更多的时候是失望和失落,贪婪的斧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棵大树或古树长成今天的模样,要经历漫漫时光,才能成为它扎根地方最古老的守望者和保护神,但伐倒它仅仅是一转身的工夫,千年历史就变成了空白。也是从它开始,我钟爱上了银杏树,它高大雄伟,宠辱不惊,静看炎凉,叶黄知秋,长寿古老,是树中的君子、智者与寿星,也是“汉语的菩提树”。在道观,在寺庙,在野地,我一次又一次地与它迎头遇见,它或被红色围墙锁闭,或挟葳蕤之势孤独地立在原野之上,无不老态龙钟,面目沧桑,只有一树叶子葱茏或华贵到底。大概是记忆中这棵树太根深蒂固了,我总认为它们都不如它老,它已以它强大而顽固的气场笼罩和覆盖了我。
直到我看见这棵银杏树。其枝干四下横生,莽莽苍苍,不堪负荷,支撑以水泥桩子,像拄着拐杖;树身老气横秋,褶皱密集龟裂,根系暴露蜿蜒,仰之遮天蔽日。我承认,眼前这棵树肯定比记忆中那棵树老,不仅因为它是“天下银杏第一树”,更因为它四千年通天入地所承载和记录的历史。穿过烟云和尘土,我仿佛看见它密如蛛网的年轮间,盘旋着多少兴盛衰亡往事……
其实我曾与它擦肩错过。那是七年前,也是在夏季,我们以林业的名义来到这座海滨城市采风,独木也成林的它本来是必看的景点,但由于通往它的道路正在维修,我们只能站在海边,望着它内陆的方向而兴叹。从进入这座城市,我们便听说蛰居在山上的它病了,叶片开始干枯,说者神情凝重,听者陪着担忧,四千岁的它牵动着老老少少的心,就像一把火,烧过它又蔓延向无数人的心,叶片似的心在蜷曲、在抽搐。三天后我们离开,仍然没有它好转的消息传来。一个多月后,台风“达维”在这座城市登陆,我愈加为它揪心。庆幸的是,它渐渐地好转了,也扛住了“达维”,毫发无损。
它也是一棵野树。它从一粒果实开始,也许是随着一阵风飘浮而来,也许是顺着一场雨漂浮而下。你不相信吗?我就亲眼看见过下雨时天上掉鱼的情景,既然雨能“下”鱼,为什么不能“下”银杏果呢?还也许是一只鸟,比如一只喜鹊,它不知从哪儿衔了一粒银杏果,它怕同伴抢夺,躲到了一边,想着独自慢慢地享用,它相中了一棵松树,准备跃到松树最高的枝头,这时它头顶上翱翔着一只鹰,它清楚地看见鹰爪下意识地探了探,这是鹰发起攻击的习惯性动作,它心慌意乱,一松口,银杏果摇摇晃晃地落了下去……当然,这些都是想象。任何想象都是逼近真相的一种途径,想象还可以有另外一些。但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四千年前的一天,一粒银杏果落到了浮来山的山坳间,生根发芽,渐渐地枝繁叶茂,根系深入泥土数丈,扎在石灰岩溶蚀阶地上,像一只铁拳,紧紧地攫住山石,任由狂风暴雨、地震海啸也撼动不了。浮来山——一座姓浮名来的山,山也可以浮来吗?像这棵树一样,飘浮或漂浮而来。我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个好名字,动感十足,禅意也浓,浮来一座山,又浮来一棵树。
这棵树的生长过程是多么不容易呀,像世上所有的树一样,它要忍受和承担一棵树与生俱来的宿命,比如风摧、雨打、雷劈、霜冻、雪压、鸟啄、虫咬、火烧、斧砍、战争……除了这些,由于距离大海不远,它还得接受台风和海啸的洗礼,它们都是它生长道路上的劫难与定数,这个过程漫长而危险,它不会拔起自己躲避,只能站在原地一声不吭地逆来顺受,默默地往下扎根,朝上和四周扩张。它幸运地躲过了一次次天灾人祸,直到它足够健壮和强大了,一些宿命对它没了威胁,束手无策了,另一些宿命仍然如影随形地追逐着它,窥伺着它,时时刻刻,伴随它一生。它在与身边的同伴们赛跑,在年轮的跑道里跑,一圈又一圈地跑,这是些比它年老和比它年轻的树,跑着跑着它成了浮来山上最老的树。树当然比人长寿,此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自己身边居然有这么一棵树,活过了许多代人,他们开始意识到它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是它将纵横驰骋的根系扎入包容他们生死的土地,成为土地的一部分,共同托起了他们。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荷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站在最高的枝头,俯瞰着比草芥高却如草芥一样一茬茬地生老病死的他们,却从不开口说话。他们无比信赖它,虔诚地膜拜它,因为它的力量与长寿,也因为它的生机与活力。他們在它身上看见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笼统地归之于生命力。他们生病时取一片它的叶子入药煎服,逢灾时对它祭拜祈祷化解为一抹祥云,没病没灾时系上一条红色福带,面朝它说出自己的心事、秘密甚至期望,借助它四千年的寿命,搭起与天与地对话的阶梯,也听到了雄浑苍凉的回声。
它是一棵长满故事的树。《左传》记载鲁隐公八年九月辛卯,鲁莒两国曾在此树下会盟,它见证了两国国君笙歌弦舞、化剑为犁的情景。莒国虽小,但“毋忘在莒”之典故,自春秋至西汉,犹如这棵树繁密的根系,在《管子》《吕氏春秋》《新序》等典籍中鲜活地延伸接续,逐渐地由庙堂之上臣子规劝君王居安思危、不可忘本,不要忘记过去的窘迫,演变为江湖之中普通人之间相互提醒或告诫,具有广泛的平民色彩和情感诉求。而“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则有揪出罪魁祸首,不杀不足以求安宁、平民愤的意味……这些都发生在它眼皮底下,四千年不过它一年四季,由绿转黄,从繁华到凋零,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它扎根于历史腹地,矗立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历二十朝代,阅人无数,以史为鉴,铭记多少成败是非,洞悉多少善恶兴亡。
到公元495年,一个叫刘勰的莒地读书人,先后经历了丧父和丧母的打击,又以一介清贫白衣,在寺院中孤苦伶仃地苦读十年,在而立之年的一个夜晚,他梦见自己手捧红色祭器,追随孔子南行。醒来后,他将自己梦见孔子比作当年孔子梦见周公,认为这是孔子在暗示他要有所担当,遂下决心著书立说,树德建言。此后历经四个寒暑,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之中,终生未娶的他终于有了他一生最得意的孩子——《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的问世,使刘勰人因文显,名噪一时,他也终于从寺院中走出来,做了一系列小官。正当他渴盼施展政治抱负之际,梁武帝下诏解除他的职务,敕令他重回寺院编纂经藏。两年后,完成编纂任务的他“燔发出家”,决然将自己的眉毛和胡子烧掉,上表请求出家为僧并得到允许,改名慧地。从此,俗世少了一个官,寺院青灯之下多了一个清高孤傲的身影。通往这棵银杏树的黄泥古道上,常常能够看见他鹑衣百结,竹杖芒鞋,目不斜视,飘然而过。万人如海,他孤身一人,本无牵无挂,滚滚红尘躲他于三丈开外,他无所谓藏,无所谓看轻看淡,也无所谓放下拿起。校经楼中,晨钟暮鼓,青灯黄卷,楼外银杏树绿了黄了,经年不辍,他无欲无求了此残生,渐如油枯灯灭……
一千五百年后,我到孔林拜谒孔子墓,耳畔犹自响亮着《论语》的泼剌水声。又来到银杏树下,我是在替刘勰还南行之愿,我以我抑扬顿挫的脚步,从泗水之源,捕捉着大海咸涩的气息,一路顺流而下至此。我才意识到一部《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乡愁,也是一棵结满累累成语、格言和警句的银杏树。这棵树何其有幸,氤氲着千载充沛文气,雕版着千年工笔乡愁。
我绕着这棵树走了一圈,又走一圈,再走一圈。我是想能够生长如此长寿树的地方,必得吸纳天地之精华,才可拥出抱出这么一棵树。我要围绕着它,呼吸它的空气,啜饮它的甘泉。临走我还要拾一片它的落叶,我要将它夹入我记忆中。由它纤细的茎出发,我将重温我曾被它荫庇的童年和少年。归来我仍是中年,但从此,我记忆中那棵银杏树,便与我眼前这棵银杏树,合株同心,难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