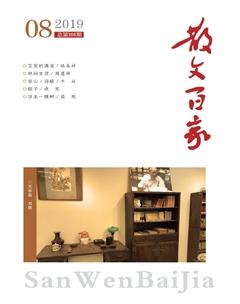林间生灵
周蓬桦
白山栅栏
怎样向你描述我住在白山脚下的临时住所呢?有时候语言是无力的,文字更是无力,连对某个现场的真实还原都做不到——因此,我从不盲目听信另一个人对我滔滔不绝地讲述某一件事物。
如果用一幅中国画将我的白山住所勾勒出来,大约是一幢简陋的砖瓦房,门前是一片稀疏的白桦树林,背景是远山云影——这曾经是一幢守林人的小屋,经过一番改造装修,成了专门为旅人准备的出租屋。为了完成一部作品,我要在这里住上整整一个夏季。但是,我要说,这只不过是周围地貌的一小部分,连五分之一都达不到。中国画讲究简约意境,画外有画,可它永远也画不出身临其境的诸多细节。
在白天,森林似乎安静得像一座古堡:枝叶被微风吹拂,发出轻轻的低语;蜀葵在溪水旁,结出一串花穗,野蜂在草丛中飞翔;屋后高大的古松下,一个大大的蚂蚁窝,蚂蚁们正在日光下忙碌着搬运食物。每天早晨和黄昏,我沿着屋后的溪水散步,时常与松鼠和野兔相遇,我们对视片刻,然后各自礼让地走开。极目远眺,巍峨的白山顶上飘弋着一团变幻多姿的五彩云朵,阳光投下的金线布满整个林间空地和每一片在风中燃烧的树叶。
有一次,遇到一只白狐,它先是在河的对岸一路小跑,似乎在追逐什么猎物,起初我还以为是一只流浪狗,但它优美的奔跑姿势比狗好看得多。它很快从独木桥上越过溪水,爬上土坡,然后一个箭步跃上了一堆被人废弃的木柴垛——这个木柴垛离我不过百米之遥。眼看着我与它的距离越来越近,我怕惊扰了它,只好暂时停下脚步远远地观察,并且有意地侧着身子向一棵大树靠拢,后来,我躲到树身后,可以方便观察和拍摄这只白狐的全貌。应该说,这只白狐太漂亮了,全身的皮毛简直一尘不染,它的眼睛像天使的眼睛,只是习惯性地眯成了一条细线,像一弯勾魂的新月,让人陷入迷幻。
我当时想,为什么这是一只独自活动的白狐呢?这么漂亮的动物不应该是孤单的。我怀疑,动物界大约是不分美丑的吧?在它们眼里,有的只是强悍与柔弱,这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丛林法则。
一只鹰隼从松枝上飞来,大概瞄准了河岸上的山鸡。只听得空中响起一声尖叫,机警的白狐从木柴垛上飞也似地逃遁。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只白狐,但我能隐隐地感知到它的存在,它的巢穴就在附近,它的影子在月光下游荡。有好几次,我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白狐的气味。这气味不太好闻,但很快便被森林的气息稀释覆盖。
在森林里,顶好闻的是雨后湿地散发的气味,树木经过一场雨的洗礼,很快发酵出馥郁的香气,松油夹杂着各种花草的香气,附近的河水也制造出比平时更好闻的气味。雨后,我提着一只篮子在松林里寻找从树上落下的松果和野果,以及從空地上突然冒出的野葱和野蒜。揭开一丛鼓起的软土,露出一只香喷喷的白蘑菇,再往前搜寻,又发现一丛黑木耳或野生猴头。那么,整整一天的食物都有了。每当篮子被各种野货塞满的时候,我便忍不住喃喃自语:“哦,大地是多么丰富、慷慨、奇妙!”
我把满满一篮子林中山珍拿到河边清洗干净,到厨房里收拾一下,从小冰柜里取出一块野猪肉,点燃木柴,把野味在灶前慢慢炖熟煨烂,让香气飘远,飘到河的对岸,炊烟在水面上飘散,在森林上空萦绕。饭做好以后,我把野味盛到碗里,端到河边一株躺倒的红松旁边,望着流动的河水,坐在树身上大快朵颐,野葱蘸酱的味道招来一群游鱼,在脚下吐水泡泡。
当然,在白山度过的那个夏天,也不全是浪漫和宁静。比如,有一次,一只白色大鸟在深夜突然降临到我的窗户前,它制造出的动静着实吓了我一跳。它有着长长的鸟喙、尖尖的利爪、古怪的叫声,和一双能够刺穿黑暗、散发幽蓝荧光的眼睛,尤其骇人的是一双巨大的翅膀,张开来几乎占据了整个窗户。
我对生物学的功课做得不够,至今叫不出它的名字。好在夏天很快过去了,我的林间写作也告一段落,我便收拾行装,离开了那幢诗意的森林小屋。
第二年春天,我又来到白山,特意开车绕了好远一段路寻访故地。远远看去,那幢小屋子居然还在,只是屋子周围被一根根白栅栏圈住了,栅栏门上还落了一把铁锁,已经锈迹斑斑。
白桦树皮
“嘿,你做的白桦树皮灯罩收到了。”当快递员把包裹传递到我的手里,我一时呆愣住了。对不起,从白山归来,便陷入日常忙碌,竟然忘记了我们的林间约定。
但当我打开邮件,内心瞬间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悦占据——这只白桦树皮制作的灯罩,薄如白纸,更像透明的蝉翼,带有天然的纹理。白桦是俄罗斯的“国树”,是举世公认的“艺术之树”。而这只灯罩太漂亮了,通体散发树木的清香,让我的灵魂瞬间插上翅膀重返白山。我把灯罩摆在案头,仿佛感知到自然的空灵与神性——自然赋予白桦树皮以生命和呼吸。灯罩同时带有你的灵性和你的气息,让我觉得你时时在我身边,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坐在书房里努力工作的情形,我冥思苦索发呆的面容。谁都无法想象,它的前身来自一种北方树木,经过你一双巧手的精心改造,演变成了一只沾满幸福味道的灯罩。
从此,我幽寂的书房里有了一盏桔黄色的小灯,它陪伴着我孤独落寞的夜晚,陪伴着屋檐的露水、墙角下的猫,以及蝙蝠、蜘蛛、蛐蛐和各种夜游的生物。眼前已是夏天,窗外又开始落雨了,阳台上从白山采来的松枝还泛着青绿,你送给我的登山木杖,还沾着河滩卵石的水草屑。
在通往白山的路上,阳光浮动,天高地阔,溪水在路两边流淌,树叶在风中喧哗有声,水边摇曳着野花。微风拂面,把沉睡一冬的心情也吹醒了,我打开封闭多年的话匣,对你讲述我的困惑、我的内省、我的焦虑,以及我对于未来的一些不成熟的设想。在路上奔走了这么多年,航标灯依然在黑夜的心海照亮,北斗星在头顶、在滩涂、在茂密的桦树林上空寂寞燃烧。
车轮滚动,碾过初夏时节起伏不定的柏油路;车轮像读秒器,一页页翻过,阅读着大地这部无穷无尽的天书:丛林、田野、山岳、河流、湖泊、微风和低矮的乡村农舍。每当经过一座屯子,我们都停下车来,进行一番考察。我们看到老人在树阴下闲叙家常,一只黑狗在柳树身上撒尿,女人端着簸箕到场院里晾晒大豆。而男人们早早醒来,赶着牛车,到黑土地上开始一天的劳作。白山脚下的一些屯子里,一些年轻人走了,到遥远的城里打工谋生,挣钱养家;另有一些年轻人读完了大学后,却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故乡,让双脚重新沾满了白山的泥巴和麦草屑。有许多从异乡的城市落户到屯子的年轻人,在这里娶妻生子,成了白山永久的居民。他们说:“白山空气好,水土好,在这里度过一生是值得的。”
好空气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稀缺资源,而原生的水土,是让一个地方葆有一世宁静和生生不息的前提要素。一切都没有那么复杂,选择适合个人的生存环境比你追我赶、失魂落魄的从众心态重要。我不由地想起我从前的居住地,那个以工业增长速度著称的城市,长期以来,天空看不到清晰的星月,流淌两千年的河流枯竭,曾经郁郁葱葱的山林光秃,摩天大厦遮挡住了日光,让生命一天天发霉变质。
是的,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真正有责任感的智者、思想者和科学思维精英分子,是持续的建设性和对自然法则的足够尊重,是一种能够经得起时光追究的内心秩序和接纳宇宙八面来风的开阔格局,而不是一场又一场的功利表演和言行不一的人格分裂及扭曲。
在白山茂密的白桦林中,我们忘情地陶醉于野生灌木和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仿佛置身于列维坦的名作《白桦丛》中的画境:明亮的光线,茂密的草丛,清澈的溪流,美丽的白桦……我们搂定一棵高大光洁的白桦,与树身上的一双双眼睛互相对视,沉默良久。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是一双双神灵的眼睛。在这片人迹罕至的白桦林中,我们发现了一株被风吹倒在地连根拔起的白桦,它的树身上有被松鼠咬啮的痕迹,有被暴风雪猛烈打击的痕迹。烈日吸走了它的水分和汁液,野兽曾经朝它身上泼洒污水,不知是哪一年的山火焚毁了它的根须,树干也开始糟烂腐朽。它死了,从植物学的角度而言,它已经没了生命感知,没有了担忧和苦痛。但它的树皮却依然光滑鲜亮,可以制作一百只灯罩。
你小心地把这一片片伟大的树皮取下来,放到一块蓝布头巾里。
萤火天堂
傍晚,我照例在林间散步,不小心进入了一处山崖与峡谷布置的迷阵,细雨及时地飘落下来。
眼前忽现一个山洞,洞内通明,隐隐传出阵阵奇妙细小的微响——我被吸引,快步走了进去,顿时被洞内的阴凉气息袭击。我发现山洞很大,幽深不见出口,湿漉漉的石壁上聚满了流水,一些细小的葛藤顽强地从石缝中探出叶片;而洞内的一片光亮在忽高忽低地起伏飞翔,把山洞营造得扑朔迷离,如梦似幻。
起初,我还以为是森林管理员精心打造的效果,或者他们要开发这个山洞,以此招徕游客。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判断,因为山洞外太狭窄了,脚下即是万丈深渊,开发空间几无可能。
那么,洞内的光亮究竟源自何处呢?至今是个谜。当然,我怀疑是萤火虫,因为只有它们身上背负着一个小小的发光器,夜晚发射神秘的光源,在黑夜的屏幕上划出一道道轨迹——试想,如果追溯到远古时代,旷野茫茫,夜幕如铁,这道道光亮的出现是个多么伟大的奇迹。
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曾经在故乡水库旁边的营地度过一个漫长的假期,每天在生满芦苇的水中游泳嬉戏,时光一晃夏天转瞬过去。有一次,夜幕降临,我提着泳衣走上堤坝,穿过林间返回营地,忽然发现有成群的萤火虫在我周身飞翔,它们没有声音,却照亮了林中道路。那一刻,我置身森林,左顾右盼,脚步轻盈,仿佛进入天堂般的梦境。
自那以后,我便格外怀念这一缕缕微弱而神奇的萤火。当黑夜行走在荒野上时,它們便和夜空的星群呼应,在我眼前飘荡,让我接受上苍冥冥之中的暗示。我在瞬间获得了安宁,面对眼前的处境坦然而从容,不再疑虑,也不再恐惧。其实,在人类的生活中,只需要一点萤火的光照就够了,就可以把凄苦的日子酿造出希望的蜜浆。
还有一次,我在下山时遇到三只梅花鹿,它们隐藏在美人松后的雪窝里。起初,看不到它们的长脖颈和脑袋,树身下闪动着几只毛茸茸的尾巴,后屁股居然静止到一动不动。显然,是我们在山上的说话声惊动了它们——人在山上说话,哪怕声音不大,也会像石子一样滚下山坡,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山下的生灵耳朵灵敏,老远就能听到。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白山原本是一座神山,可以喷火,也可以涌泉,山上山下被互相打通,自然也就没有秘密可言,人说的每一句话连山上的草都能听懂。当你在山上唱歌,说些吉利的话时,漫山的动物和植物都会跟着高兴,随风舞蹈拍手鼓掌。如果你在山腰上不小心跌倒或者受伤了,嘴里发出抱怨和责骂声时,整座山都会黑下脸来,山体飕飕地向外散发冷气。
那天,鹿们一听到人语,便躲到了大树后,屏住呼吸静等人的脚步声远去。只是,这次遇到的三只鹿未免太憨厚朴实了些,觉得眼睛避开了人,人就看不到它们硕大的躯体,这样就算藏了起来。因此,我们当即认定,这是动物界中品性良好的三只鹿,没有什么城府,对人类更是无害。
与其它的猛兽不同,白山一带的梅花鹿以温柔著称,尽管身材高高大大,却是动物中最面善的族类。通常,它们与世无争,对任何动物都表示友好。鹿的眼睛流露温和,声音也是和声细雨的,让人感觉亲近。在世界面前,它们永远投去平静温驯的目光:没有哀怨、没有挣扎、没有欲望……常常,鹿身上无端地落满了苍蝇,落满了麻雀的粪便,落满了雨雪和冰雹的刀剑,但它们总是若无其事地从容散步,面带微笑,隐忍着走过危险的布满陷阱的丛林。夏天,雨水瀑布一样泼洒下来,可爱的鹿们只是伸出粉红的小舌头,舔舔雨水,用身体蹭蹭崖壁,内心企盼着阳光的照耀。
当我在林间游历,面对千年火山岩石和躺倒在地的百年枯木,灵魂时常被巨大的孤独感充塞,感到失望而无助,觉得生命在天地间如此渺小,人生太短暂了;但当我转身向后朝丛林深处走去,看到雨后的草地上野花绽放,叶片上的露珠闪烁光亮,我又情不自禁感到生而为人的庆幸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