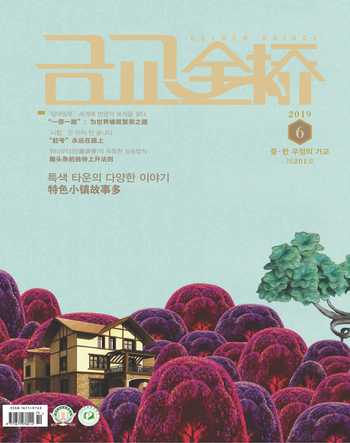读《世说》,感怀魏晋风骨
凡一



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句句脍炙人口的经典佳句,至今为人诵读,朗朗上口;难兄难弟、拾人牙慧、一往情深、卿卿我我……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历尽传承,今天,仍被人们信手拈来。不过,关于它们的来源出处——《世说新语》未必众所周知。
《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刘宋年间,作者是当时的临川王刘义庆(一说由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后人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故又名《世说新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
全书原8卷,梁代刘孝标注本分为10卷,今传本皆作3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36门,全书共1000多则,记载了从汉末到东晋年间,上流社会王公名士的嘉言懿行、奇闻轶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传世名著。鲁迅称其为“一部名士的教科書”,冯友兰也把《世说新语》当作“中国人的风流宝鉴”,而大翻译家傅雷对此书更是爱不释手,他在写给儿子傅聪的信里说: “《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它当做枕中秘宝。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特立独行的人物和精彩纷呈的故事,既有对一些孝子、贤妻、良母、廉吏事迹的表彰,也有对士族中某些人物贪婪、酷虐、吝啬、虚伪行为的揭露和讽刺,读之如行山路,移步换景,美不胜收。
此书的编纂成书固然与刘宋家族对魏晋风流的喜好和追慕有关,然而刘义庆之所以对魏晋人士情有独钟,花大气力与其门客共襄盛举,还有他个人身世的内在原因。
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堂侄,在刘宋诸王中也是颇为出色的人物,自幼就为刘裕看重。
他为人性简洁、寡嗜欲,爱好文艺、富有同情心,但他不热衷于政治,虽一生历任要职,在政治才能和政绩上却是乏善可陈。除本身个性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卷入刘宋皇室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刘裕死后,为了争夺王位,刘宋宗室骨肉相残、同室操戈的血腥场面不断,为避免卷入这场漩涡风暴中,刘义庆请求外放,远离京师,以退让的处世哲学,逃避险恶奸谲的政治圈。此后他便寄情文学,将经世之才驰骋于文章,以求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一书。
书中用大量篇幅记载了魏晋名士的清谈,其中有一组人真正能代表这时期士人狂放的新人生观,他们就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成、尚秀、王戎等7人。由于他们常在竹林聚会,纵情畅饮,世称“竹林七贤”。七贤的才学、声誉甚高,他们种种任性荒唐的行为,为西晋以后贵族子弟争相效仿,后代也将晋代的淫逸之风归咎于七贤。其实七贤的狂妄行径,并非无所为而为,追根究底,都只是要表达对世界的反抗。
可惜的是,《世说》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便身患重病,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
《世说新语》作为一部笔记小说,由于其内容有创新性及丰富性,而且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自然成为历代创作竞相仿效的原典。例如,元朝关汉卿的杂剧《温太真玉镜台》、明朝杨慎的《兰亭会》、明朝陆采的《怀香记》等,都源自于《世说新语》中脍炙人口的故事;而《三国演义》中的“黄绢幼妇”“击鼓骂曹”“望梅止渴”“七步成诗”等故事情节也均取材自《世说新语》。
不仅如此, 《世说新语》还将许多情节铸成生动的文学语言,在历代的沿用之下,成为许多众人熟知的成语,如:身无长物、皮里阳秋、期期艾艾、鹤立鸡群、覆巢之下无完卵等。
而且,《世说新语》善用作比较、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年耶!”是东晋名士桓温的名句,就出自《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特立独行的人物和精彩纷呈的故事,既有对一些孝子、贤妻、良母、廉吏事迹的表彰,也有对士族中某些人物贪婪、酷虐、吝啬、虚伪行为的揭露和讽刺,读之如行山路,移步换景,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