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官员偏爱籍贯地的机制研究—基于资源转移的视角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徐现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李书娟 本文节选自《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本文认为,官员籍贯地偏爱源于资源转移。在任的官员关注籍贯地发展,有能力为籍贯地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籍贯地则拥有了相对更多的公共服务,从而籍贯地的资本边际产出更高。在统一、竞争性的资本市场上,其他地区的资本将会流向籍贯地,直到两地的资本边际产出重新相等为止。这种资源转移最终将转化为两地间的经济绩效差异,从而出现文献所观察到的籍贯地偏爱现象。简言之,地方官员关注籍贯地经济发展将通过市场竞争带来资源转移,从而出现籍贯地偏爱现象。本文把这一想法模型化,在一个简单的资本竞争模型中证明了这条机制的存在性。
本文考察了一个看似异常的现象—官员偏爱籍贯地发展。籍贯地既可能在其辖区内,也可能在其辖区外。现有文献主要考察官员发展辖区经济的激励机制和手段等,还没有考察官员偏爱籍贯地发展的机制。因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究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
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竞争性市场上当官员关注其籍贯地经济发展时,资源将向官员籍贯地转移从而出现地区偏爱的现象。在实证上,本文采用1998—2013年间的全国县级层面的制造业数据,发现省内制造业资本向官员籍贯地转移。省级官员在任期间其籍贯地制造业资本平均增长约1.5%,制造业企业数量增长约9%,进入率提高约4个百分点,退出率下降约13个百分点,但企业的平均资本规模没有显著变化。另外,本文还发现无论是采用总产值还是灯光亮度度量,籍贯地经济增长都提高了约2%。
精准扶贫中群众的“求贫”心理与情感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卫小将 本文节选自《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7期

我们聚焦于近年来扶贫工作中出现的“求贫”和“争当贫困户”现象,诉诸于情感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进行了剖析。
一方面,“求贫”心理的生成是一个社会情境和个体行为互构的结果。从社会情境看,社会软控制机制开始式微,社区对于个体的软约束力逐步开始“失灵”,与此同时主流社会不断的建构“贫困者”的需求和匮乏形象,贫困也开始逐步走出个体化和去道德化并迈向社会化,再加上消费社会和个体社会对于“物质万能”的默会知识的形成,这些交织形成了情境性因素。就个体行为而言,贫困的责任主体由个体逐步向社会外推,问题内化导向问题外化,贫困个体沿着主流的社会建构而积极建构自身的需求,承担“贫困名义”带来的物质资源远大于“污名”的付出代价。这种个体和情境的交织作用形成了“求贫”逻辑与机制的。
另一方面,对于“求贫”的情感治理需要诉诸“以理驭情”和“以情治情”两大理论框架,主要围绕三类群体展开。
一是针对扶贫工作者应悬置“情感(热情)扶贫”,回归科学理性和专业扶贫,以强化其持续动力。
二是针对贫困群众,根据其情绪和行为特征同样分为三类群体,第一类是长期贫困者,基本将贫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此单一的物质给予是很难获得改变,应致力于“贫困亚文化”进行干预,激发其改变的动力。第二类是刚刚陷入贫困者,他们的常态生活打破堕入贫困状态,充满怨恨与不满,并不缺乏改变的能力,而是缺乏资源与机会。对此,在提供宣泄渠道和安抚怨恨的同时应提供资源与机会,使其重拾生命的连续性。第三类即将脱贫者憧憬未来的同时对现实表现出不满,对此应引导其合理评估自我,巩固其改变的动力和持续性。
三是针对一般的群众的嫉妒、不满和失衡心理进行积极的干预,使其同贫困群众建立良好的情感纽带关系。
美国国会亲台势力的回潮及其影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台湾研究中心 信强 本文节选自《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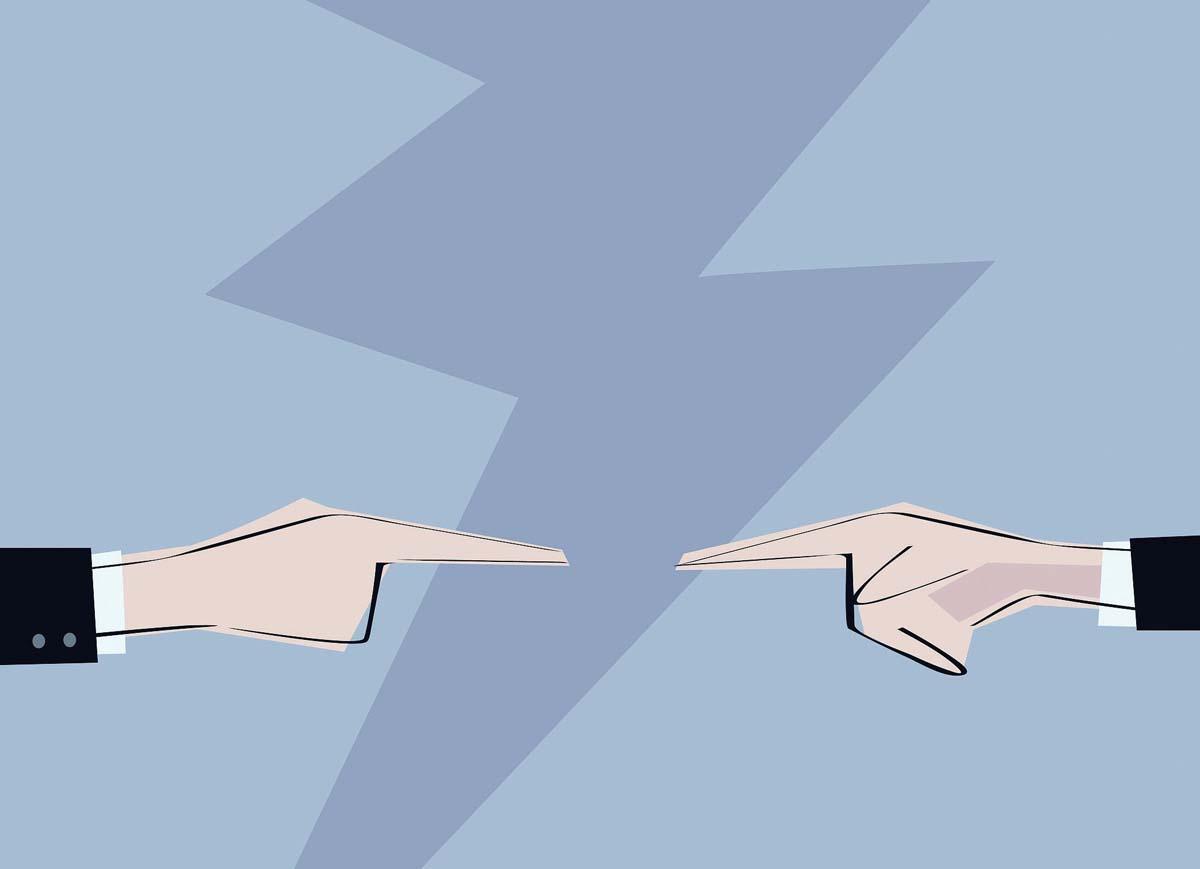
近年来国会亲台势力的回潮可谓势头强劲,立法提案的内容也日益富有挑衅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美地缘战略博弈的加剧为亲台势力的回潮提供了动力。自从台湾问题产生以来,国会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大的亲台势力。对于目前活跃的新一代亲台议员而言,其动因固然包含将台湾视为“民主盟友”的因素,但是更主要的驱动力量则在于,面对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已被视为一个“修正主义的战略对手”,是对美国霸权的“头号威胁”,亲台议员试图通过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将之打造成为一枚与大陆更加疏远和对立,同时也更有意愿和能力配合美国围堵大陆的战略棋子,以服务于其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霸权这一根本战略利益。
其次,两岸关系的降温为亲台势力的回潮提供了抓手。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流,亲台议员虽然也曾提出过一些法案,但是并未掀起太大波澜。而在蔡英文上台后,为了对抗中国大陆,台湾当局竭力谋求美国的扶持,从而为亲台议员利用台海局势的恶化,出台法案支持台湾当局提供了抓手。亲台议员一方面指责奥巴马“对大陆过于软弱”,另一方面则鼓吹必须“全面提升”美台关系,以显示美国对“民主台湾”的鼓励和支持。其实质就是要配合民进党“联美抗陆”的政策,为蔡英文当局坚持“台独”立场、抗拒统一的图谋保驾护航。
再次,亲台利益集团的复苏为亲台势力的回潮提供了助力。在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后,美国国内许多支持“台独”的利益集团和组织,如“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台湾国际联盟”等也随之复苏。此外,以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哈得逊研究所为代表的保守派智库,与“2049计划研究所”以及“全球台湾研究院”等立场完全倾向于台湾当局的机构密切配合,对美国国会、学术界、舆论界施加影响,合力推动美台关系的提升。
在当今中美两国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对抗性不断升高的背景下,国会在涉台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对中美关系的危害性也会更高。
第一,“红线意识”的淡漠,导致国会亲台议员不断挑战美台关系的“禁区”,从而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进而对中美关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近年来亲台议员所提出的诸多法案,其实质目的就是将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来对待,实现美台政治和军事关系的“正常化”,而这无疑将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冲击。较之于以往,当前亲台议员的立法提案内容,无论是要求舉行联合军事演习,全面解禁台湾当局高官访美,抑或是推动美国军舰访问台湾,均无疑是对“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红线”的公然挑战。
第二,行政部门制衡的弱化,使得国会亲台势力危害中美关系的种种挑衅行为不仅不会受到有效的阻遏,甚至在行政部门的默许与支持之下得以逐步落实。在美国外交决策体制下,总统及其掌控的行政部门往往会基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对国会不负责任的过激行为予以劝阻和制衡,扮演“刹车闸”的作用,以免中美关系遭到重创。但是特朗普本人显然对于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缺乏了解,从其与蔡英文通话事件以及签署《与台湾交往法》即可见一斑。
第三,新世代亲台议员的涌现不仅意味着亲台势力实现了“新老交替”,而且其表现更为积极活跃,举措也更具破坏性,从而势必会对美国涉台决策造成长期而深远的消极影响。在当前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制定的重要亲台议员当中,固然有一些老面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还出现了许多新面孔,其中不乏颇具前途的政治新星。这些议员虽然资历尚浅,但是却在涉台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活跃,成为亲台议员的新一代领军人物。随着他们在国会任职时间的增长,或是有朝一日进入行政部门占据权力要津,势必会对美国涉台决策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