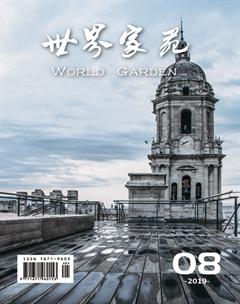中国特色法治实践视角下对“枫桥经验”的再认识
张兆宇
摘要:林业是一个国家农业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构成,林业产业发展的好坏对于一个国家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及经济提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林业发展重要的发展地位,我国林业产业也在不断革新与进步,特别是在林业育种方面,高产、高抗、耐寒的林业树种很受欢迎。本文中,笔者立足于我国林业产业发展现状,具体就林业育种质量的提升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林业育种;作用;发展前景
“枫桥经验”是1963年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并经毛泽东充分肯定为教育人、改造人的经验。
“枫桥经验”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采用调解的方式使得矛盾提前消解、就地化解,而在消除矛盾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本文将就此进行讨论,从而发现并克服“枫桥经验”的缺陷,使其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更强大的力量。
1“枫桥经验”鼓励将矛盾在当地化解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枫桥经验”提倡不将矛盾上移,本意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消解民众的不满。但若一味地强调不将矛盾上移,不鼓励甚至限制上级国家机关参与到社会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由于基层国家机关化解矛盾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不足,就有可能造成民众的不满,导致对社会矛盾的消除起到反作用。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主流思维中,民众天然的认为更高一级的国家机关拥有更高的司法权威性,能够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处理矛盾和分配利益,处理结果必定令人信服。尤其是中央国家机关,更是让民众无条件的信服。相反的,大多数的民众厌恶甚至恐惧基层的国家机关,认为基层国家机关无法做到公平更正的审判,其作出的决定极有可能导致自身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因此,在古代的社会中,民众往往尽力避免基层国家机关对自身的管辖权,或者至少不能让基层国家机关的审判成为最终结果,就会最大限度地寻求引起更高一级的国家机关的介入以解决矛盾,对于更高级别的国家机关的决策结果也往往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拥护和支持。而造成这一文化心理的原因是体制设计和生活实践共同作用所形成的:
(1)中国的国家权力的分配方式。自秦朝建立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以来,中国的权力体系分配方式始终自上而下进行的,权力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是自上而下逐级递减的。越靠近皇帝,和中央,则权力越大,合法性也越强。越是靠近基层,则权力越小,合法性越弱。一切权力的大小与合法性的强弱都来自于皇帝的赏赐,都取决于与皇帝的亲密程度。皇帝是国家的统治者,拥有天然的合法性,处于权力链条的顶端,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皇帝首先将一部分权力分割给了中央的国家机关和官员,因此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官员拥有仅次于皇帝的权力,在面对皇帝以外的国家机关和个人时便拥有了绝对的权威与合法性。在中央机关之下,地方国家机关和地方官员也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分割,但这一部分权力是小于皇帝与中央的。依次类推,当权力的分配到达与民众朝夕相处的基层官员的时候,权力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已经消耗殆尽。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民众所接触的并非国家官员,而是所谓“乡贤”,“长老”,这些人在国家统治机器难以触及的基层承担着国家的管理职能,但其并非是国家正式官员,因此其做出的决定也往往缺少足够的合法性。缺少合法性的国家机关和官员,做出的决策和审判既没有足够的力量撼动已然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也没有强大的动力实施公平公正的审判,自然难以保护民众的利益。
(2)中国的古代政治体制默许甚至鼓励民众博取拥有更大权力的更高国家机关的关注以解决问题。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司法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民众向更高级别的国家机关进行申诉和控告,例如,古代的“鸣冤鼓”即是允许民众越级上诉,国家机关借此发现冤情,消除冤案。更有甚者,古代的民众可以阻拦皇帝的出行为自己伸冤,所谓“拦御驾”,直接向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申诉冤情。如果确有冤情存在,甚至可以免除惊扰皇帝的严重罪刑。这些方式,确实为民众提供了上诉的渠道,也在潜移默化中让民众习惯于寻找更高层级的机关和官员为自己讨回公道。时至今日,上访仍然是我国获取案件线索和解决冤假错案的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精英与民众都始终认可将民众的越级上诉作为解决和消除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
(3)在现实的实践中,层级越高的国家机关,意味着更高的素质和能力。以审判机关为例,不同级别的法院,其处理案件的能力必然有所差别。相差的级别越大,审判水平的差距也就越大。从大体上看,更高级别的法院,其处理案件的能力和裁决的公正程度必然是更高的。正因如此,我国的司法解释也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而非其它层级的法院。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亦是如此。对于民众而言,能够获得更高级级别的国家机关的处理,就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得公正的裁决和审判;越向上申诉,就越能够获得更加优质的国家资源。此外,更高级别的国家机关与官员由于与一般案件的距离较为遥远,利益牵涉和情感纠葛更小,客观上也确实有利于作出更加公正合理的判决。
2“枫桥经验”鼓励将矛盾的解决过程前移
在矛盾产生之前就要预防问题、发现矛盾,采取预防的手段避免矛盾的产生。预警在先、矛盾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工作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在矛盾出现之后,力求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预防和调解的工作行为是由司法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所作出,这就会导致对司法权力的侵蚀与损害,并且可能滋生腐败与不公。
在“枫桥经验”的概念内,调解可以由很多部门做出:既有司法机关做出的调解,也有行政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所做出的调解。在不同主体所做出的调解中,毫无疑问司法机关做出的调解最具有权威性。这是因为司法机关的职责是独立公正的行使司法权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其唯一的追求。司法机关的调解的目的是为了让双方当事人获得公平正义;而行政机关则有所不同: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其职责是实现社会的有序管理,社会公平正义虽是其考量标准之一,却并非其唯一考量。这也就有可能导致其所做出的调解有可能因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调解的公平性,甚至为了达到行政目的而做出扭曲事实、損害公平的不合理调解。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调解活动中,由于其缺少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其所作出的调解活动容易变成“和稀泥”,不追求调解的合法合理,一味地息事宁人,导致调解忽略了对正义的追求,变成了让人保持沉默的工具。因此,当调解由司法机关以外的组织机构作出时,就很有可能产生不公正、不合理的调解,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3“枫桥经验”强调使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司法诉讼情形的发生
“枫桥经验”注重调解的倾向表现出司法审判行为是社会矛盾没有得到有效化解的表现,甚至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但这种观念有失偏颇。虽然“枫桥经验”所提倡的调解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加快社会矛盾的化解速度,是较为缓和平稳的追求社会正义的途径。但在很多情况下,调解,调解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并非是最优的选择。在基层矛盾的处理和化解过程中,不能将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的首选方式,一味地强调调解。即使审判活动较为冗长,费时费力,占用社会资源,但司法审判过程是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基层矛盾的处理和化解仍然需要坚持以司法程序(审判为主)为先的矛盾解决方式,不可偏废、主次颠倒。
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的手段,与审判相比,具有诸多劣势。
(1)调解过程较为隐秘,缺乏透明性,而缺乏透明性的地方往往容易被人为的操纵与控制,从而滋生腐败和不公。审判则恰恰相反,审判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公开透明,每一个案件的审判都是受到监督的,因此能够保证案件的公正公开,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2)调解的形式过于随意。调解没有固定的形式和过程,一切的调解行为都是调解人员与当事人按照具体情况随机应变。这就会导致调解的过程会有很多的漏洞,而这些漏洞一旦被人利用,就会造成当事人利益的损害和调解的不公,损害调解的权威性和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审判的形式则较为固定,并且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设计出一套较为完整缜密的流程和形式。因此审判的过程往往连环相扣、衔接紧密,不给人以利用制度漏洞的可乘之机,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司法权威。
(3)调解人员的专业性不足。主持调解的人员本身并没有受过专业的调解训练,往往身兼数职。一方面专业的调解技能不足,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其他事务而分散自己的精力。调解人员的这种天然不足会影响到调解的有效性,,会对调解的效果产生不利影响。而审判的人员往往受到过专业的司法训练,有相关的从业资格和技能。因此,进行审判的人员往往能够更好地实现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与保护,也能够更有力的维护国家司法的权威。
参考文献:
[1]俞红霞.““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J].中共党史资料,2006(02).
[2]谌洪果.““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生成模式[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01).
[3]吴錦良.““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J].浙江社会科学,2010(07).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