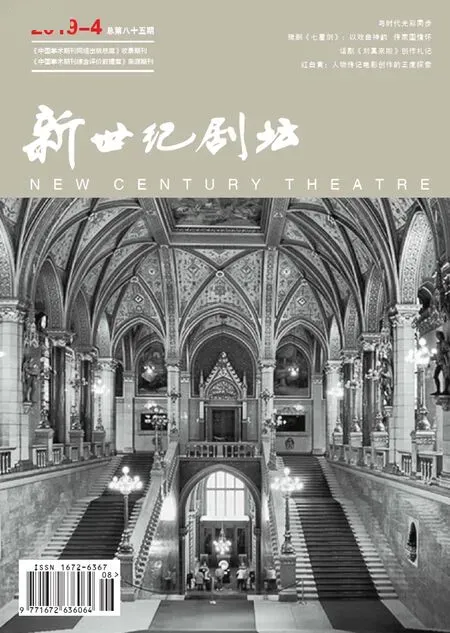精神光源对现实世界的可能观照
——以陈彦秦腔现代戏“西京三部曲”为例
蒋 演
触摸原典,其实更是触摸先哲们性情深处的本来温度,从而准确把握精神光源对现实世界的可能照耀。
——陈彦《对经典需有温情和敬意》
一
谈及中国戏曲,特别是在现代历史语境下讨论相关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及王国维先生,尤其是那本1913年完成的《宋元戏曲史》,已然成为我国现代学术史上戏剧研究的开山之作,亦奠定了现代中国戏曲研究的学术基础。自此以降,中国戏曲的现代研究框架与脉络得到了不断丰富与完善。先生开篇即追问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因此谈及戏曲领域的中华美学问题,就要沿着王国维先生的目光逆流而上,在民族历史文化这条河流上打捞和寻找属于我们最初的语言。对于原初性问题的追问常常是复杂的,亦是艰难和困惑的。牟宗三先生从中西文化互相照映的纬度出发对《庄子·天下》中的“一孔之见”进行了精妙的阐述,“所谓一孔之见,就是《庄子·天下》篇说的‘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就是一孔,你察察这面,我察察那面。人就是如此,道是完整的,它是个全。由于人各得一察焉以自好,于是‘道术将天下裂’”,“一孔之见”构成了一种边界,隐含了一种内在限制性。在“一孔之中”人就有了局限,而目之所及的外在限制性和身心所感的内在限制性也就构成了一种人在通孔中表现出的精神生活。
“道”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最早的宇宙观念和宇宙意识渊源于上古时期,从思想文化角度考察,“道”最初的意义是“道路”,后经不断引申与丰富成为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原语言,道最初来源于生活,后来又与生活分离,道具备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品性。而“问道”便是去寻找、去追问。因此,对中华美学的考察或者说追问,抑或建构,便是一种“问道”,既然问道,我们便在其中,在其中便有一种困惑,即进入“一孔”或“一察”。是故,先秦之前道家发展的“道”,亦或儒家发展的“仁”都源于最初的“道”,是对“道”的不同演绎。这里必要说明的是用“发展”而不是“创立”,在于从思想渊源之角度考察,“道”在老庄和孔孟等先贤手中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河流的原典高地,而源头并不在于他们那里,而在上古时期我们祖先“一孔之见”所洞悉的话语片段。所以,先秦之前道家“道”与儒家的“仁”都来源于我们民族最初的“一孔之见”,而这个“道”最初源于“生活”。后经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诸位先贤学问“交光互照”之后,错综复杂,逐渐生成了稳定的固象,用“道”字概括和提炼我们民族的美学精神最初的品性轮廓和基本概念是最为恰当的,也更能够把握和深入中华民族美学的精髓。也由此,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说的生命的学问。它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来安顿我们的生命。”

秦腔《迟开的玫瑰》剧照
无独有偶,宗白华先生在1943年撰写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指出,“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而‘道’则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后面他又进一步对“道”进行了阐述,“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出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因此,“道”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最初原型,后来我们的先贤皆通过那个通孔来表现我们的精神品质,建构属于我们的家园概念,而不同的话语片段均是以“道”为原型,不断推演、发展和丰富,用白宗华先生的话说就是“交光互照”。而戏曲作为兴盛于宋元时期的艺术样式,和诗、书法以及绘画相比,其历史远远在其后,而中华美学则多在后者中显现。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观点,抒情文学在于“情”,叙事文学在于“事”,而“戏曲文学的目的,却是那外境事实和内心情绪交互影响产生的结果——人的‘行为’。”因此,在他看来,戏曲的中心,就是“行为”的艺术的表现。由此,戏曲是文艺最好的制作,也是最难的制作。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开篇考证戏曲起源问题时,强调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巫觋祭祀属于严肃的,流露着人混沌的宇宙观念和意识,而优则具有“弄”的含义,在一定意义上“优”脱胎于“巫”。因此,戏曲自诞生以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有些尴尬。是故,戏曲作为一门独立的门类后,它的美学精神也是多元化的,它本身是综合的艺术,很难去概括。因此,多涉及“道术”层面的问题,即所谓的艺术形式和方法等,比如“程式化”、“虚拟化”、“意象化”等。因此,戏曲既然作为一种行为的表现的艺术,那么关于戏曲的中国美学还是要回到中国哲学精神的“道”中去,所以,戏曲的中国美学也于以人物“行动”来阐释我们的生命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以道为原、以经为宗”来建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然要表现人的行动,那么人物的品性也多以爱、德、义、礼、智、信、勇、和、中、忠、孝、悌、勤、廉、耻等作为评价标准而构成的“仁道”。因此,戏曲中所蕴含的中华美学多是以我们贤能之士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品行之德。而“程式化”、“虚拟化”以及“意象化”则是呈现人物身上的“品行”的技术问题,使以舞台为空间建构起来的艺术表演便于接受和传播。考察优从巫中脱胎出来这一源流,不难理解王国维等诸公的深意。
二
这里举要的陈彦的“西京三部曲”是指其创作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三部秦腔现代戏。它们都取材于发生在西京城的真实故事,对其进行艺术升华与创造,使其符合戏曲表演的艺术要求。如《大树西迁》根据20世纪50年代以交大为代表的一批高校、科研院所响应党的号召,从沿海大规模西迁内地,投身于西部开发建设这一史实为背景创作。全剧讲述孟冰茜教授一家三代人西迁五十年的奋斗历程,展现了共和国知识分子“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的理想信念,体现了他们前赴后继、甘于奉献、勇于吃苦的高尚人格和家国情怀,同时也表现了陕西人民对西迁一代知识分子的尊重与呵护。
从内容的角度来讲,陈彦的“西京三部曲”把握了时代社会中的人物行为。
陈彦的“西京三部曲”能够成为秦腔现代戏的代表作的意义也在于此,这一点是戏剧艺术的普遍性。何为普遍性,就是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都表现出人的奉献精神,无论是为国家社会、还是为家庭,有人要走向“塔尖”,就要有人去托举起他们,陈彦的“托举”这个词用得很传神。这就是作者在处理现实素材与艺术理想需要的一个姿态。以《大树西迁》为例,九十年代初,孟冰茜过生日,祖孙三代欢聚一堂。孟冰茜得知儿子在工作中冻坏了脚趾,辐射毁掉了他浓密的头发,孟冰茜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工作繁忙的儿子就要赶回新疆,询问孟冰茜技术问题,她决定与儿子一同前往。新世纪到来时,孟冰茜已回到上海,周教授代表西交大的学子们希望孟冰茜能再回西安,并为她弹唱了秦腔,在孟冰茜犹豫之际离开。最终她唤来女儿收拾行李,回到西安。在苏毅教授的纪念碑前,孟冰茜一家老少三代人与所有交大学子一起向苏教授献礼,感慨西迁,感恩一代西迁人。整部戏把一家三代人支援西部建设、敢于奉献的执著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们相互“托举”的姿态照亮了整部戏。

秦腔《大树西迁》剧照
陈彦在散文《西安赐我戏剧》中交代了“西京三部曲”题材的来源,比如《迟开的玫瑰》最初源于一个通下水道师傅。作为社会底层的一份子,他处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末梢,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要疏通社会底层的污水管道,下水道和自来水管道共同构成了城市的地下和地上的巨大网络,这也是一种结构,但下水道见不得光。社会结构的单元是家庭,家庭某些隐秘的东西其实也见不得光。通下水道师傅触发了陈彦从底层社会到整个社会运转的思考,“想想下水道师傅,想想社会底层对于整个社会运转的作用。最后落在一个家庭中,构想有人欲登上社会的‘塔尖’,不知其中作出牺牲的成员,是怎样一种托举的姿态和无法与人道来的窘迫。”同样,身处社会结构末梢的农民工,由乡村进入城市,为了托举家庭中那些欲登社会塔尖的人而付出和托举的方式,也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陈彦的《西京故事》。在《西京故事》中作为在繁华都市底层打工者的代表,罗天福勤劳善良、吃苦耐劳、保守隐忍。他以卖饼为生,以诚实劳动,合法收入,推进着他的城市梦想。他以最卑微的人生,最苦焦的劳作,默默无闻,恪守做人的本分,坚持着一些大人物已不具有的光亮人格。正如东方雨老人所说的罗天福就是“民族的脊梁”。然而他的生存法则在城市巨大冲突和矛盾的洪流中却遭遇着各种冲击,儿子的虚荣心挫伤后滑向“叛逆”,女儿则选择承受和迎难而上。特别是儿子离家出走后,在矿区寻找到儿子时,罗天福的跪地妥协,老泪纵横的场面,把人的无奈、无望、绝望表现得慷慨激昂,让人内心惊颤不已。
总之,陈彦的“西京三部曲”于时代社会中准确地把握了“人的行为”,特别是对时代底层人物群体精神的概括与提炼。《迟开的玫瑰》中的大姐乔雪梅在家庭遭变故后,承担起了家庭“母亲”的角色,三十六年知行合一默默奉献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而在剧中与大姐乔雪梅有同样地位的另一主角则是那个通下水道的许师傅,前者奉献为家庭,后者奉献为社会,前者是明线,后者是暗线。大姐的精神光芒照耀着许师傅,最终走到了一起。《西京故事》中则展现了农民工罗天福和妻子淑惠对于儿女的奉献,而这部戏也获得较高赞誉。陈彦的“西京三部曲”如果说从大到小划分其人物的奉献,那么依次可以看作是:对社会的奉献、对家庭的奉献、对亲人的奉献。戏剧作为一个以“小空间”表达“大内容”的艺术形式,所囊括的内容信息太多,观众的“四识”为“眼、耳、身、意”,若要体味艺术空间展现出现实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很难的。因此,要“聚焦小”,“以小见大”“可见一斑”,戏剧要做到“真实、丰富、深透”,“力透纸背”却又“气韵生动”,融汇“写实”与“会意”的暗功夫,把“人的行为”展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戏剧只能以“横截面”展现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或一个棱角,没法实现“史诗般”的品质,诗、小说、影视等可以实现。所以陈彦《西京故事》功夫也在此处,后来陈彦把它改成了小说,这是另一回事。当然,小说改编成戏剧那也是要抓精髓,同样的道理。
从形式的角度来讲,陈彦的“西京三部曲”正确处理了“戏曲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陈彦通过对于秦腔艺术史料以及其艺术大师的“阅读”,完成了《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这三部秦腔现代戏,在《坚挺的表达》一书的开篇《生命的呐喊》中,陈彦写道:“截止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哪一门艺术能够如此酣畅淋漓地表达一个人的生命激情,如此热血涌顶地呐喊着一个人生命的渴望,如此深入腠理地宣泄一个人的生命悲苦,那就是秦腔,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待见不待见,珍视不珍视,它都以固有的方式存在着,不因振兴的口号乎得山响而振兴,不因‘黄昏’的论调弹得地动而‘黄昏’,也不因时尚的猛料生氽桑拿蒸馏煮而时尚,总之是我行我素,处变不惊,全然一副‘铜豌豆’做派。”作为一个剧作家,他知道我们的传统艺术植根于我们身后的文化,那是浩浩荡荡气势雄浑的五千年文明,那是我们的底气,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源所在。秦腔和其他传统戏曲一样,我想都是在表现生命的“一口气”。这口气,其实和前面我们提到的“生命的通孔”“一孔”或“一察”是一致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这三部秦腔现代戏中分别表现了人物的“底气、勇气、正义、和气、怨气、力气、怒气、语气、叹气、福气、戾气、神气、俗气”等等,也正是这些在人物行为中展开,我们通过行为看到了他的精神征象,在内心中可以描绘出他的大致轮廓。再来把目光拉回到两晋南北朝时期,那是一个“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把“文气”提升到很高位置,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后来所谓的“文以载道”狭隘化了。

秦腔《西京故事》剧照
我们再回到“西京三部曲”上来,陈彦洞悉和表现了时代中我们人民群众身上的生命之气,这就是时代生命身上的精神征象。我们看到了社会进程的曲折,也看到了人物的“托举”姿态,“底气”“勇气”“正气”“和气”“力气”与“怨气”“怒气”“戾气”“俗气”等等共存,矛盾也就出来了,这就有了戏剧的张力。戏者弄也,读读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剧史》就知道戏曲“自巫优二者出”。我们可以这么说,巫术祭祀则多反映人精神的“底气、勇气、正气、力气”,至于“和气”“怒气”“戾气”“俗气”则多有“弄”之意。当然二者很难明确区分出来,我们“生命的通孔”表现出来的最初概念应该是“混沌的”。盘古开天辟地,天地分离便有了区分。
总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都把“戏曲传统经验”作为根本,这是我们“生命的碗”,这是“我们的血气”,生生不息来源在这里。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曲戏传统经验”是我们民族艺术生生不息的“毫末”和“累土”,这是“托举”民族艺术大厦第一步,这一步有底气、有力气,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第二步,这样我们就会失去了走路的技能,那我们遗忘的是“自我”,我们遗忘的是“我是谁”的问题,也就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古今中西都在不断重复一句话,认识你自己。不论苏格拉底,还是孔子,其实都是在教导我们如何认识自己。陈彦在“传统戏曲”与“现代化”之间,准确说是戏曲的现代化,找到了平衡之道,知道根在哪里,知道本末所在。至于举要“西京三部曲”的舞台呈现的详细阐释,因为不同导演观念不同,所以很难总结概括。要说“戏曲现代化”中“歌舞元素”不断在强化,使得“戏曲不像戏曲”,舞台空间依靠技术手段增强呈现效果,比如“音效、灯光加强了虚拟化和意象化的效果”,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很多,在此不一一阐述,我以为价值并不是很大。
三
其实,上面已经提到了中国戏曲的传承与创新问题。以下观点,我想只要我们回过头去看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前后的文献资料,可能更有益于我们思考中国戏曲的传承与创新问题。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这话是老生常谈的道理。“生生谓之易”,没有变化何来生生不息呢?笔者以为要建设中国戏曲,其实当下之意就是如何有效推进中国戏曲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之间需求一种解决之道?这就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随着消费主义文化风起云涌,影视把我们老祖宗的饭碗砸得稀巴烂,可谓到处都是窟窿。庄子是个伟大的哲学家,那篇《天下》大家可以找来读读。笔者以为“程式化”是中国戏曲艺术经验的血气,如白宗华先生在《戏曲在文艺上的地位》所言,传统戏曲中“人积习深厚,积势洪大”,“有许多坚强的特性,不能够推翻,也不必推翻。”这就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态度和原则,改良戏曲内容和一些不合理的程式化,使其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当然戏剧的中心始终是人物,戏剧表演是以“人”饰“人”,以“行动”演“行动”,以“现在”表现“过去”或“未来”,这体现为一种“游”的美学精神。
那么如何“去游”就是一个问题,或许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可供我们参考一二,先生的境界说,我们细细想之却有一番韵味。在《人间词话》中先生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而现代戏曲却游而不知所踪,在“造景”一脉中大作特作,我并不反对技术,但“道法自然”要始终有度。传统戏曲中,一人挥手瞬息,人生的色与空皆生,悲、欢、离、合缓缓呈现出来。读读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再读读评论家李敬泽则的那篇名为《修行在人间——陈彦长篇小说〈装台〉》的评论,我想已经足够启发我们。传统戏曲的精妙在于“化实为虚”,把巨大的社会历史结构运行体系囊括于“方寸”之间,那一挥手,便是“一孔之见”,也是我们传统戏曲的天地观念所在,它与我们最初的宇宙观念和意识血浓于水。因此,笔者以为人物的行动是戏剧的核心,而演员则是舞台的核心,当然“现代戏剧”出现了“导”和“演”本末颠倒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外在的社会“繁华”与“喧嚣”很容易吸引我们的眼球,物欲横流和理想主义微式之下,很难免不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