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现实,也“看到超出表象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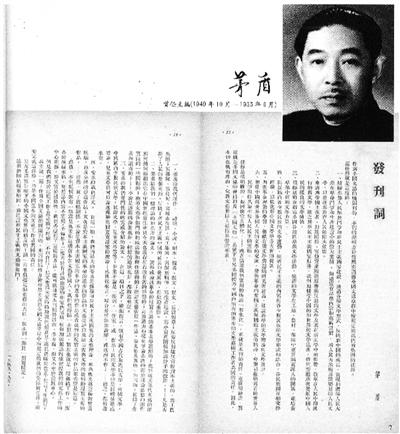

《人民文学》也伴随着整个开放改革的年代。复刊之后, 《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时代的文学作品,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刘心武的《班主任》、何士光的《乡场上》、王蒙的《春之声》、高晓声的 《陈奂生上城》和北岛的《宣告》等。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发自北京
1976年,在科尔沁草原上读小学三年级的施战军,家里订有刚复刊的《人民文学》杂志。这个具有一半蒙古族血统的少年也许想不到,三十六年后自己能和文学史上的人物茅盾、张天翼、王蒙一样,成为这份国家级文学刊物的主编。
在家里订阅的另一份杂志《中国青年》上,施战军读过至今还印象很深的两篇小说——韩少功的《飞过蓝天》和王安忆的《庸常之辈》。
还有两位民间前辈影响了施战军。
施战军将要小学毕业时,“乡绅”一样的邻居王爷爷常揪住他,给他吟诵古诗和老庄、《论语》,让他跟着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还有一位姓沈的姨夫,会英、日、俄三种外语。他用俄语背诵普希金的诗歌,却更喜欢叶赛宁;又大声用英语背出《李尔王》片断,还说看到的译本都不算好,将来最好能读原著。
在那所并非重点的高中,一年只考上施战军一个文科大学生。在四平师院(注:现名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常泡图书馆的施战军获准进入教师参考室,翻阅了不少善本和现代老期刊。他读完了能找到的“二周”——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的著作,又延伸到沈从文、李健吾、芦焚、萧乾和李广田等一批京派作家。
施战军感到当代人对很多现代作家读得不够,比如师陀(注:作家王长简继芦焚之后使用的笔名)在上海郊区撰写的精短的小说集《果园城记》。其中《阿嚏》里那个活泼的小水鬼,对世界无比好奇,但世界对他只有不对应的回馈。“好多篇到现在还可以在《人民文学》发头条。”施战军说。
施战军得益最多的是李健吾,薄薄的《咀华集》令他呆住了——文学批评可以这样写。李健吾对福楼拜的研究和翻译可谓无人能及,戏剧、小说,以及散文《切梦刀》都有个性特点,“他是特别全面的一个好的、大的文学家”。他的一篇毕业作业是舒婷诗歌《童话诗人》的读后感,就模仿了李健吾、唐湜的文风。任课的杨朴老师很欣赏,他便留校任教于当代文学教研室。
1996年开始,施战军一边在山东大学教书,一边在《作家报》兼职做理论评论版编辑。在山东,他与年龄相仿的评论家王光东、张清华和吴义勤经常活跃地讨论问题,频频发表跟踪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对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令他将两者贯通考察,“现代文学越来越像后盾,写的文章以当代文学批评为主”。
施战军发现,评论家李敬泽为一套诗人小说家丛书撰写的短序“很有才华”。在北京一次研讨会上见面时,他约李敬泽在《作家报》开“小说月评”专栏。《作家报》停刊后,李敬泽的专栏转移到《南方周末》,更名为“新作观止”。
开始产生交集的两人当然不知道,他们将相继担任《人民文学》的主编。
“从学术上把他们 复归成原本的 样子”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第一任主编为茅盾。他还是中国作协前身全国文协的第一任主席和《文艺报》的第一任主编,鲁迅文学院前身中央文学研究所也是他签字批准成立的。
“我们过去的文学史有时候从某个缩略的角度单纯化一个作家,1980年代接受海外汉学影响的时候,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单纯化了一些作家,今天我们应该从学术上把他们复归成原本的样子。”在施战军眼中,茅盾应是“有坚定的唯物史观,又深谙文学精义的文坛引领者”。
1980年代,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人们展开了文学史另外的面貌,令公众感到需要重新解读和认识沈从文、张天翼、张爱玲和钱锺书等现代作家,一时兴起的“重写文学史”也与此相关。施战军认为这会产生偏向效应,当时对茅盾、郭沫若的评价带有逆反心理,甚至也有对鲁迅的质疑。
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和老舍的《正红旗下》,在施战军看来都是“半部杰作”,他观察到《红楼梦》对他们的影响痕迹。而茅盾在左翼文学时期的作品,被批评为有自然主义倾向。他写过《西洋文学通论》,研究最深的还是欧洲文学,“不能从阶级观念之类的角度把他看成很简单的作家”。施战军推崇茅盾的《蚀》三部曲,认为它们“把中国成长小说的模式都框定了”。
作为评论家,施战军特别注意茅盾的学术作品和随笔。像引起很大争议的《从牯岭到东京》,谈文学思考,论创作现象,其实是在坦陈和揭示心路历程,“表述得很坦然很深入”。
施战军还注意到,茅盾对创作和艺术性的审美相当重视,并一直保持敏锐。1950年代后期,在“大跃进”背景下,他发现了茹志娟、王愿坚这批作家,充满欣喜地及时评论推介,用“静夜箫声”形容茹志鹃的作品。在施战军看来,茅盾撰写的发刊词“由衷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寻绎法度”,涵盖如何书写时代、重视新人,坚持什么样的创作方向等等。
接替茅盾的是文艺理论家邵荃麟,之后两任主编严文井和张天翼都是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早在1930年代就以《大林和小林》闻名,后来又写出拍成电影的《宝葫芦的秘密》。
在施战军看来,张天翼也是在不同时期被不同角度“单纯化了的”作家。他早年跟戴望舒、施蛰存、杜衡是同学,一起办刊。他一度被视为“讽刺小说”大家。施战军认为,早于《华威先生》的《包氏父子》超出了“讽刺小说”的范畴,是白话新文学正典一路的光荣。可惜,张天翼是“前十七年”的最后一任《人民文学》主编。1966年5月之后,杂志停了十年。
1976年1月,《人民文学》复刊,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兼任主编。第一期发表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他是七名编委之一。这篇小说受到了批判,但结果并不特别严重。毕竟,中国历史临近巨大的转折点。
“文学突然回来 干预现实了”
1977年11月,以词作家和戏剧家闻名的主编张光年发现了一位文学新人刘心武,这位担任中学教师多年的作家带着他的《班主任》走向新时期。十年后,这位新人接替王蒙成为《人民文学》主编。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也是从《人民文学》开始的。”2008年从诗人主编韩作荣手里接棒的李敬泽说。不仅如此,《人民文学》也伴随着整个开放改革的年代。复刊之后,《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时代的文学作品,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王蒙的《春之声》、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北岛的《宣告》等。
进入19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发表了阿城的《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黑氏》、张炜的《一潭清水》等重要作品。在评论家黄发有看来,它们“具备了一种无法被时间迅速掩埋的审美穿透力与艺术生命力”。
施战军赞同这个评价。“最近在北师大驻校作家入校仪式上,好多人突然就说起了张炜的《声音》和《一潭清水》,而且故事复述得很清楚,那是他二十多岁时写的。”出席了现场的施战军说。
王蒙担任主编期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集中登上《人民文学》。黄发有形容这些作品“张扬个性意识与自由精神”。
施战军认为,现代主义强势耀眼,以“先锋”之名傲视“保守”“老套”的现实主义文学,但文学更多的民众基础还是在现实相关处。1990年代,个人化写作风潮达到顶峰,但如何与背后巨大的时运发生“化合关系”,作家和刊物思考得较少。1996年前后,刘白羽和程树榛任主编时期,文学突然回来干预现实了,谈歌的《大厂》等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出现在《人民文学》上。
“每当文学和现实之间产生一种‘贴身肉搏的情况,文学都会成为热点。”施战军说,近年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和阿耐的《大江大河》与影视的互动就是例证。
为缩短作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2012年之前《人民文学》已经开始提倡非虚构写作,口号是“人民大地,文学无疆”。梁鸿的现实非虚构《中国在梁庄》、阿来的历史非虚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就是这种倡导的实绩。
但现实在不断变化中,不会停留在某一时间点上静止不动。
“抓出这个时代的 代表作品来”
施战军小时候生活在充盈着大风、草甸子、沙坨子的科尔沁。前一段他又去内蒙古,原来满眼的沙丘、盐碱地不见了,代之以一片片杏树林、蒙古黄榆林,草葱茏树茂盛。风电的白色大风车矗立在蓝天绿地背景上,高科技覆盖了农业,牧民也使用起微信。
“我都认不出来了。”施战军思考当今文学应有的样貌,“通向相对物质上比较高级的过程中,人的新的生存状态、新的指望、新的欢乐忧伤是怎样的?”
面对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如何将之与艺术融合起来,对于作家是新挑战。2019年《人民文学》发表了有关内蒙古扶贫题材的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那个扶贫点现在一点贫困的感觉也找不到了”。直到作者艾平听到一位七旬老人几次回去寻找失散的姐姐的故事,才有了动笔的灵感。“如果只有一个扶贫的主面而其他都光秃,故事就没多少味道,甚至没法看。”施战军说。
“我们刊物是《人民文学》,不是以别的名字命名的,有包容也有审美边界。”施战军说。发表在1956年9月《人民文学》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作者何直就是时任副主编秦兆阳。秦兆阳编发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一批直面当时现实的作品。 “前十七年”时期,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都在《人民文学》杂志首发,《林海雪原》片段也先发表于这里。新时期之初,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创作发表过程中,《人民文学》责任编辑、后来的副主编周明不仅读稿子谈意见,还数度跟随徐迟到采访现场。
“我们今天也得抓出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品来。”施战军说,当下的作者有时还沉浸在个人化写作那种旧梦中,幻想、虚拟现在的生活,因此还要发挥编辑的作用。
1980年,受当时的主编李季之约,奔赴前线的徐怀中创作了代表新时期军事文学转型的领军之作——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自此之后,军事文学里的人、人情、人性才进入正典”。三十八年后,徐怀中把《牵风记》交给了施战军,这部作品刚刚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去年秋天我拿到小说稿时候就想,与九十岁老人的杰作有着创编关系,‘自豪‘荣幸等词真是太苍白了。”施战军说。
令施战军印象深刻的军旅作家作品,还有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徐贵祥的中篇小说《鲜花岭上鲜花开》、黄传会的报告文学《大国行动》、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说《科恰里特山下》等。从五六年前开始,《人民文学》每年8月开设军事文学专号,试图给近年军事文学尤其是新锐创作多些展示身手的舞台。他认为,在长久的和平时期里,虽然亲历战争的机会很少,但撤侨、护航、对抗性军事训练甚至军改中军人安置的故事,其展现的英雄主义精神依然吸引着读者。
对人和万物报以理解、体恤,然后再判断
2012年春天,与施战军交接时,李敬泽已经编妥的一期稿件中包括刘慈欣的四篇科幻小说。年底,《人民文学》和浙江宁海合办的柔石小说奖,聘请了作家莫言(注:莫言的《红高梁》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三期)担任评委会主任。施战军印象深刻的获奖作品,除了王蒙的《山中有历日》,就是刘慈欣的《赡养上帝》。
早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人民文学》就发表了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和叶永烈的《腐蚀》等科幻小说。“你得对时代的风气、审美风尚知情,还要看到超出表象的东西,有未来感。”施战军尝试进一步拓展科幻作品。 《人民文学》的外文版最初只有英语版《路灯》(Pathlight)一种。施战军跟总监商定了一个主题叫“未来”,以译介中国科幻文学为主,选择了王晋康、刘慈欣、郝景芳和陈楸帆等近十位优秀科幻作家的作品。这一期杂志推出后,在海外和国内都产生了轰动效应。
《人民文学》2015年第七期又推出“科幻小说辑”,发表了《三体》英译者刘宇昆的《人在旅途》、陈楸帆的《巴鳞》和宝树的《坠入黑暗》等短篇小说。《人民文学》2019年第七期上王晋康的《宇宙晶卵》,是该杂志第一次发表长篇科幻小说。随着《人民文学》外文版扩大到日、德、意等近十个语种,韩松、夏笳、宝树、飞氘、杨平等人的作品陆续被翻译发表于中国科幻文学专号。
重视科幻作品,是推进文学多元化发展的自然结果。
施战军的蒙古族姥姥有三个亲生孩子,收养了更多孩子。逢年过节,院子里停满车马,来了数不清的说蒙古语的阿姨和舅舅。他多次跟随妈妈和舅舅去草原深处的亲戚家,听他们唱长调短调,开阔透亮又婉转伤感。“我读契诃夫的《草原》,觉得那个漫漫长途上去亲戚家的孩子,怀着对大自然、特别的人和事的无边的好奇,也被电闪雷鸣震慑,就是我。”施战军说,“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文学趣味,以及观察事物的角度和对问题的容纳,可能在下意识中也对我办刊物有影响。”
在文学现象相当驳杂的情况下,施战军希望在办刊物时尽量包容多样性,对人和万物报以理解、体恤,然后再判断。
2012年10月底,施战军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稚推荐来的作品——徐皓峰的《师父》,篇幅很短。他看后非常喜欢,从已在校对阶段的第十二期拿下来一篇小说,换上《师父》。后来《人民文学》又推出武侠作品小辑,其中有徐皓峰的《武人琴音》。现在,徐皓峰的作品,诸如《师父》《道士下山》《箭士柳白猿》《刀背藏身》,一部部改编为电影。
发表儿童文学本来就是《人民文学》的传统。2013年开始,每年第六期基本变成少儿文学专号,发表小说、童话、散文和诗歌。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不仅以《古船》《你在高原》等现实主义作品闻名,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寻找鱼王》也获得了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国外译者问起中国有没有自然文学时,施战军回答“当然有”。他感到,近些年中国有丰富的创作,和欧美文学现象能够直接产生比对效应,不再是以仰视崇拜的方式对话了。中国近年来自然文学勃兴,但和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然文学基本上是荒野文学,是田野考察、野地行走这种方式的记述,更注重自然与人对立的关系。中国从来没有把自然和人的生活切开,而是天人合一,人和自然一直是一体的。”施战军说,像《人民文学》发表的阿来的《三只虫草》、南翔的《珊瑚裸尾鼠》这样的自然文学,就绝不是写花花草草、旅游所见,也不只是环境文学或环保文学。
“一个国度的文学只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成为世界通行的文学作品是不可能的。”施战军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不仅仅是国际政治,不仅仅是地球文明,对审美也有深刻启示。”

